|
“青春诗会”是中国诗歌界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是青年诗人亮相的舞台与成长的摇篮。《诗刊》社从1980年起,已成功举办了39届“青春诗会”,吸纳了570多位优秀青年诗人参加,每届诗会推出的诗人和诗歌,都引起文坛广泛的关注。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为以诗歌为媒介传递青春的诗意,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家协会将于7月18日至24日在杭州和北京两地举办“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来自金砖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国的诗人们,将与中国诗人一道,青春同行,歌咏言志。
开幕式上,将以诗歌朗诵、情境表演、声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金砖成员国的历史文化和诗意之美。十国诗人将围绕诗歌创作等相关话题,展开“青春诗会”学术对话。活动期间,各国诗人将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还将举行金砖国家青春诗人手稿捐赠仪式,让诗歌见证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和诗人间的情谊!
“愿如风有信”,“诗人兴会更无前”,我们期盼“以诗之名”的“国际青春诗会”,必将是一场如约而至的青春盛会。从即日起,中国作家网将陆续推出介绍参会各国文学和诗歌创作情况的文章,邀请您一起,在各国文学之林来一次青春漫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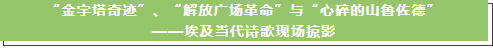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讲师
唐珺
“藏起你所有的旧诗,来吧,为今日的埃及书写与之媲美的诗篇。
从今往后,沉默不再为恐惧压迫。来吧,为埃及的尼罗河与子民书写安宁。
你的双眸是一对至美的少女,坚信这些恐惧必将终结逝去。
你的双手是两片释放爱恋的大地,你的面庞在高空被尊为神明。
街头的我们被严寒霜冻戏谑,无人出面表态释疑。
我们相互取暖,看见你露出微笑,便忘却了寒意。”
这是2011年埃及诗人希沙姆·朱赫(1978-)参加风靡阿拉伯世界的诗歌选秀节目“阿拉伯诗王大赛”并入围第四季决赛时创作并朗诵的诗作片段。彼时的他从埃及前往阿联酋参加决赛录制,刚刚亲历了埃及“1·25革命”,见证了埃及青年人在开罗解放广场的反政府抗议与街头的流血牺牲,及随后穆巴拉克政府的倒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骇浪中,诗歌成为街头阿拉伯青年们鼓舞气势的有力武器。其中,埃及诗歌作为阿拉伯文学与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见证阿拉伯现当代诗歌创作的重要现场,并与埃及社会现实局势的变化保持紧密的联动性。

希沙姆·朱赫在诗歌朗诵会
“诗王”及其他:阿拉伯现代诗歌复兴先驱
诗歌历来就有“阿拉伯人的文献”之称,由古至今一直是阿拉伯人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阿拉伯诗王大赛”中“诗王”称号之渊源,来自埃及著名诗人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他是阿拉伯现代诗坛早期重要流派“新古典主义”、或“复兴派”的代表诗人,因诗歌成就斐然被阿拉伯诗坛赋予“诗王”之尊称。而阿拉伯近现代诗坛的复兴运动,即始于他的祖国——阿拉伯世界最早经历文化复兴的埃及。这一片自古以法老文明、金字塔、尼罗河为荣耀的、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老土地,崛起并发展出阿拉伯诗歌现代复兴运动中的多个重要流派和诗坛巨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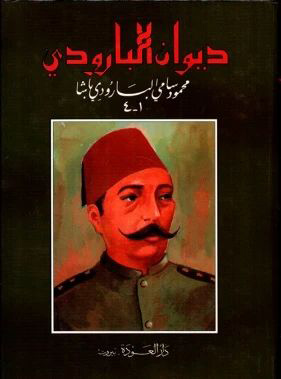
哈茂德·巴鲁迪的诗集封面
伴随19世纪下半叶近代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开启,阿拉伯文学、诗歌也随之逐步突破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抄袭古人、玩弄辞藻、矫揉造作之窠臼,迎来巨大变革。埃及诗人马哈茂德·巴鲁迪(1839-1904)被公认为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先驱,他继承了阿拉伯古典诗歌、尤其是阿拔斯王朝初期的风格,在形式上严格遵循古典诗歌的格律,沿袭古诗凝练、质朴的风格,讲究语言美和音韵美;在内容上既抒发个人情感,也反映国家民族的苦难、愿望和时代精神,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兴亡结合一体,并敢于针砭时弊。由此,以巴鲁迪、萨布里(1854-1923)、艾哈迈德·邵基、哈菲兹·易卜拉欣(1872-1932)为代表的“复兴派”诗人一扫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诗坛脱离现实、玩弄辞藻的颓废之风,使质朴有力、豁达豪放的诗歌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密切结合,成为反对封建压迫和殖民统治的时代号角与战斗檄文,广受埃及民众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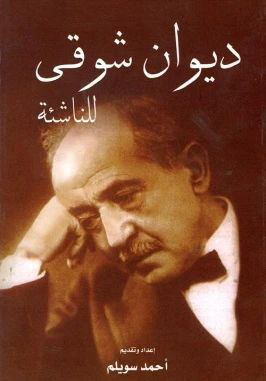
艾哈迈德·邵基诗集封面
随后,由埃及诗人创建的阿拉伯重要诗歌流派包括:以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1886-1958)、易卜拉欣·马齐尼(1889-1949)和阿卡德(1889-1964)为核心的“笛旺派”。他们出版的诗集以“笛旺”(意为诗集)为题,主张诗歌从个人体验出发,真诚地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真情实感。由艾布·沙迪(1892-1955)、易卜拉欣·纳吉(1898-1953)、阿里·马哈茂德·塔哈(1902-1949)等人创建的“阿波罗诗社”,借用希腊神话中司诗歌与音乐之神“阿波罗”之名,主要倾向浪漫主义风格。上世纪40年代,完全打破传统韵律束缚的自由体新诗在伊拉克诞生,并迅速风靡阿拉伯各国。在埃及经由萨拉赫·阿卜杜·萨布尔(1931—1981)、艾哈迈德·希贾齐(1935-)、穆罕默德·阿菲菲·马特尔(1935-2010)、法鲁克·舒夏(1936-2016)、艾迈勒·冬古勒(1940—1983)、法鲁克·朱威戴(1945— )等人发扬光大。自由体新诗主张完全打破诗歌格律,在结构、主题、美学上全面创新,探索阿拉伯诗歌创作的现代性与可能性。进入21世纪,以阿俀夫·阿卜杜·阿齐兹(1956-)、易卜拉欣·达乌德(1961-)、法特希·萨米厄(1963-)等为代表的“70、80年代”诗人成为中流砥柱。艾哈迈德·耶迈尼(1970-)、迪玛·马哈茂德(1972-)等为代表的“90年代”诗人,加之丽达·艾哈迈德(1986-)、伊斯拉·纳米尔(1991-)、伊斯兰·努瓦尔(1992-)等新生代诗人也崭露头角,在阿拉伯与国际诗坛继续发出流光溢彩的埃及之音。
同其他见证20世纪世界风云的阿拉伯诗人一样,埃及诗人也特别重视通过诗歌创作对时代的热点问题——战争、和平、社会巨变、国家民族等主题展开深刻思考,他们忧心忡忡,但也始终充满着阿拉伯民族的壮志豪情,一如先驱巴鲁迪曾写下诗句:
向辽阔的吉萨询问埃及金字塔吧,或许你会知晓不为人知的奥秘。
这些建筑抵御住时间的侵袭,奇迹般战胜了荏苒光阴。
历尽沧桑的它们傲然挺立,苍茫大漠间证明建造者们的丰功伟绩。
有多少民族与朝代烟消云散,唯有它们是视觉与智慧的奇迹。
借由对金字塔、尼罗河等埃及古迹与自然地理的歌颂,埃及诗人们满怀豪情地赞颂民族、祖国与祖先创下的荣耀,希望阿拉伯民族自强自立,恢复一如昔日古埃及法老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时期般辉煌的荣耀。老一代诗人们敢于冲破束缚,摆脱传统诗歌在修辞上、格律上的限制,主张诗歌体现时代的思想与情感,在诗作中借事抒情、借古喻今、夹叙夹议。在以巴鲁迪、邵基为代表的诗歌灯塔的照耀下,埃及当代诗人们的创作不断见证新的变化,同生存年代与社会现实持续保持互动联系。
“政治与革命”:埃及当代诗关键词
作为“阿拉伯人文献”的诗歌,在当代依旧是阿拉伯人的喉舌,他们借此表达对于重大问题或公共事件的观照。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致使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母题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联,且作家诗人们不论国籍,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公共议题给予相互的关注、支持与响应,埃及诗歌也不例外。
在长期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现实主义题材自然成为诗歌创作的重心。政治与革命、土地与祖国、现代与传统成为核心议题。现实中的种种悲剧激发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也促使他们在诗中反思当下、批判时弊。同上世纪民族独立解放时期的爱国主义诗篇相比,埃及当代诗人们淡化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赞颂与讴歌,更倾向于使用沉郁激愤的语言表达对国家未来、民族存亡的忧心与焦虑:“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沦为民族不思进取的耻辱象征,“尼罗河水”为人民终日流泪。
自2010年末起,以民生、民主为诉求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大规模爆发,发生在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1·25革命”成为重要标志。青年是变革的主力,在埃及街头,青年们高声朗诵著名革命诗人们的诗作,突尼斯诗人艾布·卡西姆·沙比(1909-1934)的“人民如欲生存,命运必须响应/黑夜必将逝去,枷锁定要打碎”等名篇再次响彻街巷。埃及各大报刊杂志也大量刊载了革命诗,渲染革命游行的氛围。部分诗人率先出版了诗集,如艾哈迈德·塞拉吉(1975-)的《对广场的审判》(2011)、2023年获阿联酋苏尔坦·欧维斯文化奖的哈桑·俀利卜(1944-)的《革命之圣经与古兰经》(2011)等诗集,都记录下诗人对埃及一月革命的感悟。一些名气更大的诗人虽未出版诗集,但也有诗作问世,鞭笞了独裁统治,为群众革命摇旗呐喊。此外,多数诗歌采用埃及方言、而不是阿拉伯标准语创作,更凸显其贴近街头民众、记录历史与鼓舞士气的功能。另一些作品更强调诗人在革命时期应持守的立场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号召诗人放下精英姿态,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至今,包括埃及诗人在内的阿拉伯诗坛召开了许多诗歌研讨会,探讨当下阿拉伯革命诗的特点与走向。诗人们从最初对“阿拉伯之春”的赞美与希冀,转变为对其作深刻的反思与质疑。大体而言,诗人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些人认为,当下的革命诗应走向通俗、走向大众;诗人应寻找更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人民的心声,写出人民看得懂的通俗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下的革命诗尚未提升至真正的革命性高度,这些诗虽数量繁多,但内容浅显直白,大都停留在描述、记录事件,思想性、深刻性不足;诗人不仅应承担起群体代言人的使命,更应对事件作反思,超越肤浅的直抒胸臆,将诗歌的政治革命题材与诗歌的美学内涵有机结合,创作出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高度艺术性的杰作。埃及诗人们普遍认为,当下的阿拉伯诗歌或许尚未达到与发生的革命事件相匹配的高度,也未产生可推动整个阿拉伯世界文化根基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影响力。真正的诗人尚需时间沉淀,才能创作出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真正革命性的诗篇。
埃及文论家拉贾·尼高什(1934-2008)曾说过:“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期间,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和艺术变革的程度理应高于任何其他时期。”随着埃及社会迎来了社会大转型期,革命运动取得一定成果,对文坛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专制统治对文学创作的束缚,诗人们获得较以往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打着民主旗号的宗教保守思潮亦已借机上位,依旧为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设下新障碍。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诗歌能否迎来真正的变革和新的发展契机,从而掀开当代埃及诗歌的新篇章,有待对埃及当代诗人的创作实践持续追踪考察。

诗人们积极参与开罗书展诗歌朗诵会等文学活动
埃及当代诗人的全球本土化“在场”
当今,阿拉伯世界的写诗者和爱好者众多,各种级别的诗歌创作、朗诵比赛不胜枚举,诗歌研讨会与沙龙也数不胜数。埃及本土较为著名的含诗歌类文学奖项有纳吉布·马哈福兹文学奖、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尼罗河埃及创作者奖、阿卜杜·拉赫曼·艾卜努迪埃及方言诗歌奖,不少埃及诗人也在各类国际诗歌节频频发声,诗集被译成英、法、西、意、中等多种文字,获得科威特巴比敦诗歌创作奖、阿联酋欧维斯诗歌奖、突尼斯艾布·卡西姆·沙比文学奖、摩洛哥诗歌之家阿尔卡纳国际诗歌奖、巴勒斯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诗歌奖等阿拉伯诗歌奖,及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马其顿诗歌金桂冠奖、希腊卡瓦菲斯国际诗歌奖等国际诗歌大奖的青睐。
互联网与自媒体的繁荣也为诗歌的展示与推广开辟了全新的空间,埃及政府与民间建立了各类诗歌网站、论坛,诗人们热衷于开设发表自己作品的个人网站、公众号。一些电视直播诗歌赛事,尤其是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与遗产局的举办年度电视选秀节目“阿拉伯诗王大赛”和“百万诗人大奖赛”,前者规定使用阿拉伯语标准语现场作诗,后者使用阿拉伯半岛“奈伯特体”方言现场作诗,吸引了来自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各国众多民间诗人前往参赛。此两档电视节目至今已分别举办十季和十一季,获得阿拉伯民众的极大关注,每个赛季的播出都保持了极高的收视率,多位参赛的埃及诗人闯入决赛,取得较好名次。
但与此同时,埃及当代诗歌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从世界范围来看,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普及,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都对严肃文学的传播造成消极影响。与此同时,诗歌也受到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体裁的冲击,被边缘化的事实不容否认。对于阿拉伯文学而言,长篇小说已成为时代新宠,更受传媒与大众的关注。此外,普通阿拉伯读者更青睐浅显直白的诗歌,追捧出口成章的选秀诗人和网络上的通俗诗,不太愿意阅读有深刻思想内容和较强艺术性的诗歌。因此,大众喜欢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沦为文化消费品。尽管如此,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诗歌传统的民族,当代埃及诗歌在世界诗歌版图上仍占据重要地位,并具有充沛的活力。在当前全球本土化写作的世界文学创作趋势下,埃及诗歌还呈现出多种独特风貌:
诗歌体裁呈现多元化且兼容古今。既有完全依照相同音步、韵脚等传统形式创作的“柱体诗”,又有只求句尾押韵的“韵尾诗”,还有打破诗歌格律、长短相间的“自由体新诗”,以及兼具散文与诗特点的“散文诗”。埃及方言诗创作也是埃及诗歌一大特色,如阿卜杜·拉赫曼·艾卜努迪(1938-2015)是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方言诗人之一,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配乐后由名歌手传唱。方言诗主要涵盖爱情、祖国、民族、乡村、农民等十分接地气的题材,尤其是上埃及的嘹亮迷人的乡村方言与风情为作品增添了许多独特的本土风味。
除了对政治、革命类题材的重点观照之外,埃及性及其身份认同是埃及当代诗人关注的另一大主题。他们或呼吁对文化传统、民族属性的坚守,或对厚古薄今的传统文化观提出质疑。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历史、神话、宗教、民间传奇等元素被诗人们反复发掘,幻化为地域性突出、空间张力强的隐喻与象征,被赋予新时代的精神,以此表达诗人应对现实各类情境的心灵体验。从风格上而言,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内容,也有魔幻与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介入。基于埃及社会发展现状,其诗歌的基调与阿拉伯诗歌总体的基调是一致的,忧心、愤怒、焦虑、呼吁变革,离不开政治主题,却又努力通过追求诗性的审美建构,实现“去政治化”的母题解构。
新生代诗人们更倾向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书写,热衷于运用新的组词与结构去表达细节、转瞬即逝的琐事和个体应对现实的复杂心境。他们的诗歌文本更聚焦自我,具有开放性和朦胧感,或表达深处群体内部的个体焦虑不安的情绪,或诉诸于幻想与苏菲主义冥想,表达逃离苦涩现实的冲动。在埃及青年诗人群体中,女诗人们表现十分突出,用女性独有的敏感、细腻笔触书写内心的私密化情感。如迪玛·马哈茂德(1972-),被评论家借用阿拉伯经典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里善讲故事感化国王的山鲁佐德,称之为“拥有一颗破碎之心的山鲁佐德”。她创作的《手袋里被啃食的手指》(2021)等诗集,聚合了蝴蝶、玫瑰、燕子、杏花、彩虹等诸多闪亮灵动的自然意象,但意象的复合性并非空洞无物的词语堆砌,而是饱含女诗人充沛涌动的内心情感,表达她与世界的连接:
我们赤裸双足,只剩下歌声。
我们将蝴蝶绑在夜的尾翼上,
被它们的翅羽遮住,便不会遭遇任何人尾随。
我们诞下欢乐,然后在阴影下奔跑。
音乐碎成裂片,后方跟着一只鸽子,
虚空被推向高处。
黑夜抖落掉罐子里的残余。
再没有人像我俩一样,终将从这正途上经过,
把幸福诱引出它的领口,
趁着河流午憩把历史驯服。
女诗人丽达·艾哈迈德(1986-)也表示,她更喜欢陷入个体的主观性之中,“我倾向于书写深藏于自我、同时与他人共享的柔弱、畏惧的细节。这些细节,你可以在街上行走时遇到,或是面对装满你心爱之物的展示柜陈列时,你在自己空荡荡的口袋里找到。我的诗一如我自己,要违抗、摆脱所有的桎梏,也会极其坦诚地倾听现实中所有的软弱、挫败、混乱,以及关乎存在、关乎世界的微不足道却暗藏危机的问题。诗歌这门艺术的实际作用是与现实交缠,打开其审美的视野,去看见真实,去剥离丑陋与虚伪。”在一些埃及文评家看来,新生代诗人群体构成埃及当代诗歌的新生血液,他们的诗歌实践与创作主张不可小觑。另一方面,从整个阿拉伯世界范围来看,自由体新诗、散文诗等不苛求韵律的诗体、及新生代诗人们创作中部分先锋的个性化内容时常引发争议或招致批评。因此青年诗人群体也认为,阿拉伯各国的诗歌鉴赏与学院派评论也亟需跟上诗歌创作的步伐,接受与时俱进而非墨守成规的审美趋势,更好地激励青年诗人们勇于创新。
诚如2022年获埃及文学国家表彰奖的埃及诗人优素福·努法勒(1938-)所述:“诗歌将一如既往地成为阿拉伯人的文献,是阿拉伯人的身份属性,它不断发展,书写着不同时代所有的人文命题。”埃及诗歌始终处于阿拉伯诗歌革命的先锋试验场,在现实困境下源源不绝地输出蓬勃多姿的创造力。在诗歌大赛现场勇于为祖国发声的希沙姆·朱赫近年来写下的诗句,大抵代表了一大批埃及新生代青年诗人们始终秉持的社会责任与创作激情:
祖国,我不得不爱你。
祖国,我不得不写诗。
诗歌,一旦碰上政治,必将惹出麻烦。
诗歌,一旦碰上像我这样的埃及人,
必将化作剑刃,无所畏惧。
我,无所畏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