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2年11月2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北京盛大开幕。这是中国作家协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部署,更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努力构建文学事业新发展格局的有力举措。在文学盛典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作协各媒体平台将陆续推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专题报道,这既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巡礼,也是对优秀写作者的致敬。敬请关注。
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各类别评奖委员会经过投票表决,产生了获奖作品。其中,许小凡译《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杨铁军译《奥麦罗斯》、陈方译《我的孩子们》、竺祖慈译《小说周边》、薛庆国译《风的作品之目录》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5部获奖作品涵盖了传记、诗歌、小说、随笔札记等不同体裁,涉及英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等语种。获奖者中,有已过古稀之年的资深出版人、翻译家,也有凭借首部文学翻译作品就获此殊荣的后起之秀;有横跨文理两界的诗人,也有穿梭于教学、研究和翻译等多个领域的高校学者。他们和文学翻译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如何游弋于两种语言之间,成为不同文化间的信使?这一系列专访将逐一呈现每位译者的翻译人生。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得主系列专访
薛庆国:阿拉伯语是我相爱最久的恋人
与阿拉伯语相伴的40年里,薛庆国对这个“恋人”的感情与日俱增。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后,回忆起在有破洞的宿舍裹着被子翻译纪伯伦的日子,怀念的仍然是文学的温暖。
薛庆国翻译阿多尼斯的诗歌源于同事、朋友一次偶然的推荐。十几年下来,与诗人的友谊成为他毕生珍视并为之自豪的精神财富。他翻译了多部阿多尼斯的诗集,欣赏诗人思想的厚重和想象的轻盈。翻译诗歌难度不小,但薛庆国并不真的觉得痛苦,那些翻译中棘手的难题,是对智力和能力的挑战,让他乐在其中。他也寄望于年轻人的成长,在老一辈研究者、翻译家开拓的基础之上,阿拉伯文学这一古老东方文学的重要一支,能够在中国获得更多的译介和关注。
通过翻译挑战智力和能力,乐在其中
中国作家网:祝贺薛老师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请您先谈谈学习阿拉伯语的经历吧。
薛庆国:我于1981年通过高考,进入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学习阿拉伯语。4年本科学习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间于1987-1988年赴埃及开罗大学进修一年。博士毕业后,我回原单位工作了两年多,后来调入北外任教至今。屈指算来,我学习阿拉伯语已超过40年了。40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在接触阿拉伯语:学习、阅读、教学、翻译、写作……可以说,我对阿拉伯语的感情与日俱增。前年有一次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时,我曾经开玩笑说:阿拉伯语才是我相爱最久的恋人!
中国作家网:您之前曾在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工作,后来回到北外,现在阿拉伯语学院任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
薛庆国:我曾于1996-1999年被外交部借调到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工作,将近三年的外交官生涯结束后,使馆领导希望我留在外交部工作,但我还是更喜欢大学的环境和工作性质,因此回到了北外。
我最早从事文学翻译,还是博士毕业刚留校工作期间。留校的第一年没有教学任务,我意外发现纪伯伦的许多英文著作都未译成中文,便从图书馆复印了原著,迫不及待地开始翻译。记得那年的初冬时节,学校为我们单身宿舍楼安装暖气,工人先在墙上打洞,一周后才把暖气片安上。冰冷的夜晚,我用纸箱子堵住墙洞,身穿厚厚的棉衣,把被子也裹在身上,在灯光下翻译纪伯伦的作品。从邻居的房间,还不时传来别人打麻将的声音。我没有感到寒冷和寂寞,心里只有温暖和充实。今天,当我捧起翻译的纪伯伦作品时,似乎还能感到墙洞里溜进的刺骨寒风,还能闻到空气里夹带的泥土气味;但我更加怀念的,是纪伯伦和阿拉伯文学带给我的温暖。
中国作家网:从事文学翻译,最让您感到有成就感的是什么?让您感到痛苦的又是什么?
薛庆国:最有成就感的,是通过我的翻译增进了广大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和文化的了解。特别幸运的是,我翻译的纪伯伦、阿多尼斯、达尔维什、马哈福兹等阿拉伯文学大师的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因而大都得到了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好评与喜爱。我总是认为,译作获得成功,首先归功于原作高超的文学水准,我的翻译固然也起了作用,但毕竟是第二位的。特别让我自豪的是,通过我对阿多尼斯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持续译介,这位阿拉伯诗人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喜爱,甚至成为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当代外国诗人之一;通过阿多尼斯,中国读者还了解了阿拉伯当代文化的魅力。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要说痛苦,我真没有感到过痛苦。我也经常为如何理解原文、如何找到合适的译文表述而绞尽脑汁,但这算不上痛苦,而是通过翻译,挑战自己的智力和能力,可以说乐在其中。
中国作家网:除了阿多尼斯,您还翻译过诸如巴勒斯坦作家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等阿拉伯诗人的诗作,您是从文学翻译之初就从事诗歌翻译吗?
薛庆国:没错,我还翻译过达尔维什的诗歌选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并在《世界文学》《星星》等刊物译介过多位阿拉伯现当代诗人的专辑。我最初翻译的是纪伯伦作品,共译了他的7部著作,包括散文、散文诗、诗歌、传记、书信集等,后来还译过诺奖得主马哈福兹的随感类作品《自传的回声》,以及其他作家的剧作、短篇小说等。我还和叙利亚著名学者费拉斯合作,对外译介了《老子》《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但我译介最多的,还是现当代阿拉伯诗歌。近期还会出版一本阿拉伯现当代名家诗选;当然,以后还会继续翻译阿多尼斯的作品。
中国作家网:大家都熟悉一句话“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您认为,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歌翻译是否更有难度,如果有,困难之处具体在哪里?
薛庆国:诗歌在翻译中固然会失去一些东西,如音乐感、节奏感,诗人精心设计的某些隐喻、双关等等。但是,在失去的同时,译诗也会得到一些东西。译诗就是“移植”,当外国诗歌“移植”到汉语这门有着悠久深厚诗歌传统的语言中时,汉语诗歌和中国文化的沃土,往往会让译诗的枝头绽放出神奇的花朵。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学阶段阅读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开篇第一句“江声浩荡”带给我的震撼。后来听法语老师说,原文是由8个单词组成的一个句子。正是傅雷先生的妙笔,为译文赋予了原文没有的诗意、气势和冲击力。我总觉得,汉语是非常具有文学气质的一门语言。
比起其他门类,诗歌翻译的难度总是要大一些,因为译者不仅要翻译原诗的意思、意象和意境,还要传达原诗的音韵节奏,而后者在我看来是最难的。有时候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首很好的阿语诗译完后,原诗的字面内容都已传达,但译诗读来读去、改来改去都没有诗歌的感觉,或者说没有了原诗的诗意。因为无法舍弃拿不出手的译诗,我认为翻译一本完整的诗集比翻译诗选更难。
他的作品中永远闪耀着思想和理性的锋芒
中国作家网:阿多尼斯的第一本引人注目的中译本作品是2009年出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您怎样和阿多尼斯结缘?
薛庆国:这说来话长。我简要介绍一下:2008年,唐晓渡、西川任主编的《当代国际诗坛》创刊,编辑部在讨论重点译介哪些外国诗人时,诗人树才介绍了一个情况:他不久去法国见到老朋友、著名诗人博纳富瓦,当他问博纳富瓦目前法国有哪些重要诗人时,博纳富瓦提到的第一个诗人,便是旅法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因此,树才跟编辑部建议,一定要出个阿多尼斯专辑,最好请懂阿拉伯语的译者直接从原文翻译。后来,编辑部通过我的北外同事、俄语诗歌翻译家兼诗人汪剑钊找到我,希望我翻译阿多尼斯的诗作。于是,我译了2000多行诗,在《当代国际诗坛》第二期发表。后来,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理行对我说:每年诺奖宣布前,阿多尼斯的名字都被人提起,而我国还没有出版他的诗集,一旦他获奖,你们这些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翻译的人岂不很被动?他建议我翻译一本阿多尼斯的诗集出版。我在原有译文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诗人大部分新的译作。译文完成后,我应出版社的要求,费尽周折找到阿多尼斯的联系方式,去信请求他将版权授予出版社,同时邀请他来中国出席诗选首发式。他欣然答应,于2009年3月来华出席《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首发式。我和阿多尼斯由此结缘。
中国作家网:对于阿多尼斯的创作经历来说,2009年的中译本不算早了,他没有更早为中国读者所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薛庆国:正如刚才所说,这主要是我们这些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翻译者的疏忽。其实,早在1980年,阿多尼斯作为黎巴嫩作家代表团的唯一成员首次来访中国(1980年,阿多尼斯生活在黎巴嫩,因具有叙利亚和黎巴嫩双重国籍,此次他以黎巴嫩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华)。此行他在华共逗留10天,去了北京、上海、苏州三地。据30多年后再度访华的阿多尼斯自述,首次访华的许多细节他都记不清了,好在回到黎巴嫩后不久,他就把这次中国之行的感想和印象分两次发表在当地主要报纸,其中详尽记录了他在当时的中国作协(也可能是文联)座谈的内容。文中提及,参加座谈的中方代表共有20多人,其中包括夏衍等3位文联(或作协)副主席,以及多位作家、诗人和文学刊物主编。或许因为当时中国国门刚刚打开,来访的外国作家很少,所以中方在接待这位来自小国黎巴嫩、在国际上还没有太大名气的诗人时,安排了20多位作家跟他对话,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外事礼遇了。阿多尼斯对此次座谈的记录十分详尽,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他对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呈现的蓬勃朝气印象深刻,对中国作家们的反思意识给予高度评价。我认为,中国作家们的这些严肃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影响了阿多尼斯的诗学观和文化观。
中国作家网:《风的作品之目录》主要收录阿多尼斯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十三首诗,90年代在阿多尼斯的创作过程中是怎样的一个时期?
薛庆国:上世纪90年代是阿多尼斯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特别是大部头诗集《书:昨天,空间,现在》(1995年第一卷,1998年第二卷),第三卷于2002年出版。他在谈及此作时曾表示:“这三大卷诗集,是我诗歌生涯的巅峰之作。它是我几十年前就已着手的重新审视阿拉伯政治史、文化史这一文化工程的重要里程碑……还可以说,这部诗集既向阿拉伯历史表达爱恋,同时又跟它做痛苦的决斗。”《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收入了这部巨著中可以单独成篇的几首诗,如《札记》《T城》《Z城》《G城》。
阿多尼斯有一个习惯,在创作鸿篇巨制时,往往同时创作一些轻松、灵动的短章作为调剂,用他的话来说,“短章仿佛小草或幼苗,生长在长诗——大树——的荫下;短章是闪烁的星星,燃烧的蜡烛;长诗是尽情流溢的光明,是史诗的灯盏。两者只在形式上存在差异,本质上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共同构成了我的诗歌实践。”《风的作品之目录》的十三首诗,都是由同一主题的短章构成,可以视之为大树荫下的小草,皎洁明月旁的星星。记得阿多尼斯曾告诉我,其中《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包括数十个短章的长诗,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于一个上午完成的。我知道他有个习惯——口袋里会放个本子,随时随地记录思绪或灵感。我猜想那个上午他完成的这首诗,不少内容来自口袋里那个本子。
中国作家网:这部诗集给人整体印象偏轻松,作为译者,您觉得这部诗集体现了阿多尼斯诗歌怎样的阶段性特点?
薛庆国:和诗人创作的许多思想厚重、风格晦涩的诗作不同,这本诗集是诗人从大自然中采撷的醇酿。诗人怀着诗心和童心,去观察、认识大千世界,写下那些清新隽永、令人读完唇齿留香的诗篇。这些诗是“天空之嘴凑近大地耳畔的低语”,是“从树的喉咙升腾起的歌”,它像雨一样润物无声,像风一样轻拂人心。诗集总体上呈轻盈灵动的特点,但也蕴含着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许多诗句触及政治和社会,但通过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呈现,令人过目不忘:“这个时代是灰烬,/但是,我只愿师从火焰。”“我的祖国和我/身披同一具枷锁,/我如何能同祖国分开?/我如何能不爱祖国?”这些诗歌短章里呈现的特点,在阿多尼斯不同阶段的诗作中都有体现。
中国作家网:您是阿多尼斯作品的译者,也是他挚爱的朋友。阿多尼斯在他的中国题材长诗《桂花》首页特别为您写了献词:“献给薛庆国”。您怎样评价这位年长的叙利亚诗人朋友?
薛庆国:和阿多尼斯结下的友谊,是我人生莫大的荣幸,也是令我毕生珍视、自豪的精神财富。除了公认的诗歌成就以外,阿多尼斯还是一位多重批判者:既勇于批评丑陋的阿拉伯政治与现实,也揭露阿拉伯文化的深层弊端,同时对自私而傲慢的西方政治,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给与批判。他拒绝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作品中永远闪耀着思想和理性的锋芒。
此外,他对未来具有深刻洞察。十多年前他对“阿拉伯之春”的批判和预言,已被残酷的阿拉伯现实所证实。而早在此之前,他就判断阿拉伯世界即将面临剧变,恐怖主义将成为“盘踞在世界王座上的女王”。对于美国政治主导世界的时代,他一直怀有深深的忧虑。早在1980年第一次访华时,他就被开始焕发朝气的中国所打动,在文中写下:“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另类的世界;在不远的将来,她或将创造另一个世界。”今天,深受疫情和战争阴云困扰的我们,读到阿多尼斯于上世纪末写下的诗句时,更会惊叹于他深刻的预见性。
阿多尼斯虽然个人饱经磨难,祖国和家乡遭受战火蹂躏,但他仍然宠辱不惊,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年逾九旬的老人,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一个个写作计划。当我在工作中偶感懈怠时,想起阿多尼斯——90多岁的老人还那么勤勉,便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懈怠?
阿语文学译介需要中青年学者的成长
中国作家网:阿拉伯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成就的文学之一,也是东方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阿拉伯文学作品,如《天方夜谭》等在中国的译介最早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了,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关注、研究和译介有怎样的新特点?
薛庆国: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老一辈阿拉伯文学研究者逐渐退出舞台;中青年学者很快成长起来,有不少研究和翻译成果问世。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更强,多数学者聚焦阿拉伯现当代文学,有的跟踪阿拉伯文学的热点,也有人关注跨学科议题。得益于各种出版资助计划,已有数十部阿拉伯文学的译作问世,其中以长篇小说居多。
中国作家网:老一辈翻译家仲跻昆、郅溥浩先生等为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译介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也在阿语文学研究译介和中阿文学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阿语文学研究译介队伍构成情况如何?您在北外任教,是否关注到有更为年轻的力量有志于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薛庆国:老一辈阿拉伯文学研究和翻译专家仲跻昆、郅溥浩先生近年已先后辞世,这是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翻译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怀念、感激他们。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译介队伍主要以高校阿拉伯语教师为主,还有来自研究机构、出版社的少量人员。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是个十分团结进取的学术团体,比较固定、活跃的成员约有50人,其中年轻人约占一半,每年都举办一次年会,此外还有不定期的其他活动。
中国作家网:未来我国阿语文学研究和译介应更注重哪些方面的发展?
薛庆国:我国阿语文学研究和译介的力量还不算雄厚,研究需要开垦的处女地还不少,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我们产出的著译成果与阿拉伯文化、文学的重要性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公众、甚至知识界对于阿拉伯文学、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对此,我作为从事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时间较长的一员,作为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专注不够,与许多前辈乃至同朋相比,还有着一定差距。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同时帮助、提携更多的年轻人尽快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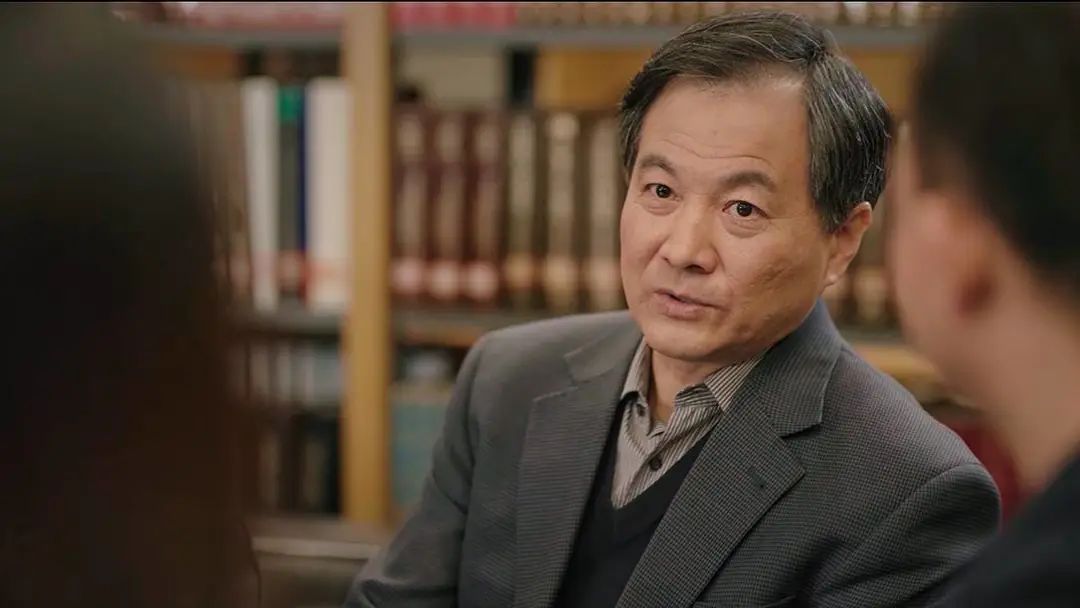
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阿拉伯文化与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已发表各类著译作品近30种。其翻译的纪伯伦、阿多尼斯等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大师作品深受中国读者欢迎。曾获卡塔尔国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2022年8月25日,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