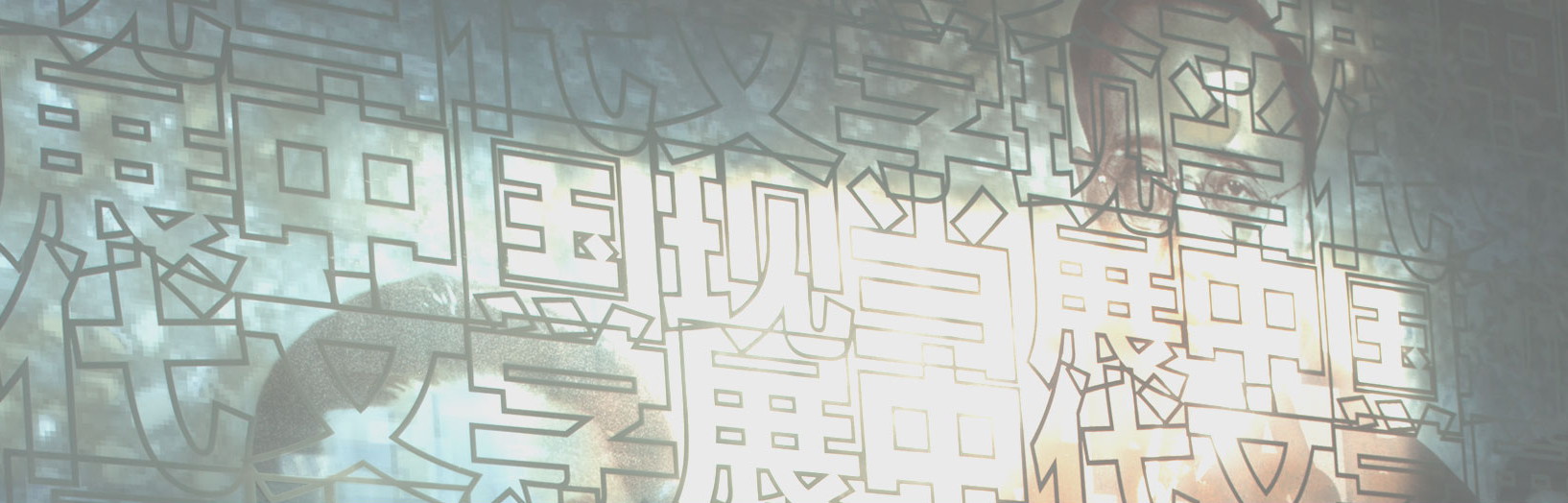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在现代文学史上,萧军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一生牵涉到许多重要的史实。鲁迅是他的恩师,毛泽东引他为知己。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是撰写中国人民奋勇抗日小说的第一人。他一生遭际坎坷,这与二十世纪中国大环境有关,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非常不平凡的。在这个世纪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壮举是千千万万的人百折不挠才成就的。萧军是其中一人。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鹿野在纪念萧军的文章中写道,“萧军曾多次对我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为人,为文的目的有四:就是求得祖国的独立;求得民族的解放;求得人民的翻身;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如今这四个目的基本都达到了,因此,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同时萧军个人的性格也是他坎坷遭遇的重要原因。他在与《萧军评传》的作者王科、徐塞谈话时多次戏称自己是碾盘沟里蹦出来的“石头疙瘩”。这样的自嘲是萧军的知己之论,是非常契合他的性格特征和人生遭际的。 碾盘沟“屁股温冰”的少年 “屁股温冰”是鲁迅对萧军小时候一种恶癖的叫法。萧军在《我的童年》里写道:“卧冰是我儿时一种要挟人的恶癖。当我四五岁时,还穿着活裆裤的年代,大人们如果惹了我或责骂了我,冬天,院中有着结成冰的水堆,我会把裤子剥开……坐到冰堆上去。有时候可以使自己的体温把那冰化成两个小小的洼。”萧军对自己的这一做法解释是“恃宠而骄”。这需要多么倔强多么壮盛的灵魂才能做到呀,是怎样的生活练成了萧军如此灵魂的?难怪萧红要说萧军是具有强盗灵魂的人。 1907年7月3日,萧军降生在辽西一个大约有着两三百户人家的下碾盘沟村。俗语云“母凭子贵”,萧军的出生却没有带给他的母亲任何一丝“贵”气。脾气暴躁的父亲对母亲的一顿残酷鞭挞,使母亲失掉了对人世的留恋和生的希望。她一声不响地吞吃了大量鸦片,舍下才七个月大的孩子走了。嗷嗷待哺的萧军白天经常由家人抱着到每一家有乳儿的女人那里去“赶奶”,晚上就吃浆糊。最后好容易寻到了一位乳母,这位乳母把萧军喂养到了五岁,后被辞退。乳母哭着不舍得离开,萧军哭着不让她离开。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分开了。 萧军懵懵懂懂地知道了母亲的死与父亲相关时,他那童稚的心即刻被强烈的复仇的欲望所充满——长大了我要“给妈妈报仇啊”,他开始憎恶父亲——“我愿意见到任何人,却不愿意见到他,不管他对我是偶然的爱抚或亲近,我却永远惧恐和憎恶他。甚至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像由春天一下子跌进秋天,我要逃跑啊!我不愿见到他!永远也不愿见到他啊!” 父亲常年为作坊忙着,还野心勃勃地经营了一家商号。“一些镇上警兵们,经常挂着枪到父亲的商号和工场里来行走了。……一到夜间,祖父和父亲总是检查着帐目;或者是无言相对地垂下自己的头。……有时候虽然已近夜深,祖父也还是骑了那匹大黑驴,悄悄地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能回来——他是去筹钱。”这诸多的工作和诸多的不顺,父亲他哪有闲暇哪有心情对萧军有好声气呢!“父亲从来对我是没有怜惜的,我在外面和孩子们打架无论吃了怎样的亏,他总是责骂或则殴打我;如果我打了人,他要责骂我不该欺负人;我被被人打了,他又责骂我无能,不是他的种子,没有出息,是‘脓包货’!” 祖母和姑姑是爱他的。祖母和姑姑的爱却是不完全的。姑姑出嫁了生育了,萧军感到姑姑更爱她自己的孩子了。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心里钻进了一块冰。他的世界一片寒凉啊! 萧军的童年岁月是民不聊生的乱世。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瓜分了东北,满清灭亡后东北人民又是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统治之下。在这严苛冷酷的乱世中经常有被生活抛出正常轨道的人们。这些生活无着的人有一条出路就是上山当“胡匪”。萧军的二叔也上山了。全家人因此凄凄惶惶地过日子,家里的氛围总是有点诡异,“家中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关于二叔的任何消息,他们全鬼鬼祟祟嘁嘁嚓嚓地谈话。”有一次二叔和官兵打仗受伤了,他偷偷地来到村子最东端僻静的四姑家,想养几天并弄点药。祖父和祖母知道后默默地赶去见他。萧军偷偷地跟在后面赶到四姑家,贴着窗台,尖起耳朵想听到屋内的动静。祖父的咳嗽声、祖父和祖母的争吵声、四姑的责备声……当二叔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时,萧军不顾一切地推门而进。屋内人全都吓着了,发现是萧军时,“也没有见过你们这孩子,胆大包天……”四姑责备萧军道。 听到四姑四这句话,萧军先则不满,继而愤怒,终而伤心。“因为她竟把我叫做‘你们这孩子’而这是明显地把我和‘她的’孩子分隔开了!……她竟这样一条鱼儿似的把我抛出她那母亲之爱的河水之外。”姑姑不是妈妈! 五姑生第一个孩子,萧军与四姑一起去看望她。五姑可能担心萧军打架有失娘家和自己的体面,她告诫萧军:“我们村里可不许骂人,打架……人家要笑话。这里的人不会骂人……听见么?”萧军“觉得五姑不再是我原来的五姑了,自从她出嫁以后,似乎不再关心到我。虽然我是那般认真地想念着她,关心她……但她却忽视了我的心!这使我感到一种悲哀和寒凉。”姑姑的村不是萧军的,姑姑的生活里萧军占的分量不大。 一种空漠漠的哀愁笼罩着萧军,这人间是如此空旷而孤独呀,自己和谁也没有关联。于是桀骜不驯的萧军不管不顾地打架、逃学。强梁的坚硬的个性在没有母爱的润泽下逐渐形成了。 “成葫芦”是这样炼成的 “成葫芦”与“瘪葫芦”是一对反义词,我理解为有出息的孩子即是成葫芦,反之就是瘪葫芦。萧军6岁进族人设立的私塾馆,半年后转入沈家台镇的洋学堂。一个从小没有了娘的野孩子,成天要学“人、手、足、刀”什么的,多无聊呀!萧军想念家乡的山、想念一同放牛羊、放猪、打柴的小伙伴。他没法忍受学堂生活,他开始逃学了。父亲拿萧军没办法,痛打了他一顿后,只好放他回碾盘沟村了。 世事如此难料,8岁那年父亲因商号发行的债券无法兑现,破产了。萧军跟着祖父和父亲过起了一段流亡生活。回来后,萧军或上山砍柴或下田锄草。看着那些读书的孩子,心里非常嫉妒和痛苦。他想读书,为了听清楚房里的读书声,他爬上平顶小房,蹲在房顶上。有一次被先生发现了,先生了解情况后,愿意免费教他。“在这次读书中,我却一次也没逃过学,而且成了一个好学生。”即便如此,萧军还是没能读下去,他必须去打柴,否则生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破产了的父亲在长春开了家“隆记玻璃庄”,稍有了点积蓄就托人把萧军带到他的身边来。1917年冬萧军被村人带到长春。不久,父亲又送萧军上了吉长道立商埠国民高等小学。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萧军非常珍惜。这是长春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萧军开始在小学二年级插班,很快就转入了三年级。在这所学校,萧军的文才得到了崔树屏、李景唐两位老师的赏识。崔老师对萧军四年级毕业作文评价尤高,他这样激励萧军“鹏程万里,未可限量,孔子曰,后生可畏,好自为之”。主持“军国民教育”的王老师还指派他为军歌领唱。老师的肯定对学生有着不同一般的魔力。或许曾经的失学经历也激发了萧军的求知欲,他像一条饥肠辘辘的蚕不停地啃食桑叶那样,拼命地读书。他喜好楚辞,爱读小说,历史、武侠、志怪、公案、言情一个也不放过。碾盘沟村的石头疙瘩竟是一块可雕琢的宝石。 人生总有许多不能预料的事。当萧军在商埠小学进到高等三年级时,崔李两位老师双双离开了。这对萧军是一个打击。“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犹如一个人进入了一座空荡荡的没有人烟的古城堡一般。”这时“屁股温冰”的一根筋的固执劲又出来了,萧军没能很好地调适自己,任由情感狂潮淹没自己,看哪个老师都不顺眼。没有人填补崔李两位老师在萧军心中的空缺。相反级任巴老师还经常挖苦萧军,“你们的崔老师总是到处夸奖你的作文如何如何好,就是怎么两下子呀?”或许是萧军无意的“目中无人”刺激了级任老师?体育教员叶老师也看不惯萧军,在出“球杆”操时,萧军做错了一个动作,叶老师批评他,并要求他出列。萧军把球杆摔在地上说:“出来就出来!我就不上你这门团体操!你个‘夜猫子’!”这下石头疙瘩萧军遇上了楞头青。叶老师把情况报告给校长,并提出辞职。不如此,就得开除萧军。校长要求萧军向叶老师赔个礼,萧军拒绝赔礼,接受了开除。 由于学校对萧军的处罚与他的过错太不相当,有几位同学为了表示抗议愤而退学了。这几位同学主张萧军先不要告诉父亲,每天都假装上学。其中一位叫王世忱的同学不但为他联系了一个处所“山东会馆”——一个空置的二层小楼,还每天为他提供午餐,“一大卷裹着油条的热热的煎饼和一壶开水”。萧军天天到山东会馆去“上学”。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半年。这半年萧军读了不少书,其中就有《聊斋志异》《西游记》《济公传》《七侠五义》。 被开除的消息最终还是被父亲知道了,“你也不用隐瞒我了,你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我早看透了,你也不是那份有出息的读书胚子,……你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自谋生路去吧!”父亲对萧军的判断是不对的。他的儿子此时虽说不上满腹经纶,但胸中也是装了不少笔墨的。家道的败落和求学的坎坷成就萧军,他不是一个瘪葫芦,而是一个成葫芦。 军营中的“字儿兵” “字儿兵”是专门负责抄写文书的“见习上士”。我这里拿来借指爱读书的士兵。父亲不肯继续供萧军上学,也不愿意他跟着自己爬楼上房装嵌玻璃。萧军干什么去呢?这时东北处于大小军阀的统治下,人们把当兵看作一条出路,当成一份近乎光荣的职业。在这大时代风气的影响下,1925年春,萧军经同乡介绍到吉林巴尔虎军营当了一名骑兵,领到一份饷钱,算是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巴尔虎骑兵营有四个连,“其中只有一个连的马是官家的,称为‘官马队’;其余三个连称为‘私马队’,就是说这马是当兵的人自有的。”萧军没有马,人又有点文化,小楷也写得不错,被选为“字儿兵”。字儿兵的工作就是军营里抄写文书的,可以穿便装,随便出入营门。抄写的活儿并不多,萧军有大量的可支配时间。这军营中的生活对萧军来说其实是学生生活的延续,或者说是拿薪水的学生生活。 在巴尔虎骑兵营,萧军认识了罗炳然、偶遇徐玉诺、结识了方未艾。 精通四书五经诗词曲赋的罗炳然,罗把怎样做古体诗的看家功夫,全都教给了萧军。本来就喜欢楚辞的萧军学做古体诗热情非常高,他整天抱着《诗韵合璧》等工具书,仔细猜摸诗歌的韵律,认真熟读名家诗词。萧军的古体诗功底就是这时打下的。严家炎在萧军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如是说:“五四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以后,写旧体诗的人不多了,老一代中只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写得好, 稍后的就只有聂绀弩、萧军等在写而且写得比较出色。”萧军与徐玉诺的相遇是非常偶然的,前面说到字儿兵的活儿不多,抄写完文书以后,萧军习惯到附近的公园看书。有一天,他带着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和鲁迅的《野草》去到公园,看了一会书,感到有点乏,竟躺在一张石桌旁的躺椅上睡着了。醒来发现一个人伏在桌上写东西。这人就是徐玉诺。看到萧军多带的两本书,徐玉诺把萧军视为同类,侃侃而谈地给萧军讲了一通诗的理论和鲁迅的散文诗。萧军对鲁迅的喜爱或许是徐玉诺种下的种子。方未艾对萧军的影响主要在新文学方面,在与他的交往中,萧军开始接触到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他阅读内地出版的新刊物,如《小说月报》《语丝》等,阅读《苦闷的象征》《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拜伦和雪莱的诗歌。萧军以后弃武从文的道路选择,在这里埋下了根由。 1928年冬天,萧军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9期炮兵科。“那是的军校,除开军事教程及参考书以外,任何杂书都不许涉猎,特别是进步文学作品。”一次平射炮演习,萧军做为预备炮手。他利用空闲时间拿出《石达开诗抄》来读,没成想一下子读进去了。当有人踢醒他时,炮已经在半里地之外了。这天夜间,萧军为此遭到了一顿毒打。如此迷恋书,如此不务正业,好像不太适合在军营呆下去了。 1930年夏,在讲武堂就要举行毕业典礼前夕,“石头疙瘩”萧军又一次被开除了。这次被开除的表层原因和上次一样,也是“冒犯尊长”。深层原因是“石头疙瘩”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一天,炮兵队挖掩体回来,经过步兵队战壕作业区。由于误会,两队发生了口角。这时步兵队队长殴打了萧军的同学,萧军上前制止,这位队长就作势殴打萧军。萧军顺手抄起一把铁锹朝他的头顶劈下去。要不是有人抱住了他,非出人命不可。 萧军离开了讲武堂,基本上结束了学生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