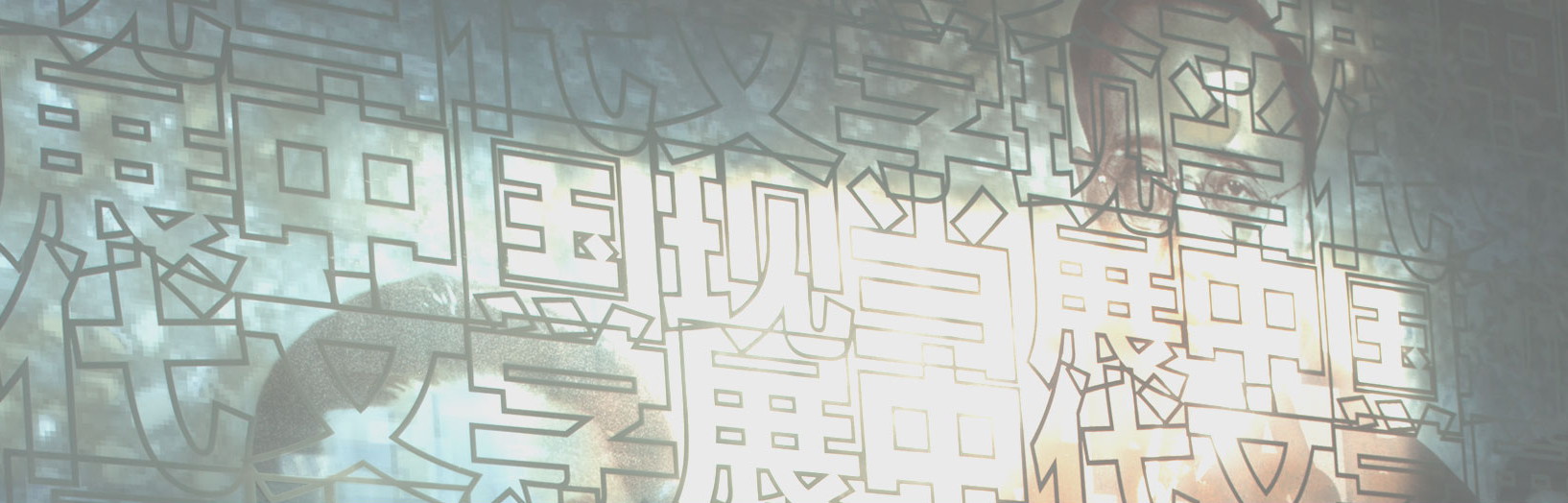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艾青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诗人,特别是在新诗发展的第三个十年,艾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的诗歌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他身上,世界的潮流、时代的声音还有个人的气质实现了最完美的统一。 艾青的诗歌创作从《会合——东方部的会合》开始(作于1932年1月16日),“艾青”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则是诗歌《芦笛——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时,然而让艾青声名鹊起,引起文坛注意的则是他作于狱中,1934年5月发表在《春光》上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也以其巨大的感人力量成为艾青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笔者认为,《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奠定了艾青整个诗歌创作的基调,是他诗歌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一、 诗歌与生命的同构 诗歌作品于真正的诗人而言,绝不仅仅是文字工作的结果,而是他最真诚的呼吸,是他整个生命的寄托与升华。古人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字斟句酌,今人也有海子这样将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到诗歌火焰中的诗人,虽死犹生。可以说,诗人的诗歌与其自身生命有一种同构关系。 艾青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在他一出生是就发生了。他生于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出生时算命先生说他会克父克母,所以一直到四岁他都被寄养在他的乳母大叶荷(诗歌中取其谐音“大堰河”)家中,五岁时才被父母接回自己的家中,但也只能叫父母叔叔、婶婶。可以说,艾青童年的生活是富裕的,但却不是幸福的,他相当于是一个生活上有父母,但精神上却没有父母的孩子。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能所有人都不能说清楚,但大家都必须承认这种影响,它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而文学家天性中的敏感因子又把这种影响放大了,大家如曹禺、张爱玲者,读者都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出这种影响。幸运的是,精神失怙的艾青却有大叶荷这个乳母,关于乳母的温馨回忆成了他巨大的精神财富。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火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经熟了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的爱简单的朴实无华,却带着她特有的厚重与温暖。无论是“灶火”、“炭灰”,还是煮熟的饭,拿起的第一颗鸡蛋都带着自己的温度和大堰河的爱一起融入了艾青的生命之中。在一生最初的时刻,艾青便接触了真爱,接触了地气,开始在古老和广阔的土地上扎根、生长。 当艾青在狱中想起了自己的乳母,想起了自己不幸但也有温馨的童年,一同席卷而来的还有她仿佛无穷无尽的苦难。“大堰河,含泪的去了!//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斯人已逝,长歌当哭,她带走了自己的辛酸,苦难还是在这片土地上横亘。其中“几尺长方埋棺材的土地”可能是最令人产生共鸣和思考的意象。古老中国社会,一个农民最大的梦想无过于对土地的渴求,有了土地也就有了衣食丰足,儿女恭顺,也就有了一切,而往往这些只是一个美好的意愿,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能将他们埋葬,却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在这人世间要做一场无根的漂泊,带着苦难辛酸,最终要化为孤魂野鬼控诉头顶那片阴霾的天空,这种控诉到了艾青的诗中就化为了对大堰河苦难的血泪诉说,是“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当诗人在狱中深深怀念和悼念乳母的时候,早已时过境迁,“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杯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此时的爱情也不是那个在乳母怀中的乳儿,他已经成为一个进步的青年,一个接受过“欧风美雨”的的熏陶毅然回国投身进步活动的有为青年。1932年,艾青回国不久就加入了“左联”美术家协会,并和江丰、力扬等人组成了“春地画会”,发型美术画报并举办画展。他们一系列的活动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他和几位朋友被捕入狱并以“危害民国罪”等罪名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很多人都说诗人的不幸有时恰是诗歌幸事,此语在许多屈原、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身上都有其有道理的一面。在艾青身上亦然。在狱中,缺少了绘画需要的颜料和其他素材,艾青的艺术创作开始从绘画转为诗歌,这对中国现代诗歌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一个大诗人由此诞生。 此时的艾青鲜明地看到,那些深重的苦难不只存在自己的乳母大堰河的身上,她只是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这种苦难一直以来都笼罩在他们的头顶,笼罩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儿子般的大堰河。”对自己乳母的经历和苦难有设身处地的痛,也许这才是最真挚、最好的“赞美诗”;对这片广阔土地上更广大的人群有一样的同情与理解,这才是一个伟大诗人的胸怀。苦难的土地、苦难的人民自此成了艾青诗歌中无法抹去的身影,土地更成了艾青诗歌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 二、 诗歌与时代的同构 好的诗人有优秀与伟大之别,笔者认为:伟大诗人的特质之一是他能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带动诗歌的走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开启诗歌的一扇大门,通向一条更广阔的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这便是大诗人的独到之处,苏东坡开豪放词一派也是一样的道理。而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也有这样具有开拓性和指向性的诗人,郭沫若是一人,艾青也是一人。郭沫若让白话诗倡导以来在创作实践上有了重要的实绩,而且在新诗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上大大开阔。而艾青的诗歌则是新诗第三个十年最成功的范例,既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同时与蓬勃的民族解放斗争血肉相连,达到了诗歌与时代的完美契合。 意象是诗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每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意象”(《现代文学三十年》p616),正如“香草”“美人”之于屈原,“月光”之于李白,“麦地”之于海子,古今皆然。如上文所述,“土地”是艾青诗歌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我爱这土地》 与《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样,这首《我爱这土地》也是艾青最脍炙人口的诗歌之一。在这首诗里,对祖国“土地”的热爱得到了最集中和最生动的体现。尽管这“土地”屡遭磨难,被“暴风雨打击者”,河流永远“汹涌这我们的悲愤”,刮着“无止息”的“激怒的风”,然而诗人的眼中还是“眼里常含泪水”,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如同对大堰河的“赞美”一样,诗人仍愿化为“一只鸟”,即使喉咙嘶哑,也要为这土地不停“歌唱”。 在这里,我们没必要把这里的“土地”和《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大地”做字眼上的生硬联系,两者在本质上本来就是相同的,它们的关联生长在诗人的血液中。从生命的一开始诗人便扎根在农民的怀中,真切地接触这这片土地上深切的灾难;在诗歌创作的一开始,诗人就将这种对苦难的言说与体悟贯穿始终。诗人的脚步从未离开满目疮痍的土地,他的诗歌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最终果实累累。 从时代的大潮而言,诗人是幸运的,他不幸生在民族危亡之时,他又有幸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从生命深处迸发出了耀眼的火焰和光芒,如凤凰涅槃一般甩掉一身枷锁,最终获得重生。体现在诗歌中,便是无处不在的希望。“希望”有许多不同的体现形式,“火把”、“黎明”、“太阳”等都是它的表征,而这些也成为了艾青诗歌中重要的意象,与“土地”一起构成了爱情诗歌创作中的主题,也将艾青的诗歌与时代紧紧连在了一起。“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太阳》) 深处在一个火热的时代,自然会充满希望,也自然会发出战斗的呼声,像《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这样的诗歌便是此例,然而艾青在对希望以及战斗呼声进行书写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苦难的深重,“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两者是诗中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有了对苦难的书写,才不至于让那份希望成了无本之木,变得虚无缥缈,也正因此那份希望愈发的灿烂光辉,也更加地催人奋进。这种“苦难”与“希望”之间的互动关系让艾青的诗歌有了独特的深沉忧郁的品质。他的忧郁不像象征派诗人和现代派诗人那样,在时代低潮时发着无奈的叹息,散发着幽微纤细的抑郁,艾青诗中的忧郁饱含这一种对苦难的深刻揭露和深切的同情。可以说,艾青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感受和书写着时代的脉动,他的忧郁也变得深沉和厚重。 艾青在创作伊始便被胡风成为“芦笛诗人”,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的诗作《芦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诗歌中体现出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胡风便指出他的诗“明显地看得出西方近代诗人凡尔哈仑、波特莱尔的影响”。从这一点而言,艾青的诗歌也达到了与世界诗歌艺术的同步。所以在他的诗歌中世界的潮流、时代的声音还有个人的气质实现了最完美的统一。而这一切,都源自于诗人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可以说诗人是用自己全部的人生经历和对这个民族、这片土地最真切的体悟进行创作,而这一切都是从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