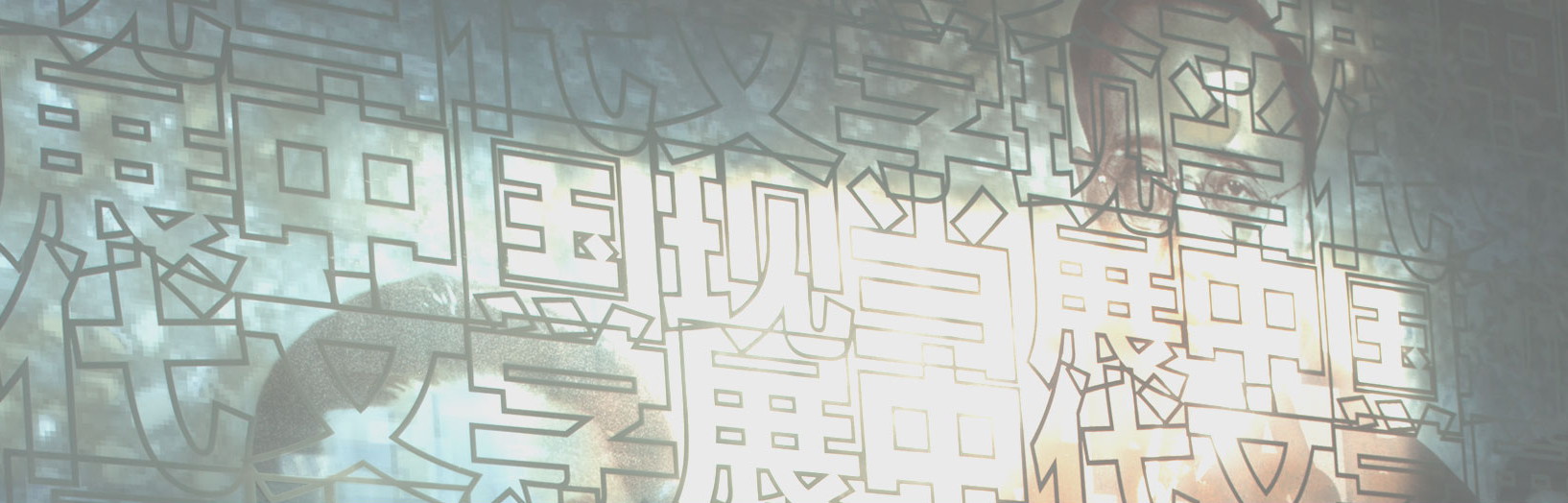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近闻,人生追求之终极,大致可谓“留因有二”:一为基因(gene),二为影因(meme)。基因者乃为人的本能所在,传宗接代,生命赖此绵延进化;影因者乃为人的影响因素,创造创化,精神赖此传播弘扬。很多英雄志士、英雌才女,灿若群星的文化名人、各界名流,概而言之,大都矢志追求生命的赓续和精神的传扬,特别是后者,能够体现为“人之为人”的文化品行及其达到的精神境界。其中,能够达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境界者,当为师者,影因巨大,堪为师表。在笔者看来,茅盾,无论其为人为文,做人做事,大致而言就达到了此种境界,可堪为人师表处甚多。或可谓,其人格臻于高尚挺拔之境,有如白杨;其文学达至一代大师水平,有如翘楚。故任何诋毁妄言,都无法泯灭其充满文化活力的影因,在其传播方面也是“给力”的,值得关注的。而那些或因政治,或因人品,或因误解等而恶意攻击茅盾者,自己倒是需要认真“反思”一下的。
文化名人大抵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并赖此形成不泯的影因和可资比较的话题。笔者曾在拙著《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中指出:恰是各种文化影响因素塑造了鲁迅与茅盾的“人格”和“文格”,二者相比,可以说鲁迅是新型文化的开路派、前卫派,主要以创造者的激情和战斗者的胆识,思想家的智慧和文学家的才华,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谱就了惊心动魄的人生乐章;而茅盾作为新型文化的稳健派、建构派,却主要以政治家的理智,文学家的细腻和活动家的才能以及分析家的明敏,建构了自己的人生世界, 谱写了悠远昂扬的人生之歌。他们的文化个性、创作个性都异常鲜明,无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还是面向文化发展的现实和未来,都可以说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鲜明个性及重大影响的文化巨人。就其有用于世的人生追求而言,则可以说: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的相当完美的结合;茅盾也当得起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师”,而非“文学小师”,更非“文学劣师”,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影响。即使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或不足,也实难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而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上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也已形成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主导方面看也已成为后人应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将鲁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成立的。而作为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于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实际业已证明了这点。正是这“天赐良机”的“新时期”接续上了自近代以来便萌发的立人立国的现代化之梦。五四时代的强音再度响彻云霄,透入人们的心底。由此我们看到了鲁迅、茅盾们的“复活”。值得说明的是,和鲁迅一样,茅盾将如何做人视为第一要务,将勇于担当、为国为民以及忠诚于信仰视为人格建构、文学创作的原则和律令,由此使其人其文具有了现实关切和堂堂正气,故茅盾绝不是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隶。特别重要的是,茅盾是一位特别执着于人生追求的求真务实的人,他最为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被损害者的人生。大抵而言,他的生命样态与鲁迅相仿,也显得特别成熟,甚至神圣,是民族的“脊梁”和时代的“良心”,难能可贵且不可或缺。尽管此类人也都有自己作为人而非神的难以避免的某些局限,但与时代同行的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必要,而且在民族危机或其他重要关头,他们总是那种挺身而出的多所奉献的人。这使笔者想起每逢国难当头或灾害袭来,固然会暴露出社会人生的许多问题,但也一定会由“脊梁”们张扬出天地之间难以泯灭的一股清正之气,着实令人感动感奋。对于民族、国家或人类社会而言,如果没有这种“脊梁”式的人们而只有那些私字在胸、玩字当头、损人利己的“顽主”,是否还能存在或者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也便成了疑问。显然,鲁迅与茅盾都是富有入世进取精神的中国人的优秀代表,尽管一位是善于医治心病的“医生”,一位是善于导引激励的“老师”,但他们的“职业”对中国人来说,其意义都是非同寻常且十分重要的。
是的,在笔者心目中,茅盾先生就是一位善于引导和激励他人且令人尊敬的老师,是古今中外文化“磨合”而成的独具魅力的“这一个”。这既可以显示出他的人格和文格,也可以显示出他为人为文的特色及影因,在文化界文学界尤其足以为人师表。固然,一个民族要有浪漫不羁的大作家,要有眷恋大自然的山水诗人,甚至也要有现代性爱小说和通俗文学大师等等,但无可争议的是,也特别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关注现实的严肃型作家。茅盾就是这种类型作家的最为优秀的代表之一。茅盾在其一生中都是做事注重“大事”、做人注重“大节”的,他能够密切关注时局政治,对国家命运的紧张思考也清晰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有些思考是相当有特色的,比如其代表作《子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实际是将其视为民族悲剧来描写的,将资本运作和都市生活的异化形态进行了生动叙述,并不是简单地认同了某种“主义”,也没有将生活的复杂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演绎。他的《子夜》、《腐蚀》、《蚀》、《霜叶红似二月花》、《林家铺子》、《春蚕》、《创造》、《白杨礼赞》等作品,都是堪称经典性的作品。并由这些熠熠闪光的作品,建构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和可以称之为“茅盾范式”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对建构国家文学、民族文学意义重大,对建构新型的理性主义、小康社会及当代文化等也均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其影因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诚然,文学世界本是艺术个性可以自由生长的园地,茅盾的文学实践自然也是在“种自己的园地”,何况他的历史影响业已产生,特别是他的史诗品格与艺术范式对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确实影响显著,而今虽有变化,但仍在延续着,只是方式复杂些、迹象幽微些罢了。比如被誉为新史诗的《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就曾表白,自己在年轻时就读完了茅盾的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就有着茅盾的重要影响,无论别人怎样看,茅盾先生的大师地位在其心目中都是永存的。(见《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在陈忠实看来“文学依然神圣”,而茅盾也依然是文学大师。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口吻听起来不是一种愚顽,而是一种执着的诚实,相当令人感动。即使仅从茅盾在文体创新方面看,他也不是那种甘于亦步亦趋的人,他在努力地超越着,建构着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个性。茅盾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方面投入了他最大的精力,其卓越的建树已被《子夜》、《虹》、《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长篇力作所证明了,而他身后设立的“茅盾文学奖”的比较普遍的被承认,多少也可以说明他对长篇小说文体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从茅盾生前的有关言论和同意设立文学奖来看,其实他对自己长篇小说成就还是颇为自信的。尤其是《子夜》在文体上的创造,开启和确立了现代小说社会分析派的审美范式。因此完全可以说,茅盾在现代长篇小说方面的创造性贡献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小说创作中发挥了他最大的艺术才能,成为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杰出人物和最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那种也许是因为意识原因而非文体原因有意贬低或无视茅盾文体创造的观点,是很难让人赞同的。
师者的影因存于有言无言之间。而茅盾的文化个性及影因的延宕,确已构成了一片亮丽的文化风景。这不仅在上世纪文艺界批评界可以领略到这样的胜景,也可以在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实践中领略到茅盾文化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更可以便捷地从“茅盾文学奖”等标志性事项及成果中,领略到“茅盾范式”的影因力量。是的,从茅盾文学奖的设立和评选中即可看出茅公的影因所产生持久的重要影响。其中既有其高尚人格(勇于担当、守正求变、谨言慎行等)的积极影响,也有其文格(史诗追求、现实主义、社会分析等审美范式)的重要影响。该奖自1981年设立以来,30年间举办了7届(第8届正在评选),共评选出33部作品(含获荣誉奖《浴血罗霄》、《金瓯缺》)。尽管水平有差异,过程存争议,但作为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最高文学奖之一,其专项性质(长篇小说)和限项运作(一般四年一次且仅评几本小说等)使其拥有了严肃周正的性质,颇有茅公为人处世的风范,其基本成功的评选实践使之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事实上,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文学界一个业界品牌,创品牌难,守品牌更难,不仅要正视和警惕那些总要砸牌子的言论和行为,而且要深切领会茅盾先生的人格和文格,认识和领略其精魂和影因,并将“茅盾文化”作为“教育资源”进行积极开发,充分发挥其化育人心、行为世范、砥砺创新的影响作用。
在此,笔者由衷对诞生115周年的茅公赞美一声:堪为师表的茅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