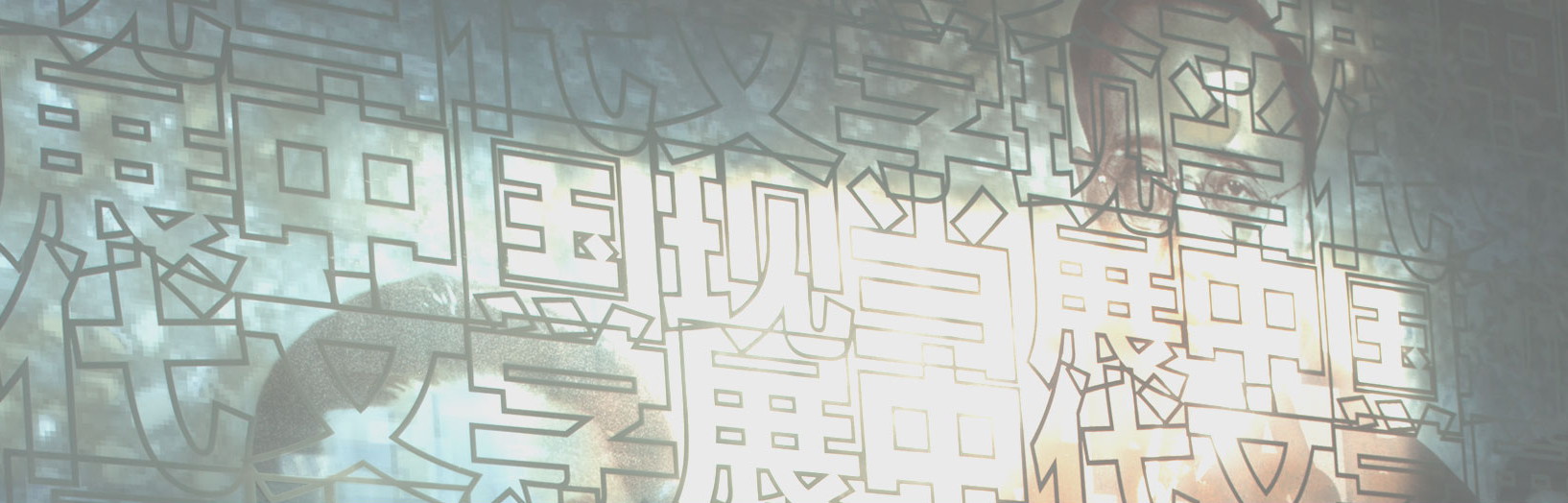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被文学界、语文教育界双双认同、赞赏,是中学语文教材选文的最基本前提。《背影》一文最早发表在1925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上,1933年被选入《国文》教科书,就是对其文学价值和传播价值的全面肯定。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其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第四册”,1982年又重新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自此,《背影》才不断地被解释、建构,实现自我增值。这种“解释、建构、增值”的过程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基本完成的。
尽管如此,伴随每次教材的修订和课程改革,也都会有质疑或反对的声音出现,从而引发大范围的讨论、争执。有人质疑其典范性,认为该作品不能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并加以极端的否定,乃至推翻朱自清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70多年来,围绕《背影》入选与否,文学界、语文教育届一直就断断续续地讨论着,其影响上及国家政治意识层面,下及普通个体审美层面,这就在中学语文视野中形成了一种现象——“背影”现象。
“背影”现象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背影》被要求退出教材的事件主要发生在三个时间段:1951年下半年至1960年、“文革”时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
前两个时期,《背影》被认为是“是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地位被极端地否定。1951年7月《人民教育》刊发了一位中学老师的文章,在该文的“按语”中说:“《背影》是表现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感情的,在现在实在没有选作教材的必要,语文课本中是不应该有它的地位的。”此后,一系列否定性的文章接连发表,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否定了《背影》的价值。接着,教材编写者硬性将其定调、删除。
第三个时期,《背影》的地位又遭到怀疑。2003年9月,鄂版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人员决定将《背影》逐出课本,理由是多数学生认为《背影》中“父亲不遵守交通规则”,“父亲形象不够潇洒”。2010年7月北外副教授丁启阵又发“猛炮”。他认为《背影》的感动是“不健康的”,“父亲跳下月台买橘子的情节”是不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表现,建议将其删去。文学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广大师生和普通群众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尖锐的批评。
《背影》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一篇文章,七十多年来几经取舍,在文学界、语文界引发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定下心来,全面梳理语文课程改革、朱自清作品、文化人格和人们接受心理之间的关系,以求得一个妥善的认知。
“背影”现象的本质
“背影”现象不仅勾勒出70多年来中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标准的变化。《背影》的入选、落选和争议只是表面现象,折射的却是“初中语文课改理念”和“文学经典教育与传承”的双重命题。
20世纪50年代对《背影》的彻底否定,只要我们密切联系当时具体的语境,就不难做出解释。这是当时思想文化界总体形势在语文教材编选和朱自清研究领域内(这一时期也是朱自清研究的冷落期)的具体反映。只要想想当时文学界对《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等文化事件的来龙去脉,《背影》被驱除出中学语文教材的原因就不难理解,那就是:教材编选者更多地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
后者则是目前民众不满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现状而发出的一种极端化的“声音”。当然,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这种勇于发表见解、关注课程改革的参与方式。“语文课改”可不是简单几个专家的事!倘若是积极地提出建设性的问题,当是大力倡导的;但是,如果把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当作游戏化、戏谑化的对象,这实在是很危险、很不负责任的破坏性行径。“父亲跳下月台买橘子的情节”被认为“不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表现”,这至少暴露了该作者人伦情感的隔膜性、空心化和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无知性。以“不理性和实用主义”来解释这一场景,实在站不住脚。至于以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很不潇洒”为由而将《背影》删除,充其量也就是一场闹剧,徒增笑料。
特定时期决定哪些作品选入,哪些作品撤下,只要合情合理,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背影”现象背后一直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极端评判倾向,即不以文章本身的文学价值论事,而总是以非文学性的尺度决定孰优孰劣。脱离了文章本身的文学价值,而将非文学性的东西生拉硬拽地撮合在一起,并把这当成删除《背影》的绝对理由,于情于理,这都是站不住脚的。若照此标准来衡定,语文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可疑的,都应被撤换。这就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怪圈。再者,一部分专家学者对语文教材中那些早已深入人心的作品似乎总怀有一种“敌意”:绞尽脑汁地恶搞、戏谑;好发惊世骇俗之言,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实际上,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学科建设,而是借此炒作自己。近期出现的所谓“鲁迅作品大撤退”事件,与此也如出一辙。
当然,非文学性的解释并非不科学、不实际、不需要,而要看哪种角度、哪种目的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背影》之所以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多是反动的、专治的,属于被打倒的对象,而朱自清的《背影》传达的却是传统的父子之爱,这激活了那一代读者潜意识里久违了的父爱情结。同样道理,一部分师生不喜欢鲁迅作品,也可以从教师队伍素养和教学理念寻找答案。这是由于多年以来,中学语文教育以知识性和工具性的授课理念和方式讲授鲁迅作品,过多地关注鲁迅作品的思想性、批判性内涵,弱化、忽视乃至抽离文学性因素和美学风格所致。脱离具体的语境断章取义地肢解鲁迅作品,这样,语文教育界制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幻想”,形成了一个“接受的怪圈”,即认为鲁迅作品思想深刻、不易接受。
其实,中学语文教材中朱自清(包括鲁迅)的作品大都以人性化的语言,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充满童心童趣,满溢灵思慧心,是其“人品”和“文品”高度融合的艺术结晶。其内在审美风范与中学生、普通民众感受事物的方式最为接近,因此,在当代中学语文教材中,像朱自清这样以真性情感受自然、社会、人生的作家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背影”现象的思考
(一)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背影”现象强化了人们对朱自清文化人格的认知,从正反两方面确证了优秀作家崇高的人格魅力。
人们称颂朱自清的文化人格为“完美的人格”,更因毛主席的评价——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而家喻户晓。他在为人和治学上的认真谦虚、外柔内刚、至情至性、大义凛然堪称一代学人的楷模和标杆。
这不仅见诸于后人的评论,更见诸于同时代作家学者的一系列文章中。王瑶、王力、吕叔湘、杨振生、吴组缃、李广田、郑振作、叶圣陶、吴晗、冯至、余冠英等都曾写过回忆性文字,称赞朱自清这种文化人格的魅力。曾华鹏教授曾把这种文化人格概括为“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形成的自由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心忧天下的士大夫精神,地域文化形成的空灵毓秀的文人气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人格恰恰在历次争论中,更加深入人心。
中学语文课程体系中的朱自清作品皆是其“人品”与“文品”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就是按照最严格意义上的“文如其人”或“风格即人”的美学定义,也能经得起检验。其实,反对者愈是极端性的言论,往往俞是反衬出其虚妄、空泛、伪善的本性。因此,朱自清和他的作品,恰如一面镜子,照出这喧嚣语境里“社会沉渣”本来的面目。
(二) 以《背影》为代表的朱自清作品为中国当代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预设了最好的课程资源,为传统经典文学教育与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初中语文教科书的选文标准的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时间阶段:1978——1990、1992——2000和2000年以来。这三个阶段提出的经典文学的选文标准分别是“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文质兼美,语言文字要合乎规范,难易适度、适合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此标准来看,改革开放以来, 《背影》高度暗合了中学语文课程改革的这种理念。
朱自清早期的代表作品——《背影》、《绿》、《春》、《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匆匆》等——早被选入课本而为广大师生所熟知;推而广之,朱自清的后期作品——《你我》、《欧游杂记》、《伦敦游记》中的篇章——完全可以当作选文或课外阅读的范本。其实,后期代表作品以口语为主,显得更纯正、地道、成熟,理应得到重视。
(三) 朱自清的作品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最好的范本。
在中学语文教育视野内,朱自清的作品较之鲁迅、郭沫若、茅盾、丰子恺等现代文学名家,其语言、主题、选材、美学风格等更适合于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趣味。不同的调查问卷都表明,语文教材里最受欢迎的现代文学名家,除了鲁迅,就是朱自清。这种喜欢不是——比如鲁迅作品——语文界强行灌输的结果,而多是平等对话、心灵相惜的自发产物。朱自清作品语言上的美感效应——汉语的节奏、质感、韵律、用词的讲究、语法的规范、修辞的搭配、口语的意味等——具有先天的优势,最适合于语文教学。美的语言表达的又是日常的生活场景、朴素的个体认知和普适性的道德情感,与中学生的认知规律、价值观念、成长过程构成了某种一致性。加之,朱自清本身就是一本上佳的“教科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