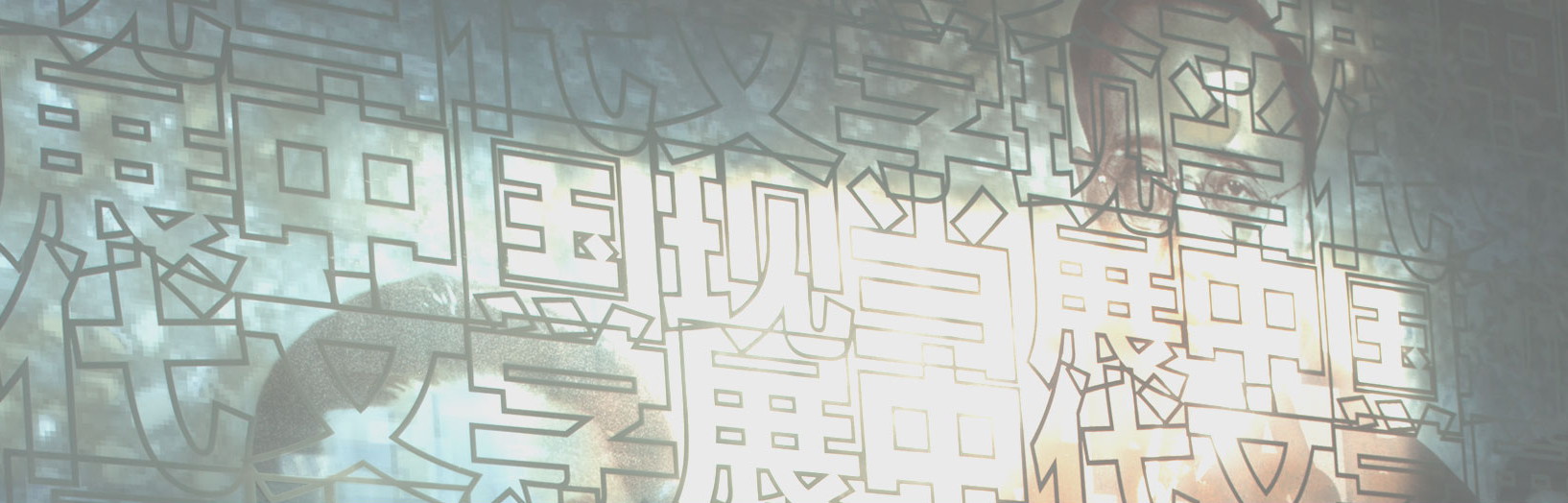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现当代作家姚雪垠是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姚学垠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上的贡献几乎无人知道。其实,与文学创作相比,姚雪垠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取得的文艺理论成绝不逊色,完全可以跻身中国现当代大文学批评家行列。姚雪垠不但在文学创作上开辟了一条历史小说创作的新路,而且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长篇历史小说美学上也取得了独特贡献。
姚雪垠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追求自由为目的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朱光潜在《自由主义与文艺》这篇论文中集中概括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观。这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观认为,第一、文艺应自由,意思是说它能自主,不是一种奴隶的活动。奴隶的特征是自己没有独立自主的身份,随时都要受制于人,就这个意义说,人都多少是自然需要的奴隶,脱离不了因果律的命定,没有翅膀就不能高飞,绝饮食就会饿死,落在自然的圈套,便要受自然的限制。“惟有在艺术的活动方面,人超脱了自然的限制,能把自然拿在手里来玩弄,剪裁它,重新给予它一个生命与形式。而他的这种作为,并不像饮食男女的事,有一个实用的需要在驱遣,它完全服从他自己的心灵上的要求。”第二、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艺术使人自由,因为她解放人的束缚和限制。第一,它解放可能被压抑的情感,免除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所说的精神失常。其次,它解放人的蔽于习惯的狭小的见地,使他随时见出人生世相的新鲜有趣,因而提高他的生命的力量,不致天天感到人生乏味。”文艺的自由就是自主,就创造的活动说,就是自主自发。“文艺所凭借的心理活动,是直觉和想象,而不是思考和意志力,直觉和想象的特性是自由,是自主自发。”(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481页。)与这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观不同,姚雪垠推崇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首先,姚雪垠尖锐地批判了文学想象万能论,认为文学是想象的产物和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完全在于作家的能力这些文学观念是浅薄的,这种文学想象万能论是观念论的,是受了浪漫主义文学观的余毒。在作家的天才和世界观的关系上,姚雪垠认为作家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几乎比需要天才还要重要。“处在我们这样矛盾冲突尖锐化极了的时代,一切现象都在动乱状态中存在、消灭,想认识现实,把握现实,非有科学的工具——正确的宇宙观不可。同是一个事象,由于作家宇宙观的有无或不同,有的仅看见表面,有的直看透了全体。没有宇宙观或宇宙观错误的人,虽然面对现实,也是直视无睹;纵令经验了许多事情,仍旧看不见事情的本来面目。”(《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和第8—9页。)
其次,姚雪垠反对文学是情感的产物,认为“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们,他们不理解这一层,因之把情感看做了文学的惟一源泉,他们放纵着自己的情感,于是甚焉者便任情胡为,装疯装狂。社会上因之骂作家,说作家是神经病,是不近人情的怪物。因之浪漫就在一般人心目中变做了吊儿郎当的同义语。”(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在作家的理智和情感的关系上,姚雪垠认为作家的理智和情感是矛盾而又统一的,“作家在选取题材,处理题材,以及完成他的写作过程中,他的情感固然起重要作用,而理智所起的作用更要重要。”(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强调科学的思想武装,“如果想避免无意中把有毒的、庸俗的,甚至卑下的情感传染给人,作家也必须使自己用科学的思想(理智)来支配情感,洗炼情感。”
最后,姚雪垠坚决反对作家脱离现实生活,认为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凭着想象,凭着热情,凭着技巧与天才,所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浮面的、空洞的,甚至是歪曲。这些作家们本身既不站在斗争的尖端,他们的作品当然不容易成为时代所必需。”(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在姚雪垠看来,那些终年关在屋子里的作家,就不会对宇宙的变化发生敏感,同样也不能对现实世界有深刻认识。而只有生活得深、观察得深,才能够思想得深。“所谓作家的敏感和作家的思想深度是不可分的,而这二者又和生活的宽度和深度成正比例。”
姚雪垠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姚雪垠认为:“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都是存在于客观社会现实里边的。只有忠实于现实的人,才能够从现实中发现真理。”因此,姚雪垠认为那些不敢正视现实、深入现实的人,不配做作家;那些对现实生活认识肤浅的人,不配做作家。“对现实生活认识肤浅的人偏要从事创作,结果对人类无益,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在姚雪垠看来,忠实于现实,故忠实于真理;深入于现实,故不能不有真恨、真爱、真的感情,不能不有所拥护、有所抗议,拥护那合乎真理的,而抗议那违反真理的。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充实;没有这,你的作品就空虚。有了这,你的作品就深刻;没有这,你的作品就肤浅。有了这,你的作品就崇高;没有这,你的作品就庸俗。而一切肤浅毛病、武断和偏见,都是产生于不能忠实现实、深入现实。(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159页。)
在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上,姚雪垠认为作品所表现的现实是否忠实、是否深刻是主要的,而作品的倾向则是次要的。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倾向,自然是不能够轻视的。但是,“单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好的倾向,没有深入现实的生活,你可以写口号文学、宣传文学、公式主义的作品,然而你写不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反过来看,只要你曾经在现实中深刻地生活过,透彻地认识过,你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会内容深刻、丰富,具备着好的倾向。”(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157页。)因此,姚雪垠提出主观倾向应服从客观生活,我们首先重视生活,其次才重视倾向。姚雪垠在批评使人臧克家的诗时指出,臧克家的诗只表现了主观方面的“真”,没有表现出客观方面的“真”,主客观没有变为一致。而“诗只有主观情感的‘真’还不够,主客观统一起来,才能够获得更高和更完全的‘真’。”(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姚雪垠认为作品的成功与否,内容深刻是主要的,艺术技巧则是次要的。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内容愈深刻的作品,愈能够感动人,愈能够引起广大的共鸣,愈能够抓住多数人的灵魂,愈能够引导人们恨所当恨的、爱所当爱的,愈能够使人们接近真理。一句话,能深刻方能感人,能感人方能影响人。(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在热情与小趣味的关系上,姚雪垠提倡真恨、真爱、真的感情,轻视小趣味。姚雪垠认为,自古而今,无论中外,凡是伟大作家对现实都极忠实,凡是伟大作品所表现的现实都极深刻。而忠实于现实,才能够深入现实,深入现实之后,才能够透彻地理解现实,对现实发生热情;而这热情,反过来又督促你忠实于现实、深入于现实。脱离现实,对现实的热情便要减弱,热情枯竭之后,就更不愿接触现实。而写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只能算是小趣味,不能算做热情。姚雪垠深刻地区别了热情与小趣味,认为“热情是向外奔放的,小趣味是向内收敛的;热情使你进取,而小趣味使你退隐。”(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那些对现实抱超然态度的人是写不出感动人的伟大作品的。姚雪垠有力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后期散文,认为周作人,“不管他怎样从《谈龙》、《谈虎》到《画蛇》、《听鬼》,谈鸟兽虫鱼,闭在苦雨斋里吃苦茶、讲笑话,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生活转变过程,是现实的一个侧面。在极其动荡和矛盾的现代中国,周作人反映出来——那从五四革命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特别脆弱的,含着眼泪没落下去的某种知识群。”(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上,姚雪垠强调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反对离开现实单纯强调理想,认为“虚构应该扎根于历史的深厚土壤,而不是扎根于脱离历史的空想。”(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提出了“深入”与“跳出”的文学理论,认为“写历史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先研究历史,做到处处心中有数,然后去组织小说细节,烘托人物,表现主题思想。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也就是既要深入历史,也要跳出历史。深入与跳出是辩证的,而基础是在深入。”(《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1985年1月,姚雪垠对这种“深入”与“跳出”的文学观有所升华和扩展,认为杰出的作家“或者对现实生活,或者对历史生活,在各自要写的生活领域,都需要一是深入,二是跳出。深入生活是跳出的基础和前提,而跳出是来自深入,虚构源于现实(历史是以往的现实)。能跳出才能有艺术,才有创作。”(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在艺术感染力与文学的娱乐作用的关系上,姚雪垠严格地甄别了有些无聊的有趣和艺术感染力的不同。姚雪垠虽然赞同小说应该有趣味,能够吸引人;但他不用“趣味”一词,而是用“艺术魅力”一词。(参见《姚雪垠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8页。)而姚雪垠之所以用“艺术魅力”一词而不用“趣味”一词,是因为“趣味”毕竟反映的是人的主观嗜好。姚雪垠认为真正的艺术不靠色情,不靠离奇古怪的情节。有些无聊的有趣,也有人入迷,但不能打动人心。而艺术感染力是能打动人心,使人感动。《红楼梦》非常吸引人,令人百看不厌,但是《红楼梦》丝毫不依靠曲折离奇的情节,更不制造惊险的故事,它吸引人是它内部的逻辑,情节本身的逻辑。
姚雪垠的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重视不够,甚至相当忽视,但是由于它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更为先进的力量——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总结和概括,所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姚雪垠虽然偶尔涉及文艺批评,但是他的这些文学批评不但十分犀利,而且相当透彻。姚雪垠划分中国“五四”新文学革命为“文体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前后两个阶段、梳理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演变过程并指出他同鲁迅的不和是两条道路的决裂、总结茅盾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卓越贡献、批评臧克家诗集《泥土的歌》的有些诗的主观的“真”和客观的“真”不能够溶合渗透以及细腻解剖臧克家的冲淡与陶潜王维的冲淡的不同,等等,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文学批评。姚雪垠不但在这种文学批评实践中留下了丰富的文艺批评思想,而且在深刻把握作家与文学批评家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精辟之论。首先,姚雪垠认为美与丑是有客观标准的。姚雪垠指出,美与丑毕竟有一个客观标准,并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漫无标准。这标准就是真理。其次,姚雪垠充分肯定文学批评的作用,认为深入、切实的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实践的指路灯。“文坛上如果没有批评,固然可以万邦协和,相安无事,但进步也不免停滞起来。批评不是相轻,而是相助。是求好的得以发扬,坏的得以改正。”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认为文学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是诤友关系,“批评家不是作家的敌人,也不是作家的捧场者,而是诤友。”然而,姚雪垠所期望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成为诤友的现象却很少出现。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作家缺乏接受文艺批评的雅量。因此,姚雪垠既反对小圈子作风,也反对主观主义,认为“门户之见,主观主义,和残留的旧文人的孤傲习性,都会障碍作家和批评家握起手来。”恳切要求作家既不要过于自私,也不要过于自恃。“倘若批评家指出来真正毛病,作家应该毫无吝惜的将原作加以修改,好让这作品对社会发生更好的影响。”这就是说,作家对批评既要虚心,也要自信。若不虚心,就不能接受批评;若不自信,就不能对批评有所选择。姚雪垠在对作家提出这些要求的同时,对文学批评家也提出了严格要求。这就是姚雪垠提出了不同于“捧杀”和“棒杀”的“默杀”这个概念。姚雪垠认为,如果“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管作品好也好,歹也好,大家默然。从表面上看,文坛上风平浪静,一团和气,但是这种现象的骨子里却很坏,它会使这文坛荒芜起来。”这就是“默杀”。而文学批评家要开展深入、切实的文学批评,就“不仅要有社会科学修养,同样也须具备着美学知识,而对于现实生活知道得愈多愈好。如是,批评才能够深入、切实,成为创作实践的指路灯。”(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146页。)1944年,姚雪垠在批评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时对当时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解剖。姚雪垠不但指出了当时理论落后在创作后面这个事实,而且深刻地解剖了这种文学批评现状产生的原因。但是,姚雪垠却没有肤浅地追究文学批评家单方面的责任,而是认为“如今大家都不肯态度严肃地写批评,一部分实在应该由批评家去负,一部分应该由我们作家来负”。这是全面而深刻的。接着,姚雪垠深入地挖掘了严肃的文学批评少的原因,认为“即让有人想做批评家,不是限于修养、便是限于气度,不能够担当得起这严肃的任务;至于作家方面,气量之小,也往往与所谓批评家不相上下,只愿意听颂词,不高兴听良言。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坦白说话,都不要民主作风,都当面做乡愿而背后做山大王,唯我独尊。严肃的批评也就少了。”姚雪垠尖锐地批评了诚诚恳恳地批评别人或接受别人批评的双重障碍,“一重是自信过强的,唯我独尊的英雄主义或主观主义;一重是小圈子作风,行帮作风。”主观主义和小圈子作风常常是互为因果,相生相成的。有些文学批评家主观色彩太强,把自己封锁在小圈子里,对圈外人缺乏诚恳态度,甚而不是一笔抹杀,便是默杀。有些作家犯了这同样的毛病,一方面不肯接受别人(特别是小圈子以外人)的批评,一方面常爱拉几个自家人写一点替自己捧场的批评。(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姚雪垠所指出的文学批评的弊病至今似乎更为严重。可见,姚雪垠的文学批评思想仍然没有过时,值得后人倍加珍视。
正是由于姚雪垠在文艺理论上造诣深厚,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他能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并积极地推动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人们认真研究《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就会发现姚雪垠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从1974年7月到1980年2月,在这七年时间里,姚雪垠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和作家茅盾通信88封。《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收入了他们围绕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问题和其它重要文艺理论问题的通信73封。姚雪垠和茅盾这些信中的美学思想曾经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1977年6月25日,姚雪垠摘抄茅盾关于《李自成》第二卷的评论在《光明日报》发表,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的标志。这就是说,姚雪垠(包括茅盾)在推动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的解放运动中是相当积极和自觉的。
首先,姚雪垠(包括茅盾)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深入。
姚雪垠和茅盾在通信中不但有力地抵制了当时文艺批评不谈艺术的不良倾向,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简单化、公式化、表面化的现象。姚雪垠认为茅盾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探讨“正是我们文艺评论界多年来所忽略了的或回避不谈的。”(《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而“许多年来,没有人能细谈艺术,文学作品的欣赏和评论,只剩了几条筋,影响很坏。”(同上,第91页。)姚雪垠坚决反对文艺创作的简单化、公式化、表面化,“不论小说或电影,看了开头就大体知道结局,好人和坏人都可以一眼看清,连儿童都立刻知道刚出现的是好人或是坏人。满足于将敌人从表面上加以丑化,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不肯写人物的深处,不追求写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有的作品只能将敌我斗争的故事写得曲折一点,但无救于表面化。”(同上,第85页。)追求“艺术的完美和深度”。姚雪垠关于人物描写的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朱光潜和刘再复。不过,朱光潜在1980年的《谈美书简》中反对描写见不出冲突发展的“平板人物”,提倡描写见出冲突发展的“圆整人物”,刘再复在1984年提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虽然和姚雪垠关于人物描写的美学思想近似,但比姚雪垠的文艺思想要僵化得多。
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尖锐地提出:“为什么我们读有的作品除得到思想教育之外同时也得到较多的美学享受,而读另外的作品,尽管它反映的内容很不错,却得不到美学享受?为什么《红楼梦》在艺术上那么感人,具有魅力?”(同上,第141页。)然后,姚雪垠正确地回答了这个尖锐的问题:“一部长篇小说应该给读者积极的思想教育,也应该给读者丰富健康的美学享受。忽略了后者,小说就不能感人深刻,更不能使读者多看不厌。”(同上,第70页。)姚雪垠在写《李自成》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探索了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姚雪垠和茅盾的通信从《李自成》的创作实际出发,除内容方面的问题之外,集中探索了一些艺术上的问题,包括如何追求语言的丰富多彩,写人物和场景如何将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手法并用,细节描写应如何穿插变化,铺垫和埋伏,有虚有实,各种人物应如何搭配,各单元应如何大开大阖,大起大落,有张有弛,忽断忽续,波诡云谲……等等。姚雪垠把这些要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探索的艺术技巧问题统称“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茅盾则用“艺术技巧”概称。姚雪垠高度肯定了茅盾的文艺评论,认为茅盾“具有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学力,总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小说作品,而不同于从干枯死板的条条框框出发。”(同上,第69页。)茅盾的这些文字,是茅盾晚年留下的重要文献,会引起后代的重视。这不仅因为茅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很有贡献的老作家,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不少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精辟意见。姚雪垠认为茅盾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分析和评论,“实为文艺评论的典范。”(同上,第57页。)姚雪垠不仅是重视茅盾的文学批评,而且努力推动这种正确的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姚雪垠反对简单化的文学批评,认为“简单化是目前文艺批评与创作的大病。”(同上,第84页。)提倡茅盾的文学批评。后来,姚雪垠从茅盾的信中将谈论小说艺术的部分抄出来发表,“推动重视艺术性的文艺风气。”(同上,第91页。)1977年,《光明日报》发表了茅盾致姚雪垠的主要谈论小说艺术技巧的书信摘抄,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艺术的认识。1983年,姚雪垠还挖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简单化这种偏向产生的历史根源,认为“解放区的文学也不是完美无缺。今天回想起来,从苏区到解放区,文学直接参加战斗,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政治要求强调过多,对艺术强调不够,则是一种偏向。这个偏向一直带到解放后,成为一种指导思想,谈文艺光谈政治,不谈艺术,不谈美学。”(《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点粗浅看法》,《姚雪垠书系》第18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而姚雪垠(包括茅盾)之所以能够推动文学批评的科学发展,是因为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追求进步。姚雪垠追求真理,认为他对历史“翻案的目的必须仅限于弄清历史真相,而不能是为着追求个人有所创获而标新立异。”(《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不断追求进步,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没有匆忙完成,而是必须在艺术上有比较显然新探索,方才脱手。姚雪垠(包括茅盾)的这种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潮流。
姚雪垠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1978年,为了纠正中国当代文学在人物刻画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不感人的倾向,姚雪垠总结了《红楼梦》的创作经验,认为“曹雪芹如果考虑的不是写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而是考虑如何写出同一阶级的共性,便写不出那么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红楼梦》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创作典型性格的光辉典范。(《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姚雪垠书系》第2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页。)1980年,姚雪垠要求《红楼梦》研究要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竭力避免将我们现代人的政治感情、思想觉悟强加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人物身上,“彻底摆脱从政治出发给学术研究所定的调子或框框,也摆脱从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出发,对《红楼梦》做些不实事求是的比拟或解释。”尤其反对迷信权威人物的结论。(《致〈红楼梦〉学术谈论会》,《姚雪垠书系》第2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89—590页。)1993年,姚雪垠还批评了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新迷信,一是认为“从美学上(或艺术上)分析《红楼梦》的成败得失就不能算是学问”;二是将《红楼梦》看成十全十美,无法逾越的里程碑。(《致张国光》,《姚雪垠书系》第20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10—511页。)姚雪垠在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思想解放的基础上致力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1980年7月19日,姚雪垠认为新中国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绩,人所共见。特别是在关于《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发现和考订,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更大。”在回顾新中国三十年《红楼梦》研究的基础上,姚雪垠强调对《红楼梦》进行艺术研究。姚雪垠提出了《红楼梦》研究今后努力的两大方向:一是除对曹雪芹的身世问题、《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脂批问题等等,继续进行发现和深入研究之外,“最好能分出相当力量从事这部伟大作品的艺术研究”;二是古为今用,即将研究与创作挂钩,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和研究提高中国文艺理论水平、文学史研究水平,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就是既要全面地分析和研究《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要分析它的不足之处,总结和“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指导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致〈红楼梦〉学术谈论会》,《姚雪垠书系》第2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590页。)姚雪垠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通过对《红楼梦》的研究,总结和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这些规律既指出了历史经验,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启发和指导作用。可是,中国当代红学界只提俞平伯的倡导,而遗忘了姚雪垠的贡献。
1985年,中国当代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片面强调“内部规律”的文艺潮流。有人提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在这种片面强调“内部规律”的文艺潮流中,姚雪垠(包括茅盾)这种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遭到遮蔽就不可避免了。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经过25年的发展,伟大的文艺作品却仍然难觅。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提姚雪垠(包括茅盾)提出的这些深刻的美学思想。
其次,姚雪垠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深入。
姚雪垠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种编写方法,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深入。1980年1月15日,姚雪垠在致茅盾的信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对“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给予充分论述。“我们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设立专章论述清末的风气变化和一些曾起过重要间接作用的前驱者。梁任公、黄遵宪等人的新运动(新小说运动和所谓‘诗界革命’),已经在动摇着旧文学的阵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替‘五四’新文学准备条件。至于清末的翻译西方文学和各地出现的白话小报,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这是大家都比较重视的,现代文学史的前边也应有篇幅论述。”(见《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接着,姚雪垠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只论述“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另外有一种编写方法,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故名之曰“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姚雪垠所说的“大文学史”,第一,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还有民国初年和“五四”以后的章回体小说家,也应该将其中较有成就的在新文学史中加以论述。“以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考虑的另一种编写方法,仍以‘五四’以来的文学主流为骨架,旁及主流以外的各派作家和诗人,决不混淆主次之分。”(同上,第131页。)姚雪垠着重提了与新文学运动对抗的流派“礼拜六派”。在发表此信所加的《跋》中,姚雪垠又提了这样几个作家:从“礼拜六派”分化出去,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做出过贡献的作家刘半农,在包笑天和张恨水这一部分作家中起过较大影响的徐枕亚,抗战末期和大陆解放前夕应该提一提徐訏,当时上海的女作家应该提到张爱玲。另外,有些住在海外华籍作家,只要具有一定影响,当然也应该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而这种“大文学史”观就是对当时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1980年7月19日,姚雪垠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姚雪垠所构想的研究《红楼梦》的学术史既包括索隐派,也包括王国维,带有总结性质。台湾的、港澳的、日本和欧美的“红学”情况也包括进去。重新评价胡适和俞平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极“左”思想的影响,教条主义的干扰,都要写进去。这部红学史既要反映“红学”的研究成就,也要反映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弯路。(《致〈红楼梦〉学术谈论会》,《姚雪垠书系》第2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91—592页。)姚雪垠提出的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姚雪垠的这种“大文学史”观是他推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深入的结果。1980年9月28日,姚雪垠提出了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两个原则,一是编写文学史,必须从具体作品出发,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二是编写现代和当代文学史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脚点进行工作,放眼各个流派,各个方面。姚雪垠坚决反对文学史编写的“关门主义”倾向,即一部文学史成为宗派文学史,认为“文学派别不等于政治派别。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不断分化,不断重新组合。所以现代文学史应以分析作品为主要任务,不应该轻视作家的具体作品而偏重政治倾向。政治倾向应该注意,但对作家说,最应该重视的还是他们的作品。作品是作家的主要的社会实践。”(《致吴小如》,《姚雪垠书系》第20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440页。)中国当代那些“重写文学史”的人不但在重写文学史中少提甚至不提姚雪垠,而且埋没姚雪垠这种独特的贡献。
姚雪垠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重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他的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观与那些“重写文学史”的人的“重写”观是根本不同的。一,姚雪垠重视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反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就深刻地揭示了李自成失败的历史命运,“英雄人物在事业发展和有巨大成就时,他同广大群众(甚至旧日战友)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往往是二者相兼具。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总会有一批人由于各种原因在领袖人物周围筑起一道墙,甚至几道墙。”(《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这是《李自成》在历史哲学上对历史上的长篇历史小说的根本超越。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潮流恰恰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回避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二,姚雪垠提出的“大文学史”一方面要求尊重客观的文学事实,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兼容并收,即没有主次的分别。而有人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围,认为不能停留在形式上,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文学观念,修正文学批评尺度,即坚决否认为鲁迅、茅盾、张恨水、程小青、王度庐、还珠楼主、周瘦鹃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存在价值高下的分别。(高玉的《放宽评价尺度,扩大研究范围》,《文艺争鸣》2008年第3期。)因此,那些鼓吹改变价值观的“重写文学史”的人忽略、遗忘甚至遮蔽姚雪垠的独特贡献就不是偶然的了。
姚雪垠不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同“左”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斗争。1956年,姚雪垠尖锐地指出清规与戒律的害处:“创作题材的狭隘,内容的千篇一律,风格的单调,正面人物形象的四平八稳,如泥塑木雕,都同清规与戒律的作祟有关。由于清规与戒律太多,恐怕有不少作家的潜力不能够很好的发挥。”(《谈打破清规与戒律》,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页。)认为“只有不断地打破清规与戒律,文学的园地里才能够开满大小不同、形状各异、色彩千变万化,无限鲜艳和灿烂的花朵。”(同上,第253页。)姚雪垠不但提出打破清规与戒律,而且深刻地指出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是产生各种各样清规与戒律的主要源泉。可以说,姚雪垠提出不断地打破清规与戒律,就是反对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1957年初,姚雪垠坚决反对轻视甚至忽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的“左”的思想倾向,认为“如果说旧的生活经验完全无用,或轻视旧的生活经验,显然也是十分错误的。这是机械地把生活经验划分新旧,割断了生活的纵的关系,不承认生活永远是历史的运动过程,前后承接。”(《创作问题杂谈》,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姚雪垠不但在公开场合同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而且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中进行抵制。姚雪垠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时不顾任何压力,在完成第二卷的过程中蔑视所谓“三突出”的创作经验。(《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就是在一部作品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至于所谓反面人物(以阶级划线),可以不写,或只是简单地写,加以贬词。这种“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中是没有踪迹的。1973年夏天,姚雪垠公开质疑“三突出”的原则,认为“三突出”的原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只适用于一定领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于山水画、抒情诗、小歌曲等等这些不写人物的文艺作品,不以“三突出”原则去硬套,将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否则就会妨碍其发展。(参见《姚雪垠传》,许建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1页;程涛平的《“文革”中姚雪垠对“三突出”的质疑》,《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三期。)姚雪垠亲身感受和经历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发展史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错误的文艺思想的斗争。
因此,姚雪垠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运动中虽然受过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甚至在某些时期泛滥成灾,但是始终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错误的思想在进行抵制和斗争,从来不是一面倒。……在某些历史阶段,虽然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教条主义甚嚣尘上,甚至用组织和政治手段推行这种错误思想,但它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的,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尽管在某些时候受压抑,受打击,坚持的人不是多数,但它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是中国文学运动史的主旋律。”(《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见《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2—423页。)这和陈涌对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把握是完全相同的。陈涌指出:“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一方面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有过严重的错误,而且错误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需要继续大力加以彻底清理。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自有革命文艺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一直是强大的。即使在错误的思想和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也没有泯灭,不但没有泯灭,而且,相反的,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受到锻炼,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革命的敌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压迫,是不择手段的,而革命文艺阵线内部指导思想的错误倾向又屡屡出现。但正是在和外部敌人和革命内部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因此也越见其坚强。”(《文学主体性论争集》,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5页。)可以说,姚雪垠和陈涌对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发展史的这种把握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姚雪垠的这种文艺思想不能说没有任何缺憾。这就是姚雪垠的文艺思想过于偏重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而轻视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甚至在有些方面还贬斥浪漫主义文学观。因而,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坛流行浪漫主义文学观时,姚雪垠包括他的文学创作就难免遭到排斥和轻视。姚雪垠的这种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曲折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