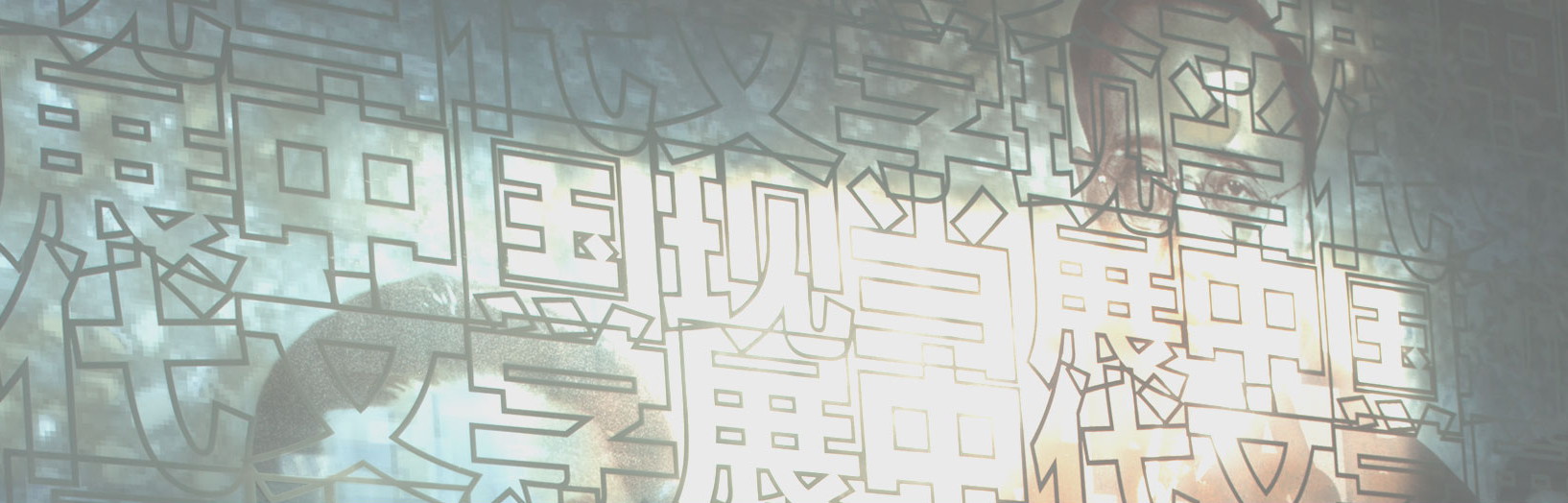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诗人唐湜认为,艺术家要追求“自己所需要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成”。这个“自我”,包蕴了艺术创作的精义之一,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艺术家自身的情性、天赋和体验对于文学创作,是多么的重要。因而,读懂一个艺术家,就要“带了肌肉官能的感觉与欲望”去体验他,感受他所感受的,体验他所体验的,痛苦他所痛苦的,乃至理解他所师法的……如此,才能真正感受一个艺术家的情性与精魂。而郁达夫正是这样一个钟情于自己创作情性的人,他对文学的贡献正在于他对自己感受力的忠实。对于这样一位用心用情书写自我的作家,我们不妨将自己沉浸于他的文学世界中,放下一切的冥思苦想的脑力思考,随着心性的方向自然体验他作品中那流动着的情思,这种流动的、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受的力量,或许是真正能够体现作家艺术魅力的地方。也或许正是他的作品真正吸引读者的地方。
感受
借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同样,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也在实践着他这种为自我而写作的理念。这个“自我”是作者自身的直观感受力。它借助作品中的人物或意境得以呈现。郁达夫进行文学创作,毋宁说他是在完成自我,这也即是他所说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因而,这种忠实于自身的文学,必定是依赖于作家丰富的感受力的,它也必定会将作品直接传达于读者的感官,继而引发人的共鸣。
品读郁达夫的几篇名作,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还是《迟桂花》等,都以其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现之于读者,这种心理之真实、丰富、复杂,令读者感同身受,仿佛窥探到了另一个自己。细细体验这种感受力的传达方式——即是引起读者身心共鸣的方式——也即是能够呈现世界和人的那种“流动”的真实感,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郁达夫的艺术世界不是先验的、概念的,而是血肉一体的真实感,这种艺术感觉与“公式化”、“概念化”相反,是一种“流动”的鲜活,这或许才是艺术真实的题中之义。我们来看《银灰色的死》中的一段景物描写。
他胡乱的喝了几杯酒,吃了几盘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来。外边街上,人声嘈杂得很。穿过了一条街,他就走到了一条清净的路上,走了几步,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看着太阳已经打斜了。远远的回转头来一看,植物园内的树林的梢头,都染成了一片绛黄的颜色,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都起了一种惜别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身,背负了夕阳的残照,向东的走上长坡去了。
如此描写,将主人公寂寥落寞的悲凉心境烘托得恰到好处。此情此景,正能引得读者去感受主人公心境的复杂。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感受力的浑然天成而苛责郁达夫的作品寻不到“思想”的影子。恰恰相反,创作对象的丰富性是不能仅用“思想”就能概括的,或者说,“思想”一旦说出口,便极易成为固定的教条化的东西,它可以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却无法传递创作对象那种真实的感受。而郁达夫正是以其天赋的敏感,将他的体验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出来,那正是他生活的结果。而这种生活中陶冶出来的体验和感受,往往是最丰富最打动人的东西。
仔细分析,郁达夫的感受力,并非天马行空地任意想象,而是扎根于他的切实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审美想象力,艺术的真实,正是需要这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来传达,而不是需要那种外加的理念和思想,。因而,他正是沉浸在生活本身之中创作的,这种创作,契合他的体验、经历、性格、兴趣,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和浑融。至此,我们可以说,在对“自我”与“个人”的感受中,郁达夫完成了他自己。
选择
选择写什么,或者说,作家想要表现什么,往往是文学创作的第一步。选择,是创作者对自我创作敏感区的细致梳理,也是作家对创作期待值的主要实现途径。因为,一个作家喜欢关注什么,他必然喜欢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什么;反之,一部作品中主要体现什么,那么它也必然是作家思维的敏感区和兴奋点。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作家的感受力和敏感区,构成了他创作天赋的核心所在。
选择有体验的生活进行创作,这也是郁达夫的选择。综观郁达夫的作品,大凡经典之作,无不与“零余者”有关。“零余者”是一类无关别人之痛痒的人,他们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可是现实的残酷让他们看不到希望,世间的一切欢乐似乎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能在颓靡中自生自灭。这种得不到认可的感觉正是当时社会中多数青年的心理写照,同时也是作家郁达夫深切体验。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沉沦》中的这段话,将“零余者”们的高傲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相信,郁达夫的体验,使得他真正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人物,并且传神地表达出了主人公的心态。这种刻画是创作者与创作对象合二为一的结果,一切的创作尽可跟着作家的感觉走,整个创作变成了一次酣畅淋漓的自我叙写,变成了一场不得不写的情感释放。而这,往往是创作的最佳状态。我相信,这种状态是愉悦的、充实的。
选择,是围绕自身感受力的选择。郁达夫对“零余者”的偏爱,毋宁说是对他自己感受力的偏爱。他对自我和个人的书写的敏感,使得他总是围绕这个兴奋点选择题材,这种选择可以说是不由自主的。因为,只有选择这类题材,郁达夫才能将自己的感受力最大程度地表达出来,并以此冲击读者的感知系统。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既然郁达夫的很多主人公都可以用“零余者”来概括,那么郁达夫的很多“零余者”作品就可以看成是“零余者”在不同时空的人生经历。这些不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组成了作家郁达夫的选择轨迹,也构成了郁达夫自己完整的“自叙传”。
转型
转型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作家力求突破自己的创作实践,郁达夫也不外如此。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抗战与救亡的呼声愈演愈烈,革命文学应运而生。在这个激流涌动、热血沸腾的年代中,任何一个心系民族危难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安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之中,郁达夫也是这样。
新文学之初,郁达夫解剖自我、展示自我内心欲求的文学创作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文学的桎梏,并以其惊世骇俗的先锋性形成摧枯拉朽之势。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文学的革命性,因为这种创作对于旧文学乃至旧体制的冲击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试想,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学,什么时候赤裸裸地关注过个人、关注过自我?又有哪一种文学如郁达夫这般敢于解剖自己的内心,坦诚地公布于读者眼前?因而,这种对于民众自我意识的启蒙和洗礼,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自我意识启迪了民众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追求精神,从思想积淀中日益洗刷了几千年来中国民众“精神奴役的创伤”。
可是,到了二三十年代,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小我”对于旧文学的冲击已经不再能够与集体主义的“大我”相提并论。这个时候的社会形势,急切呼唤着民众的革命意识,因而,革命的“大我”精神应运而生。此时,文学需要呼唤民众投身革命,去摧毁一个旧时代,建立一个新时代。因而,那种有统一、鲜明的革命立场,反映革命的历史进步和历史必然性的文学创作成为时代最需要的文体。
要想知道革命文学是否能为郁达夫所擅长,只须论证郁达夫自我意识的“小我”与革命文学之“大我”是否合流即可。这个问题很明显,在“大我”所必须的统一的思想和革命立场下,“小我”须要遵守这个立场和旨归。这就意味着,郁达夫所擅长的对自我意识和内心真实欲求的感受力必须受到革命的集体意识的约束和匡正,他对“小我”的展现必须要得出“大我”的结论。
我们上文分析到,郁达夫的艺术感受和艺术创作选择是天然地融为一体的,他的天赋要求他只能选择类似《沉沦》的表现方式来叙写内心的创作冲动。我们有理由相信,郁达夫创作冲动的真正实现,不应受到任何外加的“思想”和“观念”的约束,即使要表现某种理念,也应该是作品自然体现的,其中不应看到任何人为和技巧的成分。因此,革命意识的体现就应像“零余者”的内心一样,让读者深入其中,产生共鸣。
但郁达夫的此类创作并不如人意。首先,他的创作不可能回避自己的优势,因而,对于革命本质的体现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意识,要么喧宾夺主,要么不伦不类。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刻画了三类志趣不同的女性形象——奋斗的女性、犹豫的女性和堕落的女性。其中的堕落者郑秀岳是一个类似“零余者”的形象,也是作者最为擅长的人物形象。但是这次,郁达夫显然将她作为一个否定形象来刻画,以此彰显奋斗女性的光明。但是,此次,郁达夫善于刻画“零余者”内心的创作感受力却与他的选择显得格格不入。一方面,是令读者可感可触的“弱女子”,另一方面,那对于革命本质的体现的奋斗的女性形象却是显得那样概念化。最终,读者的感受仍然被郑秀岳所牵引,随她走入了她命运的深处。宏大叙事被个人命运的感伤所淹没,原本主题先行的“结论”成了一种外在的附加。郁达夫的转型最终没有战胜自己的个性和感受。
在认知与天赋之间
一个艺术家的认知可以归结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认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他们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世界观。一般来说,世界观对于作家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在上述郁达夫的“转型”中,郁达夫对创作的自我调整,正是他对革命现实认知的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将自己的创作感受力、敏感区与他的认知融合为一个整体。
如果我们把郁达夫的认知系统看做一个理性占主导的领域,那么这种理性对于创作的指导就与他先前呼之欲出、不能不写的艺术冲动有了本质的区别。在艺术创作领域,生活的积淀与磨砺、作家的兴趣与体验、现实环境的变换与催化,都可以影响作家艺术感受力的形成和艺术冲动的实现。其实,所谓的感受力和艺术冲动,虽然看起来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却是扎根于作家切实的生活体验而形成的,它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那种基于人类共同心性的体验与现实世界的真实碰撞。因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我们可以将一个作家对现实世界感受力的强弱看做他艺术天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天赋感受力与作家所经历的现实密不可分。因而,它不是一个不可琢磨的神秘领域,而是生活的真实与作家先天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讲过,现实的真实性不能流于机械、概念和固定,因为,一切公式化的东西都不能完全涵盖生活的丰富性。而艺术的魅力和价值也正是体现在它能够以艺术的真实去洞见和呈现现实的真实,再现现实的丰富与具体,并将这种丰富性以可感的方式直接作用于人心。在这一方面,艺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既然如此,理性的认知要想真正以艺术的形式发挥作用,那就必须转化为作家的感受。
让感觉整合理性认知,与真实的生活体验亲密无间,这是使得理性认知切实发挥艺术感召力的唯一方式。因而,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集体主义创作主宰文坛之际,批评家和广大作家首先强调的总是“深入体验群众生活”,可见,深谙艺术规律的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抹杀“体验”和“感受”对于艺术的巨大作用。
但是,让感受整合理性认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融合着作家生活经历、性格、兴趣、创作敏感区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个不能强迫整合的过程。因为,如果不能尊重这个过程的复杂性,那么便会极易让理性束缚住作家鲜活的感受力,从而让思想和理念成为作家感受的附加物,最终演化为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说到底,“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而作家需要做的,便是让自己的生命之树去汲取理论的养分而日益壮大,而不是让理论成为生命之树的附加物。如此,理性认知与艺术感受才能做到真正地融合。因此,我们不能苛责郁达夫的转型创作,因为,他的生活体验和经历、他的艺术感受和选择,实在不能让他迅速融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的艺术天地之中去。毕竟,作家不能无视自己的生活轨迹。
内涵
郁达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天赋和局限。他对于文学创作作如下解:“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体验。”因而,当他写出掺杂着理念先行的《她是一个弱女子》时,连他自己也说:“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成我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郁达夫或许对自己过于苛责了,但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他对先验的主题没有转化为自己的创作体验的懊恼。
本着一个作家的创作轨迹来分析,郁达夫其实一直致力于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以修养自身的体验,来达到自身的新的“完成”。当这种完成自我的努力在文学创作中遭遇阻力之时,他仍然无奈地说道:“做文士也好,做官也好,做什么都好,主要的总觉是在自己的完成。”
如果理解了郁达夫这种感受,我们就可以理解,完成自我,是艺术家不断追求“新”的自我体验,以期完成更广阔的生活与自我合二为一的艺术旨归。从这一点上讲,郁达夫的内涵在于他不但在自己的天赋感受中完成了自我,而且在艺术追求中明白了怎样才能完成自我。在当时纷乱的文坛中,他不失为一个清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