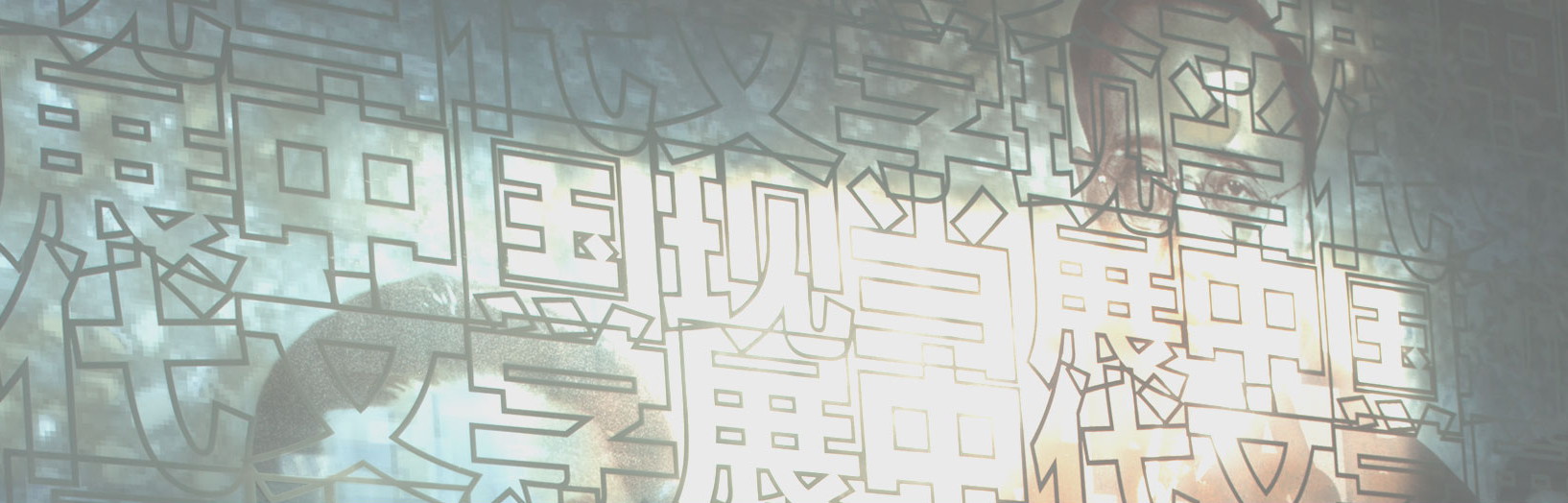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郁达夫自《沉沦》小说发表登上文坛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不仅因为作品内容的性本能描写而被视为性描写作家、“颓废作家”、“零余者”书写者,而且还因为其纤细敏感、激情张扬的个性与沸沸扬扬的家庭婚变而一再被人提起,成为人们议论的闲资和炒作的噱头,而忽视了其文艺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内在嬗变的精神历程。事实上,郁达夫的文艺思想、审美精神关照和文学创作在不断演变,其中既有较为稳定的内在精神结构,又有着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拓展丰富的思想意蕴。本文拟从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演变视角,来展现一个为常人和研究者所忽视、遮蔽的郁达夫,探寻其文艺思想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启示。
一、从“颓废作家”到城市底层书写者
在郁达夫早期的小说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患有精神郁郁症或肺病患者的叙述者形象。在福柯和苏珊·桑塔格看来,疾病有着两种不同的隐喻:一个是,患病者因为疾病的发生在带来的精神恐慌和情感缺失,受到周围人的“驱逐”和“隔离”;另一个是,患病者又因为疾病的发生而拥有了“敏感”、“创造力”、“形单影只”的“卓然独立”“艺术家”精神品质。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的病患者,不仅有着较为明显的神经抑郁和肺病症状,而且还有着由于身体疾病而带来的独特精神气质,即实现了从生理病人到“艺术家”、精神病人的隐喻性转换。
《沉沦》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忧郁症愈闹愈甚了”的“他”。“他”不仅要“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把自己变成“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这个具有“创造力”和艺术家精神气质的病患者渐次展示了“飞云逝电”的心思和“无边无际的空想”:病之抑郁、生之苦闷、性之压抑、离乡之苦、国衰之痛。“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从个体生命疾病体验到民族国家的精神创伤,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不是简单地精神放逐和自我遗弃,而是在其无限伤感、颓唐、忧伤的背后,有着深深的自我救赎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正如郁达夫在《茑萝集》自序中所言,“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然而,存在的悖论就在于,小说中的“他”在享乐纵欲和洁身自救之间苦苦挣扎,但最终又在强烈的性本能和“复仇”意识之下陷入欲望放纵和精神放逐、自我否定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沉痛不已。因此,我们在看到赤裸裸的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中,还应该考量到一个纵欲主义背后的道德戒律和精神救赎,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灵魂的迷茫、困惑、挣扎、拷问和鞭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早期小说成为五四文学主观抒情流派的代表性作品,有着重要开创性价值。
郁达夫回国之后,其文学创作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从以往“性之苦闷”转向“生之苦闷”,作品叙述视角和故事结构有了更加宽广、坚实的社会基础,主人公也从单一的疾病患者转换为城市底层劳动者。《春风沉醉的晚上》是一个过渡性作品,作者审美观照的中心已经转向城市底层的被剥削者——烟厂女工陈二妹。通过巧妙的故事构思,“我”遇到了在城市举目无亲陈二妹,在一系列“误会”中,展现出了城市底层美好善良的心灵。“我”在瞬间所涌起的“性欲冲动”也在陈二妹纯洁心灵感召下,得以净化和升华。1930年代的《薄奠》是郁达夫城市底层叙述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故事发生发展的重要见证者。“我”有着一副人道主义热心肠,同情人力车夫劳作的艰辛,虽然做不了什么,但是“总爱和洋车夫谈闲话,想以我的言语来缓和他的劳动之苦”,实行一种“浅薄的社会主义”。通过聊天,有了缘分,接连坐了好几次,我们渐渐熟起来了。“我”开始介入了人力车夫的生活,了解城市底层生存之苦、社会剥削之痛。物价的飞涨、洋车东家的挑剔与狡诈、女人不会治家的苦恼,“这个年头儿真教人生存不得”。“我”不仅听他悲哀的诉说,而且看到了夫妻二人因为不布匹的争吵,过着一种简陋心酸的非人生活。车夫最终在一场雨灾中死去了,而“我”和他的妻子揣测他是因为不堪没有希望的剥削之苦自杀而死。所以,结尾中,“我”不禁对着红男绿女大声斥责:“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至此,作为小说叙述的原动力已经彻底从性本能欲望转化为一种对城市底层的人道主义情结,小说叙述从原来的性心理、性行为叙述彻底转向城市底层叙述,主人公的“我”也从一个颓废的个体生活“零余者”转向积极的社会生活“介入者”了。
二、从城市底层书写到农民、大众文艺的倡导
1920年代风云激荡。作为创造社的元老和主将之一的郁达夫,很快就感受到中国社会现实的快速发展变化。正如鲁迅所认识的那样,坚持思想启蒙是重要的,但是思想启蒙审美功效太慢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郁达夫的文艺思想在从性之苦闷到生之苦闷的转换过程中,也意识到了仅仅关注主观自我心灵世界是不够的,仅仅关注城市底层也是不够的,开始思考起了一个更加宽广、更加核心、更加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文化重建问题。中国农民思想意识没有现代化,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就实现不了;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能够为古老的乡土中国社会转型、文化重建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倡导和建构具有乡土中国本土意义的农民文艺。
整个1920 年代,中国各种文化力量开始了对乡土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逐渐发现了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极大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认识,在文学审美想象中产生了一种的新的形象塑造要求和对无产阶级文学、农民文学的文学新召唤。1923年12月,茅盾敏锐地反对“吟风弄月”的恶习、“醉罢;美呀”的所谓唯美的文学、颓废倾向的文学。他批评中国知识阶级中了名士思想的毒,大力主张“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现代“活文学”,大声呼唤“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 1925年5月到10月,茅盾连续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系列文章,提出了受压迫群体之一的农民艺术观点。
倡导唯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早期创造社主将之一的郭沫若也开始文艺思想的反思。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认为现在进入了“第四阶级革命的时代”,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地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地,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地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经过去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关注农民运动的文化洪流中,郁达夫文艺思想有了的新的演变。1926年,郁达夫发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若要追溯他的渊源,也与人类一样的古”,并把“反抗”、“否定”、“申诉”“攻击”视为“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品格。这与鲁迅所倡导“撄人心”的“摩罗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1927年9月,郁达夫在《农民文艺的提倡》提倡一种新型农民文艺。他认为,“说到农民与文艺,向来就很少,尤其是在中国”,陶渊明、范成大的那些田园杂咏是不能称之为“农民文艺”的。“文艺是人生的表现,应当将人生各方面全部表现出来的。现在组成我们的社会的分子,不单是游惰的资产阶级,凶悍的军人阶级,和劳苦的工人阶级而已。在这些阶级之外,农民阶级,要占最大多数,最大优势。而我们中国的新文艺,描写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是有了,讽刺军人的横暴残虐的是有了,代替劳动者申诉不平的是有了,独于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农民的苦楚,却不见有人出来描写过,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新文艺的耻辱。” 因此,郁达夫倡导,“亲自到农民中间去生活,将这一块新文艺上的未垦地开发出来,或者对于乡村的文学青年,加以征搜奖励,使他们有生气勃勃的带泥土气的创作产生出来。……提倡这泥土的文艺,大地的文艺。” 可见,郁达夫倡导的“农民文艺”是一种农民为本体和主导地位的新型文艺观。
郁达夫不仅从理论上倡导新型的农民文艺,而且身体力行从事农民题材的小说创作,对从乡土中国沉默的大多数极其悲惨命运进行审美观照。《微雪的早晨》和《出奔》是郁达夫描写乡土中国农民生活的重要作品。《微雪的早晨》借助“我”这个叙述者,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因为与朱君要好,所以受到邀请来到他的农村老家,不仅发现朱君的两件伤心事,“第一是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里的贫穷”。之后,开始描写朱君性格、行为的“变异”:极为节俭的开始喝酒、放声谴责社会、过于用功导致精神失常。结尾展现朱君悲剧的直接根源是军阀强娶他的初恋情人。朱君是一个被侮辱、被剥削、被损害的乡村农民知识青年形象,他没有找到一条能够反抗悲剧的道路,而成为不幸的牺牲者,这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郁达夫“零余者”系列审美形象。1935年,郁达夫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描写了一个青年革命者钱时英被地主腐蚀、收买、利用,直到觉悟、复仇的过程,揭示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奸诈狡猾,呈现了这一时期作者对乡土中国现代转型和中国农民命运问题的思索。显然,钱时英已经从“零余者”系列形象中走出来,成为一个革命者、觉醒者和反抗者。对于郁达夫的文艺思想而言,这无疑是有着新质的意义和价值。
郁达夫不仅倡导农民文艺,思考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而且还有着更为宏大和开阔的审美视野。1927年,郁达夫在《民众》发刊词中,谈到乡土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中国目下的民众,实在是一点儿势力也没有,一点儿声气也没有”,所以“我们要唤醒民众的醉梦,增进民众的地位,完成民众的革命”。1928年,郁达夫在《大众文艺》第一期,明确提出,“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抗战文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时期,郁达夫进一步思考文艺的价值、功能和受众对象的问题。他的“大众文艺”观也越来越充实、丰富和具体化。1939年,郁达夫认为,在这个大转变时期的十字路口,大众的注意,“全转注入了活的社会现实”,因而,反对“抗战八股”,建设“有充实的生活”和“满含正义人道自由真理的内容”的文艺。在《抗战建国中的文艺》一文,他进一步提出抗战文艺,“是有民众总体演成的这一篇大史诗”,要“还给全体的民众,使他们得享受、批评”,倡导“艺术——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实践”。
然而,遗憾的是,郁达夫没有能够进一步实践他所提出的“农民文艺”、“大众文艺”,就被日寇秘密杀害了。从一生的文学创作来看,郁达夫一直在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有着较为稳定的精神结构,无论是《沉沦》中的患有抑郁症的“他”,《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 ”、《薄奠》中洋车夫,还是到《微雪的早晨》中的“朱君”,贯穿始终的是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塑造和从不妥协的反抗、控诉、斗争精神。正如,郁达夫在《创造月刊》第一期卷头语所言:“天地若没有合拢来的时候,人生的缺陷,大约是永远地这样的持续下去吧!啊啊,社会的混乱错杂!人世的不平!多磨的好事!难救的众生!……在这个弱者处处受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或许,郁达夫的城市底层书写实践和农民大众文艺思想,离他所倡导的文艺主张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其一生秉持的“弱者人格”和“为农民大众、为弱者写作”的文学精神,无疑在新世纪的今天有着强烈的精神启示和现实意义。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和还原一个立体的、多样精神气质和思想追求的郁达夫,而且还要从中汲取可贵的文学精神和创作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