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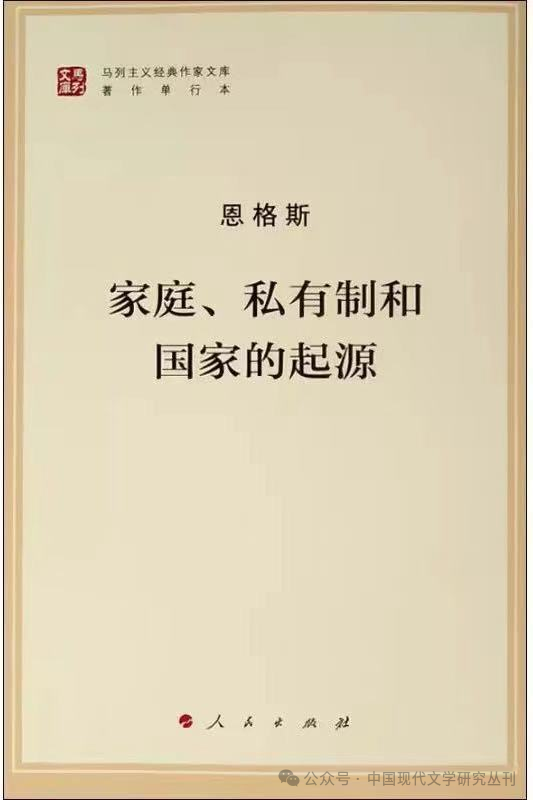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白露春分》书写了一个由三代人组成的家庭的日常故事,通过平和细致的描摹触及了中国家庭面临的诸多难题。小说揭示了“超稳定家庭”在当代的表现与遭遇的挑战,指出这类家庭规训成员所使用的惩罚“有情者”的策略。作者没有直抒胸臆地做出黑白判断,而是以直观呈现的方式关切难题背后具体的个体生命。“向前看”的生活哲学在小说中处于暧昧尴尬的位置,遮蔽了小说敞开更多面向的路径与解决结构性难题的诸多可能,提示了当下社会面对家庭难题时在外在制度保障、内在价值观念等多重层面的建设不足。
关 键 词
辽京 家庭伦理 超稳定家庭 有情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曾指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本质,即“专偶制家庭是一种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1],强调家庭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必然性,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家”除了具有“房中有豕”等经济内涵,逐渐形成了更为复杂完备的文化体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观理想之外,家和万事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多子多福等民间家庭观念历经千百年传承,成为一种自私而强大的“模因”[2],融进中国人的精神与气质。然而,中国人又似乎总在与自己建构的文化、传统作斗争,如果反抗家庭与父权的《西厢记》《红楼梦》还因其凤毛麟角而被千古传颂,那么自“五四”以来就不断被召唤出的“走出/背叛家庭”叙事模式已然具有革命的意义,对个体自由的追寻成为新生的现代“模因”。及至当下,新媒体环境的日新月异催生了更为驳杂、多元的精神症候,在诸多西方理论的普及之下,“原生家庭”“童年创伤”“恋母/父情结”等概念成为常识,“长大成人”的中国子女终于进入反思家庭关系与亲情伦理的历史阶段。思想与观念的变迁即便没有陷入历史循环论,在各种意义上,也总是上演着退步或回旋。于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阅读到的,是价值、观念、形式、形象都处于参差不齐状态的各类家庭故事,辽京的长篇小说《白露春分》就是其中的一部。
生于1983年的辽京迟至2015年才开始创作,写作或许是其开始承担母职后的某种调剂或疗愈。相继出版小说集《新婚之夜》《有人跳舞》和长篇小说《晚婚》后,“作家辽京”逐渐显现出自己的独特面目,她擅长书写家庭与婚姻故事、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与她们隐秘的不安。及至《白露春分》,辽京的叙事技术更加娴熟。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称不上最悲惨或最愉悦的,也不是最特别或最深刻的,然而,辽京平缓的叙述水面之下潜伏了陡峭的冰山,她不动声色地将沉重的结构性问题步步拆解,制作成一根根纤细却锋利的银针,直刺读者的神经与内心。在叙事技艺层面,《白露春分》未见形式上的先锋探索,采用的是相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但辽京的笔调曲径通幽、引人入胜,她在讲述情感浓度如此之高的家庭故事时却不直抒胸臆,她的无奈、抗争、坚持、妥协都显得暧昧而内敛,呈现出动荡之中的淡然、残酷之中的温柔。辽京正在向我们展现一种并不标新立异的现实主义审美的力量。
一 “超稳定家庭”的延续与分裂
《白露春分》中的家庭里有三代人,第一代主角秀梅生育了三儿两女,而第三代的佳圆、佳月、张昊辰都没有兄弟姐妹,在20世纪80年代写入宪法的“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独生子女”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代际现象。在198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陆续进入人生的中年,他们不仅要处理自身婚育生活的“一地鸡毛”,还要承受父母逐渐老去需要他们赡养的现实。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传承的“由一到多”模式悄然翻转为“由多到一”的倒金字塔型,曾经获得了父母双方、祖辈四人关注的第三代进入全面“反哺”的人生阶段。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高考制度的成熟稳定,这一代人也成为“优绩主义”的第一波“受益者/受害者”,他们默认了竞争机制的合理、合法,也被迫投身其中,见证、参与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国际地位的变化。家与国的多重变迁并非一夕之间,扑面而来的却是鲜活具体的日常生活。
作者辽京和她笔下的佳月和佳圆都是“80后”一代。小说并非要替一代人诉苦,只是记录他们面对的真实而具体的生活情境。当佳月又一次因为奶奶的吃饭问题打算请假回家看望时,男朋友飞凡说:“人都是要逼一逼的,现在一有什么事,有个风吹草动,就来找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放不下,所以乐得撒手,什么事都不管,反正有事叫佳月就行了。这又不是你的责任,你就装一次傻,实在没人管了,你再想想办法。”“一有事就指望你帮忙,将来怎么办呢?将来你也有自己的家要照顾的。”[3]佳月完美诠释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孝顺,而飞凡说出了现代人生活的真相,“将来你也有自己的家”,这个“自己的家”应该是他和佳月组成的新的小家庭,而非有着几代人的“大家”。飞凡试图更新佳月的观念,但他可能低估了形塑佳月生活方式的力量的强大——佳月生长于一个父权极为稳定的传统家庭。比如,即便祖父带给整个家庭的只是创伤和暴戾的记忆,他依然在过世多年后影响着整个家庭的决定。秀梅多次表示不愿意和丈夫合葬,即便佳月几次提醒,秀梅的儿子们也并不将其放在心上。成功逃离家庭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立秋面对一事无成的哥哥们,依然知道“哥哥们看不起她,并不是看不起她这个人,而是看不起所有女人,秀梅挨了半辈子打,手被打断过,断着手做家务,他们以为女人不外如此”[4]。
如果这个家庭的情况出现在今天的短视频或者热搜中,定会引来网友的“互联网升堂”,但辽京并没有沉溺于单独描写女性身处的家庭苦难,她难得地看到了这苦难之中的矛盾与复杂。小说特别提及了秀梅与佳月母亲、佳圆母亲的矛盾,再次触及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婆媳关系”。秀梅对儿媳百般挑剔和羞辱,在她又一次当着孙女的面抱怨孙女的母亲时,“佳圆站起来就出去了,天擦黑才回来。佳月想,如果离家出走的结局总是回来,也是真没意思”[5]。作为女性和曾经的儿媳,秀梅不仅不体谅自己的儿媳,还时常恶语相加,也无法意识到这样的行为会怎样伤害自己的孙女。秀梅也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一类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们忍辱负重多年,“媳妇熬成婆”后便多少有“转移复仇”的需要,祖母疼爱孙女是真心,婆婆抱怨儿媳也是真情流露。孙女唯一能做的,只是“站起来就出去”,而在场的另一个孙女观察到的,是“结局总是回来”,这句“真没意思”容纳了三代女性的人生悲苦。这种无边的绝望埋下了佳圆日后诸多祸事的种子,也使得佳月陷入绵延多年的精神压抑。
辽京以平淡的语句写出了最为残酷的事实,以父权为基础建构的中国家庭,依然伤害着被认为在蜜罐中长大的“80后”一代。当下中国社会历史层面的“超稳定结构”[6]早已灰飞烟灭,潜伏于结构内部的传统道德、社会观念、家庭伦理显然并未质变,“超稳定家庭”似乎如铁钉一般,嵌入中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肌理,铁锈联结着血肉与筋骨,孕育着隐痛与危机。辽京笔下的这个“超稳定家庭”一边艰难维持着祖父、父亲的权威,一边又以第三代“无子”的方式切断了父权的承袭,作为“替代品”的佳圆、佳月分别走上了“逆子”“孝子”两条路径,并将这个家庭的暗黑丑陋逐一暴露。佳圆和佳月在多个层面被动地陷入伦理困境:原生家庭没有给予子辈足够的爱与支持,子辈是否依然有义务无条件回馈家庭?父辈家暴、出轨、撒谎、不知悔改,子辈是否可以由此不再为父辈付出?给予了爱也给予了伤害的女性长辈,除了回报爱与关怀,对她的局限、不公、无理是否可以有批判或违逆?这些深藏在佳圆、佳月多年的成长创伤与日常烦恼中的问题,同样也深藏在被规训千百年的子辈内心之中,这对现代人来说并非简单的问题。“佳月”和“佳圆”两个人物的设定正是辽京选定的两副代表性面孔,她们在“超稳定”与“解构超稳定”之间摇摆、撕扯。
二 家庭规训的潜在路径
在这个“超稳定家庭”中,秀梅是必须着重提及的人物。她本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含辛茹苦养育五个子女长大,又帮忙照看两个孙女,也算得上儿孙满堂,却晚景狼狈,连体面老去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小说以秀梅的身体状况为线索,故事的聚焦视角仍然是第三代的孙女。或者说,读者看到的,仍然是老龄化社会给年轻人带来的现实难题,这难题包含晚辈对长辈的同情、悲悯与愧疚,更包含被困扰的一代对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进行认知与思考的欲望。
在《白露春分》的故事中,应该承担赡养秀梅责任的是佳月的父辈五人——按照更为传统的中国家庭伦理,应该是立远、立生、立民三个儿子,然而,小说中真正承担责任的是孙女佳月和女儿立秋。三个儿子以相似的暴力与品行问题失婚,又以相似的方法逃避着对母亲的责任,在他们背后,是三个饱受暴力压迫而出走的儿媳。即便女性主义思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盛行多年,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故事里,依然可见深陷各式各样泥潭的女性。辽京展现了新的社会家庭结构下女性正在或即将面临的新一轮困境——养老的难题。2012年,同为“80后”女作家的蔡东发表短篇小说《往生》,讲述了六十一岁的儿媳康莲伺候八十五岁公公的故事,蔡东以极致的细节描写带读者领略了侍奉失智老人的煎熬与绝望。康莲没有逃走,还替耍小聪明的妯娌承担了责任,康莲在这里是和佳月一样的受困者、利他者:
女儿落在了大城市,生活工作都不容易,再说了,谁能同她一起轮?拖累独生女儿的人生,当妈的怎么忍心?她再也不能像上辈人一样,指望儿女了,到底该指望什么,她也找不到答案。康莲在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段日子她总是莫名地惊惧。她清楚地感觉到,从小城留州到大城深圳,女儿的心底也有惶然和惊惧,但女儿已然离不开深圳,女儿这一代的日子跟她们不同了,有些什么东西变了。[7]
康莲意识到了社会的变化,她知道自己是传统的养儿防老型关系与现代的亲子独立型关系的过渡者。然而,年轻的佳月甚至陷入比康莲更深的困境。中国家庭的养老问题、亲子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诚如李蔚超所说,“居于两个阶段期间的是新中国第一代城市家庭,由农村进城、双职工、多子女构成的,它们是处于乡—城、家族—家庭的过渡状态,包含几代人的城市大家庭当中既包含着乡土社会家族的秩序和意识,又因作为国家集体的成员而具有现代因素,呈现出既新且旧的杂糅状态”[8],这种“既新且旧”以残酷的多重面孔凸显着“中国家庭”的“倒退式前进”。在虚构的小说之外,女作家薛舒也曾以非虚构的“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9]记录父亲患阿尔兹海默症后的生活状态。叙述人经济富足、有孝心、情绪稳定,还有支持她的家人、医生朋友,然而,即便具备如此“完美”的客观条件,她经历的一切依然让读者潸然落泪,“经过照顾老爸的这些年,我甚至觉得,当家里有一个失能失智的老人时,谈‘尊严’之类的问题有些奢侈,也可能是一些健康的、年轻的人们何不食肉糜的自我感动”[10]。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我们习惯将养老问题和“孝”等伦理道德做关联,然而,在外在制度保障与内在观念双重缺位的社会中,“尽孝”只能意味着“有人”不得不牺牲与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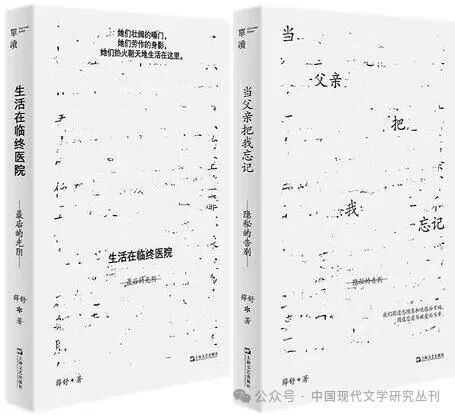
薛舒 生命两部曲
康莲对公公的照护当然是“孝”,即便她只是在努力尽一个儿媳的责任,在她的认知中,只有“向下延伸的爱才是无条件的,自发的,充满耐心,不厌其烦”[11],所以她能够完全站在女儿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愿增添哪怕一点点女儿的负担。在佳月这里,对祖母的“孝”带着自发的成分,她的“充满耐心,不厌其烦”来自情感层面对与秀梅共度的童年时光的珍视,“小说用许多细腻的细节构造了两个女孩曾经温馨甜蜜的童年记忆,这是小说最动人的部分:秀梅与佳圆佳月祖孙之间的亲情,弥补了父母无暇顾及的爱,替代了家庭教养的责任”[12]。尽管秀梅无数次表现出对佳圆的偏爱,佳月依然铭记着这份温情并倾心回报,而应该只是受道德约束的康莲,即便自己已经身心俱疲,却仍对弱势无助的公公心生怜悯,挣扎起来给予细致的关怀。不管是《往生》《白露春分》,又或是薛舒的真实经历,似乎都在用人的情感——尤其是女性的情感——作为当下社会结构性难题的可能性解决方案:谁拥有更丰富的情感、更柔软的内心,谁就是那个承担更多责任的人。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式“超稳定家庭”对“有情者”的直接索取与潜在规训,小说中的她们维护了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坚实地构成了“有情的个人史”,但更可能会深陷于“有情的困境”。
三 拒绝妥协与承认循环
和佳圆、佳月一样背负责任的“有情者”是秀梅的小女儿立秋,她在市场经济还未完全席卷时便丢弃铁饭碗,勇闯大城市,她的付出不曾为她赢得家庭男性成员的尊重,但她得到了侄女们的敬爱,也得到了母亲秀梅的认可:
早年,立秋在这里上过班,当会计,接了秀梅的班。更早的时候,秀梅干的是体力活儿。现在这厂区冷冷清清的,看不见人,都放假了。从前厂子红火的时候,是日夜三班倒,生产不停的。
“这厂子就跟我一样。”车子离开的时候,秀梅说,“老了,没用了。”
立秋说:“这种污染企业,就该早点关掉。看看这边的树,树叶子上都是一层灰,多少人得肺病,得矽肺。”
“厂子关了,工人上哪儿去?”
“爱上哪儿上哪儿。我辞职了,现在过得也挺好。”
“你有本事,他们有什么本事?”秀梅说,“就咱们家这哥儿几个,谁也不能像你一样。”[13]

东北厂区
立秋以自己的力量对抗了时代的风暴,但更多人如秀梅所说,成为不知道该去哪里的下岗工人。近年来,因为“新东北文学”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那段改革阵痛重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由于“铁西三剑客”创作和影视剧改编的兴盛,这段历史被默认为只属于曾经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事实上,“‘东北’是一个比喻,老工业区的境遇有相似之处”[14],那是席卷全国的改革浪潮,但浪潮中每个人的选择和命运却千差万别。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以“为父正名”的姿态追问历史、审视当下,身处北京的辽京恰恰走向“为父正名”的反面,她以隐晦的行文捕捉了历史列车轰然碾过的另一种痕迹。
当佳月询问飞凡为什么要分手时,飞凡回应,“你老是想问为什么,很多事没有为什么,就自然地变了样子”“不要纠结在这里,向前看”。[15]飞凡是那个自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理性的现代年轻人,他对他和佳月的感情不可谓不真诚,那句“向前看”显然也是出自善意,只是对于佳月来说,她可能无法如此轻易地做到“向前看”。当她陪着怀孕的佳圆爬山却半途而废时,她必须找一天重来一遍爬到山顶才能放下牵挂,看着熟悉的风景,儿时共度美好时光的记忆便涌上心头,“有情者”再次爆发能量:
她们看见什么都能联想到自己,联想到未来,眼前是小的,局限的,用脚丈量却走不出多远的乡下地方,但是未来是大的,是无限的。那时候她们什么也不懂,除了好奇和勇气一无所有。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长大就是把一切都翻转过来的过程。眼睛望得见那么远,天那么高,山那么长,却清楚地知道界线在哪里。世界一点点撕掉迷离的面纱,向长大的人显露崎岖的真容,而真相是谈不上善恶美丑的,因为它不会结束,没有终点,所有的定论都操之过急,所有的答案都追不上它,“你只要向前看”。[16]
这段描写可能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文眼”。在“一切都反过来了”的成人世界生活的佳月一直被记忆中的儿时光阴所绑架,于是背负情感责任,也背负现实后果。在同代人、上代人都已经卸下包袱轻装前行时,她也不断被指点和教育:向前看。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向前看”?是不是接受了进化论的所有现代人都应该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接受“向前看”的指引?这种带有摩登色彩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当了摆脱过去泥淖的完美借口,也成为推动线性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的动力。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向前看”,至少对于来自倒退着前进的“中国家庭”的佳月来说,“并不是别人要她向前看,而是除了前方,她无处可去”[17]。如此真实,如此绝望。
当我们将目光从佳月转回到立秋可能会发现,背叛传统生活方式的立秋没有成为自怨自艾的时代弃儿,却也没有成为在风口上起飞的获益者,她只是在主体意识的支配下获得了成为普通打工者的权利。秀梅病重时,曾经潇洒恣肆的立秋此时已经度过了求职的过渡期,无法长时间侍疾,“假期只有那几天,她很珍惜现在的工作”“再请假就只有丧假了”。[18]那个作为童年榜样的幺姑,那个在秀梅眼中称得上“有本事”的立秋,拼尽全力也不过是勉强支撑起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体面。
小说结束于佳月出差到了前男友飞凡生活的成都,在街头偶遇,“只见飞凡和一个女人在一起,那女人手里牵着个小男孩”,“吸引佳月注意力的,却是飞凡身上那件毛衣,八十年代服装杂志上的款式,好在这次没有缀上可爱的小圆球。佳月不自觉地微笑,妈妈爱心牌,看来一切都好”。[19]这其实并非一个高明的结尾,似乎整个故事、佳月的转变必须由一个“他者”来终结或完成,而这个人是曾经对佳月产生重要影响的前男友。对辽京来说,这可能构成了完整的故事闭环,但似乎也说明了在处理这类家庭问题时,作者以及作者所预设的读者依然需要一个明显的作为“标志”的结局,这一标志大概率还是我们熟悉的婚姻、家庭、男性。是不是正是因为这种需要的存在,因为“往事”总能走向一个节点,“向前看”成为一种不得不被接受的“妥协的结局”?这其中遮蔽的,是问题真正被解决的方案。

往前看,别回头
对于衰落的东北来说,“向前看”可能象征着发展意义上的正确抉择,如黄平所说,“‘往前看,别回头’,并不是遮蔽历史——恰恰是‘新东北’的创作者将东北从被遗忘的边缘地带,带回到舞台的中央,擦亮了往昔的尊严。我们是在‘再回首’中‘往前看’,告别荆棘密布的旧梦,穿越幽幽暗暗的过往,无尽长路,且在寒夜中前行”[20]。然而,在更为精细和微妙的家庭结构中,这种思维逻辑该如何实现?如果只有“向下延伸的爱才是无条件的”,那么“向上的孝”到底如何在当下越发原子化的家庭中践行?为什么无力自理的婴儿能收获宠爱,而病弱的老人则遭到家人的嫌弃?是否因为婴儿有可创造价值的未来,而老人只剩索取与拖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否只存在于可能带来收益的“前面”?这或许也是“持续进步、合目的性、不可逆转地发展的时间观念影响下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21]定义下的现代性,给予现代人的集体无意识。然而,这种无意识所引发的问题尤为严重,首先体现在社会层面在生活设施、养老制度、医疗机构及代际扶助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例如,2024年广为流传的那篇帖子《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以细腻而沉痛的笔触,向我们揭示了养老照护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涵盖了从现有观念到制度细节的诸多层面。“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我们的世界主要是为青年人设计的。”[22]当下的社会效率与观念认知水平密切相关,提醒着我们正身处双重压力之中。
在《白露春分》中,立远、立民以猝死的方式完成了对个体罪恶的救赎,也由此消解了真正的“清算”和“理解”。而佳圆注定要重复大姑立春或秀梅的人生悲剧,立春的儿子张昊辰则正在成为新一代的立远、立民。从白露到春分或许是这个家庭三代人生活状态的象征,恐怕也是季节流转循环的呈现,对这个家庭来说,不同代际男性和女性的命运也陷入了循环。

火车
佳月想起小时候跟着秀梅去铁道边看火车,不知道火车打哪儿来,奔哪儿去。问秀梅,秀梅说,铁轨上来,铁轨上去,你瞧它不是一直在铁轨上吗?哄孩子的大白话像一句机锋。[23]
正是这一句“哄孩子的大白话像一句机锋”概括了秀梅的一生,恐怕也概括了佳月、佳圆、立秋、立春的一生,甚至概括了与这个家庭类似的无数个“超稳定家庭”的难题。铁轨上的火车始终向前,从未脱轨,却像玩耍的小狗一样一直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或许小说是在暗示我们,到了该停下来、“向后看”的时刻了,看看这已然生锈却依然坚固的铁家伙来时的路,看看它带着我们一路走来犯下的错与许下的愿。在这结构性的“铁笼”之中,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期待本雅明描述过的“历史的天使”,背对着未来向前进,与重复倒退或回旋路径的中国家庭真正并肩同行,关注正在不断生成的困住有情者的“废墟”,那应该是我们拒绝妥协与承认循环的证据。
结 语
辽京的笔触绵里藏针,表面平静悠远,却能尖锐地刺痛人心。她只是书写了具体的生活,书写中国家庭在几千年时间长河中的一个截面、一个瞬间,触目惊心的故事不过是对生活的“临摹”,这或许更让人心生绝望。然而,对辽京来说,对“超稳定家庭”的临摹过程是深入理解和塑造“有情者”的旅程,是对“向前看”的不安和反思,但更多的,可能是对某种记忆与往事的重提,是对记忆与往事中受过伤害的自己的重新拥抱,是对有情者深陷废墟的尝试性突围。
小狗长大了,小猫长大了。香椿树抽出嫩芽,杏花开了。她专门打电话给孩子们,有没有人回家来看看。哪怕是为了小猫小狗也行。[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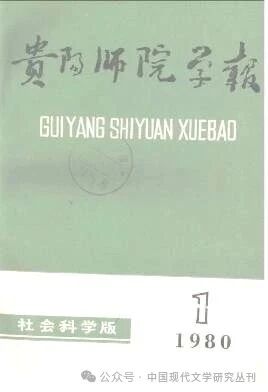
金观涛、刘青峰论文发表刊物
小猫、小狗,或香椿树、杏花如果都象征着美好幸福的童年,那么“常回家看看”便有了充分的合理性,不过,这只是秀梅的一厢情愿,多的是向前看、不回头的子孙后代。解体后的“超稳定家庭”,在当下社会已经分裂为一个个原子式的“超稳定小家庭”,新的规训“有情者”的机制正在生成,“向前看”的心理机制正在变本加厉地鼓励着不公正。然而,即便只是一次微弱的记录和发声,一次回顾和追忆,也并非毫无意义。辽京的同代人在过渡状态的中国家庭中出生、成长,辽京小说里所呈现的,那些无法宣之于口的家庭故事背后,正是由一代人的鲜活生命所感知到的伤痛与愉悦。在记录下这些生命经验并给予他人力量的作家中,辽京并非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樊迎春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讲习所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2期)
注 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2]“模因”最早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首次提到,书中将“模因”(Meme)定义为与生物基因类似的概念,生物基因复制遗传生理特性,模因则遗传复制人类文明,包括文化、语言、风俗、观念、思想等,同时具有与生物基因类似的变异、选择等特性。参见理查德·道基斯《自私的基因》(四十周年增订本),卢允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3]辽京:《白露春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278、279页。
[4][5]辽京:《白露春分》,第353、15页。
[6]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2期。
[7]蔡东:《往生》,《人民文学》2012年第6期。
[8]李蔚超:《在疗愈叙事中解码家的伦理——评辽京〈白露春分〉》,《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9]薛舒:《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10]罗昕:《作家薛舒:在老年病房陪伴父亲,看到更广大的社会图景》,澎湃新闻“文化课”,2024年1月11日,
https://m.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25974805。
[11]蔡东:《往生》,《人民文学》2012年第6期。
[12]李蔚超:《在疗愈叙事中解码家的伦理——评辽京〈白露春分〉》,《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13]辽京:《白露春分》,第181页。
[14]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15][16]辽京:《白露春分》,第325、358页。
[17][18][19]辽京:《白露春分》,第325、371、381~382页。
[20]黄平:《“新东北”:一份辩词》,《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2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三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22]参见王之言、胡泳《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微信公众号“凤凰网”,2024年4月9日。
[23]辽京:《白露春分》,第368页。
[24]辽京:《白露春分》,第15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