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
内容提要
“十七年”文学对高尔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人道主义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始者和奠基者三重身份的形塑,从多元视角厘清了高尔基自身的复杂性。这些身份形塑的背后实则潜隐着政治革命和人道主义两种思想观念的博弈,寄寓着中国学界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诉求。此时中国学界对高尔基的身份形塑,不仅直接触发了20世纪80年代有关文学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研讨,同时对于当下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十七年”文学 高尔基 身份形塑 政治革命 人道主义
高尔基在20世纪初就已进入中国文学的版图与视野[1],但在晚清至“五四”时期却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高尔基才成为备受中国文坛瞩目与推崇的人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政界与主流学界,高尔基是无数革命青年“精神上的维他命”[2]。然而对高尔基政治身份的刻意凸显,也造成了对高尔基的片面化理解,导致了中国文坛的“左”倾激进化问题。及至“十七年”时期,中国依然处于高度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中,但新中国的成立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3]却使当时的文坛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国学界不断洞悉高尔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人道主义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和奠基者三重身份的复杂性。基于此,“十七年”时期可以视为考辨高尔基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和文学场域。

《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一期)刊载《种族小说:忧患余生,原名犹太人之浮生》
一 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
“十七年”时期,高尔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身份得到了中国学界持续而广泛的关注,但评论视角和言说方式较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了明显不同。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并不是从文学文本和客观事实出发解读高尔基,而是更多地追随俄苏官方,将其视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权威代表,从政治层面品评与估衡其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十七年”时期,学者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审视高尔基其人其文,在评价高尔基时,虽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规约,有一定激进化的痕迹,但较以往却呈现出客观化的评论态势。他们在形塑高尔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身份时,主要是通过对高尔基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密切关系的史料梳理、高尔基与中俄作家思想观念的比较,以及对其作品中显露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捕捉等几方面来加以阐释与说明。
“十七年”时期,一些学者以回溯的方式梳理与考证了高尔基与中国革命“相伴而行”的脉络与谱系:早在1900年,当中国发起义和团运动时,高尔基就对这次反帝爱国运动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两次写信邀约契诃夫赴中国切身体验这次战争,可惜最终未能成行;1909年和1911年,高尔基相继创作《夏天》《诉苦》两部小说揭露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东北为战场和侵略中国领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当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时,高尔基于1912年10月12日从疗养地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及时发来贺信,对其表示祝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年)时期,高尔基密切关注这次革命的发展变化,并将这次革命称为“最宏伟的事业”[4];“九一八”事变后,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给予了深深的鄙夷与斥责;1934年9月2日,高尔基从《真理报》上读到了中国红军在湖南省取得胜利的消息,当晚他就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的中国革命作家晚会上诚挚地表达了对这次胜利的祝贺……可以说,高尔基终其一生都在热切地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

高尔基(右)与契诃夫(左)
“十七年”时期,学者们以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视角对高尔基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比如有学者指出,高尔基曾尖锐地批评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受一切痛苦”“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5]高尔基深刻地认识到,当时俄国人民正处于遭受奴役与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境况,两位作家“不仅不揭露刽子手的罪行,反而出来反对人民的革命运动”[6],宣传“忍耐”和“勿抗恶”的思想,这无疑是“非常丑恶和可耻的”。[7]在高尔基看来,俄国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底层人民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唯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高尔基的思想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迥异,他始终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为“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他的思想根基在此,他的文学创作旨归亦在此。[8]也正是在这一基点上,中国学者将鲁迅与高尔基联系在了一起。1951年,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就曾写道:“高尔基和鲁迅,都是在一个民族的革命过程中战斗了一生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为了摧毁旧的、创造新的而战斗了一生的。所以,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同时也就是人民大众底喜怒哀乐,就不得不是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历史心灵底声音。”[9]在这里,胡风寻绎到高尔基和鲁迅在革命本质上的同一性,即他们始终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战斗了一生,他们与大众实为“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因此,他们的心声就是人民大众的心声,他们斗争的历史就是人民大众反抗强权、摧毁旧制度,建设新制度的历史。也正是基于此,他们可以被视为无产阶级最为“诚实的战士”。[10]

高尔基和工人群众在一起
学者们还重点论述了高尔基作品中彰显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一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了《切尔卡什》《科诺瓦洛夫》等描写流浪汉的作品,认为从高尔基这些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俄罗斯革命者“逐渐成长的性格”,在这些流浪汉的身上实则折射着作者的身影,流浪汉革命意识的“成长”,也映衬着作者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观念的“成长”。[11]另一方面,学者们充分注意到了《鹰之歌》《海燕之歌》《母亲》等作品中涵纳的革命质素,认为这些作品不仅对具有勇敢战斗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给予了歌颂,同时对那些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进而指出,“只有像高尔基这样在精神上完全年青的人”,才能“向人民指出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才能创造出像雄鹰、海燕、丹柯、巴威尔这样过去所没有的具有革命寓意的文学形象。[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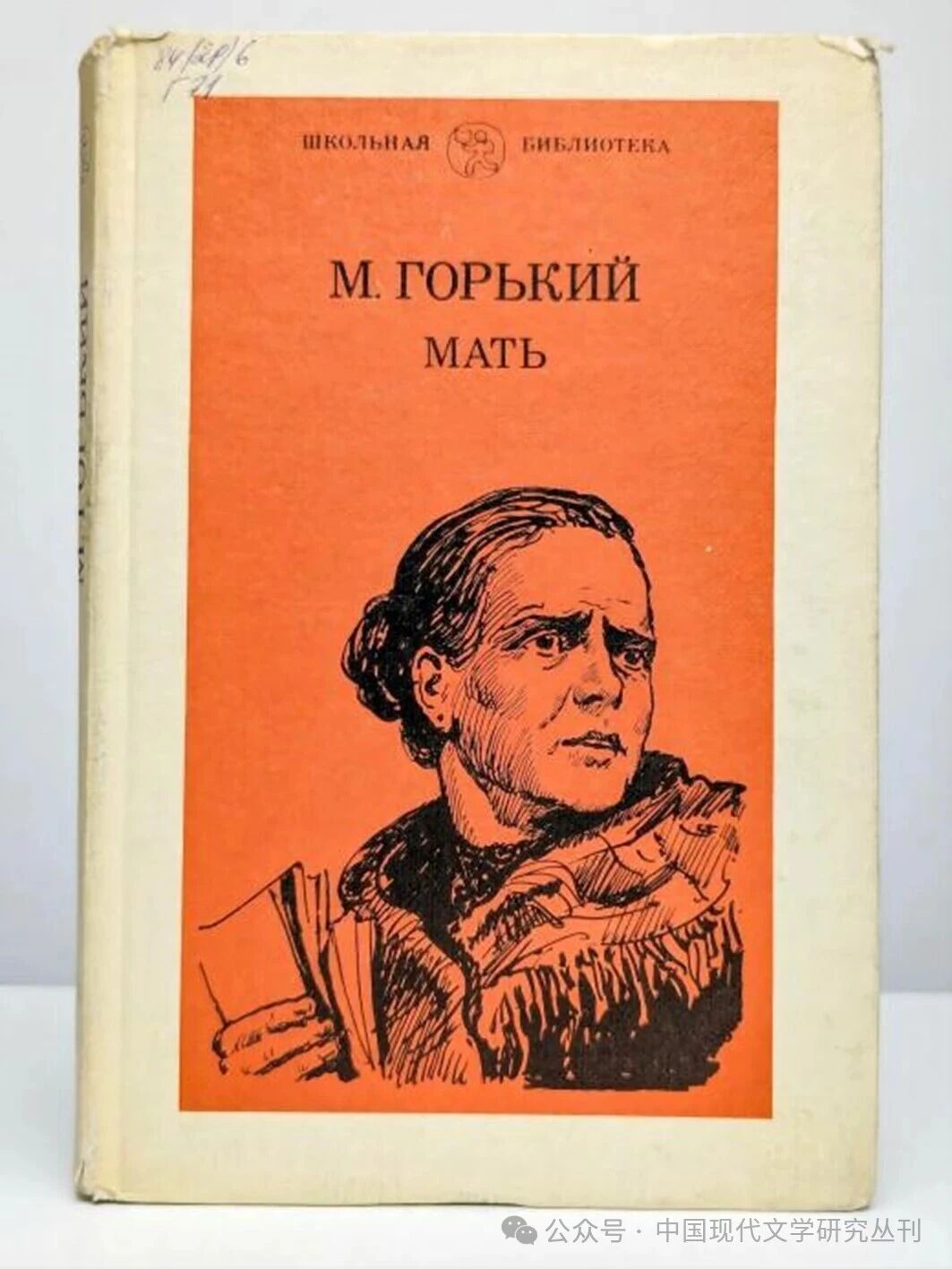
高尔基《母亲》
其实,学者们在“十七年”时期对高尔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身份的形塑,实则是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考虑。当时中国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获得了全国的解放,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还处于初步的建设时期,还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重要转型期。尤其是在文学与文化思想层面,无产阶级文学与文化还很不成熟,还存在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侵扰的可能性。而在苏联,高尔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权威人物,尤其是他的《黄色恶魔的城市》《美丽的法兰西》《母亲》等作品,无情地批判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于是,高尔基自然成为中国文学界学习的对象。正如夏衍所言,在“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严酷斗争中,“想起高尔基这个伟大的名字,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13]另有学者强调:“今天,当人民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尖锐化到极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高尔基那种无情地暴露敌人,狠狠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观点和方法。”[14]
二 人道主义作家高尔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茅盾、胡风等左翼代表就曾对高尔基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涉猎。鲁迅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和“启蒙民众、重铸民族灵魂”的“立人”思想中触及了高尔基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并与之发生了共鸣。[15]茅盾从“为人生”的视角出发,从人类学的角度对高尔基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给予了总结性的评价:“高尔基的一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不屈的。”[16]胡风则指出,在高尔基一生的全部著述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无限地爱人们和世界”的粗大“红线”,始终传达着其挚爱坚强和善良之“人”的心声,并认为,“这才是真实地肯定了人底价值”。[17]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时代语境,高尔基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遭受了遮蔽与压抑,造成了中国学界对高尔基的片面化理解。
相较于三四十年代,在“十七年”的文学语境中,高尔基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得到了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特别是1957年钱谷融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以高尔基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为依据而写作,使高尔基人道主义作家的身份得以集中聚焦:“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依循着高尔基“人学”的思想理路,钱谷融指出文学不应该将“整体现实”作为描写对象,更不应该以达到反映“整体现实”之目的而将人趋于从属地位。反之,文学应该将“人”作为描写对象,应该将影响人、教育人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同时,钱谷融强调作家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美学理想的决定作用,认为一切宝贵的文学遗产之所以还能获得今天读者的珍视与喜爱,皆是由于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人道主义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他曾言,人民性这个“最高标准”也许不是所有作家都会运用,但人道主义精神这个“最低标准”却是所有作家“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而人道主义是通达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必备条件,没有人道主义就不会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18]
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不久,就在反右运动中遭受了批判,依据高尔基的“人学”思想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念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在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中存在两种类型的人道主义,一种是宣扬仁慈、同情、忍耐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另一种是宣扬革命、战斗、反抗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高尔基批判的是前者,肯定的是后者。而钱谷融对高尔基所谈论的这两种人道主义不仅未加区分,而且用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谈论“文学是人学”,这既违背了高尔基人学、人道主义思想的原意,同时也暴露了其排斥文学阶级性、取消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修正主义者的伎俩。[19]另有学者认为,高尔基所谈论的“人”是敢于反抗和斗争的“大写的人”,而不是钱谷融等资产阶级人性论者所宣扬的“抽象的人”。[20]还有学者强调,按照高尔基的原意,并非“文学”是“人学”,而是“人种志学”是“人学”。[21]面对质疑,钱谷融坦陈,知晓高尔基将文学视为“人学”的想法,是从阅读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了解到的。因为不懂俄文,为了谨慎起见,依凭高尔基的“人学”思想撰写文章时,最初确定的题目是《论文学是“人学”》。后来,听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许杰的意见,将题目改为《论“文学是人学”》。没想到,文章一发表,就遭到质疑。对此也曾想过改为原题,但觉得“文学是人学”这一理念,并非高尔基的个人“新发明”,而是包括高尔基在内的许多哲人和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因此未作修改。[22]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这场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论争延续了数十年,直到新世纪之初,钱谷融在遭到一些学者质疑时,还在对这一命题进行不断的解释与说明,可“文学是人学”是否出于高尔基的本意仍未有定论。其实,高尔基早在1902年就在其剧作《底层》中表达了“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的文学理想;[23]1907年又在其散文诗《人》中再次重申了“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人”的文学诉求。[24]对“人”的审视与书写,实则是贯穿了高尔基文学创作始终的核心命题。另外,高尔基所强调的“人”,也并不仅是“大写的人”,而是处于一切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一切不幸的人。至于人道主义,高尔基虽然对其进行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分,但他的人道主义最终指向是确立人的主体性,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一点上,高尔基和钱谷融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高尔基虽未直言“文学是人学”,但其文学思想是与之相通的。因此,钱谷融将高尔基作为“文学是人学”的代表,本无可置喙。
钱谷融依据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了“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看到了彼时在政治革命和人道主义尖锐的对立与冲突中,人道主义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真实状态。同时人道主义思想的倡导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一元化创作观念,且直接触发与深化了八十年代学界对人的主体性、文学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相关问题的思索与探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始者与奠基者高尔基
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周扬、冯雪峰等为代表的主流学者通常认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者与奠基者。基于此,主流学者首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做出了区分:“批判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前最高形式的现实主义。”[25]同时指出,在旧俄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体现出很高的文学与思想价值。然而,他们仅仅止步于揭露与批判,却没有“依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受剥削与压迫的民众“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26]直到20世纪初高尔基小说《母亲》的出现,才打破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拘囿,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阶段,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并将其和“社会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教育劳动人民”,为其指出一条获得自由和解放之出路的目的,最终引领劳动人民步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27]其次,学者们强调了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认为高尔基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深刻地领会“列宁关于党性原则的实质”,并肯定了“共产主义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灵魂”,是“人民性和阶级性的最高标志”。[28]最后,学者阐明了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指出高尔基将浪漫主义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种类型。[29]前者“粉饰现实,努力与现实相妥协”;后者则肯定人的生活意志,唤醒人对现实“一切压迫的反抗心”。[30]高尔基否定的是前者,肯定的是后者,并且把后者——积极浪漫主义(又称“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发挥了想象未来现实的重要功用。[31]
周扬、冯雪峰等学者在对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进行解读的同时,还对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中国本土化的拓展与延伸。比如他们指出,以高尔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以“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创作基础,这可以有效“指导和帮助作家去把握生产发展的规律”,[32]并能够促发作家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度来“观察一切人,一切事物”。而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是“十七年”时期的一个迫切任务。[33]同时,学者们依循高尔基倡导的党性原则,一方面进一步强调党性原则“是宇宙观的最高表现,也是人民性、阶级性和革命实践性的最高表现”[34],另一方面则由党性原则衍生出“典型”和“夸张”也是“党性问题”的论断,认为只有创造出正面典型,才能更好地彰显党性,“典型创造得愈完全,党性也就表现的愈完全”。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应该将其“所拥护的东西”和“所反对的东西”加以夸大,从而引起人们对新事物的赞成,对旧事物的反对,最终揭示“阶级的本质”,因此“夸张也是一种党性问题”。[35]另外,有的学者在肯定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观点的过程中,不仅发展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念,而且引申出“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的判断。并进而指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实则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反映”,而用这种“相结合的方法”来表现“十七年”时期人民的精神状态“更为合适”。[36]
针对来自周扬、冯雪峰等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阐释,秦兆阳、钱谷融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秦兆阳认为,周扬、冯雪峰等学者强调的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的观点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精神“一定是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如果以这种固定而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去指导创作,必然会使“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基于此,秦兆阳指出,文学绝不单纯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完成某种政治任务的工具,而是应该遵循人学与人道主义思想,在充分尊重客观真实和艺术特性的基础上,以达到高度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为鹄的。在秦兆阳看来,高尔基和鲁迅恰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秦兆阳对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苏联官方代表之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片面化理解给予了否定与批评,认为其强调的文学阶级性、歌颂光明、塑造正面人物典型等观点,实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教条主义”的解释,规约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多元性与广阔性。[37]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从以上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述理路来看,周扬、冯雪峰等主流学者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蕴含的阶级观念、党性原则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秦兆阳、钱谷融等学者强调的则是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和艺术的客观真实性。而饶有意味的是,双方都以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方法为佐证,来论证自身文学观念的正确性。那么论争双方哪一方更为接近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呢?其实,虽然以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为首的苏联官方将高尔基定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和奠基者,将其小说《母亲》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但这一切行为的背后,实则是基于高尔基在苏联文坛的影响力,是为了借助高尔基文学权威的地位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以在苏联文坛更快更好地落实,并以此来增强苏联官方的政治宣传影响力,发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重要功用。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和奠基者并非高尔基,而是以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为首的苏联官方。不仅如此,高尔基所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与苏联官方存在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性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中得以集中彰显。本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将之前在苏联官方主导下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写入作家协会章程。[38]在这次大会上,苏联官方代表日丹诺夫不仅从政治倾向性角度解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且明确表示,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可能有那种没有阶级性、倾向性和“不问政治的文学”[39]。相较于日丹诺夫,担任本次大会主席的高尔基则给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定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存在是行动,是创造,其目的是为了战胜自然,为了人的健康和长寿,为了人生在世的幸福,而不断发展人的最有价值的内在才能,并根据人的需要的不断增长,而把整个世界改造为联合成一家的人类美好的住所。[40]
高尔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通过改造人的内在才能,从而战胜自然,最终使人类获得幸福和美好住所的重要手段”[41]。其中蕴含着高尔基浓郁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从这一定义来看,显然秦兆阳、钱谷融等学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读更为接近高尔基,而周扬、冯雪峰等学者所言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苏联官方。因此,以周扬、冯雪峰等为代表的主流学者对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实则存在着误读,而他们给予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始者与奠基者的身份定位也需要商榷。然而,尽管学者们对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正解,也有误读。但双方的研讨与论争,却深化了学界对现实主义驳杂性的认识,加深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主席高尔基(第一排左二)与其他参会者
结 语
“十七年”时期学者们对高尔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人道主义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始者和奠基者的三重身份形塑,不仅厘清了高尔基自身的复杂性,而且能够发现这些身份形塑的背后实则伴随着政治革命和人道主义两种思想观念的博弈。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考虑,周扬、冯雪峰等主流学者在对高尔基身份形塑时,将高尔基视为政治革命作家的典型代表,试图以高尔基的革命精神教育与鼓舞民众,推动社会主义的文学与文化建设,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服务;秦兆阳、钱谷融等学者则试图使文学摆脱政治的束缚,在对高尔基人学、人道主义思想的阐发中,坚守人的主体性、文学的主体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两相比较,虽然双方看似在两个维度里,但最终的诉求却是基本一致的,即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由于“十七年”时代语境的限制,双方却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但即便如此,当时学者们对高尔基的身份形塑和由此展开的论争,其意义也不应小觑。因为它不仅直接触发了20世纪80年代有关文学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研讨,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构的进程,而且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文艺观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侯敏 吉小岑
辽宁大学文学院
110136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9期)
注 释
[1]1907年,清末翻译家吴梼根据长谷川二叶亭的日译本重译的高尔基发表于1898年的短篇小说《该隐和阿尔乔姆》(Каин и Артем),载《东方杂志》第4年第1期至第4期小说栏内,题名为《种族小说:忧患余生,原名犹太人之浮生》,旁注“俄国戈厉机著”,下著“日本长谷川二叶亭译,钱唐吴梼重演”。这是高尔基作品的最早中译本。
[2]郭沫若:《不要把自己的作品偶像化》,《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4]戈宝权:《高尔基和中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5]何洛:《伟大的开拓者——高尔基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教学与研究》1953年第3期。
[6]李辉凡:《“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试论》,《文学评论》1963年第2期。
[7]高尔基:《谈谈小市民习气》,《高尔基政论杂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99页。
[8]叶水夫:《纪念高尔基》,《文学评论》1963年第2期。
[9]胡风:《关于鲁迅论高尔基——纪念高尔基逝世十五周年》,《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3页。
[10]胡风:《关于鲁迅论高尔基——纪念高尔基逝世十五周年》,《胡风选集》第一卷,第62页。
[11]王西彦:《读高尔基描写流浪汉的作品》,《世界文学》1959年第10期。
[12]李辉凡:《“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试论》,《文学评论》1963年第2期。
[13]夏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斗士——纪念高尔基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文学》1958年第3期。
[14]汪梧封:《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4期。
[15]侯敏:《论鲁迅与高尔基国民性话语中的人道主义》,《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4期。
[16]茅盾:《高尔基和中国文学》,《茅盾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17]胡风:《M.高尔基断片——当作我底悼词》,《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18]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
[19]欧阳文彬:《高尔基论人道主义》,《文艺月报》1958年第6期。
[20]李希凡:《召唤着新人的诞生——谈高尔基早期作品的一点感想》,《世界文学》1963年第4期。
[21]刘保端:《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即人学”考》,《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
[22]李世涛:《“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先生访谈录》,《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期。
[23]高尔基:《底层》,《高尔基剧作集》(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24]高尔基:《人》,《高尔基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6页。
[25]翁义钦:《略谈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9期。
[26]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页。
[27]《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28]翁义钦:《略谈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9期。
[29]参见周扬《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30][34]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0、529页。
[31]参见马铁丁《人,学习,题材及其他——读高尔基〈文学论文选〉札记》,《世界文学》1959年第3期。
[32]冯雪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讲》,《冯雪峰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319页。
[33]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35]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周扬文集》第二卷,第197~199页。
[36]周扬:《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周扬文集》第三卷,第60~63页。
[37]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38]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39]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讲话》,《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辑要》,刘逢祺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40]高尔基:《关于苏联的文学报告》,《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辑要》,刘逢祺译,第18页。
[41]侯敏:《中国左翼文学对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之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