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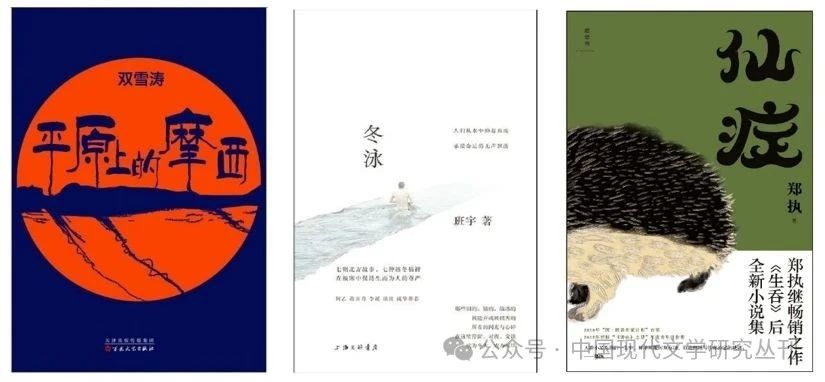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郑执:《仙症》,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
内容提要
近年来,以“东北”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工业生产因为追溯“下岗潮”前后的社会生活、呈现父子两代人的关系,并充分利用新旧多种媒介资源而赢得广泛关注,值得讨论的不仅是这些作品本身,它们掀起的热潮也是一种时代症候。热潮发生的原因、其广泛和持久的作用都在映现当下社会心态和文化面貌。热潮围绕东北展开,不仅源于东北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史上的重要性,更是由于百余年来的东北书写使东北成为中国情感结构的重要载体,因而书写东北既能调动历史记忆,又利于体现历史变迁的余震。热潮之广泛还在于这批东北书写挖掘出深层的危机,折射了普遍的焦虑。热潮之持久则源于东北在书写中的逐渐空洞化,与拟象化时代的文化状态产生呼应,它满足了当下文化生产的需求,甚至参与了新的文化格局建构。东北书写与讨论成为“热”潮,体现的是当前中国正经历物质世界和象征系统的双重变革。
关 键 词
“新东北作家群” “东北文艺复兴” 现代化危机 情感结构 拟象
2019年,“东北文艺复兴”口号在大众文化领域出现时,[1]文学评论界对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一代东北作家的研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随后,这批东北作家被冠以“新东北作家群”之名,与“东北文艺复兴”等大众文化现象一同引起广泛关注。这股“东北风”席卷多种文艺领域,日渐将其他带有东北元素的作品也吸纳进讨论范畴,并催生出一批批新作。数年间,“东北热”不仅声势不减,反而愈发强劲。
研究界密切关注这股东北热潮,学者们梳理了当前东北书写的历史文化寓意、社会现实关怀、文学和美学传承以及文化工业生产的特性,从文中呈现的“下岗潮”“父与子”等出发,解读作品的历史反思和情感结构,也从文本组织起的中/外、雅/俗等各类文化要素来管窥当前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可谓挖掘了东北书写的方方面面。[3]但至今为止,研究仍侧重对作品的解析,而“东北热”也是一种现象,它汇集多种类型文本,既有严肃文学也有通俗文艺,甚至相关研究也已构成东北书写的组成部分,虽然此前文艺界也多有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化生产的结合,文学创作与批评也时常协力,但“东北热”中的这些文本的结合,却是多种文艺类型的受众跨媒介地将这些本不直接相关的作品放置在一起,发掘出它们背后共通的主题、思想和情感。因此,围绕东北形成的创作与研究热潮是一种共同心态的表征,需要解析的不仅是创作者们对东北的书写,还有这股书写与讨论东北的热潮因何而起,它何以能够如此持久且广泛深入,以及这一热潮本身是怎样的症候。
本文第一节将综述当前“东北热”关涉的多种对象,总结提炼这批东北书写的共通特征,从而辨明到底是什么在“热”;第二节着眼于何以是东北书写引起热议,通过梳理“东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中国想象,解析当下东北书写在继承以往文艺和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再现能力,并阐明是文艺再现而非仅是社会历史背景赋予了“东北”以如此丰富的意义;第三节分析热潮的广泛性,从“东北”受到不具有相关历史背景的读者的关注入手,挖掘文本隐含的普遍焦虑,剖析这些新的书写如何触动了当前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第四节聚焦这场热潮何以持续,揭示“东北”意义的空洞化和这种空洞化所折射出的文化心态与危机。
一 多面的“东北热”
在双雪涛等作家被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之前,这一名称已然存在。《渤海大学学报》在2011年发起“新东北作家群”讨论,四年后刊物主编林嵒对已开展的研究情况做出总结,将孙惠芬、白天光、丁宗皓等近三十位作家归入“新东北作家群”[4],但这时的命名显然是延续文学史对“东北作家群”的定义,数十位作家间风格差异很大,难以形成有效的问题域,所以相关成果并未掀起波澜。2015年以降,双雪涛、班宇、郑执先后在文坛崭露头角,三位作家作为下岗职工第二代的历史书写引起关注,并逐渐形成对“铁西三剑客”的研讨,[5]但此时讨论也局限于文学评论界内部,尚未产生后来的现象级影响。此外,也有学者追溯政策上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6]将此视为当前“东北热”的前身,但“振兴东北”侧重经济和社会问题,和当下“东北热”聚焦文化层面不同,所以认可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不多。

铁西区
图片来源: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86302
真正有力地掀起了“东北热”的是黄平发表于2020年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7],而热潮的发酵也有赖于其后一段时间内,一批资深和新锐学者围绕几位东北作家发表评论,以及报纸杂志特设专栏对这一话题进行持续讨论。是这些评论与研究日益明确了当前“新东北作家群”的所指,并追溯此前一系列对新一批东北作家的研讨,为“新东北作家群”建立了更长的学脉;也是自此时起,“新东北作家群”和大众文化领域明确联系起来,“东北”得以越出严肃文学范畴,汇集多种文化要素,衍生各类话题。此后数年,一批批学者继续推进和扩充论域,使“东北”调动的思考更加丰富和系统。
话题的缘起已经说明了此次热潮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学者和传媒的推动。若无此次选题并对新东北书写的发展进行溯源,“铁西三剑客”的研讨已近尾声,三位作家也已转向其他写作对象。制造学术话题本是学者和学术刊物的职责之一,它有利于开掘并反思学术研究中的盲区,所以每年都有一些话题被提出。这说明了“东北热”不仅是一股创作热潮,读者反应和学术研究也是助力其成为热潮的必要条件。但既然这种推动方式广泛存在,“学者和传媒”这一因素就解释不了何以是东北书写在近年众多话题中脱颖而出。要明晰这一问题,还是需要先梳理“东北热”包含了哪些对象,确认到底是哪种或哪些书写产生了如此吸引力,且经得起长久的开掘。
基于从缘起到拓展的线索,目前“东北热”包含的对象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一代东北作家的严肃文学写作;第二,东北出身或具有东北经历的创作者的流行文化生产,创作者带着明确的地域身份自觉展开创作,此类创作与第一类的作家创作有很大交叉,二者可以说是“东北热”的两个圆心,为便于称呼,下文同时涉及二者时将称之为“新东北书写”;第三,从“新东北书写”衍生出的其他创作,既包括作品的跨媒介改编,如《平原上的摩西》《生吞》等的影视化,也包括被继续纳入这个范畴的非虚构写作,如《张医生与王医生》《生死十日谈》等,[8]以及学者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而展开的东北历史文化叙述,如黄平和刘岩等学者的研究所讲出的东北历史、王德威提出的“东北学”等,[9]还有因“东北热”而被追溯进来的作品,如《铁西区》《钢的琴》等,这些作品和讨论虽然在不同领域产生影响,但都是将“新东北书写”所打开的接口衔接到更多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是对东北论题的有效扩充和深化;第四,带有东北元素,因“东北热”而被吸收进来,或受到“东北热”启发而创作的作品,如影视作品《黑土无言》、歌曲《漠河舞厅》等,它们利用了东北具有的既定印象来完成表意,并不丰富东北的意义,但在效果上保持了人们对东北的关注。可以说,前两类构成了“东北热”得以发端的基础性文本;第三类是基于基础性文本而拓展开的相关书写,也是这些作品推动“东北热”进一步发酵;第四类则是这股热潮继续发展至今所衍生的产物。

电影《刺杀小说家》,2021;
电视剧《胆小鬼》,优酷平台,2022;
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爱奇艺平台,2023;
电影《刺猬》,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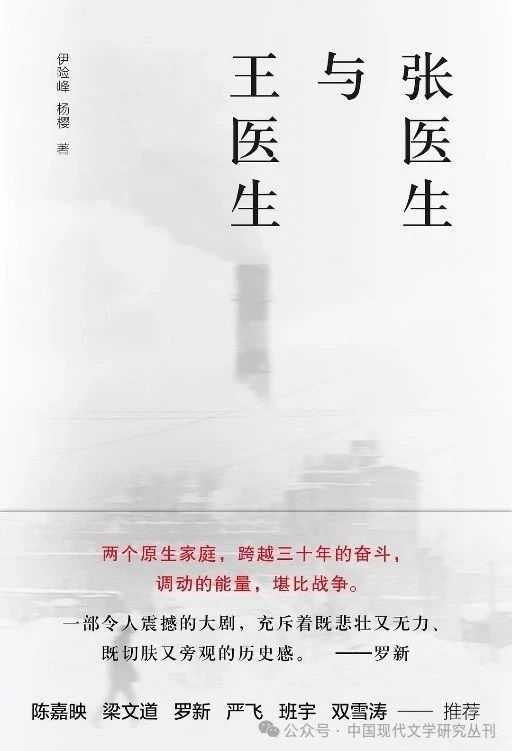
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

电影《钢的琴》,2011
并非所有东北相关书写都会被视为“新东北书写”的组成部分,比如近五年间迟子建仍不断推出她的东北题材创作、梁晓声的《人世间》也以东北为背景展现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变迁,但直到“东北热”的所指高度泛化后,讨论者才会将他们纳入考察对象,可见“东北热”所包括的文本虽然混杂,却有一定的共性。由于触发这层层拓展的东北再现的是“新东北作家群”,所以要解析这类书写的特性,还是需要从“新东北作家群”怎样书写东北入手。
尽管不同研究者在归纳“新东北作家群”时会加入多位作家,但交集总是在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所以解析“新东北作家群”,首先要把握的就是这三位作家的创作共性。《“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已然提炼出这类书写的关键词:体现“下岗潮”(及东北的衰落)、书写父子关系、融合类型文学的写作手法等。丛治辰、金钢、刘岩[10]等诸多学者进一步整理和明晰了这些共性的社会史和文学史渊源,使这些特征更为突出,成为诠释这些创作时的必谈话题。综合以往研究,东北书写与讨论的“热”点包括:情节内容上,作品普遍以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为背景,塑造父子两代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形象,也是基于这样的情节背景,作品展现了既因为“下岗潮”而陷入萧条,又因港台流行文化的袭来而表现出浮华生态的东北景观;叙事方法上,作家惯于采用子一代人对历史的怀旧视角,并加入悬疑式的结构,在回顾父一代的困窘的过程中,以解谜的方式发掘历史现场中未被言说的部分,并通过揭示历史之谜完成对父一代也是对历史的理解与认同;语言风格上,作品多用短促的语句,叙事上呈现碎片化特征,情感色彩上保持一种相对零度的观察姿态,这种叙事上的不完整性和情感上的中性增加了解读的难度,使小说具有神秘色彩和多义性。
这些要素相结合,组成了一种典型的东北印象:萧条而苍茫的土地上,徘徊着孤独的人群,他们各有奇才和理想,也有过辉煌的岁月,但曾经的辉煌和理想在此刻都化为残迹。丰富的书写方法承袭自乡土文学、青春文学、先锋小说以及通俗类型小说等多种叙述传统,任何一个要素对于具有相应审美趣味和研究兴趣的读者群体来说,都具有吸引力,这可以解释作品何以受到欢迎。作品中的怀旧视角在历史与当下、历史与个人之间搭建桥梁,使叙述既连接历史反思,也照见当下现实;悬疑的加入以及碎片化的叙事也增加了解读的角度,让多元化的反思都可以以其为对象开展;文中所应用的多种历史和文化要素,也可以在解读中衔接上各类叙述,从而拓开了影视、非虚构及学术研究等其他东北呈现的空间,成为“东北热”发展的条件。“新东北书写”因此得以变幻无穷,在数年间经历多次再创作,仍未耗尽它的可能性。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东北书写”已经形成一种高效的再现方式,吸引了一批稳定的读者,甚至吸引了对东北历史并不了解的“小资读者”群体。[11]但这也引出一个问题:既然这种再现方法如此有效,为何它集中出现在对东北的书写上?“怀旧”并不罕见,告别故乡和告别过往都是成长叙事中的惯例,故土的衰败或温馨的氛围自20世纪初的乡土文学以来就广泛存在;“下岗”也不只出现于东北,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都会面临这种困境;对于底层的关注也已出现“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潮流,但其读者反应远不如“新东北书写”一般广泛。那么,东北到底为何具有如此超乎寻常的吸引力,甚至五年过去,其热潮仍未散去?因此,有必要继续分析何以是东北引起热潮,以及热潮何以能够广泛且持续。
二 何以是东北:叙述传统的继承与变奏
现有研究基于东北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以及在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的作用,指出对东北的书写能够体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因而在体现历史反思上具有代表性。[12]但这些阐释并不完整:第一,如果反响只是因为东北本身的历史意义,那么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等应更能赢得读者青睐,但仍是这批文艺作品的出现才掀起热潮,可见文艺的感染力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第二,由于部分研究以社会史眼光来看东北,直接搬出研究界对东北问题的整理和总结,没能继续解读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焦虑和关怀是否折射出更深层的隐患,也就导致反思局限在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已经给出的结论上;第三,对作品深层的历史关怀考察不足,就绕开了何以其他同类题材书写没能引起如此大的声浪的问题。所以,解读“东北热”需要正视“新东北书写”是文艺创作,它们在观照现实的同时,也建立在前人叙述基础上,调动了已有的叙述方法和情感结构,由此获得了包容性和吸引力;也唯有通过对照此前的书写,发掘这批新书写所做出的变化,才能明晰新书写揭示了什么新问题,凸显当下的历史反思。

萧红:《生死场》,奴隶社1935年版
“新东北书写”之所以起到反思多重历史的作用,源于此前的文艺创作已经围绕东北形成了叙述传统。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为东北打造了两大形象群。第一类形象凝缩了中国自原始到帝国、到近代遭遇顿挫、再到复兴的历史进程,东北历史就是中国民族历史的一个缩影。“东北”进入现代中国读者的视野,发端于“东北作家群”,作家们带给读者的东北,表现为原始而富于生命力的景观:萧红笔下方生方死的野蛮生活,烘托出天地洪荒般的神话氛围;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开篇即言“这是每个鴜鹭湖畔的子孙们,都能背诵的一段记忆里的传说”,为整部作品奠定了史诗基调,随后小说描述“二百年前,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向那神秘的关东草原奔去”“他们转过了一重山,又转过了一道水,从早晨到夜晚在炎阳底下奔,向着那不可知的命运赶去”,[13]营造了民族起源神话的色调;就连侧重表现现代战争的萧军,也首先描绘出天地间的苍茫轮廓。[14]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也以这些东北书写充实民族危亡叙述,呼唤民族精神,比如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作的序中写道:作者对故土的书写“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15];胡风介绍《生死场》虽然只是写哈尔滨附近的一个村庄,“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16]。所以,东北书写为构建中国的现代民族神话提供了资源,读者通过东北联想到的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曾属于东北流亡作家一员的马加在土改题材小说《江山村十日》中,仍以“多少年前,这里就是当年的北大荒呵”[17]的抒情笔法,将东北经由土改而新生的现实与东北自拓荒到实现独立的现代民族神话联结起来,为革命奠定悠长的历史底蕴;进入20世纪80年代,梁晓声将视野放在神秘而恐怖的北大荒,小说也围绕知青们如何战胜“鬼沼”展开;[18]迟子建对“北极村童话”、对伪满洲国历史以及对额尔古纳河的书写等,也在展现东北多民族多地域生活面貌和发展全景的同时,营造了东北的神秘色彩。因此,百年来的东北书写参与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民族神话和史诗。诸多学者已经指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它需要经由叙述的构建才能形成自己的历史起源,[19]而在中国,东北书写是构建中华民族起源的载体之一,它既以自身从沦陷到解放的历史叙述凝缩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也以富于神话色彩的形式为民族叙述增添光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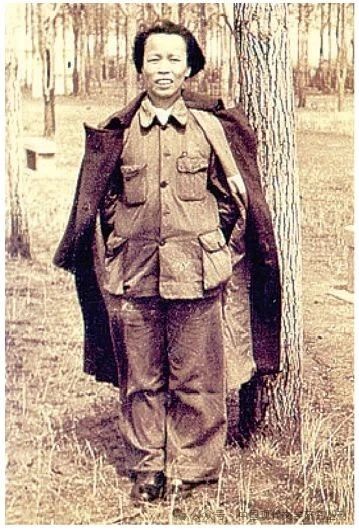
作家草明
第二类形象是工业化与现代化形象,从当代文学中工业题材的开山之作《原动力》(草明,1949)、《火车头》(草明,1950)体现新中国在改造日本殖民工业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电力和铁路工业基础的图景,到描绘矿业生产的《五月的矿山》(萧军,1951),再到展现鞍钢独特生产体制和工人动力的《百炼成钢》(艾芜,1957)、《乘风破浪》(草明,1959),以及长线索叙述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并发展矿业的《沸腾的群山》(李云德,1965),东北工业书写构筑出中国的工业长城。小说之外,还有《桥》《光芒万丈》《在前进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特快列车》《创业》等一系列工业题材故事片,以及数不尽的报告文学、纪录片和绘画作品,它们均通过东北来展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路线和生产关系,通过呈现工业景观和塑造工人形象,将社会主义建设化作可感的对象。
两大形象群相结合,交织出东北既原始又现代、既农业又工业、既古老又青春的复合形象,昭示了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书写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人们观察和理解东北的方式,更参与塑造了中国的情感结构,使东北成为开启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一把钥匙。斯蒂格勒详细区分了三种维度的记忆:第一记忆是正在流逝的此刻时间在人身上唤起的感应,第二记忆是人为了将感应持留下来而做出的记忆动作,第三记忆是因为记忆的不稳定性,人们为了保存记忆而将之技术化加工的产物。[20]斯蒂格勒的目的在于分析记忆的技术化,本不侧重解析文艺作用,不过,在新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文艺是有效的技术,它保存记忆并塑造记忆,使之突破经验的限制而为他人共享。由于此前的东北叙述为当代中国构建了一种共同记忆和情感结构,所以当双雪涛等人写出对故土的告别与怀想,触动的便是当代中国人的共同感知。
在这样的传承中,“新东北书写”又通过重新组织和调动以往的资源,形成了更贴合当下青年的历史观照角度。文学场域自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21]一个重要表现是“后冷战”以来的历史反思困境导致了历史书写的困难,已然成熟的作家尚且可以延续旧有的叙述方式来梳理宏大历史,但成长于“后冷战”时代的青年们却难以将自身处境与以往历史叙述结合起来。“80后”作家的浮出开启了一种新的处理历史的方法,他们以自身所在的时代为视点来挖掘并解读历史与自己的关系,“新东北书写”延续这一方法,以悬疑和解密的方式进入历史,将民族史、社会主义探索史的种种因由和当下个人的苦痛挣扎结合起来。所以,不同于此前书写从宏观的历史进程来把握个体命运,“新东北书写”从己身出发挖掘历史要素来解释此刻的困境,使历史的繁华与衰落都构成映照当下境况与心绪的镜子,从而重获叙述历史的能力。
“新东北书写”吸收到作品中的各类文化要素又帮助东北打开更多的面向,召唤其他叙述进入当前东北形象群,如赵本山小品中的日常生活、“二手玫瑰”乐队的地方曲艺、毛不易歌曲中的集体化时代记忆等。围绕东北展开的学术研究也当仁不让,学者们既挖掘“新东北书写”的历史和思想深度,也协助完善东北的形象与意义:“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将当下文学面貌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书写联系起来;刘岩等学者追溯了自社会主义时代以来的东北文艺源流,体现了新书写建立在怎样的文艺基础上;黄平将自己的东北研究结集为《出东北记》,这种集结塑造了他心中的东北寓言和东北文艺群像。研究者也将更多的作品纳入这个东北形象系统,日益丰富东北的多元面貌,使东北成为中国方方面面的代表。可见,“东北热”虽然以地域来命名讨论对象,却绝非仅关注一个地域,而是选取这一切片来看到更广泛的中国和更纵深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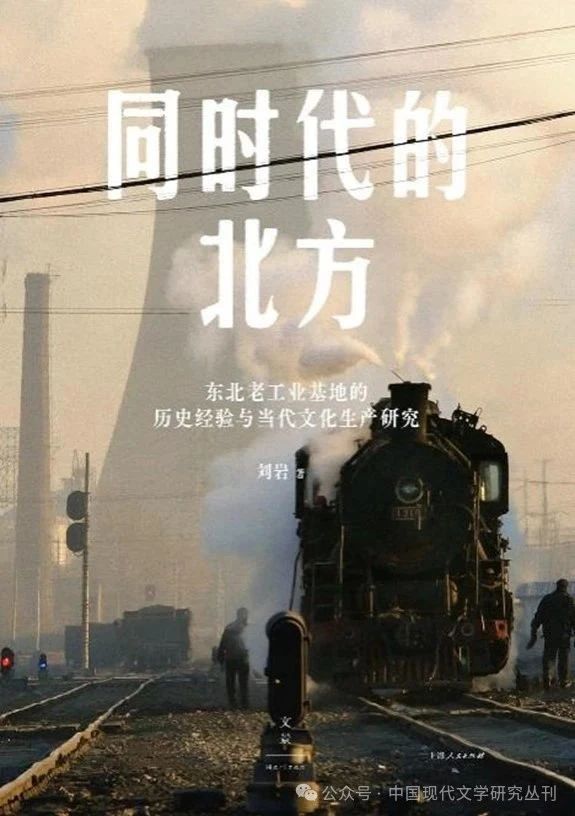
刘岩:《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此外,如戴锦华、刘岩等学者所指出并总结,东北曾有丰厚的文艺积淀,[22]这为新一代文艺创作者的涌现奠定了基础。具有东北经验的创作者们讲出自己的故事,为东北叙述提供不竭的动力,这也成为“东北热”得以持续的人力条件。由此,东北书写既有东北所肩负的历史象征性,又有大批创作者,在地利人和之上产出不息。
三 热潮的广泛:现代的衰亡与普遍的焦虑
要成为备受瞩目的讨论对象,光是作品量充足还不够,“质”也不可或缺。“新东北书写”受到关注的另一方面,是它的历史反思性博得认可。学界已经对这些作品所包含的20世纪90年代或“后冷战”反思做了扎实的研究,对此本文不再赘言。不过,由于子一代的历史反思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往往认为写作针对的是集体化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的衰落,而从读者反应来看,并未深刻受到此前情感结构影响的一代人也产生了强烈共鸣,因此,作品不仅触碰到社会主义的顿挫,还揭示了更广泛的精神伤痕和更深层的结构塌陷。

王兵“铁西区”系列摄影
图片来源:https://www.cphoto.com.cn/content/article/100499.html

王兵“铁西区”系列摄影
图片来源:https://www.cphoto.com.cn/content/article/100499.html
这批被称为“小资读者”的群体通常是城市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与“小资”一词原本所指的不具有且很难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人群不同,[23]今日能够在城市就学和谋生的群体,往往已经踏上成为中产阶级的第一层阶梯。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逐渐固化的社会阶层来看,“小资读者”的父辈应已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基础,哪怕仍未达到中产标准,也有能力支持下一代实现阶层跃升,而从时间上推算,这样的父辈恰恰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幸存下来甚至因之获利的群体。因此,吊诡的是这些获得红利的群体的下一代却对“失败者”的下一代产生共鸣,这讽刺般地反映了拥抱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另一类“父一代”也遭遇了失败:他们的“成功”并没能形成有效的身份指认,以致其下一代自以为是“失败者”;他们也没能建构自己的历史叙述,导致过往仅从“失败者”的口中讲出。比起失败者,他们更是失语的。假如“下岗”带来的衰败当真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探索的挫折,那么成功地从转型中脱险的人们本该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建构历史,然而长久以来,“90年代”书写可谓面临着全球性的沉默,这段历史只能以残片形式存在。
这种内在的危机感揭开了东北历史的另一方面。东北大工业的兴盛不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支持的结果,它既有此前日本殖民现代化的遗存,也有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力图建设和发展重工业的政治和经济需求。即便从直接原因来说,苏联的扶持也只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北重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原因之一,整个世界都在发挥作用:因为“二战”摧毁了包括列强在内的多国工业,所以战后各国的重建需求为彼此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以及自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压力下,后发现代化国家也纷纷加入工业化阵营。所以,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是发展自身现代工业、加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及适应“冷战”局势的多方面需求的结果。就世界现代格局来看,中国正处于萨米尔·阿明所定义的边缘位置上,这一位置因中心的变动而被迫变动。[24]随着列强工业体系的恢复,工业化需求降低,重工业呈现衰落趋势,在20世纪中期,工业锈带就已在诸多发达国家出现,比如美国东北工业基地、德国鲁尔区、英国中部工业基地等传统工业区接连面临资源短缺、市场饱和、技术增长缓慢等问题,从全盛走向衰落,而这些中心区域的动荡势必带来边缘地区的剧变。吕新雨在分析纪录片《铁西区》时,指出影片第一部《工厂》被译为“锈带”是把中国工业放置在了西方工业的历史谱系中,“它一方面提醒的是:中国的工业史其实离不开与西方工业史之间的关涉,工业化的过程是总体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个西方工业文明历史进化图谱的先在与合法,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欧洲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25]这一解读把握了中国工业体系与世界工业的关系,不过,结合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需求是为了抵抗并跟上西方工业的步伐,铁西区的衰落不应被称为“重演”,因为“重演”意味着中国工业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工业的复制。东北的衰落表明现代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它的尾声阶段,或者至少是一个段落的终结,这种终结使现代结构边缘处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也走向了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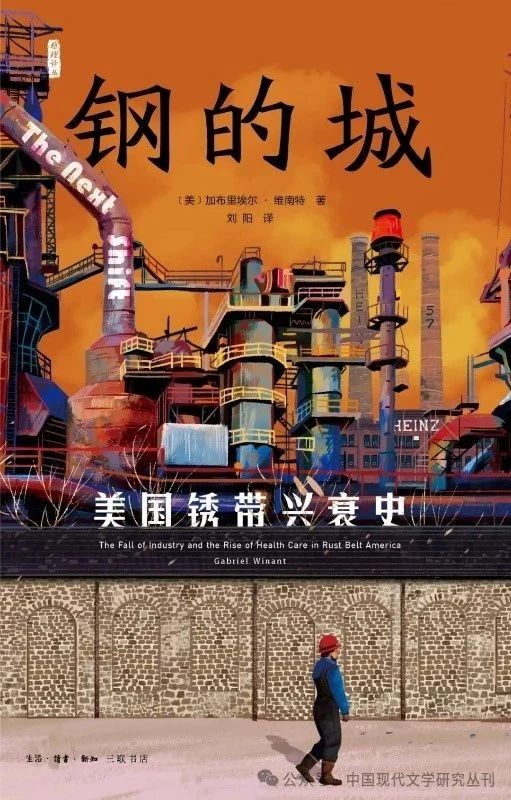
加布里埃尔·维南特:《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刘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
新东北书写对于港台流行文化的呈现也因此负有双重意义:它既体现东北衰落之时,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渗入社会主义日常生活,导致后者的逐步崩解;这些消费景观也是作为怀旧对象存在的,近二十年的历史见证了港台流行文化也在走向衰落,“新东北书写”对它们的呈现表现出悼亡青春的基调。所以,东北的衰落是整个世界产业结构变化的征兆,“新东北书写”映照的是全球的危机,它因而震动了更加普遍的情感。
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小资读者”并不真正面临失败的现实,但焦虑却是真实存在的,并充斥于各种社交平台的表达。焦虑的表达有时带有表演性和煽动性,但它如此普遍还是源于现实,因为当前青年确实面临就业难、青年贫困等压力,[26]即便尚未置身危险位置的群体,也仍然感到巨大的恐慌。他们与失落的父子两代人的共鸣、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向往,都可以对应当下现实的变动,而这种现实中的阶层跌落也表明全球化经济不能保证看似胜利的一方的稳定。书写者们在创作时想必未预期会收获这些群体的共鸣,正是当下现实将变革中的两部分人群的共同焦虑接合了起来,这种“天时”配上了东北叙述本有的“地利人和”,时代之声就在文本中留下了印记。就这一点来说,有学者将“东北文艺复兴”一词追溯到“振兴东北”的政策也是合理的,尽管“东北热”并不直接源于“振兴东北”的举措,但二者源自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背景,分享对于现实困境的焦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东北书写”的悼亡基调,不仅是挥别曾经的集体化生活,也暗示了20世纪的产业体系以及建立在这一体系基础上的“现代”已成为过往。“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走向海外,[27]引起广泛共鸣,正是世界格局激烈变化的表征。
四 热潮的持续:以空洞化为代价
黄平曾以“寓言”来命名班宇(但显然包含双雪涛等)的东北书写,“寓言”借鉴的是本雅明的理论,它和象征相对:象征意味着完整连贯的意义系统,对应完整的、自足的世界,内容和形式在其中能够组成有机整体;而寓言是破碎的,它使作品的主题或寓意关联到外在于作品的、彼此独立的对象,产生出多层次的含义。这确实点出了“新东北书写”的作用:它们因为碎片性,也因为高度简化的语言所富有的多义性而唤起读者的广泛联想,让被压抑的历史得到言说和追问。
但当一种寓言被反复生产,它的寓言性就需要警惕了。在当前东北书写体现出无穷生产力的另一面,这种生产方式也因为便捷而走向模式化。“东北”逐渐凝固为一段历史、一类人生经历、一种叙事套路,以致现在提及东北,读者便想到关于萧条和谜案的叙事。东北逐渐从体现历史复杂性的寓言,转向了某种未被言说但已然言说的历史的象征。
这种变化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有意悬置了历史。双雪涛、班宇笔下反复出现的封冻与湖水意象构成了历史的标本库:《光明堂》中,身上带有数十年来的秘密的廖澄湖和柳丁等人溺亡于湖中;《冬泳》中,隋菲父亲溺毙湖中,湖水掩盖了隋菲前夫刘晓东或“我”在数年前的犯罪证据,以及这场犯罪背后的“下岗”历史;《夜莺湖》中,“我”对儿时朋友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记忆封存于湖水。冰与水既保护了历史的现场,又将历史封在了下面,隔绝了历史与当下的直接交流。借用双雪涛对东北之冬的描述,这些作品形成“悬停的琥珀”[28]而封存了历史的身体。双雪涛曾说《跷跷板》的原名是《骸骨》,[29]而这具骸骨象征着产业结构调整时代人们的精神变化,一具未被发现的骸骨正是一段未被清理就戛然而止的历史。历史本身不再能表达,只能等待作为书写者的子一代的祭奠,而子一代的祭奠却是为了告别。相对而言,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所采用的视角有所不同,它以父一代为中心视点来展现父的自我救赎。不过,由于编剧和导演是“80后”的辛爽,该剧仍然是子一代对父一代的想象。剧作结尾的“往前看,别回头”便代表了子一代人所理解的父一代对新的主体的冀望:你们将是一往无前的列车,从历史中驶出而不必回头。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腾讯平台,2023
历史总是经由记忆呈现,偏偏记忆又是可疑的,如《跷跷板》中当事人记忆错乱,被挖掘出来的骸骨没有明确的身份,这种暧昧性隐喻了历史是确实存在但又难以指认的。这种写法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叙事圈套,但先锋小说强调叙事技巧并提示历史的不可信,置身80年代的先锋作家们借此对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表达了含蓄的反思与抵抗;而当下的叙事空位则暗示曾有一段确定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难以言说,因此作者选择以不言说的方式去暗示这段历史的失落。他们极力保持历史的神秘状态,以此告诉读者,真相只有通过不抵达才能抵达。
创作者们刚刚开始使用这种历史叙述法时,确实为多重解读留出了空间,但一旦这种书写模式被不断复制,沉默所包含的多义性便走向了真正的虚无。创作者也调侃了这种空洞化,如《北方化为乌有》通过两个作家的对话讲出了一段历史故事,然而这段历史在两人的对证之后不再被言说。双雪涛曾在对谈中反思这个题目起得有些“机巧”,本来是想做一次元叙事的尝试,却最终还是触及了历史问题,[30]也即无意中展现了历史的消亡。但无论作家最初的立意是什么,写作的结果才是这个书写历史的时代诱惑他们发出的声音。双雪涛没有提到却更为重要的是,元小说的形式也在迫使历史缄默,两人的对话所最终抵达的真相被对话推远,“北方”因为这种叙述方式而真的化为乌有。
和严肃文学中的这种倾向相似,大众文化生产中的“东北文艺复兴”也保持着和历史若即若离的关系。《野狼Disco》式的20世纪90年代东北社会表象的刻画,固然让人触摸到置身经济变革年代的底层人群在新的文化消费中的生活场景,但流行歌曲的容量导致这样的呈现难以充分传达反思,歌曲既可以被解读为对这段历史的自嘲,也可以解读为对历史的缅怀,历史本相并不明朗,也就可以被当下涂抹。此后,更多带有东北要素的文化产品涌现,将鲜活的历史压缩为符号,组成景观性乃至游戏性的现实。当历史的意义被抽空,各种历史的表象就化作浮动的符号,这恰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即终极意义失效后,价值被交换价值所替代,人们陷于能指的狂欢。赵柔柔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废土想象,并指出这些废土想象已经逐渐脱离废土原本负载的历史语境以及社会等级寓言,成为历史记忆的残骸,记忆在这些废土景观中被抽空,废土成为遗忘的标记物,这体现出历史与记忆已经日益丧失阐释力。[31]历史的纵深被打碎成各种要素而浮上表层,世界经由编码成为拟象。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鲍德里亚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基础上,以拟象来描画消费时代的世界面貌,拟象最终脱离现实,仅与自己发生关系,并主宰了这个时代。在这种意义上的“超现实”或“非现实”“不再是梦想或幻觉的非现实,不再是彼岸或此岸的非现实,而是真实与自身的奇妙相似性的非现实”。[32]和鲍德里亚做出这种描述的时代相比,今日的拟象效果更为显著,因为鲍德里亚描述的现象是终极价值消亡后的交换价值发展,但交换尚有一般等价物作为基准,而今日则是更进一步的能指滑动,如网络所言的“押韵即真理”,韵律能够替代意义的位置而制造合理性。不仅世界的表象已然变化,人的生活方式、认识方式、表达方式也已转换。
书写东北的人们已然意识到时代的变化:班宇甚至戏谑地给出了《未来文学预言》,讲述文学将进入定制时代,只有一群人秘密结社,坚持从事写作这种古老的活动;[33]黄平整理为论文集的《出东北记》从“新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延伸向AI写作,他解释自己这种处理是因为东北书写不是一场地方性的文学潮流,而AI写作“揭示出这个算法时代对于文学、对于人性的野心”[34],也体现了新东北书写与数字化时代之间的关系,即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数字化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和趋势。但即便怀抱着这种自觉,从当前创作的成效来看,作品体现出的是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历史虚实难辨,这样的书写无益于穿透数字化表象而重返现实,它们也成为拟象的实践,不仅反映曾经世界的衰落,也参与生成新世界。班宇的“预言”固然将写作视为对智能定制的抵抗,但“写作”如果不是带有自觉性并强调创新性的“写作”,就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定制”,服务于不满足于AI写作的群体和他们的趣味。

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工业中的东北呈现和严肃文艺中的东北书写也滑向了同一平面。研究界已经注意到短视频是东北风情入侵最早的领域,[35]它早已打造了关于东北的刻板印象,可谓“东北热”的先声。大众文化因为处于此前的文化系统中的边缘或被压抑位置而更快地被新的系统所转化,这种转化的力量逐步蔓延到精英文化中,使之进入这个系统,二者虽然在趣味上仍有不同,但这种层级差异已经是在同样的拟象世界中展开,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同文艺类型的受众会将它们放置在一起。尽管并非后续的书写都是这样扁平化的处理,但近几年“东北热”的持续,仍是这种趋向的结果。甚至研究者若不对这种变化有所警觉,对东北书写的研究也将化作对符号的再生产,加速拟象化的进程。
由此来看,“东北热”刚好标志了当代文艺走入拟象世界的时刻。“东北热”的发生与持续发展,一方面源于东北历史的丰富,另一方面源于“东北”的空洞化。它是丰富的历史压缩为拟象元素之过程的表征,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参与到拟象化实践中。
结 语
“北方化为乌有”的另一边,同样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南方写作”和“新南方写作”的提出。尽管这种命名的模糊性以及过多采用地域命名的讨论遭到了质疑[36],但“新南方”确实与“新东北”内在相关:“南方”或者“新南方”是针对“北方”所象征的秩序而提出的一种离散性结构,它因为20世纪秩序的衰落而浮出,所以正是在“北方化为乌有”的另一边,“新南方”现身了。“东北热”反映出对历史的重塑,“新南方写作”反映出对文化中心问题的思考,它们是同一背景下的不同向度。
如果能够理解“新南方”和“新东北”的这种内在关系,研究就可以深化对当下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格局的分析。所以,让人遗憾的是现在的讨论过于注重“何为新南方”等概念问题,旗手们又为了证明这一论域的合理性而纳入了太多的作家,反而模糊了这一对象的价值,而把握它们各自的特征,再综合分析它们到底揭示了怎样的现实,才有利于推进这些研究。
朴婕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6期)
注 释
[1]2019年10月8日,播客“GQ Talk”上最早出现“东北文艺复兴”一词,而它的广泛传播是源于同年11月30日播出的综艺《吐槽大会》的影响。
[2]参见贺绍俊《新东北文学的命名和工人文化的崛起》,《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3]黄平、刘岩、丛治辰等学者均围绕“东北文艺复兴”问题发表过系列论文,此外,李陀、王德威等一大批学者都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具有启发性的意见或评论。因成果数量繁多,本文将随文引述。
[4]林嵒:《“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芒种》2015年第23期。
[5]参见辛阳、胡婧怡《他们,在同一文学时空相逢》,《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4日;赵乃林《辽宁“铁西三剑客”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辽宁日报》2019年11月8日。
[6]杨丹丹《“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7]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8]参见沈闪《“东北文艺复兴”场域下的“非虚构东北文艺”及其新的可能》,《小说评论》2024年第4期。
[9]参见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刘岩《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10]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丛治辰:《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金钢:《后工业时代的文学突围:东北新锐四作家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刘岩研究见前注。
[11]一些研究指出“新东北书写”的核心受众是“小资”群体,他们并非因为自己具有东北经验或者自己的父一代具有“下岗”经验而与“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产生共鸣,这构成了“东北热”问题中的一个有待分析的现象。参见张定浩、黄平《“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杨晓帆等《希望,还是虚妄?——当“东北文艺复兴”遭遇“小资”读者》,《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12]参见刘天宇《虚实之间:〈平原上的摩西〉社会史考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杨丹丹《“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13]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4]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奴隶社1935年版,第1~5页。
[15]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16]胡风:《〈生死场〉读后记》,《漫画和生活》1935年第1卷第2期。
[17]马加:《江山村十日》,《马加文集》第2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18]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贺绍俊、杨瑞平编:《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19]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岩波定本)》,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05页。
[20]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0页。
[21]近年来常常出现的“重返90年代”的讨论可谓学者们通过重新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来阐释当下现象的表征,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在2022年7月召开“细描‘90年代’——80、90后学人的视角与问题”主题会议,相关文章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2022年第12期组织的“‘两个世纪之间的九十年代’笔谈”专栏。
[22]参见戴锦华《把东北作为方法》,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699974;刘岩《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
[23]小资”这一概念的所指自20世纪以来不断发生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刚刚出现时,它指在城市中生活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群体,他们形成了一种异于工农阶级的审美趣味即“小资趣味”。这一群体及其趣味在20世纪中叶因为对工农阶级的强调而一度消失,到20世纪末再次出现“小资趣味”的讨论时,它通常被用来指代在尚未完全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生活方式而无法达到这种生活水平的青年人对自身审美品位的建构。
[24]参见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25]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读书》2004年第1期。
[26]参见张抗、冀洋《当代青年工作贫困指数测度、分解与检验》,《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刘璐婵、韩慧怡《青年劳动者工作贫困:脉络、趋势与展望》,《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5期。
[27]Dylan Levi King, “The Rough Street Blues”(《走向国际的“东北文艺复兴”》), The World of Chinese, no. 3(2022), pp. 80-82.
[28]双雪涛:《冬天的骨头》,《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16页。
[29]双雪涛:《海明威的肋骨》,《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第212页。
[30]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31]赵柔柔:《记忆残骸与现实折影:中国大众文化文本中的“废土想象”》,《文艺争鸣》2022年第12期。
[32]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33]班宇:《未来文学预言》,《鲤·时间胶囊》,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
[34]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第237页。
[35]刘诗宇:《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复兴”》,《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36]参见袁捷《新南方写作:地缘、文化与想象——第十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23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