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随着DeepSeek等先进人工智能的不断涌现,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轻松地“再造真实”,还通过算法将一切真实纳入“应然”之中,使真实远离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多样性、丰富性、可感性及芜杂性。而非虚构写作却通过文学的“求真行动”,从事真、情真、理真等不同维度,成功突破了“真实”在数字时代所遭受的日常困境,捍卫并彰显了“真实”的内在力量。面对数字时代的“信息茧房”,以及由此引发的“认知茧房”之局限,非虚构写作凭借亲历性、实证性、现场性、对话性的叙事,不仅校正了创作主体认知的幽闭性,使作者在与众多他者的交流与碰撞中,充分认识到世界的丰富、复杂与多元,还有效拓展了创作主体的文化视野,摆脱了偏执观念,并使主体的自由心性获得施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虚构写作在弥补数字时代的认知局限、提升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非虚构写作 真实 人工智能 算法 认知茧房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之所以不断引起人们注目,主要原因就是它们以田野调查的亲历性和实证性方式,呈现了大量真实、鲜活且耐人寻味的现实生活,揭示了各种不为常人所知的社会真相,有效拓展了人们对于当下现实社会的认知视野,给长久沉湎于“信息茧房”中的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且原汁原味的生活现场。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凭借自身的“求真行动”,从事真、情真、理真等不同维度,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成功突破了“真实”在数字时代所遭受的困境,也捍卫并彰显了“真实”的内在力量,并使“真实”这一概念,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伦理中具有表征性意义的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数字技术的发展,“真实”可能不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非虚构写作或许也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阅读反响。随着人工智能对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真实”所面临的困境又进一步加剧,这无疑使高举“求真”之旗的非虚构写作显得尤为可信,且弥足珍贵。尽管我们不能将非虚构写作的崛起,简单地归因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数字技术所导致的“真实”之困,但两者之间的复杂纠缠,确实值得我们深入辨析。
一
一切源于真实,却又超越了真实。当数字技术尤其是仿真技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无所不能时,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真实”,其实已经变得极为脆弱,且日渐珍贵。试想,只需要借用某个人的照片和声音,便可以让他“真实地”在镜头前谈天说地、纵论古今,或者戴上VR眼镜,人们便可以置身于海底深处或宇宙星际之间,切身体验所谓的“大海星辰”之旅。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如何定义“真实”?这显然超越了哲学或科学领域讨论的“真实”内涵,使之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伦理性命题。可以说,在人工智能全面渗透的数字时代,拟像与仿真的技术目标,绝不是简单的“拟”或“仿”,不是真实的某种摹本,更不是他者化的真实映照,而是面对真实且又超越真实的“再造性真实”。这种“再造性真实”,注定滑出了哲学讨论的起点,也必然超出科学探索的边界——因为很多时候,科学意义上的真实都坚守在“实然”之中,但它如今却向“应然”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而且,“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边界,如今也变得日趋模糊。
这便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它的影响,不仅涉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波及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可以预见的是,它将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模型及算法,迅速而高效地为人类社会提供最佳发展路径,并以此重组人类现有的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生产领域的结构形态、社会文化传承与转化形态、知识传播的专业体系结构形态等。依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很多人都乐此不疲地扮演着预言家的角色,并振振有词地宣告某些领域某些专业将失去存在价值。齐格蒙特·鲍曼甚至不无幽默地说道:“在未来的工厂中,将只剩两种活物:人和狗。人的工作是喂狗,狗的工作是确保人什么也不碰。这个笑话捕捉到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工作一直在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是人类竞争者,而是计算机和机器人。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智识劳动也将会自动化。”[1]鲍曼所看到的,还只是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智能化发展,更大的变化则是随着数据、模型与算法的不断优化,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了自身的快速迭代升级,并针对不同个体的内在诉求,在思维与情感上形成了别有意味的互动。所以人们普遍相信,人工智能的涌现,绝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而是意味着人类进入了全新的文明时代——继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数字文明”时代,并称之为人类的“第四种文明”。我们无意在此探讨人工智能究竟会给人类带来哪些重要的变化,而只想说明,立足于大数据的各种模型与算法,在驱动人类走向新的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已经轻松改写了我们对于真实的传统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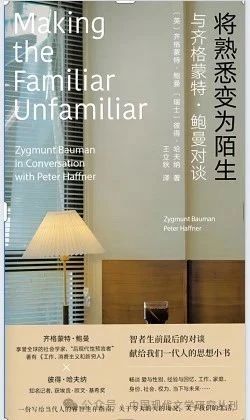
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这种对于真实的认知改变,突出地体现了数字技术从算法层面重塑真实的价值,使真实逐渐失去了日常生活中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可感性。当人工智能逐渐嵌入人类的思维方式并能够根据人类思维特点及目标诉求,提供精准的解决方案时,这种具有精确意味的真实,已变成算法的产物。而算法所秉持的信念,就是“人与万物皆可计算”,而非追求事实的准确性。致力于通过计算来“决策一切”,即通过大数据和计算逻辑,果断剔除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过滤特殊性和可感性,并对合理性和精确性负责。算法所遵循的法则,就是对各种事物进行量化分析和决策,从而规训人们的认知、行为和社会的结构。由此带来的结果,不仅使那些溢出普遍性之外的多样性、芜杂性的真实,变得无足轻重,而且让那些基于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各种专业理论,也变得多余,并使某些既有的专业理论本身开始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智能世界。韩炳哲就说道:“大数据分析可以识别能让预测成真的行为模式。假说的理论模型被直接的数据对比所取代。相互关系取代了因果关系。(数据证明的)‘就是这样’让‘为什么’这个问题变得多余:‘关于人类行为的所有理论都已经成为过去,从语言学到社会学。你尽可以把分类学、本体论和心理学都抛诸脑后。谁能说清,人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或者人们做什么事?他们就是做了,而我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对其进行追踪和测定。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数字就会自圆其说。’理论是一种构想、一个辅助手段,用来补偿数据的不足。一旦有了足够的数据,理论就变得多余。”[2]数据、模型和算法在表面上都是基于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它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那就是绝对正确的。但它忽略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恰恰是不精确的,有时也是有瑕疵和芜杂的,就像一块玉石,过于完美反而显得不够天然;至于大千世界中的个体之人,更是如此。
问题并不在于这种算法至上的真实,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多样性、丰富性的真实,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别,而在于置身这种历史大裂变过程中的我们,依然无法舍弃人与世界的传统关系模式。面对“再造性真实”时,我们既掌控不了未来,又把握不住当下。在这种尴尬的历史情境中,非虚构写作以“文学求真”的审美追求,在作者与当事人的亲历性参与中,让人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当下生活芜杂而又粗粝的真实现场,也认识到了日常现实中丰富多样且矛盾重重的人与事,并迅速形成情感的共振和思想的共鸣。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就忠实记录了作者在广州、云南、北京、上海等多地从事的十九份工作,包括快递分拣工、酒店服务生、便利店店员、加油站员工、服装店小老板、快递员、保安、自行车销售员等,展现了不同行业内部的运行机制以及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它所体现出来的叙事魅力,不在于作者选择工作的灵活与合理,也不在于讲述经历的技巧,而在于其工作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市场规则,以及纷繁复杂而又隐秘难言的人事纠葛。尤其是在作者从事快递员工作的两年时光里,从卸货、分拣、装车到送件,以及商场和小区顾客对待快递小哥的各种心态,都充满了鲜活的现场感。在这部作品中,胡安焉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直观地呈现了各种底层工作的潜在规则,打工者的酸甜苦辣,包括与各种幽暗人性的较智较力,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因为我是其中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我的叙述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和立场。但我如果过滤掉这些内容,读者就无法理解我当时的一些行为和反应。故此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我也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受情绪左右、有没有偏离客观。”[3]事实上,正是这种真诚且真实的主体情绪,激发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也让读者深切地认识了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底层生活。黄灯的《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则如实记录了作者对一些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学生的家访经历。它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在于,作者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姿态,深入到众多普通大学生的家庭内部,以及他们成长的相关社会生存环境中,多维度地呈现了学生家庭成员的教育方式和态度,也记录了这些学生进入社会之后的工作现状。作者并不回避学生们的原生家庭与当代中国教育之间的内在纠葛,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了一代年轻人成长的艰辛路程,让人们了解到当下青年成长的复杂现实。
别有意味的,还有一些写作素人的非虚构作品。按理,从未经过必要写作训练的普通作者,很难创作出引人注目的作品,但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却有一批写作素人凭借其自述传式的作品,像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杨本芬的《我本芬芳》、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阿包的《阿包》、周慧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等,赢得人们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并非这些作品拥有多少深邃的思想或独特的叙事技巧,而是因为它们以独特的真实,呈现了这个世界的丰富、微妙和复杂,使人们在日常经验中难以了解的生活真相获得了鲜活的展示。换言之,它们依靠的是作者刻骨铭心的亲历性生活,是可知可感的个案生存经历,正是这种难以复制的真实陈述,引发了读者的共情。如《阿包》的作者阿包,就是一位出生于黔东南一个贫困苗寨且只读过一年书的女人。她识字不多,根本不具备写作能力,但她在潘哥的鼓励下,通过手机口述再转录文字的方式,如实地记录了自己大半生的坎坷生活:从小被后妈阻拦无法读书,十几岁便给亲戚做保姆,而后懵懵懂懂地嫁给离过婚的老矿工,生孩子后靠打工养家,在人才市场被拐卖到河北,逃跑途中在北京被收容,艰难回到家里之后又面临婚姻危机,娘家亲人的重病每次都花掉她的有限积蓄,不经意中又遭遇电话诈骗……我们当然可以说,阿包的人生经历反映了当代中国近40年的社会变化,但《阿包》让人为之动容的,恰恰是作者对各种世态人情的切身感受,尤其是身为女人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吃苦耐劳、永不屈服的性格。同样地,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以20多篇短文,记录了作者在浙江小镇菜市场摆摊18年间的所见所闻。其中“在菜场”部分,记录了从包子铺的师傅、杀猪的屠夫、捕蛇人,到收废品的“破烂王”、修鞋的手艺人等菜场中的众生相,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展现了他们在竞争环境中努力寻求生存的生命样态。“在人间”部分,则将视角延伸到菜场之外,记录了作者家乡及周边的普通人故事,同时也不断插入了作者幼年被送养、少年生病、青年远嫁以及中年离异的曲折经历。这些故事同样充满了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了亲情和友情的力量,并自始至终洋溢着凡人特有的欢乐与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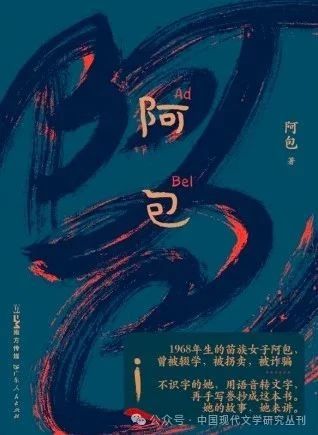
阿包:《阿包》,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作品所呈现的真实生活,不仅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种角落,而且深入到不同人物的内心深处,其多样性、丰富性和特殊性远远超过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意义。它们显然是数字技术无法取代的,也是人工智能依靠模型和算法难以抵达的真实之境。人工智能是通过统计模式,学习数据中的关联性,而非真正地“理解”知识;它依赖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无法区分因果与巧合,在逻辑链断裂时仍会强行生成答案;它以“生成流畅文本”为首要目标,并非追求事实准确性。尤其是面对丰富复杂的个人化生存及情感的真实呈现,它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这些非虚构写作义无反顾地恪守真实,并以作家自身的“求真行动”来全程保障所叙之事的真实,呈现一个个具有实证性的鲜活人物,与人工智能的模型逻辑及算法所推崇的“技术之真”,形成了有关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在互补。
二
数字技术的巨大魅力,就是它的便捷性、即时性、平等性和参与性,却唯独无法确保它的真实性。表面上看,人人都是信息的平等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即时发布者,无须面对面的交流,当然也就无法对真实负责。但这并不等于它就完全忽略了真实问题。事实上,立足于大数据的模型及算法对真实所构成的重要威胁,一方面在于它可以轻松地“再造真实”,并不断背离丰富多样的个体真实,从概率论上追求具有普适性的“精确真实”;另一方面还在于它所追求的这种“精确真实”,是终极性的问题,而不是过程性的问题,带有明确的概率化和统一性的特征。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知晓各种模型及算法里,是否隐含了强烈的排他性逻辑思维,但从它们最终提供的答案及决策导向来看,都体现了明确的唯一性。这种对“唯一性”的推崇,其实已通过概率换算折射了排他性逻辑,导致各种异质性的他者的缺失,并使人们的自我成长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同质化环境,很容易变成自恋性的主体。
更重要的是,面对如今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了解现实的基本途径,似乎只能更多地依赖于网络信息。网络是信息的基本来源,而算法是最精确的导向,为了解决不同的个体对于信息筛选的需要,一方面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并通过算法不断为不同的个体提供更便捷、更有用的“信息”,即它会充分利用个人的浏览记录、个人偏好,精准推荐符合其个人兴趣的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充分迎合人性的某些共同特点,尤其是乐于接受观点相同者的信息,在各种交流平台上,不断强化个人接收同质化的信息。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任何个人对广袤而复杂的世界的认知及视野,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就是人们常常谈及的“信息茧房”。其结果,便是个人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多地局限于个人偏好之中,既失去了他者的异质性对抗,导致“他者的消失”,也失去了多角度、多维度拓展个人社会文化视野的机会和能力,并最终导致个人思维和观念的固化,个体之人成为幽闭性的自恋主体。所以说,“信息茧房”的形成,本质上就是人工智能与人性意愿密切互动的结果,而且算法的智能程度越高,个人的信息偏食越明显,两者的共振性就越强,“信息茧房”也会越牢固。
倘若深而究之,这种由“信息茧房”所造成的幽闭性主体,无疑会因为过度自恋而进一步加剧个体之人在自我认知上的盲区,并在无形中搭起了自我强化的认知闭环,从而逐渐游离真实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感性。大数据、模型及算法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越来越重要,并对个人思考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回音室效应”,即普遍的个体之人都倾向于接收与自身观点相符的信息,而自觉回避他者化的异质性声音,从而使自己的观点不断强化。如今社交平台的推荐算法,可以让用户轻松听到自己更大的“回音”——将自我笼罩在单一的观点之中,排除各种异见,固化自己的思维。这种“回音室效应”,展示了人们在信息获取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算法推荐等原因,只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信息,从而陷入某种自我封闭的状态。韩炳哲就认为:“由于数字交流的高效和便利,我们越来越多地避免与真实的人直接接触,甚至避免与一切真实的东西接触。数字媒体让真实的对方逐渐消失于无形。它将真实的面对面看作阻碍。如此一来,数字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多地脱离肉体,脱离面容。数字媒体对雅克·拉康的关于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三界论强加以彻底的改造。它把真实界清除,把想象界绝对化。智能手机是一面电子镜子,展现了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新版本。它打开了一个自恋空间,一个想象的领域,我把自己包裹在其中。”[4]由于缺乏与真实之人的面对面接触,长期沉湎于“信息茧房”所垒砌的想象性世界中,人们在很多时候其实生活在偏狭的“同温层”之中。

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这种情形,在虚构性的小说创作中,其实或多或少已有体现。譬如,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要么执着于自我生存体验的“密室写作”,要么带着架空思维进行反现实的幻想性叙事。当他们面对复杂真实的社会现实时,往往失去了灵活有效的表达能力。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女性主义写作。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近些年对于中国当下女性生存及其命运的关注中,除了盛可以等极少数小说家还在为性别的屈辱及性别伦理进行反思之外,大多数作家都很少触及这一问题。在张莉所做的有关性别伦理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年轻女作家普遍回避“女性写作”标签,认同“雌雄同体”的跨性别叙事,认为强调性别叙事会限制文学审美价值,甚至对“Me Too”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只有铁凝、迟子建等资深作家公开承认女性视角的创作价值。[5]其言外之意是,当今社会中的性别问题,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值得过度关注的真实问题。诚然,作为虚构性的小说写作,作家有理由去追求超性别叙事,但在这种叙事的背后,是否也隐含了青年作家们长期沉湎于“信息茧房”,以至于对社会底层女性真实处境的无知?我并不喜欢极端的女性主义写作,甚至觉得“雌雄同体”的跨性别叙事应该是文明社会里作家所持的基本态度。但是,当我阅读了很多非虚构作品时,我又对这些青年女作家的超性别写作姿态保持疑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置身的现实社会里,性别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作家们进行特别关注、深度聚焦的问题。从易小荷的《盐镇》《惹作》、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杨本芬的《豆子芝麻茶》,到阿包的《阿包》、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黄灯的《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等,它们不仅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现实社会中女性极为艰难、屈辱的生存处境,还让我们深切地体察到中国传统男权思想所主导的各种世俗伦理对女性的伤害远未结束,女性的自我解放之路依然千艰万难,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依然需要漫长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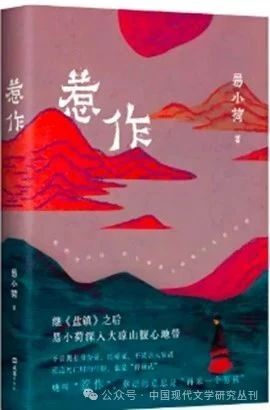
易小荷:《惹作》,文汇出版社2025年版
我们不妨在此简要分析一下这些非虚构作品。如易小荷的《盐镇》,主要叙述了四川自贡的仙市古镇里12位女性的生存际遇。从90多岁的老太陈炳芝,60多岁的王冠花,一直到中年的钟传英,20岁的少女黄欣怡,这些生活在看似静谧、闲散的古镇里的女性,一代代仍然饱受男性暴力和生活贫困的折磨。她们虽然也在进行不停的挣扎和反抗,但最后总是收获更大的屈辱和更深的伤害。按理,这个小镇并不偏远封闭,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市场经济的活跃度并不弱,连陈炳芝老太都敢开设“猫儿店”,人们对各种新潮观念也从不拒绝,但是,女性依然沦为被伤害的群体。易小荷的另一部新作《惹作》,通过追踪式的访谈与交流,从人们早已遗忘的记忆中,打捞并还原了川西凉山金阳县彝族女性苦惹作短暂的一生,同样呈现了底层女性悲苦的命运。1995年出生的苦惹作,自幼生活在大凉山一个偏远的山村,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饱受极端贫乏的折磨。十几岁便嫁到雷波县瓦曲拖村,在无尽的劳作和野草般寂寥中艰难地守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婚后她也享受了一段夫妻恩爱的美好时光,但自从丈夫苏甲哈走上吸毒之路后,苦惹作的噩梦便纷至沓来。她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来挽救丈夫,守护家庭,却依然看不到任何希望。绝望中,她用一瓶百草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年轻娇美的生命才走了十年,当众多亲人回忆起来,便几乎没有人记得她的死亡日期,就像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一样。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苦惹作的死亡,差点引发了苦、苏两个家庭之间的一场械斗。她仿佛一株野草,消失在大山深处,似乎无人惦记。如果我们再看看杨本芬的《豆子芝麻茶》里所讲述的秦老太、湘群、冬莲等女性的坎坷经历,同样深切地体察到女性被歧视、被伤害的命运。秦老太童年时就遭受父母的冷漠与暴力,成年后又屡次遭遇不幸的婚姻,最终在年迈寡居时才获得了一些自由和宽慰。湘君虽曾经是一位大学生,美丽、真诚、洒脱,但在经历了多次爱情挫折后,最终因丈夫早逝而沦为农村大妈。如果我们再联想到《阿包》中阿包的屈辱性自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看似丰裕的物质光环下,依然有太多的女性生活在没有尊严的男权伦理中。
为什么虚构性的小说创作却很少关注这些女性的生存问题?在当下的文坛中,女性作家尤其是青年女性作家可谓阵容庞大,她们的目光却很少深入这些现实的幽暗之处,无法从性别关怀中揭示并反思这些传统伦理的沉疴,其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中,难道没有“信息茧房”所催生的“回音室效应”?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正是非虚构写作备受青睐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有效突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信息茧房”,使大家于蓦然回首之际,发现日常现实中还存在着这些令人惊悚或为之动容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不是建立在作者对真人真事的记录上,而是集聚了作者、当事人、旁观者、档案材料,以及包括照片在内的原始场景记录等,是在实证性基础上进行的求真行动。像《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里,黄灯通过对正敏的家访,如实记述了她母亲范氏碧与众不同的一生。作为一位被拐卖到粤西山区的“越南新娘”,她为了带领儿女走出大山、接受教育,不顾丈夫的阻拦,坚持在镇上买房;为了追求女性应有的理想生活,她敢作敢为,屡次成为村庄里的“第一个”:第一个穿裙子、穿高跟鞋、骑摩托车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拥有驾照、QQ空间、玩抖音并常用淘宝购物的女人。而晓静的妈妈谢英华,则是来自江西赣州农村的青年女性,因家庭贫困,她很早就前往深圳打工,虽勤奋聪慧,终因知识和勇气不足,最后还是选择了嫁到广东农村结婚生子。但她并不甘心于生活现状,而是带着倔强的性格,也带着内心的孤独和不甘,不顾周围人群的世俗眼光,坚持从采茶、陪伴孩子做起,努力寻找一切机会去赚钱,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使孩子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如今她已人到中年,却依然活力四射。

黄灯:《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对于当今现实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真实书写,无论是丰富性、多样性,还是复杂性、可感性,都迥异于虚构性写作日趋同质化的倾向。其最大特点,就是作者尤其是那些写作素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信息茧房”的困扰,凭借自身的“求真行动”,或进行田野调查,或查阅相关史料,或如实讲述自我的经历与感受,跳开了由人工智能构建的各种信息陷阱或知识幻觉,将文学重新带回到充满了各种芜杂、丰饶而又鲜活的生活现场之中。
三
无须讳言,随着ChatGPT和DeepSeek的横空出世,各种大模型及其算法,已成为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关键支撑,并构筑起数字时代的重要社会发展基础,也在深刻地重塑人类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新格局。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版图的不断拓展,已催生出一系列极具效能的生产力工具,并引发人机协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最终将驱使人类生活方式、生存观念乃至思维方式的潜在变革。在这种变革中,缺乏透明度的各种算法开始掌控各种秩序,并使“真实”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困境。其中,被人工智能不断强化的“信息茧房”,引发的不只是信息的同质化及其“同温层效应”问题,还有更严重的“认知茧房”问题。韩炳哲就曾说道:“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不是数字秩序的范畴,它与计算背道而驰。计算的过程与思想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计算的步骤受到保护,不会被意外、巨变和突发事件干扰。”[6]但是以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恰恰剔除了所有的或然性、意外,使思想的光晕被约束在既定的秩序中。如果作家长期深陷于“认知茧房”,不仅会导致视野狭窄,无法了解丰富复杂的真实社会人生,还会容易产生秩序化、程式性的认知思维,最终使作品难以传达创作主体对于现实人生的前瞻性和洞穿性的独特思考。
所以说,“认知茧房”比“信息茧房”更值得我们关注。所谓“认知茧房”,主要是指个体在信息获取和认知过程中,因为长期接触单一的同质化信息,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认知状态。由于受信息偏食的影响,不同的个体都倾向于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认同的信息,忽略或排斥其他内容,形成内容和观点的同质化,即茧房内的信息多为观点相似的内容,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个体之人处于这种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中,难以接触到外部的不同观点,久而久之,便限制了其知识面和社会理解力的扩展,也无法形成全面科学的世界观,容易导致逻辑的形式化、思维的简单化,降低个人独立思考能力。鲍曼就认为:“所有的研究都表明,通过互联网交流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趋向同温层。他们会创造出一个在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回声室。你听到的只是你自己的回声。但与和你说相同的话的人交谈,这不是对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镜厅:无论往哪里看你都会看到自己的模样。于是,那些把大量时间花在网上的人开始无视自己朋友圈之外存在的现实。我能理解这非常舒爽。你会因此感到安全。你会活在这样的幻觉下:你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其他那些人的确存在,但他们不重要。就算你真在网上和人吵了起来,你也可以简单退出。你不需要谈判。在真实生活中,就不那么容易了。”[7]应该说,由数字技术建构起来的各种网络平台,表面上看是将全世界人群聚合在一起,使大家可以自由、平等、即时地进行交流,但在本质上它借助人工智能的算法,不断分化人群,让不同人群自觉生活于各自的同温层里。
问题当然不在于同温层本身,而在于同温层所形成的特殊的社群结构中——社群内的成员只接触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时,他们的思维观念也将与外界其他观点完全隔离,而众多社交媒体普遍采用的算法推荐,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这种隔离,从而导致个体之人更容易看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信息,对他者化的观点接触极少。由于缺少他者的否定性碰撞,人们在充分享受群体认同感的同时,只会不断强化自身的立场,并不会进行自觉的质询和反省,极易形成极端性的观点,最终可能导致群体观点及行为的极端化。有学者甚至认为,不同群体之间因信息隔离而缺乏交流,将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和对立,从而加剧社会的撕裂。如果作家不能自觉地对此保持警惕姿态,长期处于这种同温层中,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文化认知的片面性。因此,就文学创作而言,作家的“认知茧房”问题潜藏着更复杂的局限。但是,从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的发展态势来看,围绕着文学的“求真行动”所展开的各种叙事追求中,作家们大多专注于田野调查式的亲历性写作,这无疑很好地避开了“认知茧房”。我们虽不能说非虚构写作就是数字时代的一种典范性写作,但在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上,它确实为作家抵抗“认知茧房”提供了某些示范性的意义。
首先,作家们如果身处“认知茧房”中,失去了他者作为异质性的必要参照,会导致创作主体难以接触到跨领域、异质性的知识观念,复杂的社会现实极易被简化为标签化叙事,深度思考与价值追问逐渐消失,阻碍作家艺术思维的创新性发展。一个人的自我成长及其思想观念的形成,永远离不开他者的映照。没有他者的对抗,自我便无法确定有效的轨道。“精神的觉醒要归因于他者。他者的负面性让精神得以存活。只着眼于自己、固守自己的人是没有精神的。成就精神的是一种能够‘接受个人本身的负面性,承受永无止境的痛苦’的能力。抹杀他者的所有负面性的正面性会渐渐枯萎,成为‘死的存在’。只有突破了‘与自我的单纯关系’的精神才能创造经验。没有痛苦,没有他者的负面性,沉溺于过度的正面性之中是没有经验可言的。这就好像,人们经过了千山万水,却无法形成任何经验。人们没完没了地数数,却不能完成任何叙述。人们感知所有的事物,却不能形成任何认识。痛苦,即因为他者而存在的阈值感。”[8]但在“认知茧房”里,通常只剩下观念相同者的彼此点赞,他者处于缺席状态,人们变成了自恋性的主体。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恋,可能会导致个体陷入“知识幻觉”,误以为自己的认知足够全面,丧失主动探索多元世界的动力。“失去了负面性,就会造成正面性的粗劣聚积。基于其正面性,信息也和知识区分开来。知识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能像发现信息一样去发现知识。获取知识经常要以长期的经验为前提。因此,其时态与信息完全不同,后者是短暂的、临时的。信息的表现形式是明确的,而知识的表现则是含蓄的。”[9]这也就是说,他者不参与、不在场的信息,并不能提供知识的更新,人们要获得新的知识,完善自我,必须有更多的他者作为一种否定性存在,迫使自我在校正反省中得到知识的更新和完善。文学无疑需要呈现多层面的生活,从社会历史文化到人性命运等,作家不仅需要跨界性的视野,还需要跨领域的知识。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特征,就是作家彻底摆脱了“认知茧房”的局限,使叙事本身成为一种由不同的他者共同参与、彼此碰撞、相互映照的过程。像梁鸿笔下的梁庄人物,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身在家乡梁庄还是漂泊异地,他们都脱离了作家主体的记忆认知,变得陌生而生动,复杂而独特,正是他们不断激化并校正了作家自我的感受和思考,才使她呈现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意外、讶异而又芜杂、真实的梁庄。因此,梁鸿的“梁庄系列”,与其说是她写下的属于作家个体理解的梁庄,还不如说是由作家与梁庄的人们相互交流碰撞后重构出来的梁庄。作家远离了“认知茧房”的局限,让我们共同认识了一个真实的梁庄,一个步入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真实的结构形态及其生存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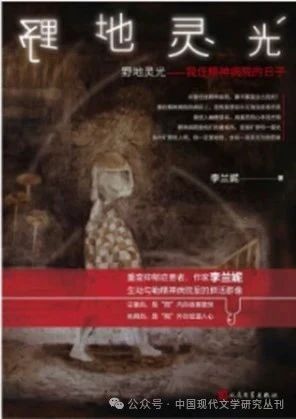
李兰妮:《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其次,作家们长期身处“认知茧房”中,还会导致创作主体对社会文化、人性等认知上的极端化,并形成观念上的偏执。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或许只是一个古老的寓言,但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一个显在的事实是,长期接触相似信息,必然会削弱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形成“认知偏误”——只接受符合既有观念的信息,排斥异见,必然导致人的思维僵化,失去灵活性与创新性。在信息彼此隔离的“信息茧房”中,处于隔离和封闭的认知环境中,人们很容易滋生极端情绪,包括对异己观点的排斥,从而加剧某些非理性的行为决策(如网络暴力、各种抢购潮等)。这种认知的极化,既是文化多样性衰退的表征,也削弱了现代社会应有的包容性与创造力。但是,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教育功能,均要求作家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健全的心智,尽管中外作家里也不乏某些观念偏执者,但思维的灵活与艺术的创新终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非虚构写作的田野调查式策略,与不同人物的深度交流,对事件的多维度查证,都彰显了作家对偏执观点的权衡、评判与校正。像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就是通过作者对大量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精神病患者、不同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同患者的家属心态,以及不同诊疗方法的效果,进行灵活多样的讲述,揭示了精神疾病背后的社会、生理及心理困境,使我们了解到这种特殊生存群体对家庭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以及被社会所拒斥的深层伦理问题。
最后,作家们如果身处“认知茧房”中,会使创作主体的精神空间乃至自由意志受到挤压甚至解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认知茧房”就是对个人“自由选择”的一种解构。因为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每个人看似拥有无限信息的选择权,实则都被算法的隐形框架所控制。而且无须讳言,算法总是受控于技术和资本的双重权力,用尼克·西弗的话来说:“算法已不再仅仅是文化建构的一部分,而已然变成文化实践本身,对算法不能仅从数学逻辑的角度去理解。”[10]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长期沉浸在这种算法文化里,便成为这种文化的产物,最终也会导致主体意志的丧失,个人的判断力被算法或群体意志所取代,沦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在韩炳哲看来,这种状况就是自恋主体逐渐沦为自我剥削的机器。现实当然不至于此。但主体的自由意志正在被算法所钳制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要突破“认知茧房”,我们不仅需要主动拥抱多样性的信息,还要积极推动技术伦理的革新,尤其是算法的透明化和公正化。只有破除算法的偏误,我们才能在开放与对话中,避免思维的固化,实现认知的破茧重生,重构并维护公共理性的价值。作家尤要如此。不同个性的人物,不同领域的生活,不同时代的历史或现实背景,都需要作家拥有跨领域学习的自觉性,并能够从与不同人群的积极交流中获得生命体验与人生经验。在这方面,非虚构写作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非虚构作品的文类形态,通常都突破了各种文体的限制,呈现出明确的开放性特征。在很多作品中,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不同人物的交流,各种理论知识的征引,各种碎片化的文本,这些叙事的特点,其实都表明了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写作素人,他们在非虚构写作中的个体心性与自由意志很少受到限制束缚。
总之,随着DeepSeek等先进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不断涌现,其在逻辑推理、数学计算、回答复杂问题等方面,都展现了强大的潜力。但是,“信息是积累的、叠加的,而真相则是排他的、有选择性的。与信息不同,真相不会堆积。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经常遇到真相。大量的真相是不存在的,但信息群却是存在的”[11]。也就是说,真相需要寻找、调查和求证,需要人们付出大量的体能和心智,从不同的表象入手,通过不同方式与不同群体深度交流,在信任共同体上才能探得。它与我们每天唾手可得的信息,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学虽然不是为了追求各种真相,但它不能无视人类生存的真相,更不能忽略对人类的存在真相及其本质的探寻。文学在认知功能和教育功能上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于人类生存真相及其本质的揭示中。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总是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很少论及甚至避而不谈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教育功能。我曾专门撰文对此进行过讨论,认为非虚构写作对于重申文学的认知功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学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借助认知功能,从社会、历史、文化、人性等不同维度,揭示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及其可能的存在状态,从而更加深远地实现其审美功能。不可否认,在虚构类的小说中,作家同样通过诸多方式,突出作品的认知功能,但受制于小说本身的虚构特质,其认知功能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作家个人的人生经验与主体思考。但是,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却以作家的亲历性、事件的实证性、叙事的在场性、思考的专业性等,从事真、情真和理真的多重维度上,挣脱了数字时代的某些“真实之困”,为人们呈现了繁复驳杂且异常鲜活的真实生活。也许,非虚构作品在审美层面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们在摆脱数字时代的某些认知局限、提升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上,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洪治纲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艺批评研究院
31112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6期)
注释
[1]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4页。
[2]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9页。
[3]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82页。
[4]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第34~35页。
[5]张莉:《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
[6]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第75页。
[7]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第199页。
[8][9]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第76~77、60页。
[10]转引自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11]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第59~6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