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冕近影
内容提要
本文以诗歌理论家谢冕近年散文、诗歌创作为中心,通过与其诗论《北京书简》对读,梳理谢冕创作的感官性特征及其背后的形式理想。感官性,在其40—60年代的创作中就已出现,在70年代的“西双版纳—瑞丽”组诗变得显豁,在80年代初诗论的论述逻辑中位于重要的中介位置。最终,将这一形式感背后的创作主体放在福建地方社会中予以观照,探寻其历史纵深。地方社会培养了谢冕重情感、多元开放、强力整合式的情感结构,帮助其安放复杂思想资源与经验,形成一种带有亚热带地域特色的富有感官性的形式追求。
关 键 词
谢冕 感官性 形式感 地方社会
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其《忧郁的热带》中对日落场景进行了长达5页的描写。关于为何要在人类学巨著中放入这样的文学描写,列维-斯特劳斯的解释是:“如果我能找到一种语言来重现那些现象,那些如此不稳定又如此难以描述的现象的话,如果我有能力向别人说明一个永远不会以同样方式再出现的独特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和次序的话,然后——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能够一口气发现我本行的最深刻的秘密:不论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会遇到如何奇怪特异的经验,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还是可以向每一个人说个明明白白。”[1]从列维-斯特劳斯所使用的“形式”“透明”“网络”等词语所暗示的,他所描写的“日落”就是一种由天体、海面、地平线、光线、气流、雾霭及其观看者的相对运动所构成的“结构”。也就是说,结构主义大师在表述一个“结构”的时候,必须借助极为富有技巧的文学语言的描绘,表述对象的复杂性,对语言形式提出了内在的要求。
由此可见,不只对文学家,即使对理论家而言,文学形式也是必要的。它意味着对思想的更深刻的组织,对感官的细腻体察,以及对真相的更整全的传达。如何让语词抵达对象,是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将语言分为日常语言、逻辑语言和诗性语言。他认为,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都依赖存在物,语言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反映的是事物不变的本质。相反,只有诗性的语言才是纯粹的语言,它会摆脱存在物的概念的束缚,反映存在本身:“如若我们一定要在所说之话中寻求语言之说,我最好是寻找一种纯粹所说,而不是无所选择地去摄取那种随意地被说出的东西。在纯粹所说中,所说之话独有的说话之完成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纯粹所说乃是诗歌。”[2]诗歌语言显现存在的方式是暗示性的,故而能够胜任揭示存在之“真理”的任务。诗使得“此在”拥有了与世界进行对话的可能,从而使得被经验和“框架”束缚着的世界得以敞亮。即,唯有特定的语词以及修辞,方可避开日常语言、逻辑语言的局限,抵达真理。
文学形式对谢冕也具有同样的构成性作用。文学形式是用来捕捉“具体”和“经验”的,是用来避免陷入“简单”的必要的“复杂”,也构成他学术研究的原始方法和基本感觉。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解码—编码方式,从另一角度去包抄真理的后路。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考察谢冕创作中的文学形式,并结合作家的主体结构对其形式追求、形式自觉进行全面的把握。贯通性地理解其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文学理论中的形式要素,对理解谢冕的重要诗学观念,尤其是他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实践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一 感官的发现:从《昨夜闲潭梦落花》的形式感说起
翻开谢冕以故乡、故人为主题的散文集《昨夜闲潭梦落花》,感官性是这批文章的一大特点。
在《三汊浦祭》,谢冕追忆童年所沉浸的一处秘密乐园。敏锐的读者首先观察到视觉性的运用。对三汊浦的正面描绘,分成三个自然段。第一、第二个自然段明朗一些。但总以隔着雾气和波光的反射来写三汊浦,这暗示了三汊浦无法以理性的视觉来直视,而必须经由想象力的中介方可显形。第三个自然段色调转为神秘。这里有明与暗,有深与浅的颜色,有蓝、绿,也有灰和黑。作者笔锋一转,这里如同深潭,水从外面流进,在此地汇聚,映衬着波光云影,“因为少阳光,那清澈的水有点发暗,闪着幽幽的光,似黑,又似蓝”[3]。光线调暗,使得文本具备了音乐性,仿佛是第一乐章的主歌,转到第二乐章的副歌,变得低回、忧伤。这呼应了三汊浦在现实中最终消失的结尾,暗示着它会变成黑漆漆的小河沟。从风景描写的明暗变化,为空间的消失埋下伏笔,体现极高的笔力与匠心。
视觉之外的感官使用尤其值得注意。这一空间,树木蔽天,玉兰花开。高大的芒果和柚子,枝叶芬芳。珠兰、含笑、茉莉,向着远处的橄榄和柑橘,近处的竹子和芭蕉,把田园铺成一片锦绣。亚热带的阳光洒成花雨。这里整天都飘着雾,连花香、阳光、月色,都带着浓浓的水汽。空气湿滑,如同女人的肌肤。
视觉性是主体对客体的有距离的观看,不管是凝视或瞥视,都意味着主客分立。而听觉、触觉和嗅觉、味觉,则是主体被客体所穿越、所浸没的。福州的郁热天气下,充满了柚子、芒果、橄榄、柑橘等水果枝叶的香气,以及湿度饱和后才可能感受到的润润且滑滑的空气触感。这一空间永远笼罩着一层凉凉的雾气,是带花香的雾气的空间。在这段回忆里,经验的呈现形态不以视觉性来作全部回收和压缩,而是保留了五感全开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
当作家进入回忆状态的时候,主体放低理性的防备,寥廓的声音缠绕于文本内。在散文《消失的故乡》,是水牛的反刍,在描写着漫长中午的寂静。教堂里,传出圣洁的音乐。站在高处,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的轮渡起航的汽笛声。据研究,听觉蕴含着被动与接受的含义,而视觉则无此意。在婴儿能用视觉区分细微差别前,听觉就已可以分辨愉快、舒畅和令人讨厌的音响。[4]因为听觉能够提供比视觉更多的世界信息,声音的消失会带来世界的压缩,对比失聪者的焦虑、孤寂与离群索居感,谢冕的文字通过声音性以传达出某种对世界的享有与通达。
除了听觉的适配外,谢冕同样擅长嗅觉的介入。在《香香的端午》,街巷间飘出菖蒲、艾蒿的香味,后来是雄黄酒,是年轻女性的香囊,再后来就是竹叶包裹的粽子,是粽叶的清香。在《木兰溪缓缓流过兴化平原》,溪岸遍布荔枝树和龙眼树,早春时节飘浮迷人的柚花香气。气味本身能唤起我们对过往事件与场景的丰富情感与生动记忆。大脑皮层储存了大量的记忆,而它是由原来专管嗅觉的机体进化而来的。在作家配置历史场景的时候,气味充当触媒,连接当下与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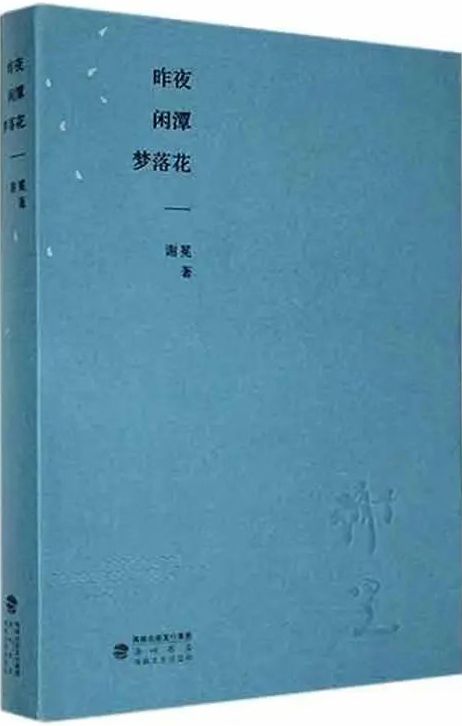
谢冕:《昨夜闲潭梦落花》
作家的回忆中倒也不乏苦难的描述。散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写道,童年是“借贷、典当、捡稻穗、被迫做童工,还有空袭警报,以及为了逃难,也因为学费,而陷于不知终点的不宁与惊恐之中”,是“动荡,忧患,还有望不到头的饥饿”。[5]谢冕1949年在福州参军,做过文艺工作,扫盲的文化教员,做过武装的土改队员,临时做过军报记者。《人生只有一个“六十年”》《重返南日岛》更记述了参加革命工作到镇守南日岛的种种艰险。只是这些苦难被作家小心翼翼地用叙述的方式予以折叠,往往做到蜻蜓点水、让人意会而已。
总体看来,关于故乡福建的叙述基调终究是温暖、醉人的。《我的梦幻年代》是三一学校里的教堂钟楼、安详的钟声、圣洁的风琴乐音,是欧陆风情的南台岛上,三角梅攀延的院落里钢琴叮咚声。《无尽的感激》是余先生用福州话吟哦的古音。《追忆少年时光》有李兆雄先生率领学生远足时的笑声、歌声。《旗袍的记忆》里,闽江两岸遍布柑橘园和橄榄林,种着茉莉和珠兰,三角梅被旗袍女子的脚步声惊醒。《我的庭院我的房》里,亚热带的阳光爬过女墙,洒下满院白玉兰的芬芳;夜晚的月色透过榕树的枝叶,满天星星碰撞得叮叮当当。《除夕的太平宴》的红糟鲢鱼、糖醋排骨、槟榔芋烧番鸭、太平宴,《最是柳梢月圆时》的肉馅汤圆,尽显闽都的丰饶。对比现代文学、现代史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写,这种差异感就更为明显。这些温暖的光线、气味、声音、味道与触感,沁出了常规的大历史叙事,甚至作家自己的理解,成为叙述之外的增补物,也引发我们的探索兴趣。
二 感官的绽放:以《以诗为梦》的70年代诗歌创作为焦点

谢冕:《以诗为梦》
感官性在谢冕这里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吗?我们抛出这样的问题。
在散文集《昨夜闲潭梦落花》的怀人文章中,谢冕着墨最多的是蔡其矫。“他是一条地下河,地面上芳草萋萋,花枝摇曳,而地层下却是惊心动魄的激流”(《最公正的是时间》[6]),指出两人之间的精神呼应。尽管谢冕与蔡其矫相差十四岁,实际联系并不多,在《蔡其矫全集》中仅收两封蔡其矫给谢冕的通信,但谢冕自己说:“和蔡其矫在一起,人们会忘记自己的知识和年龄的差别……对于我来说,他是老师,却更是朋友。”[7]谢冕在与邵燕君的访谈中提到自己“好吃、好玩、好看”的人生态度,不禁让人想起蔡其矫自诩的三好“美女、美文、美食”。相识六十年的老友洪子诚道破个中秘密,“谢冕热情,喜结交朋友,对人友善。他崇敬、追慕‘至美’,美文、美食、美景、美女、人道的社会、富道德感的完整的人……他赋予这些事物以浪漫诗意。在这个方面,他与福建老乡的浪漫诗人蔡其矫同气相求”。[8]
对读早年诗论,谢冕就已留意蔡其矫的感官之秘,或者说,就从感官性的角度去理解蔡其矫。有心人会留意,蔡其矫带有感官解放色彩的诗作所在多有,诸如《翠海,九寨沟》《断章三则》《雷鸣潮》《竹林》《客家妹子》等等。“他写《榕树林》,在那里,晨、午、昏分别有银色、绿色和金色不同色彩的梦,他对光和色的感觉是多么敏锐”,“《波隆贝斯库圆舞曲》是不具形的乐曲,《风景画》是不具声的绘画,我们把这两首诗对照起来读就会觉得:无论是从听觉中捕捉画面,还是从画面中捕捉音响和律动,蔡其矫都能打通特定艺术的墙壁。对有才能的诗人来说,五官感觉是没有太大界限的”。[9]这可以视为谢冕借评蔡诗来浇自己的块垒。
不同的感官配置方式,隐含不同的文化态度。西方主流现代性是以视觉性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比如摩天大楼就最为典型。爱斯基摩人的感官经验则是对视觉—现代性的乖离。由于冬季大地白茫茫一片,无法依靠视觉地标作为参照点,唯有通过脚下冰层的裂缝、雪地的触感、带咸味的风来判断方向,因而他们生活在一个由听觉和嗅觉组成的世界。[10]

诗人蔡其矫
翻开收录谢冕近70首诗作和近10万字诗评、诗学随笔的《以诗为梦》。最动人的是“西双版纳/瑞丽组诗”(写于1973年10月到1974年9月)。其间,感官意象的大量使用,使得这批诗歌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流诗歌之间产生疏离。这些文本中,革命秩序被放到地平线外,位于舞台中央的是边陲之地的感官之国。
《勐仑道旁的蝶舞》:“山道、水滨、竹楼、丛林/槟榔树底筒裙摇曳/罗梭江畔花伞如云/空气里饱含多少花香、果香/多少鸟鸣长唱出了原始森林的悲清。”[11]
《车停勐远》:“临水晾台上扑打着鸽翅/浮动起香茅草浓郁的香气/这么清,这么远,这么迷人/丝丝缕缕都在晨光中抖动/哦,芬香的寨子,芬香的树丛/哦,芬香的空气,芬香的水云。”[12]
对作家来说,西双版纳—瑞丽一行类似本雅明意义上的“震惊”体验。诗人在这批作品中基本采纳了一种神游姿态。热带区域密布的音响与气息,久违的温度与浓荫,怪奇的植被与昆虫,未被现代性彻底击穿和重塑的少数民族地方社会风情,让他的主体应接不暇。
再看《没有篱笆的梦》:“无处不在的月色/无处不在的虫鸣/无处不在的花香/无处不在的露珠急雨般往下倾/我的竹楼/有着美丽的造型/尽管它没有窗子/一切的色泽、音响和气息/都无阻地直行。”[13]
在组诗当中,“一切的色泽、音响和气息/都无阻地直行”成为最大特色。在《夜景》中,我们听见蛙鼓虫鸣,而静谧的背景下,亿万双透明的翼翅颤动,密林里雨水敲打如伞的阔叶。在《爱尼山的夜晚》,是如浪的雨声,喃哚河冲击河心的石块声,满山的流萤与花香。在《夜宿保山,漫步街头,即景》,是牛车队的铜铃声,豌豆凉粉摊子旁的夜来香气味。在《夜的瑞丽》,是十三只壁虎的目光、缅桂的芳香、无数的蛙唱、暴雨般的夜露。在《芒市风情》,是傍晚的蛙唱伴着雨后的地摊,孔雀尾翎、傣家少男少女、茉莉花清香与天边的虫鸣。在《边塞短诗》,则是漫道菠萝的芳香与鸡鸣。
《绿色的曼听》中感官意象有了历史纵深。主体身处西双版纳的曼听公园内,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就是绿色的雾、云、阔叶和光影,绿色不断重复堆叠。绝对的静谧,却有一种向远方的伸展感和开阔感,“当你走在曼听的小径/可以想象海底澄碧的世界/春江流水的融融”[14]。在这一无声空间中,视觉性得到孤立凸显:周围层层叠叠的绿色,形成绿色的旋风。色彩之间形成挤压和层次,绿色激起了浪涛的汹涌。“西双版纳没有风/四时都那么娴静/而当你置身在曼听的密林/立即可以感受到/绿色卷起了旋风/绿色激起了波涛的汹涌/它们拥挤着、压迫着叶、椰子、槟榔、油棕……/摔开绿色的浪纹/炸开电闪雷鸣/向着高空升腾。”[15]与革命话语中有待改造的自然形象不同,这里的自然作为一种难以被消化和超克的异在,反客为主。自然是主体得以舒展和休憩的港湾,这里没有浪涛,也没有暴风,也没有电闪雷鸣,鸟儿仿佛在幽谷歌唱,舞步盈盈的队伍,也没有任何足音。视线放远到的村寨边澜沧江水,没有任何水声,确实“鼓动着伟大的寂静”。寂静之下,是生命的“鼓动”。我们不再把这种自然性视为消极被动或死水一潭,也不是轻易可以改造的客体,而具有了与革命现代性对峙的主体位置。诗作最后的结尾意味深长,“然而,然而/也有突来的怪物打破梦境/一台运粮的拖拉机在晒场边停/打破这绿色世界的和平/马达带来真正的骚动/那红色的机身,点缀着万绿丛中的一点鲜红”[16]。在马达的轰鸣声中,革命现代性对边陲的改造正在进行,这种外来的力量被诗人潜意识视为打破梦境的“突来的怪物”。参照这首诗的写作时间——1973年12月19日,我们能体会其中的不易与意义。
回溯谢冕之前的创作,带有感官性形象的创作此前已有出现。以十二卷本的《谢冕编年文集》所收篇目看,散文至少有1940年代的《蝉声》《秋天的黄昏》《夜幕,笼罩在街上——一个算命先生的手记》,小说有1940年代的《潮》,诗作至少有1940年代的《久旱的村落》《童年的一组断片》《薄暮的悲哀》《夜市》《“迎年”》《五月小唱》《晨》《夜》,1950年代的《龙眼树下设课堂》《查铺》《唐诗》《厦门组诗》,1960年代的《十三陵组诗》《山里的风景》《告别》《迎春》《我怀念连队》,等等。这种释放感官的写作,在回忆故乡和书写南国风情的题材时较为显著,在1970年代的“西双版纳—瑞丽组诗”变得集中和显豁,并在之后的文论诗评中成为他重要的经验。
三 感官作为诗学中枢:以《北京书简》等诗论为例

谢冕:《北京书简》
感官性并不是“创作”时的无意识行为,而作为构成性条件成为谢冕文学实践的基底。我们能从谢冕1980年代早期诗论中发现感官性。例如1980年为复刊的《海燕》所写的文章里,谢冕认为创新从感官开始:“‘这里有北国雪花的凉意,密林松针的清香’,仅仅一句,我们眼前便出现了一条有特色的典型的北方的河流。的确,松花江的美丽景色是和冬天、冰雪联系在一起的,松花江常常为纷飞的雪花所装扮。把松花江水写成具有雪花的凉意,这种诉诸触觉的描写,就把它和不是北方的江河区别开来;把松花江水写成具有松针的清香,这种诉诸嗅觉的描写,就把松花江和不是发源于长白山茂密林丛的江河区别开来。是这凉意和清香带给我以真正的喜悦的。”[17]
1981年出版的《北京书简》可见系统论述。这是书信体的短论集,收录一系列关于生活、抒情、形象、想象、立意、构思、诗意、创新、精练、风格、韵律等命题的阐述。借助书信文体虚构出一个地处云南、正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文学青年,以向对方倾诉的方式展开论述。我们得以读出西双版纳经验的重要位置。
其首篇《诗与人民》,谢冕借助“人民性”为下文的展开(生活、抒情、形象等概念)获取合法性。第二篇《生活(一)》以去掉阶级论色彩的“生活”概念对抗1960年代的“主题先行”“三突出”,强调摆脱“陈词滥调”,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在这篇文章里,首次出现的“对方寄来的”书写西双版纳的诗歌,并在后面的篇幅中不断以“西双版纳”的风光来“起兴”,引发相应理论话题。
“激情”是“生活”之后第一个核心概念,奠定了谢冕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对文学青年的谆谆教诲中,《抒情》一篇把激情视为诗歌核心素质。“抒写激情,是诗的使命。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诗人,都在抒写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激情中,完成其作为诗人的使命”,“没有激情,就没有诗”,“抒写激情不是干喊。不借助形象的喊,无论喊声多大,也没有力量。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不附象,亦难感人”。[18]谢冕别具用心地引用郭沫若创作《凤凰涅槃》的诞生,描绘这种激奋状态是“神经性的发作”,又引恩格斯《反杜林论》,为激情正名。显然是呼应李泽厚在1966年被郑季翘批判的情感说,并对其进行自己的改造。“激情”概念的出现,是为感官性及其背后的身体性铺路。
正是在“激情”的框架下,引入“形象”的话题——“抒情诗要寓激情于形象”。显然,谢冕受到文艺理论界形象思维讨论的影响。“形象思维”是一个现、当代文论史上重要的概念。[19]《诗刊》1978年复刊之际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文革”后,文艺理论界第一次反拨由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启。复旦大学文艺理论教研组的《形象思维问题参考资料》于1978年5月出版,一时间从南到北各大高校纷纷编写资料集,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一部近50万字的巨著《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参与翻译)影响最大。同期,朱光潜、李泽厚、蔡仪等重要美学家活跃起来,在各类场合发表大量关于“形象思维”的理论文章。以李泽厚的《形象思维再续谈》[20]为分水岭,这场讨论逐渐分化为文艺心理学、原始思维、古代文论的分别研究,并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文论的强势进入逐渐弱化。[21]
虽然受到当时讨论的影响,但谢冕对“形象”已有自己的发明。《形象(一)》认为,既然诗歌来源于生活,而生活就是活生生的图像。“因此这种思维的全部内容是,从具体到具体,而不是从抽象到抽象(恐怕也不是具体—抽象—具体);从形象到形象,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这种形象思维本身,就包含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发展的过程。”[22]从生活形象再到艺术形象,这个转换过程何以“不是具体—抽象—具体”?这种形象思维既然终点是形象,又为何“包含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发展的过程”?形象思维本身,就是全部(本身就包含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感兴到理性的认识发展,而无须所谓“理性思维”的他律),借此暗示审美的自律性——这或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但重要的是,这里的形象还必须对接到感官性。
《形象(二)》强调诗歌形象与叙事类作品的不同,要以最省俭的语言构成形象,要有鼓动效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感官的口号:“因而,诗的形象要克服语言材料缺乏音乐美术那样直接感知的弱点。为此,许多诗人致力于使诗的形象具有听觉、视觉,乃至触觉、嗅觉等效果。”[23]如无感官,则无法取得诗歌的教育、鼓动效果。
调度感官是引发激情的前提。在解读杜甫和李贺诗作后,谢冕重点细读李瑛的《雨》:“他把单调的雨,写得丰富多彩,精到地描绘出雨中的山、山中的雨。山雨下来了:夹带着野草的清香,这是作用于嗅觉的;到处新绿闪光,是作用于视觉的;山雨下来得猛,顿时雨水汇成了小溪,发出了震耳的喧腾,这是作用于听觉的。雨后山中特有的景象,一霎时从短短的诗行中喷吐而出。他借形象让你多方面地、具体地、直接地感受到客观世界的变化。就雨写雨,写不出雨的声势和情调,借野草的清香,新绿的发光,小溪的喧闹写雨,再现了可感的声音,色泽和气味,因而这山中的雨便是生动鲜明如真的被我们看到的一样。” [24]调度创作主体和读者的感官,让“世界”得以充分显现,使诗人与读者形成感官互通,唤起彼此的生命激情。
诗歌的形象在于感官的立体,还在于可以通过想象力的介入,“化无形为真实可感”。他引用惠特曼《从巴门诺克开始》和贺敬之《放声歌唱》,强调想象力可以将不同的形象连缀起来。这里是呼应前文对诗人主体性的强调。诗人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总是从形象的感受入手,而后对生活提供的形象进行典型化(尤其是个性化)的再创造。诗歌的典型化,就是主体对看似无关形象的跳跃式“焊接”。在《想象》一篇里,谢冕再次提起“对方”的西双版纳经验。还是从“西双版纳—瑞丽组诗”中选择出来的意象:“写到这里,想起了你寄自西双版纳的诗,西双版纳实在是让人幻想的地方。黎明之城飘浮着槟榔叶子香气的黄昏,罗梭江畔虫鸣似海的月夜,橄榄坝的椰树和竹楼在亚热带的艳阳下凝思,国境线上勐满街头赞哈抒情的吟哦,还有,那无所不在的西双版纳的绿,绿的天地,绿的云彩和雾气……”[25]这些活泼泼的感官体验,正是激发想象力的契机。
上文索引,目的在于从谢冕的《北京书简》中梳理出一条“生活—激情—形象—感官—想象力”的论述逻辑[26]。感官处于中枢位置,是诗人主体提取生活、产生激情的入口,是塑造形象的抓手,也是诗人调动想象力的出发点。带有感官性的诗写,方能以最俭省的语言构造形象,发挥最大的鼓动效能,承载和激发最大限度的激情。
多年以后,洪子诚评价谢冕:“最突出的是他的生活热情,审美感悟的直接、敏锐。那种富历史感的宏观视野,和在细节把握基础上充溢诗意的概括力。”[27]“在细节把握基础上充溢诗意的概括力”,实为一针见血的评价——对诗的概括本身必须忠实和保留细节,概括的本身必须充盈着诗意。作为以诗论见长的学者,谢冕在理论文章中时隐时现的感受力,在创作中释放为了感官性。或者说,这些伸张的感官性使他在面对诗歌文本的时候具备了异乎寻常的感受力,使其理论概括力具备了诗意和对细节的含纳。
四 感官的溯源:主体与地方社会
伴随从散文、诗歌到诗论的跋涉,我们感受到谢冕创作的密码——一种以感官性为特征与动力的文学感知与生成方式。
谢冕的感官性,融通着传统世界的感兴诗学。兴的起点为诗学主体被外物所动,受外物所感。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作注因物而感,在这里呈现为亚热带地区的感官体验。谢冕出生于福州,战乱中迁居南台岛(现属福州仓山区)。闽江在南台岛首尾分而又合,斜贯中部。此地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热冬温,四季分明。作者追忆故乡往事,难免沉浸在亚热带水乡的阳光、月色、空气、水、雾、花雨之中。空气中尽是珠兰、含笑、茉莉、橄榄、柑橘、芒果、柚子的或浓或淡的香气。青年时期驻扎的南日岛,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东南部兴化湾,那里曾经遍布剑麻、木麻黄和台湾相思。1970年代所居的西双版纳—瑞丽,蛙鸣虫唱、瓜果飘香,似乎唤起作者在亚热带故乡的体验方式,是流落他乡,也是精神回乡。这种感官性的书写与亚热带地域的地理—心理空间密不可分。下面,我们对这种现代感兴形态背后的主体再做一番系统考察。

段义孚:《恋地情结》
首先,感官性的背后,是一种有情的主体状态。
兴者,情也。感物抒情,感官性的背后是一种“有情”的观照世界的方式。由地方风物而感兴,其情多温暖。谢冕怀念亲友师长的文章为数不少。散文集《昨夜闲潭梦落花》首篇却是《兄弟久别重逢》——严格说来,只是一封家信。将这一重要位置,留给文体上的异类,可见家族亲情在谢冕心中的位置。再看怀念母亲的《昨夜闲潭梦落花》《母亲的发饰》、感恩启蒙恩师的《无尽的感激》《追忆少年时光》,“爱”的涌流随处可见。这不只是童年记忆的滤镜效果。感兴与抒情的融通,唤起的是位于更底层的“乡族社会”的情感结构。由此,我们方可理解谢冕对“情”的重视。如今看来,无论山水有情,还是亲情友情,抑或文学形式的抒情性,这些情与调,都带着特殊的“乡族社会”印记。
“有情”主体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撑。傅衣凌、郑振满曾经研究过明清到近代福建的乡族社会特点。在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下,宋明理学地方化为福建构造了相对稳固的知识阶级和伦理秩序。由于赋役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逐渐放弃了对里甲户籍、水利设施及各种社会文化事业的管理权,从而导致了基层社会的全面自治化,士绅阶级由此崛起。清中叶前后,书院之类的地方教育机构及各种赈恤事业的兴起,地方社会的自主性进一步提升。中国近代乡土社会经历了崩坏的过程,但是福建乡族—士绅社会在近代虽然遭遇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但仍然通过一系列转型和协商,保存了一定活力。[28]例如在福州三坊七巷的近代名人、清末到民国海军占多数的福建籍官兵身上,就可见乡族社会的网络联结。
家族成为基层民间重要的权力节点,也是基层个体所居间生存的真实环境与中介力量。“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具有十分全面的社会功能。在政治方面,家族组织与里甲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逐渐演变为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治安、司法、产籍管理、赋役征派等主要行政职能。在经济方面,家族组织不仅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而且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社会救济等再生产领域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文化方面,家族组织延师设教,培养科举人才,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组织各种民俗文艺活动,是推行道德教化和维护传统价值观念的主体力量。”[29]谢冕自陈拜访冰心老人时,冰心亲口确认彼此同属谢姓“宝树堂”这一“房”,而称谢冕为“同宗”。如渠敬东提示的,个人不是社会世界构造的原点,而是关系点,是联络点,依照相对应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程度的关联,逐次外推。[30]
单就谢冕这一家而言,家境清贫,适逢战乱,父亲失业,苦无生计,家庭却并未涣散,甚至不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依靠家庭内部的分工与互助,使谢冕有了求学的机会。谢家二哥毕业于福州高等中学,后来在台湾以报业谋生,虽孤悬海外,却以有限薪水为弟妹先后置业、在福州购得多座华屋,此后依然心念厚葬祖母。谢冕家庭的独特情感结构放在社会形态中方可理解。“家”及其背后的关系网络,对于谢冕有了支撑性的重要意涵。

谢冕中学就读的福州三一学院(现为福州外国语学校)
其次,感官性的背后,是一种舒展的主体状态。
谢冕自述深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冰心与巴金。有趣的是,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文学教育,也是从感性的角度。“沈先生是把各种人事、风景,自然界的各种颜色、声音、气味加于他的印象、感觉都算是对自己的教育的。……对于颜色、声音、气味的敏感,是一个画家,一个诗人必需具备的条件。这种敏感是要从小培养的。沈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就说过:要训练自己的感觉。学生之中有人学会一点感觉,从沈先生的谈吐里,从他的书里。沈先生说他从小就爱到处看,到处听,还到处嗅闻。‘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一本《从文自传》就是一些声音、颜色、气味的记录”[31]。感官性是直接的,是身体与世界的碰撞。当然不可简单比附沈从文、汪曾祺,但有一处明显的相似。尽管背景、年代、观念迥然不同,但这种感官性的释放,与一种作家不经由政治概念为中介、以自我直接面对世界并创造性理解现实的强大主体状态相关。
这种舒张感,让人想起海洋文化的开放性。福建多山少土,虽硗确之地,也耕褥殆尽。由于濒海,从汉晋时代发展起来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历唐、五代,至宋元臻于极盛。与此同时,福建人下南洋讨生活,足迹遍布东南亚,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产生影响,侨民回返亦带回东南亚文化的多元性。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福建占据其二,西方现代性由此进入。柯文所谓的“条约港知识分子”,以王韬、蒋敦复、管嗣复、李善兰、冯桂芬和郑观应为最著名者。通商口岸由于西方列强特权的存在而有别于其他城市,它们游离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重心之外,成为不同文化交汇碰撞的节点。
如谢冕散文《感谢帖》所叙:“我自小生活在福州的南台岛,那里更是西方文明的集结地,教堂、赛马场、咖啡厅、西餐馆、舞厅,以及更多的医院和教会学校,西方有的,我们也都有。我中学上的是英国人主办的福州三一学院——最近在牛津和爱丁堡我都找到了三一的姐妹学校,陈景润也在三一待过,他高中是在英华中学,美国人办的学校。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域外另一种或多种文明的广泛的熏陶,它们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同样深刻影响了我们并成为我们内心积淀的一部分。”[32]这一文化历史孕育出了开放包容、吸纳多元的主体结构。这种主体状态与1980年写出《在新的崛起面前》的谢冕、在《北京书简》中建构“激情诗学”的谢冕,可谓一脉相承。
这一主体结构也吸纳了一定的宗教因子。无独有偶,几位福建作家(冰心、林语堂和许地山)均一定程度受到基督教精神感染。20世纪初,福建基督教会信徒人数在全国排第三名,如以每万人的受洗人数看则遥遥领先。教会教育办学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仅次于官办学校,对福建近代教育的现代化历程产生深刻的影响。福建省的初高级小学生总数为94000余人,其中政府设立的初高级小学的学生数为64000余人,占小学生总数的67%左右;而教会创办的初高级小学校学生数31000人左右,竟占全省小学学生数的32%强。[33]《金翅》也谈到,在科举废除后,教会教育为福建家庭提供了个体进入北平乃至出国的重要通道。谢冕多次在散文中深情回忆李兆雄牧师,培养了陈景润、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三一学校。让人浮想联翩的是,在这样开放的主体结构中,这些强调献身、悲悯、对他者的善意的因子,如何经由后来历史的曲折,保存于这位理论家的主体结构之内?
最后,感官性的背后,是主体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创伤性、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强大消化能力。
异质经验之间存在着紧张与冲突,开放的主体还需要强大的消化力为支撑。福建地方社会的特点是能够将不同文化体系予以调和、安置,对此,谢冕深有所感:“好像是神就敬,是佛就拜,不论有形还是无形。……他们都是神仙,都是法力无边,护国游民,不论是佛是道,我们一样膜拜。”“仁爱的是观音,快乐的是弥勒,善良的是土地爷,仗着长剑的是威严的吕洞宾,他们都是家庭成员。家里有了他们,困难时有慰藉,危急时有援助,家居有平安,平时有欢乐。”(谢冕《闽都家庭的那些守护神》)[34]
对待西方外来现代性的时候,地方社会的整合力体现得更加明显。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宗教再入中国,加之18世纪以来的“名词与礼仪之争”,教会往往抛弃利玛窦法则,最初长达一二十年无人入教,进而急功近利,采用强硬姿态,教案频发。对比德国圣言会在山东激起民变乃至义和团运动[35],基督教20世纪初在福建地方社会的融合程度却要高得多。以林语堂为例,他父亲不仅是牧师,“而且是村民争执中的排难解纷者,民刑讼事中的律师,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务之帮闲的人”[36]。可见外来文化要在福建本土立足,唯有内嵌于乡土社会功能结构中。容纳异质因素,合理安置,化为己用,是地方社会文化整合力的体现。
毛尖对谢冕美食散文《觅食记》的评价是:“他鲸吞了一个世纪的油盐酱醋,转身馈赠出万家鼎鼐的烟火世界。”[37]20世纪的中国历史,泥沙俱下,苦辣酸甜,是怎样的精神肠胃在帮助谢冕消化一切?《时晴时雨是清明》的场景告诉了我们答案:“早春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那经过清扫显得整洁的墓地,太阳是明亮的,明亮得晃眼。人们尽情地在这里享受着眼前的欢乐,而把死亡的阴影和失去亲人的伤怀消融在现世的享受之中。”[38]欢快的仪式喷涌着消化痛苦的生命意志,体现地方文化面对异在与矛盾时的超卓消化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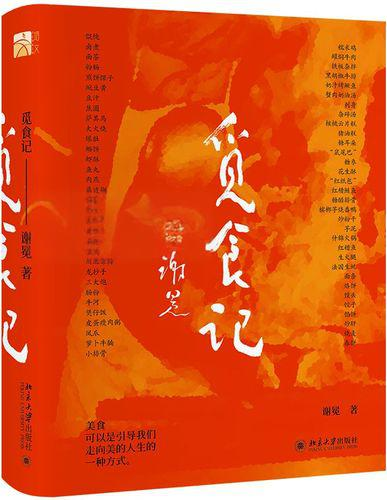
谢冕:《觅食记》
以上便是本文对这种以“感官性”为特征的形式追求所做的进一步溯源了。对背后的主体做一番知人论世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它与地处亚热带的福建地方社会的一些关联。笔力所限,不及其余,如何理解对谢冕同样影响巨大的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如何理解他在70年代的思想变化并最终整体把握80年代初“崛起论”背后的思想脉络,是否能以谢冕为样本进入30代学人和“闽派批评家”的精神世界等等问题,只能留待未来发掘了。
总之,我们在谢冕的散文、诗歌与诗论的对读当中,看到了感官性的凸显。植根于地方社会的主体结构,如同一块多孔的海绵,安置着那些看来不一定能彼此相容的新的知识与信仰,比如“五四”新文学的阅读、教会学校的教育、三四十年代的离乱遭际、参与革命工作的经验、50—70年代的北大生活、政治运动的动荡、西双版纳—瑞丽的体验、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艺、苏俄文学、西方文学的资源。这一切共同注入他的笔端,形成一种富有亚热带地域特色的文学形式感。
陈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073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4期)
注 释
[1]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2]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7页。
[3]谢冕:《昨夜闲潭梦落花》,海峡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54页。
[4]参见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页。
[5]谢冕:《昨夜闲潭梦落花》,第96页。
[6]谢冕:《昨夜闲潭梦落花》,第196页。
[7]陶然:《蔡其矫诗歌作品评论选》,香港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8]洪子诚:《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9]谢冕:《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0]参见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第14页。
[11][12][13]谢冕:《以诗为梦》,漓江出版社2024年版,第79、83~84、88页。
[14][15][16]谢冕:《以诗为梦》,第73、74、74~75页。
[17]谢冕:《诗人对生活的感受——和〈海燕〉的作者谈诗》,载《谢冕编年全集 第三卷(1979—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18]谢冕:《抒情》,载《谢冕编年文集 第三卷(1979—1981)》,573页。
[19]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象思维”这一别林斯基首创的概念,随着苏俄文论传入中国。何丹仁、胡秋原、欧阳山、赵景深、周立波进行译介,胡风予以推动,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以“形象的直觉”为核心概念,蔡仪《新艺术论》进行系统阐释。五六十年代,与美学大讨论相结合,霍松林、巴人、陈涌、温德富、周勃、蒋孔阳、叶以群、毛星、李泽厚、吴调公、狄其骆、萧殷、周扬、王方名、李树谦、虹夷、郑季翘等先后加入讨论。1959年李泽厚的《试论形象思维》作为50年代讨论的重要理论成果遭到了批判(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红旗》1966年第5期),郑季翘的批判文章配合当时种种机缘,为后来“文革”文学的“主题先行”“三突出”“三结合”开了绿灯。参见张首映《十七年文艺学格局及其在新近十年转换鸟瞰》,《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
[20]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载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57~558页。
[21]“形象思维”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参见高建平《“形象思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22]谢冕:《形象(一)》,载《谢冕编年文集 第三卷 1979—1981》,第585页。
[23]谢冕:《形象(二)》,载《谢冕编年文集 第三卷 1979—1981》,第595页。
[24]谢冕:《形象(二)》,载《谢冕编年文集 第三卷 1979—1981》,第595~596页。
[25]谢冕:《想象》,载《谢冕编年文集 第三卷 1979—1981》,第602页。
[26]本文的概括仅就《北京书简》中谢冕论述的逻辑而言。另有学者结合谢冕80年代的诗学论著,提出谢冕创造了“激情—形象—再现”的诗学评价体系和“激情—形象—寄托”的诗学发生结构。参见王宇林《诗学结构与精神谱系——20世纪80年代前期谢冕诗评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27]洪子诚:《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28]对照一下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读者不难发现所谓清末“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的出现、因国家对基层资源的单向度汲取导致的基层的贫困化与状态的掉落,更多是基于华北地区经验的认识。有心者不妨再比照林耀华人类学著作的《金翅》。《金翅》聚焦辛亥革命到1930年代日本侵华时期中国福建闽江流域的古田黄村,提供了更多历史信息。福建地方的家族通过农商协作、耕读传家以保持向上趋势和凝聚力,一定程度制衡了“赢利型经纪”及背后的国家力量,并应对近代社会的剧烈转型。
[29]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30]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31]《汪曾祺全集9 谈艺卷》,季红真主编,赵坤本卷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0、143页。
[32]谢冕:《昨夜闲潭梦落花》,第234页。
[33]《中华归主》(下册),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2~1083页,
[34][38]谢冕:《昨夜闲潭梦落花》,第142、145,132~133页。
[35]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6]《林语堂自传》,载《林语堂文选》(下),张明高、范桥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1990年版,第429页。
[37]毛尖:《保护满嘴流油的生活:谢冕和散文》,《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2年11月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