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时代的王力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渊雅精深”体“小品散文”作者中,王了一引经据典,最为淹博,其代表作《龙虫并雕斋琐语》,以《恶之花》式的“奇异”“丑恶”中的美感,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微妙变换,融合了“民族性”的视角以及诙谐滑稽情趣,呈现一种丰厚的滋味,别具生机与活力的生活观、审美观,富于适应中国抗战现实的灵活姿态。其表达特征:一、悠然的玩味:博雅之知与审美之“恶”。二、智慧的互观:中外城乡的沟通法。三、直言与隐讽交融合一的“小品散文”观。
关 键 词
抗战 王了一 小品散文 《龙虫并雕斋琐语》
随着抗战的深入和扩展,昆明重庆文坛上“渊雅精深”体“小品散文”,在内化持久坚韧的抗战精神、多方面表达中国抗战生活之际,有节制地容纳了抗战前“幽默性灵小品文”所提倡的“趣味”“幽默”,强化了其对抗战时期严峻的日常生活“生趣”或“理趣”的呈现,其行文中多“运用‘典故’或引用其他文本之语词或思想”。[1]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多称之为“学者散文”或“知性散文”。而语言学家王力则成为这一时期小品散文家王了一,他的散文融合丰厚的文化、运用典雅的语言,成就非同一般,是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学者散文/知性散文”。[2]
一 悠然的玩味:博雅之知与审美之“恶”
王了一是与钱锺书、梁实秋齐名的战时“小品散文”三大家之一。他的小品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表现了别具特色的“小品散文”渊雅风貌。其多种“语像”与“观念”并非直陈,而是置入多重的“化装”,构成耐人玩味的意蕴,恰如他在《语言的化装》中所言,“写古体字,用古语,用洋语,自创新词新句等”,均为文学的化装,其功效乃在求新奇而避平凡。[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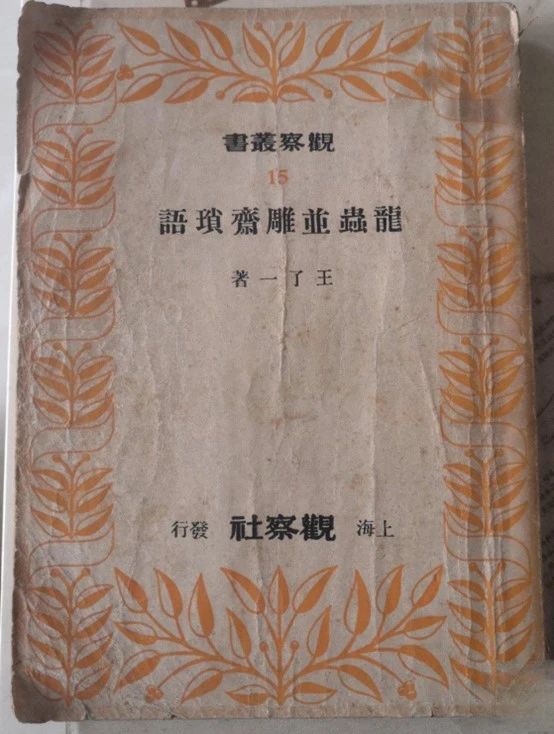
观察社本《龙虫并雕斋琐语》
《龙虫并雕斋琐语》最初两篇《姓名》和《书呆子》,分别刊登于1942年1月24日与2月14日的重庆《星期评论》。该书所收之文,令人能在百端愁苦之间,又有几欲喷饭的幽默诙谐之乐,一扫左翼文学严肃紧张的板滞;虽为平易之论,未为泛泛之谈,实有脱却士大夫掉文之积习,转为清新自然、举重若轻之貌。更值得注目的是作者在抗日的艰辛苦涩中,那种悲喜交集却平易近情的态度。一切的典故与引文,在作者的悠然玩味中,都臻化境。
在《书呆子》中,王了一咬文嚼字式地将书呆子分为四类,在“不治家人生产”的正统书呆子之外,还有“视财如命的”“不近女色的”“沙蒂主义的”三种别类书呆子:
书呆子在古代又称为“书淫”。读者如容许我望文生义的话,书淫该有两种可能的意义:一种解释是既淫于书,就不暇淫于色;另一种解释是既喜欢书,又不忘淫。世间这两种人都有。我知道有一位道学先生,在母丧期内不肯走进他的太太的屋子,三年如一日,不得已而向太太要东西的时候,也只站在门槛上,让太太把东西交出来。我又知道有两位(单我一人就知道有两位!)很用功念书的秀才,结了婚不肯和新娘子同房共榻,于是羞煞了新娘子,气煞了急于抱孙的老令公和老太君。两位老人家想尽了方法,让朋友占住书房咧,晚上骗儿子进了少奶奶的屋子就把房门锁上咧,这样那样的闹了一年半载。虽然结果是书呆子屈服了,并且拿弄璋之喜娱乐了双亲的晚景,然而这一股呆劲也就非常人所能及了。但是我又知道另一个模型的书呆子,他们非但好书如好色,而且好色如好书。不过,当他们好色的时候,那一股呆劲仍旧不让前面所说的一种人。我知道有一位手不释卷的先生为了拜访女朋友也居然释了卷,而且一聊天就是三个钟头。只可惜那一位小姐当着严冬,从有火炉的宿舍跑进冰窖般的会客室里来,身上没有穿大衣,牙齿仿着云板来恭听那些并不娓娓的谈片。关于后一种的书呆子,我本来有好多故事可述,但因本文的正义并不在此,所以从略。
视财如命的书呆子实际上不能算呆,至少一般看法是如此。我看见过一个书呆子,他积满了十元钞票便封了起来(自然是战前的十元),发誓不动用他,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向朋友告借,大家说他傻,然而后来他终于发了大财。由此看来,除了聊斋所描写的“书痴”一个类型之外,公认的书呆子恐怕只有喜欢读书而又不治家人生产的一类了。[4]
由于《龙虫并雕斋琐语》单行本删去了上引段落,因此“沙蒂主义”似乎是随意引述,又突然消失,其实放在句尾的位置,也是下一段的引子。这被删削的一段,充分表明了王了一乃至当时的所谓“知性散文”家们,并不避谈色情的话题。甚至可以说,谈及“色情”或“情欲”,在这种人生完满成熟阶段所产生的小品散文文体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抒解艰难困窘的抗战时期物质现实生活和定形的人生格局中的某些不安定情绪的一种手段。
在中国抗战时期“渊雅精深”体“小品散文”作者中,王了一引经据典,最为淹博。王了一的炫知性,且融合了波德莱尔式的对“恶”之审美的态度,在生活的细节中,充分发掘其趣味性,给人以知识展览般的展示。在述及“呆之贤者”和“呆之圣者”时,为真纯的书呆子赋予了一种神圣的色彩与刚健不屈的精神,对所谓“呆之贤者”在坚持操守的同时,稍微牺牲兴趣以免啼饥号寒、死于沟壑的让步,也充满同情:
……我们对于前者,固然愿意买丝绣之;对于后者,也并不忍苛责。波特莱尔的诗有云“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我们将为这种人痛苦之不暇,还能忍心苛责他们吗?[5]
此时的王了一,也正是“呆之贤者”中的一位,因写作《龙虫并雕斋琐语》系列小品散文,且曾受到同样在昆明承受着严峻生活磨炼的闻一多等人的批评,批评者不满的是王了一此时文中对生活痛苦细节的趣味性展览。不过,王了一对这种“大时代”对文人操守的考验,并非没有自觉,尽管其行文谐趣、沉痛兼备,但还是自觉地归附于“雅人深致”之境。
为避免雷同,有些雅人采用偏僻的名字,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6]
虽以调侃的口吻夫子自道,但自居“雅人”行列,是无疑的。“深微精雅”应该是王了一、钱锺书等人小品散文的自觉追求,对于梁实秋而言,虽不追求深微,但以平白呈现雅洁,也是他的内心旨趣。
二 智慧的互观:中外城乡的沟通法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不同阶层在战争中重新定位,这也是世界秩序重构的重要时期。王了一喜欢“你”、“我”和“咱们”并用,显示出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之游移,“咱们”的叙述口吻,是梁实秋、钱锺书所不会用的。梁实秋的叙述者尽量隐匿,有时也会有作为叙述者与人物合一的“我”或“我们”出现于文中;而钱锺书则有时采用一种小说化的笔法,以“钱锺书先生”作为一个小说中的第三人称的人物,将自我有限度地客观化。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中,常常出现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直接或间接引文,显示出作者不无视和苛责生命中融合痛楚的感觉,不回避、美化、抽象生活的文学观。

王了一译波德莱尔
王了一对中国人和西洋人互观之时的“奇观”,做了充分关注,《西洋人的中国故事》是显著的一例,但他将这种“互观惊奇”的视角,引入文本叙述内部,在繁密多变的细节中,呈现诸种“奇观”的不同图景。这是王了一与梁实秋那种以“人性”之相通相同为预设和主旨的表达,最大的不同之处。梁实秋的根基是“人性论”,而王了一的根基是《恶之花》式的“奇异”“丑恶”中的美感,融合了“民族性”的视角以及诙谐滑稽情趣,王了一把这种生活中的奇异丑恶之美,表达得生趣盎然、淋漓尽致,但总体上,也不出“人性”的藩篱。
……西洋的工人有所谓“礼拜服”,咱们中国的农民则有“宴会服”。平日几几乎袒裼裸裎的人,到了赴宴的日子,若不是绸缎衣裳,至少总有一套崭新的细布褂裤的。
西洋人往往把每年收入之半用于海滨避暑,中国人以为奇,但是,如果西洋人知道咱们中国的乡下人把每年膳食费用的一半花在端阳中秋除夕这几个佳节上头,他们又将作何感想?真的,他们平日尽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而当他们过节的时候,四个八口之家不惜凑起钱来共宰一口肥猪。久未开荤的胃肠对于佳节的佳肴也许要起若干反应,然而这又何妨?每年大泻三五次不是胜于城里人吃清导丸吗?[7]
此段文中“几几乎”单行本改为“几乎”,“细布”单行本删去。在行文上,王了一笔下也常文白互用,骈散交织,具体手法是融入骈文的对称与音韵,用典繁密,兼用白话口语连接语,插入骈体文中,[8]增强其弹性与灵活性:
乡下人的衣食虽坏,和我们这些乡下寓公毫无关系。最令人感觉得不舒服者,还是住的方面。门低直欲碰头,室小不堪立足。坏瓮渗雨,疏瓦来风。庭前晒粪,人成逐臭之夫;楼下炊粱,自是栖霞之客。而且三楹虽隘,六畜俱全。漫道晏眠已惯,鸡鸣未扰刘琨;无如好梦方酣,牛喘偏惊丙吉!直到住了几个月之后,渐能随遇而安,甚至于能从丑恶中寻出美来。[9]
此段文中“自”单行本改为“身”。能从丑恶中寻出美来,也正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精髓;与新古典主义的保守性及梁实秋式的人文主义的刻板性相较,这是一种别具生机与活力的生活观、审美观。然而,如果不加控制,则会彰显其肆意调侃和玩世不恭的色彩。
咱们别以为陋室的主人都是穷光蛋。筚门圭窦和褴褛藜藿都不足作为贫穷的证明。住破屋,穿破衣,每天挑粪汁到田里去的一位田舍翁也,就是某银行经理所住的新房子的所有者。单这处的房租一项,每月就有千元。从前是赤脚的人看见了穿袜子的人自惭形秽,现在却是穿袜子的人看见了赤脚的人自惭囊空![10]
此段文中“也”在单行本中被删,削弱和淡化了作者那种略带调侃和玩世不恭的色彩。在微带愤激与大量调侃中,王了一却也敏锐地呈现了抗战之际的社会阶层动向,那就是知识者阶层地位的下降,与工农阶层地位的上升,抗战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毁灭性破坏,也给新的社会变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工农逐渐凸显为决定战争、也就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主导力量,因此,乡下人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到抗战结束后,经过解放战争,这种社会格局分化得更为明确,知识者阶层那种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中介地位不复存在,知识者成为力求靠拢工农阶层的被改造的对象,最终成为融入工农大群的一部分。王了一也正是在这分际的关节点,表明自己虽身为知识者和君子人,但不仇视和忌恨乡下人地位上升的立场。这无疑是一种不从一己之利害出发的、对下层民众怀有同情心的立场
当我们公务员成为遍地哀鸿的时候,正是乡下人的黄金时代。非但有米出卖的人每一个“街子”的收入胜过我们一年的薪水,连卖炭的,卖柴的,卖青菜的,卖草纸的,做小工的,那一个的进帐不是使穷儒咋舌?但是,凭良心说,我们尽管对于发国难财的奸商贪官深恶痛绝,然而对于乡下人我们非但没有仇意,甚至于没有妒心。像我们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平日的享受都是过分的;如果说“民以食为天”的话,乡下人正是天所寄托者,他们千百年才得一度扬眉吐气,已经是太不公平了,我们还能忌妒他们吗?[11]
在此一时期“渊雅精深”体“小品散文”中,“咱们”“我们”“他们”的交相叠用是比较罕见的。虽平实地呈现出因“食”之匮乏,乡下人地位才得以上升,但也有乡下人为天命之所寄的传统“天命观”的影子潜蓄在背后。同时,尽管文中常有“国民性”视角的出现,但是王了一并不拘执于“国民性批判”的态度,即使有时沿用“国民性”批判的视角,也常出以谐趣之笔,使得对其荒谬之处的呈现,圆融了许多,因而没有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的严苛及阴郁感。在艰难时刻,在生活中获得一种对另一阶层(被压迫者)暂时抬头的宽容大度,这也是一种不自私的气度。王了一的这种阶层升沉观,与梁实秋之抱定自身阶级地位不放松的捍卫者立场相比,无疑要灵活得多,因此,也更能接受抗战后中国社会走向“人民”主导的局面。
他们以为我们都是上海人或北平人,偶然还问起我们属于那一国。依照他们把中国神父称为“土洋人”这一件事实来类推,我们在他们心目中大约是“下江洋人”。他们觉得下江人的风俗习惯都是难于索解的。——为什么少年夫妇会公开地谈笑,倚肩揽臂,毫不害羞?——为什么小孩不披八卦衣,不戴八仙帽子?——为什么限定时间硬要小孩坐在马桶上出恭?——为什么接生不用稳婆而用男医生?——为什么生病不求神问卜?——为什么逢年逢节全然不管,端阳节不裹粽子,中元节不烧锡箔,除夕不贴春联和门神?[12]
此处和其他地方的行文中,王了一呈现了“他们”乡下人和“我们”下江人的隔膜。基于这种隔膜的互观,有不能真正理解的痛苦,也有妙趣横生的谐趣。“下江人”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上海人或北平人,“我们”在乡下人心中是“下江洋人”;在总论“乡下人”的时候,是作者“我”作为“下江人”对乡下人的观察,在文章内部,更多地呈现了“乡下人”对“我们”“下江人”的观察。这种阶层的隔膜与“互观”,所表现的形态是无穷的惊奇感,这是唯有王了一的文字才能给予充分呈现的。
古人说“文人相轻”,现在我们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相轻。[13]
但是,王了一文中的“我们”“他们”和“城里”“乡下”并非凝定不变,而是不断地在分化与融合中获得其流动不居的内涵。因此,有时“我们”由知识者自指,扩大为并包“乡下人”和“城里人”的统称,而“城里”则由北平、上海之近现代中心城市之专名,扩展为抗战时期昆明、重庆后方的正称了。在讲述与“乡下人”交往的技巧时,虽不乏傲慢的误解与否定,但能劝阻将“下江人”的傲气用于乡下人,也是十分难得的,在笑谐中调解了潜在的阶层冲突。
王了一是炫博而无持正态度的专家,在《辣椒》一文中,举重若轻地借说“辣椒”之味,对“人类起源西来说”“人类文明西来说”进行了戏仿,提出了所谓“辣椒西来说”,对考古学中的无根假说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尽管大致仍是在“西洋人”和“中国人”的对照中,探讨中西不同的嗜欲口味,但文章写得跌宕有致,张弛有度:
辣椒之动人,在激,不在诱。而且它激得凶,一进口就像刺入了你的舌头,不像咖啡的慢性刺激。只凭这一点说,它已经具有“刚者”之强。湖南人之喜欢革命,有人归功于辣椒。依这种说法,现在西南各省支持抗战,不屈服,不妥协,自然更是受了辣椒的刚者之德的感召了。[14]
将辣椒的德性归为刚者之强,将其与嗜辣的西南诸省人对抗战的支持联系起来,认为西南人有刚者之德,这也可谓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综合视角之中的“时事”了。就此而言,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的滋味是丰厚的,视角是多样的,对现实生活的多种事项,有着超出众人的强劲吸纳力与包容力。在对“奇异”的呈现中,王了一所要消除的是人们因各自环境和历史而形成的无坚实理由的“成见”,以及这种“成见”所演变成的“偏见”;而梁实秋所要维护的是诸种“常识”,是“世相人伦之常”,而这种“常识”,也正是以“成见”为根基的。可见二人文中价值取向的差异之所在。王了一之文所以具有这种特质,大概也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精神赐予吧。
三 直言与隐讽的交融合一:王了一的“小品散文”观

王了一:《生活导报和我》
在这一时期,王了一也阐明了自己的“小品散文”理论。王了一声称:
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在这文章不值钱的时代(依物价三百倍计算,我们的稿费应该是每千字一千五百元),只有多产才不吃亏。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同是我这一个人,要我写正经的文章就为了推敲一字而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我可以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想到就写,写了就算了,等到了印出来之后,自己看看,竟又不知所云!有时候,好像是洋装书给我一点烟士披里纯,我也就欧化几句;有时候,又好像是线装书唤起我少年时代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的回忆,我也就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结果是不尴不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文体。
像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学的人,雕起龙来,姑勿论其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如果说我写“小品文”不单为卖钱,而还有别的目的的话,这另一目的就是换一换口味。这样,就是不甘岑寂,是尼姑思凡,同时,也就是不专心耕耘那大可开垦的园地,倒反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里去争取一杯羹了。[15]
此段文中“介”似为“尬”。王了一以似自贬自谦而实含忿激之情的语气,交代了自己作为语言学专家而涉足“小品”文写作的情状,谈到“小品”文体当时被称为“低级趣味”,涉足小品文写作的专家如潘光旦、雷海宗、陈雪屏、王赣愚、费孝通诸人,也不时遭受种种批评。王了一且回顾抗战前以批判“幽默性灵闲适派”小品散文而闻名的《自由谈》上“稜磨”的观点,“语言学者如果不谈他的本行,却只知道写些幽默的小品,未免太可惜了”,并且点明,“这一篇文章发表于《论语》最盛行的时候,显然是讽刺林语堂先生,其恭维我的几句只不过是旁敲侧击的一种手段而已”。王了一显然对幽默性灵闲适体小品文在抗战前与杂感文派的小品文相峙相争的复杂状况了然于心,然而并不忌惮采纳“小品”一语作为自己在《星期评论》和《中央周刊》发表过的《瓮牖剩墨》以及《生活导报》和《自由论坛》上发表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的总名,“龙乎,虫乎,无非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罢了”:
老实说,我始终不曾以什么文学家自居,也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幽默。我不会说扭扭捏捏的话,也不会把一句话分做两句说。我之所以写琐语,只是因为我实在不会写大文章。……《龙虫并雕斋琐语》根本说不上“雕”,因为太轻心了,太随便了。更进一步说,即使经心刻意地去雕,恐怕也雕不好,因为它的本质是朽木,非但龙雕不成,连虫也不会雕得好的。
不管雕得好不好,在这大时代,男儿不能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而偏有闲工夫去雕虫,恐怕总不免是一种罪名。所谓“轻松”,所谓“软性”,和标语口号的性质太相反了。不过,关于这点,不管是不是强词夺理,我们总得为自己辩护几句。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而同归。有时候,甚至于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16]
王了一承认攻击者“轻松”“软性”之判词,但声述“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而同归”,谈及其何以写小品文的苦衷,则是欲言又止,似乎非常难以形诸笔墨:“实情当讳,休嘲曼倩言虚;人事难言,莫怪留仙谈鬼。”
了解当时文坛的状况,是寻求王了一等小品散文作家的写作动机的前提。
一般文学史家的理解,抗战时期的“歌颂”和“暴露”之争,主要是在延安文坛上的两种文学取向,但是据李广田所言,抗战区的重庆、昆明文坛上,同样有着“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冲突,不过“小品散文”的作者们在这两种倾向之外采纳了另一种取向。
我个人对于抗战文学的看法是这样的:前一期,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大家都在放大了喉咙歌颂光明,后一期,在比较冷静的观察中,许多作家又板起脸来暴露或批判。到了目前,情形就更其不通……我以为,一味的歌颂光明固然不对,而一味地暴露也并不是没有缺陷。……我们已经够苦了,我们的叹息已经太多,我们的眼泪已经要把我们淹没了,我们还需要笑一笑,还需要听一听笑的声音。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散文陶铸得好像赋有了我们日常谈话的气势和结构。这就是工夫之所在,也就是我们可以完成这一艺术的地方。[17]
而当时的抗战当局,对于抗战时期文学的创作和发表,显然有着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王了一等人在写作时无法摆脱也不能明言的,其隐讽的苦衷,实在于环境的不得已。[18]但王了一不同于梁实秋,王氏有更多的对现实的疼痛感,他将这种特殊的现实感装入一个典雅而狭窄的叙述框子里,一方面吸收了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精髓,但却招致了冯至、李广田等更与现实“关情”的散文作者的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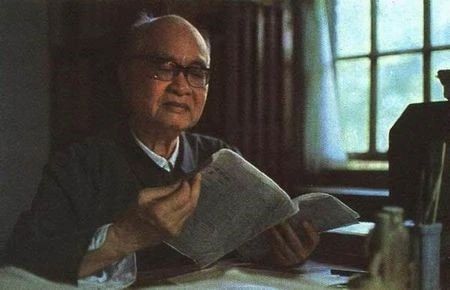
晚年王力
此外,这一时期,抗战区的“小品散文”观,确实发生了重要改变。在署名陶秀的《谈谈小品文》中,提到抗战相持阶段“小品散文”的繁荣,及其“经世”“载道”的功能与“游戏”“娱乐”的功能,并且提倡意思集中、短小精悍的小品文体式:
大概近年是小品文杂志年,小品文恐怕要走红运了吗?但是小品文究竟是什么东西,张三有张三的道理,李四有李四的说法,各人见解不同。
有人以为小品文在某种情形下是典型心理的活动,是要“经世”“载道”的,虽乎很难,譬如说,苏秦以连横说秦,以合纵说赵,《范雎说秦王》,李斯《谏逐客书》,李陵《答苏武书》,李白《与韩荆州书》,王勃《作滕王阁序》,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文》,李华《吊古战场文》,韩愈《祭十二郎文》,李密《陈情表》,都是短篇抒情文字,它们都能“经国”“载道”的,可见得小品文之难,今文与古文只不过语体上区别罢了。
有人以为小品文是游戏的作品,譬如无聊起来,写点风趣的东西吧,写篇把骈四骊六,七装八镶的骈文吧,就像玩玩骨董,浇花,养鸟一样。是文人一种消闲娱乐的方法,对自己是聊以排遣时日,对别人是只供茶余酒后之谈,小品文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是不能成正果,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其实,这种看法是蔑视小品文的评价,没有明白小品特质。
小品文是有社会性的,所谓社会性,就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相连的不能分开,否则,就是奇思幻想的偏颇文字。[19]
陶秀寄希望于“小品散文”中,能够出现一种新的健全的有效的文体,调和小品文之自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增强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涵容力与关切感。这是一种理解“小品散文”文体兴起的角度。《中央周刊》的主编陶百川,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小品散文渐趋活跃的原因。他在《接办一周年嘤鸣求友》中声言,《中央周刊》改版,是因为人们对空洞的、程式化的、枯燥乏味的抗战八股已厌倦,因此所刊登的小品散文,要采用“趣味的形式,知识的内容,斗争的精神”,使之充沛有力、丰盈活泼、幽默诙谐、趣味横生。这种破除枯燥乏味与厌弃空虚无聊的双重需求,其实是促生中国抗战大后方“渊雅精深”体“小品散文”的时代契机,也为抗战相持阶段“小品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0]
裴春芳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71004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3期)
注 释
[1]见拙作《质朴刚健或渊雅精深——抗战区“小品散文”的分流》,《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
[2]“学者散文”先后见于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1963),粱锡华《风暴的焦点——抗日战争中梁实秋的小品文》(1980)与《学者的散文》(1981),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1982),袁良骏《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1998),范培松《论四十年代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的学者散文》(2008);“知性散文”先后见于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1994),解志熙《“严肃的工作”——〈李霁野文集〉阅读札记》(2005)、《从“戏墨斋”少作到“雅舍”小品——梁实秋的几篇佚文以及现代散文的知性问题》(2005)与《别有文章出心裁——中国现代知性散文漫论》(2009)。
[3]见王了一《语言的化装》,《文学杂志》1937年6月1日第1卷第2期。
[4]见了一《瓮牖剩墨》“二 书呆子”,《星期评论》1942年2月14日第41期。这段话在“观察社丛书”《龙虫并雕斋琐语》单行本中被删去。
[5]了一:《瓮牖剩墨》“二 书呆子”,《星期评论》1942年2月14日第41期。
[6]了一:《瓮牖剩墨》“一 姓名”,《星期评论》1942年1月24日第39期。
[7]见了一《瓮牖剩墨》“第一乡下人”,《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4月2日第4卷第33期。
[8]吴澄《王了一散文论》论及,“独特奇幻的典故运用,是王了一散文作品最鲜明的标志”,“王了一作品的‘涩味’,主要表现在典故的频繁出现和‘四六’句式骈文等形式的运用上。作者运典以古代典故为主,西典为辅”,这些典故和骈文、理趣和幽默的交织融汇,构成一种“精心营造的成熟的文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9][10]见了一《瓮牖剩墨》“第一乡下人”,《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4月2日第4卷第33期。
[11][12]见了一《瓮牖剩墨》“第一乡下人”,《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4月2日第4卷第33期。
[13]见了一《瓮牖剩墨》“第一乡下人”,《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4月2日第4卷第33期。
[14]见了一《瓮牖剩墨》“辣椒”,《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4月2日第4卷第34期。
[15]见王了一《生活导报和我》,《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2年版,第16页。
[16]见王了一《生活导报和我》,《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2年版,第17页。
[17]见李广田《对于今年文艺界的三点希望》,《中央日报》1944年1月5日第3版;亦参见Bonarny Dobree著,李广田译《论现代散文风格》,《中央日报(昆明)·星期增刊》1945年2月11日第54期。
[18]吴澄《王了一散文论》也明察其为文隐衷:“作者采用‘软性’文章的写作格调,既是为让读者乐于接受,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逃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员的眼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9]见陶秀《谈谈小品文》,《民意周刊》1941年3月19日第170期。
[20]见陶百川《接办一周年嘤鸣求友》,《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4月2日第4卷第3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