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1881—1936)
内容提要
“改造国民性”问题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和鲁迅研究的关键。“国民性”的包容性和“改造”方式的主观性,却导致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多外化为政见冲突和思想争鸣的战场,内在的学术理路反倒模糊不清。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百余年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有助于总结学术规律并窥探发展趋向。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范式有过启蒙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文化心理范式的三次转换,每次转换都使鲁迅研究摆脱困境并深化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当前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面临着后现代理论危机和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具有整体性和辩证性的启示,是新的发展趋向也是正在形成的研究范式。
关 键 词
鲁迅 “改造国民性” 研究范式 学术史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鲁迅研究的中心议题,学界对“国民性”的内涵、“改造”方式、价值立场有过多次争论。随着研究深入,“国民性”概念一度被视为伪命题、假命题,是否需要“改造”、如何“改造”更众说纷纭。特别是世纪之交围绕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论战,影响延续至今,凸显当下研究的困境。有学者认为,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存在“不系统、不明确的弱点”[1];面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尤其是由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挑起的全球性文化热的学术挑战”,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缺乏本土学术理论。[2]有鉴于此,本文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这一重要议题做综述式梳理,以便在厘清来路的基础上窥探出路。
一般而言,研究范式转换都是基于学术史,本无须做特殊说明。但由于鲁迅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和“改造国民性”的现实关切,致使其成为各种政见和思想冲突的战场。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至少可分为政治视角、思想视角、学术视角三类方式:政治视角是借助鲁迅“改造国民性”这一话题参与政治的外视角,表达知识分子公共言说的欲望和家国天下的情怀,体现其参政议政的责任和义务;思想视角是知识分子通过鲁迅国民性研究与鲁迅发生对视,从而找到自己、反思自己、确定自我身份与价值的内视角,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化中反思自我、革新自我的勇气和决心;而学术视角则是按照学术规律,从问题意识出发,受方法论更新影响,呈现出研究范式更替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描绘出研究方法确立、复制、失效及重新确立的过程,具有自身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和思想的视角。
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的三种视角都有巨大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但三种视角的叠加却可能导致研究的困境和混乱。比如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听到“回归鲁迅”的呼吁或强调“当下价值”的研究倡导,这种吁求和倡导更多看重“回归”或“当下”价值,忽略了学术研究过程和走势,造成百年鲁迅研究不断在“起点”和“终点”切换的错觉。因此尽管有不少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的专项会议和综述文章,但学者在三重视角的叠加干扰下,做出“经过了一个大回旋,又回到了那里”[3]的判断,忽视了“学术”的进步和“史”的过程,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的趋势也不能做出有效预判。
“鲁迅研究的评价从来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4],抽离出纯粹的学术路线是很难的。本文只是尽量简化出相对单纯的学术理路,以凸显学术史的发展。
一 启蒙范式的形成及“国民性”可“改造”的学术共识
最早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研究一般追溯到1922年茅盾对阿Q的解读。他首先提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他“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的观点。[5]周作人也认同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6]。自此“国民性”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阿Q成为国民性的代表。稍晚的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艺术》[7]指出“国民性”的具体内容,如“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性”等几个方面。李长之的《〈阿Q正传〉之新评价》指出,国民性表现为“模糊的、不彻底的、健忘的不健全的、封建的、自私而残忍的旁观者”[8]。这些论述都带有启蒙立场和“进化论”观念,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出怒其不争的“疾视”和毫不留情的“暴露”。论者多兼有作家身份,逻辑论证较少,常以援引和类比作为论证方式,但也体现出对品性、民族类型等重要术语应用和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类文章构成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的最初范式。
“国民性”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体现出五四时代学者知识背景的现代性转变。“国民性”最早的文献记录出自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若举其大多数广察其全体,则其例殆亦与生理上相同,确然有所谓公共之心理特性者。存取族中各人之心理而综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9]其论述涉及三种知识背景的变化:其一用“国民”而非“臣民”,体现出现代政治学深入人心;其二用科学审慎的现代民族观取代传统的夷狄说,体现出从天下到世界的学术视野之改观;其三不用传统的个人“修心”,转而强调“公共之心理特性”的群体意识,体现出现代心理学的最新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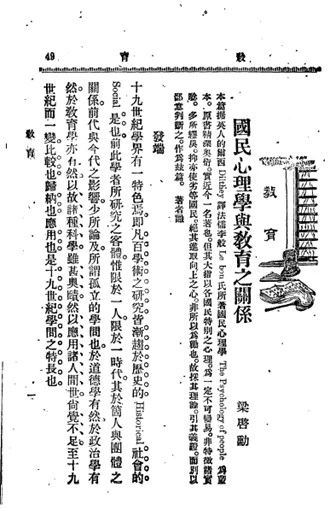
梁启勋:《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新民丛报》1903年第25号
“国民性”可以“改造”的学术共识源于进化论的理论支撑,但此进化论并非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经由赫胥黎、阿亚拉、斯特宾斯等发展演化的现代综合进化论。综合进化论强调进化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的现象,并重申“优胜劣汰”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在种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进化论深深刺激了五四学者的神经,学者普遍较为乐观地相信“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认为阿Q“可以代表中国人的死去了的病态的国民性”,并乐观地判断“现在的中国的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10]论者激进而乐观的态度往往会得出“鲁迅君或者是个悲观主义者”[11]的判断。
启蒙范式的价值在于其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型意义以及现场感和史料性。文章出自鲁迅同代学者,保留当时的社会信息和时代情绪,文献价值极大。茅盾、周作人等兼具作家和评论家身份,他们通过文本分析准确地把握住鲁迅最重要的思想,显示出高超的感悟能力和敏锐的眼光。五四学者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已经摆脱了古典学术的体系,具有从旧学到新学转型的深远意义。
启蒙范式的形成既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又处在中国学术“汉宋融合”的发展脉络中。自晚清以来汉学式微,宋学复兴,致用精神和对现实社会的关切意识也给新学的兴起做了铺垫。第一,旧学典范的危机,清末学术界“怀疑当时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汉学考据,究竟与现实政术及道德风俗有何关联”[12]。典范危机是新学兴起的前提。第二,汉学饱受质疑,宋学迎来机遇。有学者认为,“宋学不但是中国学术的高峰,而且宋儒对先秦儒家的把握其实是最高明的,宋儒对现实的关照也远胜于考证学者”[13],恢复宋学就是挽救知识与道德、知识与社会断裂的危机。这种观念在学术界相当普遍,甚至连章太炎也表示赞同,并且自我反省训诂考据之学,批评清学“琐碎识小”。第三,受宋学影响,五四启蒙时代的学者普遍以学术为跳板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方法上不再是循规蹈矩的文本研究或历史研究,却饱含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启蒙范式学者的兴趣点未必是学术研究,而是通过鲁迅表达自己对“国民性”的看法和对现实的干预和评判。
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学理性较弱,原因是作为知识来源和理论依据的社会心理学和现代综合进化论尚处于初始阶段,核心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和阐释,知识体系并不完善。学者对理论的运用也稍显粗疏笼统,论证也缺乏严密性——既有当时对西学一知半解的时代特点,也带有宋学粗疏、缺乏考证的传统痼疾。此外,由于激进主义的心态和对“进化论”的简化理解,论者忽略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长期性和艰难性,也就很难解读鲁迅思想的深刻性。
二 人文主义烛照下“国民性”的“现代性”追求
1936年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中记录:“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4]鲁迅逝世五周年时,茅盾援引了这则史料,并提出人文主义的研究视角,在对鲁迅研究做综述式梳理的基础上,肯定当时左翼学者的鲁迅研究,但随即“请一述我自己的感想: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的一个,——鲁迅!”[15]用“人性”或以“Humanist”(人文主义)概括鲁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1930年代,鲁迅“改造国民性”启蒙研究范式逐渐式微,具有较强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左翼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鲁迅进行全新的阐释。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从“国民性”置换为“阶级性”,通常研究思路是将鲁迅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进化论影响下,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文学,是不成熟的;后一阶段是以阶级论为指导的左翼文学。左翼批评家强化了鲁迅革命家的一面,有其时代合理性,但贬低了鲁迅最深刻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茅盾试图让鲁迅研究重回“改造国民性”研究,人文主义的视角体现出他的远见性和深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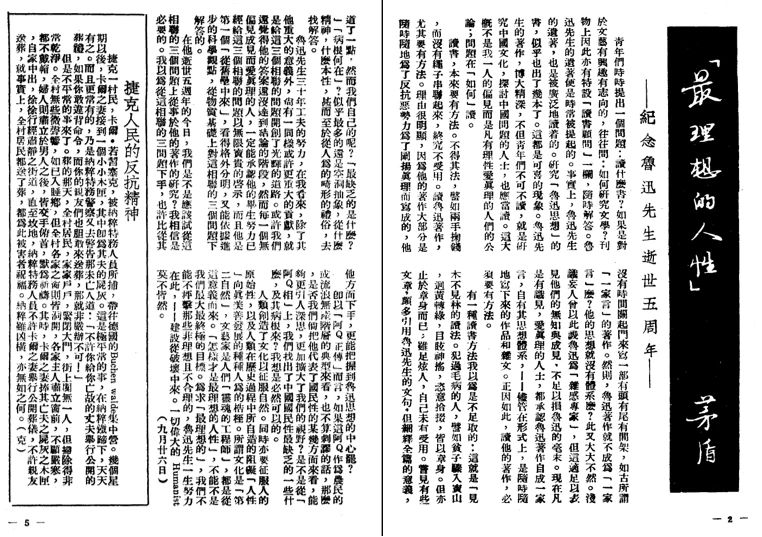
茅盾:《“最理想的人性”——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笔谈》第4期,1941年10月
但此时的人文主义视角尚不能称为范式。仅在鲁迅先生逝世的特定阶段,通过众多纪念性文章人文主义视角才得以体现,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研究更多采用政治视角和思想视角,“国民性”又被置换为“阶级性”或“人民性”。尽管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夏绀弩、孙伏园也曾关注到鲁迅“人的觉醒”[16]、“人的发现”[17],但人文主义的研究视角直到1980年代才占据主流,在学院派的努力下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范式。
1980年代的人文主义研究用“立人”思想延续并深化了许寿裳、茅盾、孙伏园的“人性”研究思路。王得后提出“立人的思想贯彻鲁迅一生始终”,“因此之故,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18]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首先承认鲁迅“国民性改造”对梁启超、严复的承接性,但严复、梁启超关注社会群体,而鲁迅“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19]钱理群进一步解释“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20]。
王富仁认为“《呐喊》与《彷徨》的重要性主要不是反映在政治革命的实践中,而是在思想革命的实践中”[21]。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用“中间物”概念透视鲁迅的精神结构。[22]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在“中间物”基础上推演出鲁迅个体的生命哲学。[23]三位学者从思想到精神再到个体生命有着明显的承接性,其结果则是不断把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内视化,凸显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个体意识。人文主义范式在揭露“劣根性”方面和启蒙范式有明显的联系,但也有所区别:第一,目的和工具的差异。启蒙主义“从一开始便被规定为工具理性”,而人文主义是“对人生终极目的的关怀”。[24]第二,启蒙范式因受进化论影响,关注民族整体命运,旨在改造重复数的“群体”;人文主义范式更尊重个体,旨在唤醒单数“个人”的自我意识。第三,启蒙范式的着力点在批判“过去”,认为可通过对“劣根性”的揭示实现改造的目的;人文主义范式则注重“将来”,表现出对标“现代性”的“改造”诉求和迫切愿望。
人文主义范式最大的价值首先在于对鲁迅精神的深度挖掘和心灵的对撞。张梦阳认为,“在鲁迅心灵的探寻中,与鲁迅毕生致力的为使中国人民‘结束精神奴化状态’的事业相接续,将鲁迅研究与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自觉联系在一起”[25]。这句评述适用于众多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第二,在与鲁迅精神世界的对望中,学者意识到“国民性”的合理性与普遍性。如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26]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防卫的心理机制。国外学者如竹内实、新岛淳良等都认为阿Q“已经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一样被列入人类典型之列”[27]。第三,1980年代学者普遍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因此理论分析更为严密。他们冗长的段落、特有的长句以及规范的注释,使学术论文作为文体呈现出专业性和规范化的特征。
然而,人文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特别是身处高校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学科建设的同时也不断强化文学的“现代性”,于是“国民性话语研究也就变成了对人的现代化过程的论述”[28]。将“改造国民性”纳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研究,有其历史根据和学理支撑。但也有学者提出疑问,“现代性的故事已经成功地构造了一个‘历史的必然’,一切似乎都是以西方的文化社会为终极范本”[29]。这种质疑不无根据,事实上,鲁迅“国民性”研究逐渐被“现代性”偷换了概念,并在差序化的思维中失去了阐释的张力。
三 文化心理多元透视与“国民性”的深层结构
2000年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认为,鲁迅的“过在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30]。这篇文章和1993年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31]相呼应,从学理性和路数上都以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为理论依据,以福柯知识考古为方式,试图从根本上解构鲁迅“改造国民性”话语。两篇文章引发轩然大波,学界就此展开激烈争论:支持者有周宁的《“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32]、刘晓南的《“国民性”:一个假想敌》[33]、贺仲明的《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34]等;反对者有高远东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35]、汪卫东等的《国民性:作为被“拿来”的历史性观念——答竹潜民先生兼与刘禾女士商榷》[36]、王学钧的《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37]和陶东风的《“国民性神话”的神话》[38]等。文化心理范式的产生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国民性”不可“改造”甚至不能“改造”的一面。特别是处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表现出“患得患失”心态:激进地“改造国民性”也许会伤及本土文化的根脉;和“劣根性”共存则可能在现代文明中再次落伍。此外,冷战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对国人的影响巨大:一种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现代性就是完美形态,其他国家只需模仿西方,世界就会趋于美好和统一;另一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社会不会被西方现代化终结,而是逐渐发展为不同文化的冲突。福山和亨廷顿的对立不仅是世界观的争论,也包含价值观的对立。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观点,学者们纷纷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中寻求启示和证据,进而表达个人观点。鲁迅“国民性”研究形成“现代性”和“民族性”的不同的“改造”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便不难理解刘禾的文章。中国学者走出国门,意识到“中国人走到哪里也是中国人”,又对“现代性”的后遗症有清醒的认识,逐渐意识到“现代性”已被附加的意识形态扭曲变形。
除了海外学者理论思潮的冲击,自民间崛起的文化“寻根”力量也深刻地影响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作家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说失去民族文化“我们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39]。“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在冥冥中突然被“弘扬民族魂”的时代精神替代了。[40]在学术界则表现为对鲁迅“国民性”研究的反向挖掘。如高远东的《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在人们所熟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吃人的定性和立论中,崛起了一种作为其批判国民劣根性主题之正题的所谓中国脊梁的墨家英雄”[41]。
文化心理模式的最大贡献在于视角的多元化。首先,海外学者、民间力量以及学院精英以不同的文化观、从不同的角度考察鲁迅“改造国民性”,从而产生丰富的学术价值。多元视角对学术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学界呈现出久违的争鸣气象。其次,后现代、后殖民、新儒家等理论的加持,让研究呈现出更为专业的学理化和前沿性。然而在学理性、理论性的背后又凸显了中国学者的自信心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我们的国民性研究,一直采用的是‘中/西’二元对立的比较方式,无论是扬此抑彼,还是褒‘我’贬‘他’,都无法走出西方国民性理论知识的阴影”[42]。
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的困境除了本土理论的阙如,还有学界内部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学界希望“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却“发现追求学术独立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研究与现实致用之间的紧张”[43]。张福贵对鲁迅研究中的“历史性研究”和“学问化研究”都持保留态度,而独尊“当代性研究”,也正是基于此种危机的有感而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适时提出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学术摆脱异化,回归社会性和平民性带来了契机。其重要启示在于“改造国民性”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国民性”的差异,依据自身特点进行“改造”,从整体性和辩证性上重新审视鲁迅“改造国民性”主题。
所谓辩证性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对“差异化”和“差序化”的比较论述。“差序化”是各国文明都在西方现代化的赛道中,追赶者不仅饱尝“优胜劣汰”的焦虑,还时刻伴有“自我”变成“他者”的隐忧。而“差异化”则认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鼓励不同民族国家用自己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显然“差异化”比“差序化”的理解更为准确,也更符合实际。以往研究多是在“差序化”的忧虑中考察鲁迅“改造国民性”,因此或强调鲁迅激进主义的一面,或突出其绝望乃至虚无的心态,或对其讽刺艺术有片面理解。其实鲁迅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困难,坚韧才是鲁迅的性格特点,激进主义只是鲁迅的表象或策略。
所谓整体性主要表现在对鲁迅思想的完整论述和对国民性的历史性考察。比如,过去总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框架中理解“国民性”,其实仍带有机械进化论的思想和激进主义的心态。真正的“改造”既不是完全否定自己的“传统”,更不是无条件地相信西方的“现代”。又如“中国”与“世界”、“民族性”与“现代性”、“城市”与“乡村”都可以在整体中评价,从而正确理解鲁迅“改造国民性”究竟是“全盘西化”还是“拿来主义”,是逃离故乡的决然还是饱含深情的“归去来兮”。
目前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的新范式尚未形成,但学界已经表现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鲁迅研究相结合的极大兴趣。如赵顺宏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百年变革的文学书写》中“复合结构”[44]的提法显然要比以往“二元对立”结构更为精当细致。这些成果都预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将悄然兴起。
石小寒
聊城大学文学院
25200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9期)
注 释
[1]张杰:《系统性研究是当务之急》,《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
[2]高旭东:《鲁迅改造国民性研究的出路》,《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
[3]迟蕊:《从鲁迅“国民性书写”研究中的问题谈起》,《渤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5]茅盾:《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
[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
[7]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艺术》,《国文周报》1934年第11卷第44期。
[8]李长之:《〈阿Q正传〉之新评价》,《鲁迅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6页。
[9]梁启勋:《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新民丛报》1903年第25号。
[10]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第3期。
[11]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12][13]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8、19页。
[14]许寿裳:《怀亡友鲁迅》,《新苗》第11期,1936年11月。
[15]茅盾:《“最理想的人性”——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笔谈》第4期,1941年10月。
[16]夏绀弩:《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中苏文化》第7卷第5期,1940年10月25日。
[17]孙伏园:《五四运动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5月。
[18]王得后:《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鲁迅研究》1981年第5辑。
[19]参见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20]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期。
[2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22]参见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参见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4]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25]张梦阳:《鲁迅的真正价值究竟在哪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逝世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版。
[26]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27]山东省鲁迅研究会编:《〈阿Q正传〉新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
[28]孙强:《国民性研究的理论反思——兼论话语研究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29]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30]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
[31]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文学史》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2]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
[33]刘晓南:《“国民性”:一个假想敌》,《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34]贺仲明:《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
[35]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
[36]汪卫东、张鑫:《国民性:作为被“拿来”的历史性观念——答竹潜民先生兼与刘禾女士商榷》,《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期。
[37]王学钧:《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8]陶东风:《“国民性神话”的神话》,《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9]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9日。
[40]樊星:《当代文学对国民性的新认识》,《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
[41]高远东:《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
[42]常立霓:《鲁迅“国民性”理论研究的困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3]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5页。
[44]赵顺宏:《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百年变革的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