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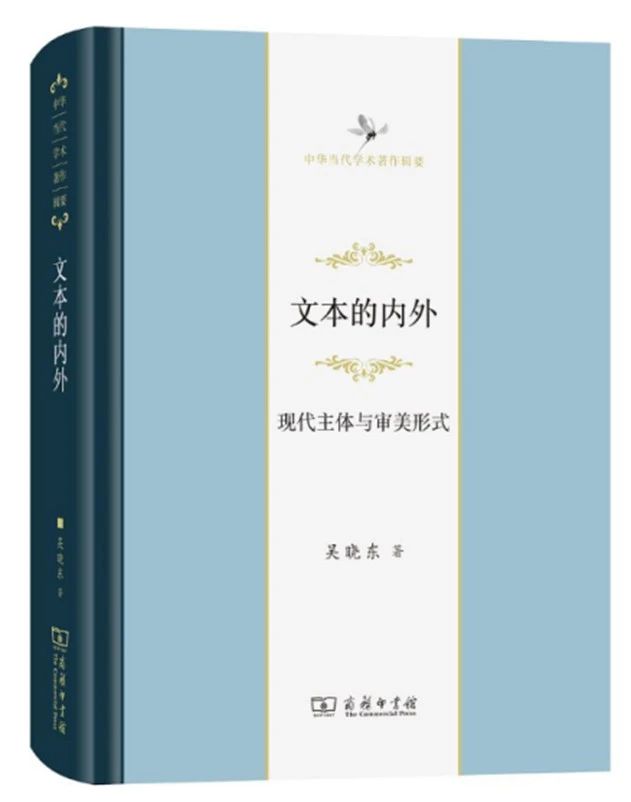
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坚持“文学性”还是继续“历史化”的议题持续引起学者的热切关注。如何在新的、更高层次的总体性视野中超越“纯文学”的概念,通过“历史化”来探寻“文学性”的内涵,同时又不让它脱离文学研究的初衷,落入社会学、历史学或其他学科的窠臼,可以通过学者吴晓东近年来的研究得到标本性的检视。他在历史化/政治性的阐释中,通过“历史化”的工作和总体性的辩证分析,阐明“文学性”与“历史性”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超越了传统的人文主义解读,为沟通“现代主体(性)”建构与美学形式、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有机关联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剖解作品的美学或诗学结构打开了新方向,同时也蕴含了超越传统人文主义解读方式与海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模式的动能。这一探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化文学阐释的主体性立场和辩证法的魅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进路,实现了范式和方法的更新,从而给当前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 键 词
文本的内外 文学性 历史性 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
近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性”与“历史化”的议题持续引起学者的热切关注。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甚至构成两种范式之争。[1]这两个概念是否水火不相容,或是构成两个南辕北辙的研究路径?如何在新的、更高层次的总体性视野中超越“纯文学”的概念,通过“历史化”的工作来探寻“文学性”的内涵,同时又不让“历史化”脱离文学研究的初衷,落入社会学、历史学或其他学科的窠臼,是在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中,不断激发学者的思索与辩论的问题意识所在。
《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是吴晓东教授近十年来论文的精选集,集中体现了他在研究方法和诗学建构上的新思考,而这种探寻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全书一共十八章的厚重分量以《文学性:经典与阐释——与洪子诚先生对话》为代序,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审美的主体”主题,分四章分别讨论了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郁达夫小说里审美主体的创生;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田汉及其浪漫主义的终结。第二部分以“心灵的形式”为题,分四章分别讨论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诗学和文本中的主体建构;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鲁迅的“回心”与“赎罪的文学”的概念和伊藤虎丸提出的鲁迅的“终末论”思想及其与“抵抗”的文化主体的关系;废名《桥》意念与心象;沈从文作为现代小说家的“生成”过程。第三部分也分四章以“文本与历史语境”为检讨重点,分别探讨沈从文《长河》中的传媒符码,包括现代大众传媒的话语空间和“现代”及“国家”想象;张爱玲小说中的空间意义生产;废名战乱年代的另类书写;战时文化语境与骆宾基小说里反讽模式的生成。
由此三个部分可见,作者既关注“审美的主体”,又聚焦于“心灵的形式”,而对它们的探寻又与对历史语境的考察紧密相连。因此后面两个部分继续以个案为例,显现这种将文本内容和美学形式有机联系的方法运用。第四部分研究文本中被建构的“风景”,三个章节分别讨论旅游产业的兴起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的原点;未完成作品《山山水水》中的政治、战争与诗意。最后的第五部分则分析母题的艺术,三章分别剖析现代派诗人作品中的艺术母题,它们作为审美和心理的双重体验及心灵与形式的合一;最后一章探究卞之琳成熟期的“最佳作”《尺八》里的“戏剧性处境”。由此分类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近年来的研究兴趣展现了对阐明“文学性”与“历史性”纠缠关系的不懈追寻。

吴晓东
自始至终,作者坚持“文学的自主性”,认为这是文学“言说世界的前提”,并提出“‘文学性’在今天依旧还构成着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终极依据”。[2]这种对“文学(性)”的“信仰”又与研究者的“本分”连接在一起:“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3]这本身体现了一位坚持传统理念的人文学者在今天所处的两面处境:一方面是在浮躁的世界不无感性色彩的对于文学的坚守,一方面是面对“理性、太理性”的学术世界层出不穷的新话语时,对于传统人文精神与经验世界的不离不弃。那么,将学术作为志业的作者如何在书中阐明这种“文学性”并非一种本质化的概念?它与作者同时强调的“历史性”又如何关联?
一 在“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双向阐发
表面上看,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话语似乎倡导以感性体验来摆脱理性的“历史理念”的束缚:
“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文学性”因此是一个值得我们倾注激情和眷顾的范畴,它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4]
作者在这里以传统的“人性”话语与文学性相连,但它并非那种非历史性的人性观,因为这里对人性的强调是建立在对人的“经验存在”的把握上:它既让人联想到一般认为是高尔基提出来的“文学是人学”的论点和1950年代由钱谷融先生再次予以讨论、1980年代流行国内文化界的这一重要命题;[5]也让人想起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及他的名言“存在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作者确实在书中提到1980年代“萨特热”带来的存在主义的文学影响,直接关涉对存在、人性以及人的境遇的新的意识的觉醒,这显然体现了时代对于学者学术传承的影响。[6]但追其实质,这种对“人性的深度”的坚持,本质上更致力于把握历史现象及生存经验本身的异质性和差异性:“一旦重新面对原初的文学史语境,以现代性理念为支撑的一元化图景就被打破了。异质性和差异性上升到文学史的前景中来。而其中最难以整合的是审美的领域。”[7]
因此,作者一方面承认“文学和审美形式”即文学性不是自律性的、自主性的、本质性的概念,而致力于去考察它的“自治性”的形成过程,即将文学理解为文化生产的结果从而具有建构性;另一方面作者所力图实践的是在动态历史中去“还原”其中体现的生存经验和“审美体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8]这种缠绕使得洪子诚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作者实际上是在承认“文学性”的历史建构性质的前提下,更关注它的恒定的、延续的因素,以避免这一命题的破碎化。[9]

洪子诚
这种表面看上去带有精英意识色彩的追求,借由作者对于“当前的文学研究的危机之一就是审美判断的能力日渐匮缺”[10]的判断与洪子诚精当指出的“人的存在经验,想象力,创造力(原创力),独特性,艺术趣味等因素”是这种“文学性”的核心内容的归纳[11],而变得更为显豁。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又由感叹当今社会“经典”“陨落”的现象,透露出他的家国情怀:他认为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自觉”出了问题。[12]与那些以“文学性”的名义否定“红色经典”的地位的学者不同的是,作者承认它“的确已经获得了被经典化的历史条件”即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本身赋予它经典地位的正当性。[13]既然作者指出对于界定什么是经典,尤其在判断什么是当代经典的问题上,一种新的文学性的视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终究要追问的是,“文学性”和“历史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新的文学性的视景”又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看到在作者坚持人文情怀之下的学术上的求真探索,体现为方法论实践上的双向互动。它一方面是在“文学性”的表现中,检视其“历史性”印记与踪迹:作者对“文学性”的坚守并非与世隔绝的“纯文学”幻想,而是恰恰相反,强调文学应具有与大众、生活实践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维度。[14]这一看似矛盾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辩证:对作者产生过深刻影响的1980年代中国文化界流行的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强调“感性”和经验世界的意义,并提出“新感性”在人的解放上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强调文学所内蕴的“政治潜能”。吴晓东认为,虽然与直接的社会实践和现实政治相比这种立场有“退却”的成分,但从“乌托邦”的角度理解这种“悲剧性”,就可以看到它恰恰是文学所内蕴的固有力量,而文学就是悲剧乌托邦。[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坚持文学内在包含“社会承担的意识”以及建构反思性历史主体的重任。[16]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负担深化而非背离作者坚持“文学性”的立场:不但“悲剧性的乌托邦”本身代表了人性最深的渴望从而正是文学(性)自身,而且借助竹内好在鲁迅身上找到的文学作为“机制的思想”和伦理实践,作者丰富了对于文学(性)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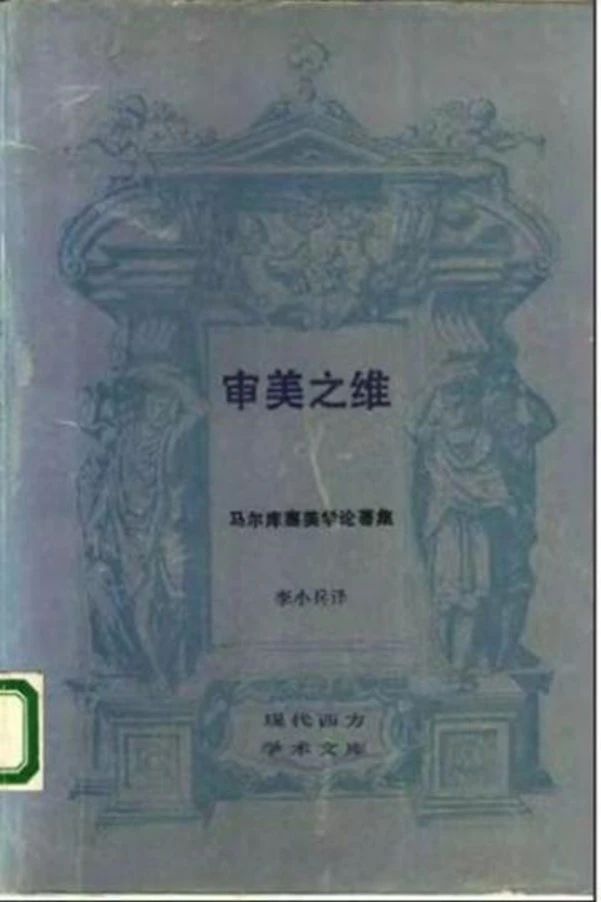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这种从“文学性”中检视其“历史性”的具体做法,是看到文本中存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两种冲动,而这是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到杰姆逊的政治阐释学都强调的分析原理。其具体的例证可以从文集中多次谈到的沈从文那里发现。一方面作者从一贯的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因为有对人生的悲悯和爱作为底色,才更具有沉甸甸的意蕴;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边城》描绘的湘西田园世界虚构的自足性的幻景暴露出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其中对完美的生命境界的追寻又隐含了一种乌托邦远景,即对于至善至美人性的渴望。[17]
这种双向互动的另一面,在于反向从历史性的探讨深入,以阐明文学性的具体的、每个历史时期的特定内涵。吴晓东强调,虽然杰姆逊最终关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诸领域,但他从不放逐形式与审美问题。他特地引用了杰姆逊的名言说明这一点:“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18]这种“从审美开始”并不意味着一开始只关注审美特征,而是说贯穿始终的是一种以历史性的角度和意识来检视文本的“文学性”,而分析的具体做法就是从“文化政治”或“诗学政治”的维度来考察文本。这里的具体例子是作者对北岛的分析。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轻视语境而重“纯文学”不同,甚至与今天的北岛本人“悔其少作”相反,作者鲜明提出北岛如今将其朦胧诗阶段的作品视为“官方话语的回声”是一种“反历史的态度”。
由此他对北岛的诗歌美学的两阶段做了考察,提出北岛在朦胧诗阶段的写作是一种反叛时代的“政治的诗学”,塑造了一个审美化的大写的主体形象;而1990年代开始则在诗歌中实践“诗学的政治”的维度,纠结着自我的重塑以及主体的再度认同的问题,以漂泊的语词的形态继续海外汉语书写,从而创造了跨语际书写和汉诗写作的新的可能性。但作为专业研究者,作者反而认为后一时期诗人的成就没有朦胧诗阶段高,这是因为此时北岛在主体认知与文化认同方面出了问题,从而影响诗歌的内部景观。正如吴晓东所指出,这种辩证认识是一种回避流行的线性“发展”价值观的态度。[19]这一分析正是在坚持审美意识的前提下,从“历史性”的角度来剖析诗人及其诗作,是在一种“知世论人”的角度下的历史化阐释。[20]显然,后期北岛拒斥政治的“纯文学”态度并不必然产生文学性更强的作品,研究者这里推崇的反而是其前期充满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崇高美学”和情感结构的作品,认为其时审美化的大写的主体形象更具有文学的感染力。
这种“语境化”正是作者将“文学性”与“历史性”加以有效连接的实践方法。但他也提到,虽然需要强调避免将文学“本质化”,但也要警惕研究中过度“历史主义”或过度“语境化”的倾向。后者不是回到历史原初面貌,而是由于缺乏了问题意识而迷失在所谓历史的丰富材料中,使得“语境化”无法在深刻的水平上进行,而只是低层次的历史材料堆积。[21]这一警省指出当前一些所谓“历史化”的工作,其实质只是将这一杰姆逊最早提出的口号当成史料搜集工作的偏颇。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由此我们看到,作者将“文学性”与“历史性”相勾连,避免了两种倾向。第一种指向了片面强调文本自足的“新批评”:在吸纳各种文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他看到这种“纯文学”方法无法有效解释文本的“文学性”,因为在语言、技术、主题、方法之外,“时代、历史、社会生活、文化变迁”也总要找上门来。[22]第二种是将历史化只当作史料搜集工作的做法;与之相反,他将“时代情境,作家传记”等因素纳入文本分析解读中,通过检视顾城杀妻事件及顾城在激流岛上的私人生活空间,从顾城最终的生命结局回溯到诗中寻求这一悲剧终结在作家心理认知上的某种的必然性,从而让“历史性”与“文学性”互相阐明;这种双向阐释是同时进行的活动,体现了一种互动的、总体性的辩证法。
二 “历史化”阐释与诗学结构的缜密探索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化的、“政治性”的阐释。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干的是南辕北辙的事情,是使文学去陌生化,或者说是祛魅的活动”[23]。这种阐释不仅“还原”原初的历史情境,也需具有政治性的思考,从而实质上是实践杰姆逊所倡导的历史/政治阐释学。但这种阐释不是为了显现政治真理,而是坚持“文学性”的导向,这显现为作者一直强调的形式问题。正如作者所言,“文学作品中内在化的思想和结构性的紧张关系最终总会在形式层面表现出来”,因此他化用了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名言说道:“形式总是内化了社会历史内容的‘有意味的形式’。”[24]但与杰姆逊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作者在关于鲁迅小说形式的一章中,着重指出自己所致力的是一种“形式诗学”。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借助对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形式,探讨“鲁迅的小说思维与文本形式的关系”,其中包括“话语世界的复杂性、对话性甚至冲突性以及探讨鲁迅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进而探讨内在的紧张、冲突的话语类型和思想模式是如何转化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借此他解释了他探索的“出发点”和“关注的问题”:
形式诗学的出发点正是寻求使小说组织成统一体的诗学机制,这种诗学机制是文本内部的,也是形式化的。形式诗学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作品的形式是怎样构成的?它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作家又是怎样通过形式传达世界的?哪些是只有通过形式才能看到的东西?一部小说如何把关于生活世界的断片化的经验缝合在一起?小说中使文本成为共同体的主导的形式因素到底是什么?由主导的形式因素又派生出哪些微观诗学机制?又有哪些诗学机制具有相对的普适性?[25]
如果在书中再找一个这种分析的典型例子,那么可以是《战时文化语境与小说反讽模式的生成》。这一章分析了作为修辞、认知和表现模式的反讽在《北望园的春天》以及《围城》这类书写1940年代战时知识分子的小说中的表现。它一方面从形式层面出发,指出反讽中蕴含了叙事者的自我嘲弄和反省,其美学效果在于文本的意义似乎一直在生成,处在不稳定的动态过程中;另一方面从历史化语境出发,说明这与战争年代的心理、人性与归属感的缺失乃至文化危机有历史性关联,体现了作家对自身处境、人性现状以及历史语境的认知方式的复杂化,包含他们对无法控制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进程的讽喻性呈现,从而使得这种认知方式和美学态度最终通往一种与战时文化语境相适应的小说美学的生成。[26]
总之,以上的分析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历史化和语境化”的理解,即“把问题放到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看看它们是不是真正成了问题,又是怎样成为问题的,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又是怎样应对的”;作者总结认为,考察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处境。[27]但他并不止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将此方法发展为对于现代性概念与实质在现代中国状况的探索,比如他这样阐明这种问题意识:“回到作家的叙事中去还原历史,去把现代想象具体化,从而避免把现代性的问题本质化……一旦回到历史叙事中,现代性就自然呈现出一种多元景观。”[28]书中以对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分析为例,说明如何通过沈从文的乡土叙事,具体考察包括现代性思想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观念怎样在他的小说情境中展开,而这些问题又怎样内在化为小说中的历史境遇。由此,作家对现代的反思就把非同质化的“现代”范畴引入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使“现代”成为蕴含着多维的甚至悖反的内容的存在。[29]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文学史研究正应该回到文学的原初景观中去,直面文学史的复杂的经验世界,直面原初的生存境遇”;而这种“反思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预设,对于重新回到经验历史有举足轻重的意义”。[30]这也是上一节我们提到的作者注重历史中的“异质性和差异性”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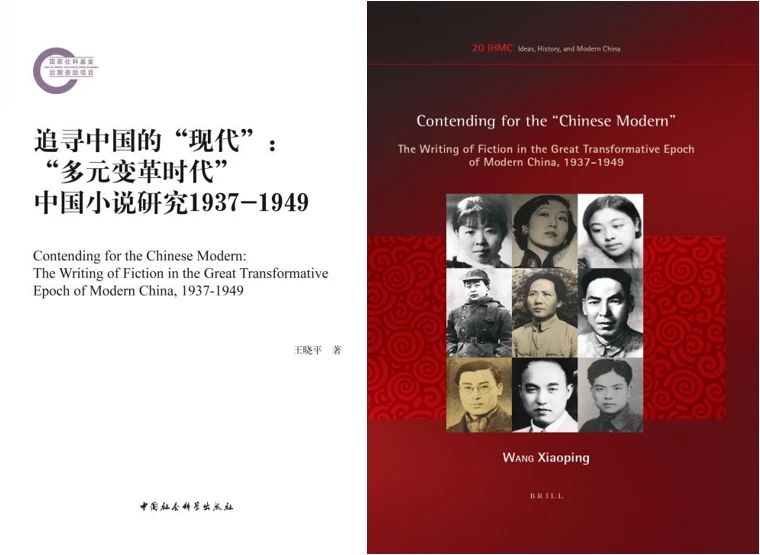
笔者相关论著的中、英文版封面
左图:《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小说研究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右图:Contending for the “Chinese Modern”: 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ve Epoc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9,荷兰Brill学术出版集团2019年版
这种扩大了层次的探讨,仍然坚持了上述历史性和文学性双向互动阐释原则。比如作者看到在郁达夫选择疾病作为作品主题的背后是现代性的机制,而这种现代性正是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主要来源于日本时期的文学影响。这种“还原”是历史化的第一步,发现了现代性建制(装置)创生了现代小说,而第二步则看到小说反过来成为促使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生成的一个重要媒介。[31]这“两步”是同时进行的、让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得以互相阐明的“文学行动”。
在经过这样的辩证双向分析后,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代感性、身体性、颓废美学的发现与现代性之间同样建立了具有必然性的关系,最终则导致了现代性主体的生成。”[32]这里对(文学的)“主体(性)”的理解并非1980年代那种人文主义的方式,而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上,将主体性看成是文本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互动结果。这里对郁达夫小说的分析实质上通过对其“题材和主题的变化”来“考察其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视野”,而其方法论则是剖析“主体置身其中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小说中的价值和立场”。[33]这其实正是杰姆逊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政治阐释学的基本原理。
这种分析方法贯穿全书,比如作者谈到鲁迅《狂人日记》和郁达夫《沉沦》这两部最早创生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主体都逃不脱意识形态的裹挟,主体位置成为意识形态中的位置。[34]在这里,作者看到审美内化为政治的过程显示审美现代性不完全是解放的力量,而可能是以一种压抑的力量来进一步使压抑内化;进而引用霍克海默关于“内化的压抑”的理论来说明审美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这使得作者超越了“人文主义”的阐释限度,达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实践这种辩证法的核心正是意识形态批评,而其中的重要概念工具是“中介”。正如作者所言,审美充当了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中介,而这其实意味着“意识形态通过审美的力量参与了主体性的生成过程”[35]。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审美主体创生的文学秘密其实就是揭开意识形态迷雾、剖解作家的政治(无)意识的过程。
于是我们进一步看到,求真探索的精神使得作者借由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主体性的讨论,通往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对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主体身份建构加以关注的关键问题:作者质询道“为什么主体性是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视角?”他认为,这是“因为二十世纪整个东方普遍面临一个现代性的冲击问题,面临文化主体性和个人主体性的危机问题,面临认同或者说身份的危机以及重新建立认同的问题”。由此,探寻的方法是“具体考察小说中的主体生成与现代性机制之间的关系,寻找文本中的主体建构与文本外历史文化的深层关联”。在此我们发现了杰姆逊关于政治阐释学具体方法的经典表述:所谓的历史不是外在于文本的东西,而是作为内化在文本中的无意识被挖掘和探寻。[36]
通过对文学文本中内化的“历史潜文本”的发现和讨论,吴晓东不但看到郁达夫漂泊的、中心离散的主体带来的外在“感伤行旅”形式之下的“内在形式”:一个在个体、爱欲与家国之间找不到主体位置的表达,[37]而且发现了中国现代派诗人重建纳蕤思母题的过程,展现了这群青年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建构。后者在东西方的艺术资源中获得审美自觉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尝试确立自我和主体的过程。但他们建构的幻美化的艺术主体“自我”是虚假的,因为它是被西方和传统话语双他者化的镜像自我,而这意味着真实的历史主体的匮乏,反映他们致力于探寻的历史主体无法建立的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历史化的分析并不脱离文本,因为正如作者所言,正是由于诗歌内化了审美体验和文化内涵,“把诗人所体验到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所构想的乌托邦远景通过审美的视角和形式的中介”[38]投射到诗歌中,因此探寻诗人的自我与主体在文本中符码化的具体历程,就能寻找到把“主体的真理”与形式诗学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即考察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历史因素在诗歌文本中的意象的内在折射,从而寻找一种诗人心灵与艺术形式的对应模式。[39]
这种结合社会与文化潜文本来探寻诗学结构另一精当的运用,表现为对卞之琳《尺八》的剖解。通过对文本中“三种时空”(追溯中的历史时空、现实时空与想象的虚拟情境)和“三重自我”(诗中的叙事者、诗中的人物和诗人自己的阐发),作者提出诗人构造了一个“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加上其“主体间性”的特征,诗人最终超越了一己的感伤,跳出了个人的小我,从而不但使诗歌的主题从个体的现实性的乡愁上升到民族、历史与文化层面,而且使得这种“情境的美学”成为对传统诗学的意象审美中心主义的拓展。[40]由此,我们看到作者操持的缜密的历史化阐释,有效实现了对作品诗学结构即“形式诗学”的探索。
三 “持久历史化”的潜能与辩证法的坚持
秉持人文主义信念的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下,对杰姆逊倡导的历史/政治阐释学颇为熟稔并力行实践,只不过他强调的是即使对一部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也要以艺术水准以及真实性为根基。[41]当然,看上去他仍然对这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师有所保留:“形式的和美学的问题在杰姆逊那里仍还有手段的迹象,而我认为形式本身正是本体和目的。”但正因为看重的是形式中“所积淀和凝聚的‘意味’”并致力于通过历史化、政治性阐释的方式“暴露”它反映的“作家的思维方式和他认知世界传达世界的方式”[42],这就不仅仅是对形式本身的探讨了,因为这些“隐含的东西”已非形式所能涵盖。实际上这种情状正是辩证法的核心,即“内容”与“形式”的同一。
杰姆逊的历史/政治阐释学正是对内容/形式二分法的扬弃:探讨历史性、社会性内容和文学形式之间的互动、交易,是以它们之间的辩证让形式的特殊性和历史的特异性交织,并作用于彼此,由此形成阐释的循环;不懈的历史化恰是为了最全面地解释文本中每个独特的审美细节。换言之,历史化不是牺牲对文本的审美素质的探索;相反,只有通过彻底的历史化,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艺术作品的审美特性。书中的“形式分析”均可以看作是在这种辩证意义上的“内容阐释”。书中每篇均在充分历史化基础上做出这种辩证解读。受到作者的方法论和思路的启发,我们可以在该书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延伸思考,从而对其倡导的将历史性与文学性进行关联的分析方法获得更多认知。由此我们将看到,作者的方法论立场和具体分析实践,实际上已经蕴含了超越传统的人文主义解读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动能。
我们可以以书中对沈从文与张爱玲的阐释为例。作者与海外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沈从文对砍头这一场景的书写,并都将其与面对相似状况时“鲁迅式的义愤”做对比。作者敏锐地看到作家“竟带有几分鉴赏和审美的观照心态,而且一如既往地沿用他那典型的田园牧歌般的抒情文类”;面对这种“文体的以及审美的层面与题材和内容间”的张力,作者借着反问句的形式“是沈从文失去了对题材内容和文体形式之间互动关系的敏感性吗?还是他有着更深的用意与图谋”来思考什么是这种用意。他的回答是“文体家的沈从文所建构的文本世界,是最具有审美主义意义上的自足性的世界。而他的文本世界中的内在的异质性和丰富性,又使得从寓言诗学的角度进行多重诠解成为可能”[43]。借由阿多诺、本雅明到卢卡奇对于小说的论述,以及杰姆逊对于寓言的论述(“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裂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的表述”),作者引入“寓言诗学”的视野,强调了沈从文的书写体现了“爱与悲悯”。[44]它指出了沈从文面对相似场景时,与鲁迅的启蒙态度不一样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叙事(甚或“抒情”)方式。沈从文这种不动声色的冷静也确然让读者感到丝丝寒意。
王德威在《从头说起》中认为沈从文的这种言说“超越了‘一’,超越了中心主义的一元论,最终恰恰返归到历史的有待无穷拆解的本真的领域”[45]。如何理解这种论断?杰姆逊认为历史以文本形式呈现,我们可以而且只能通过文本来触摸和把握历史。而这里的“无穷拆解”则暗示历史“本真”的不确定,但这种后现代史观对我们深入理解文本的文学性效用不大,也并未指出上述场景是何种寓言。当然,王氏所说的“‘亲民爱物’式的人道主义辞令,不足以解释沈写那些最残酷血腥人事的动机”,也点出了作为人道主义者的沈从文以看似淡然的零度写作,暴露冷酷的社会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现实,而这无形中展现了作家对无辜民众的同情。但对于“在悲悯之余,竟多了一层宽容”的“鉴赏”与疏离的态度,我们正可以借助吴晓东在书中操持的意识形态批评利器,探询作家以何种身份可以置身事外,他与那些看客有何不同,与鲁迅的差别在哪里,这种“诗学”的观念核心是什么,这种“寓言诗学”又指向何处,从而丰富对这种另类的“寓言诗学”的认知。

王德威
我们或需领会,一些学者秉持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是在保守(主义)立场上,以所谓“抒情美学”来代替“现代主义”的“启蒙”和“革命”的“大叙事”,从而张扬历史的“多义性”。[46]而这种态度与作者所引用的杰姆逊对于寓言建基其上的“矛盾性”并不等同。如果说,杰姆逊基于“矛盾性”的寓言论述是面对步入后现代的西方世界,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视野,努力以整体性的“认知测绘”来推动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行动的方案形成(如他提出的“跨国资本时代的第三世界寓言”论),那么海外一些学者张扬的“寓言诗学”则是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不可知论”投射到现代中国历史场域,以所谓的“多元”来否定历史的可知性和“发展进步”,从而解构左翼文学的“介入”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而探索真正的“多元”,则应如作者在书中实践的对于矛盾的历史化探寻的道路,比如作者谈到“文化视野以及意识形态远景的缺乏,则使沈从文甚至无法给故事中湘西世界的复杂局面一个哪怕是想象性的解决”[47]。那么我们正可遵循这一原则,揆诸沈从文在书写这一场景前后时的文化视野和意识形态观念,来分析他何以能将此残暴场景与湘西的牧歌情调的图景并置,何以能将“爱与悲悯”化为“宽容”与“鉴赏”,并探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态度与“多元”实践,由此比较“多元现代性”的真实场景及其竞争性关系。
作者深刻地意识到“寓言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领域构成新的挑战,借此生成中国现代的“寓言诗学”[48]。这种寓言诗学的特殊显现方式和本质特性可以予以进一步深究。书中的人性话语强调人性在历史中的形成性,不过尚未对人性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特征加以展开。但作者在书中指出当前对张爱玲的相关研究中存在去政治化倾向,并对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从国族和历史意识方向给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进路,可谓振聋发聩。[49]同时,他又认为张爱玲的审美趣味较难判断其倾向性,也很难厘清其混杂的美感中的新旧成分,因此重要的是去探究哪些历史因素与文化因素参与了其笔下的繁复的美感生成。[50]如果我们从历史化视角对作家与文本进行深入检视,会发现有着特定身世背景(遗老遗少的子嗣)、观念(与“五四”启蒙思想保持距离)与婚恋抉择(与汉奸的结合)的张爱玲,其实远非“普通市民”,因此我们可以遵循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主张,进一步清理张爱玲的“现代都市美感”的历史性特异性,并对她的“古中国”情调中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因素做出细致剖解,由此或将发现作家书写的都市生活的特殊之处,并对其审美趣味的阶级性特征有更多阐发。比如作者谈到张爱玲把空间与时间性结合起来,在空间中填满意义碎片,而这些碎片大都关涉着历史性,比如《倾城之恋》中“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又如《封锁》中所描述的那辆“电车”隐喻着沦陷时代上海的整体生存情境。对这些精辟的见解加以详细阐发,将可以极大深化我们对于张爱玲国族认同与其作品美学之间关系的认知。
这表明书中的一些分析在作者的历史化阐释视野下,实质上蕴含了更多历史化的、政治性的视野和动态发展的思辨内容。比如作者曾经谈到中国台湾学者刘纪蕙和留美学者王斑的早年论述,后者声称现代派诗人所选择的小我向大我的融入,表现出他们习惯于绕过心理分析,直接走入一种“社群思维”的解决方式,[51]从而认为这种可能性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没有获得完全展开的途径而又重新被“大他者”捕获。但这些学者表面上历史化的论断其实正是对历史发生的前因后果的省略与简化。因为不但刘纪蕙对这些作家“走向大我从而使自我向类属皈依”的简单化论述是出于对这些作家“转向”左翼立场的不满,而且王斑早期著作对“崇高美学”的贬抑,也是出于特定时代过激反应下的反拨冲动而诉诸的心理化图解,而他在后来已经对将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运用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场域的不适用性做出了反思。[52]与这些学者观点不同的是,作者在书中中肯地指出1940年代知识分子进入社会历史,打破了先前自恋的狭隘空间,开辟了重建新的自我的可能。
这种从历史即广义的“政治”角度切入检视美学问题的方法,可以以书中对卞之琳1940年代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的分析为例加以说明。这一不寻常的“诗化小说”“以一种诗意的升华方式处理延安时期的心理体验、日常经验和政治感受,试图以诗意话语去兼容和呈现群体政治话语的政治无意识”[53]。虽然这是一般文学爱好者更偏好的文体,但在作者看来并非成功之作。这是因为在作者的视界里,文本中的诗意同时是政治的某种症候,诗意在这一作品中通过“政治诗意化”过程而成为“政治的诗意”。这种诗学图景由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性”,而“政治诗意化的具体途径,就表现在比喻和象征性的话语修辞之中”。由此,作者将作品中“诗意想象、诗化细节与政治符号、政治语境之间”具体纠缠在一起的图景在话语修辞层面的表现进行了剖解,最终认为书中与战争场景相关的诗化意念和诗意联想缺乏了分寸感和真实感,反而不如另一位洋溢诗意的革命作家孙犁表现的战争浪漫主义,因为后者具有心理真实感的基础和经得起真实性检验的细节。[54]保留其阶级惯习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疏离感使得卞之琳的文学实验无法成功,而深入斗争实践使得作品带有真实历史情境书写的孙犁则抒发了具有可感性的诗意。这种具体的历史化阐释,超越了传统的人文主义解读,脱离了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陷阱,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的主体性立场和辩证法的魅力,也由此建构了自身研究的主体性。
结 语
《文本的内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实践着总体性辩证分析和杰姆逊倡导的历史化/政治性的阐释,通过“历史化”的工作阐明“文学性”如何包含“历史性”的内涵,“历史性”又如何促成“文学性”的生成,从而辩证解释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为沟通“现代主体(性)”建构与美学形式、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有机关联进行了深入的尝试,为作品的美学或诗学结构的探索打开了新方向,同时也蕴含了超越传统人文主义解读方式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模式的动能。这一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进路,实现了范式和方法的更新,进而建立了研究的主体性。
在分析鲁迅时,作者引用竹内好的论述,指出鲁迅的文学的自觉的核心是主体的真正自觉的过程,而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孙歌所阐述的“发自内部的自我否定”。作者认为,这给我们提供了鲁迅在自我挣扎、自我否定中建立自己的真正历史中的主体的形象。他更进一步指出它对当今研究者的启示:“我们今天缺乏的正是研究者自身的通过挣扎和自我否定过程的主体性的建构,缺乏的正是这种自我否定的知识。”[55]其实,我们在书中看到分析思路与方法不断拓展、日益成熟完善,正显现了这种研究者的主体性态度。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接受新理论、新方法、新思路的挑战,取其精华而化为己用,并在不断反思中探索建构研究的主体性,是该书在成功实践历史阐释学的过程之外给予学者们的有益启示。
王晓平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09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7期)
注 释
[1]参见李遇春《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2]作者说道:“中国诗歌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始终慰藉着整个二十世纪也将会慰藉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二十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与干涸。”吴晓东、洪子诚:《文学性:经典与阐释——与洪子诚先生对话》,参见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2页。
[3]参见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8页。
[4]这是因为作者认为“文学天生就具有某种感伤、颓废、游戏、为艺术而艺术的禀性,文学艺术的更本原的更根本和更持久的魅力可能恰恰隐含在这些范畴中。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上述范畴更能体现人性的渴望和深度”。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8页。
[5]关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出处和在中国文学界的流传经过,可参见刘为钦《“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6][7][8][9][10][11][12][13]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7、29、2~3、3、15、3、12、13、11页。
[14][15][16][17][18]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4,5,7,371、374,162~163页。
[19][21]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16~17、10~11页。
[20]与传统中国诗学提出评判作家作品时要“知人论世”不同,笔者曾经指出“知世论人”才是适当的分析的方式,即在了解时代和历史语境的“潜文本”的前提下,才能充分认知文本的内涵。
[22][23][24]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2、21、162页。
[25][26][27]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164,331~332、340~343,157页。
[28]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46页。又,笔者《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小说研究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即尝试将现代性问题非本质化,将其在现代中国的多元景观通过1940年代三个政治区域的文学文本中不同的“现代想象”加以具体化。
[29]作者解释这样做的“好处是使现代性的范畴成为一种叙事,成为一种可在历史叙事中进行分析的范畴,现代性的真实视野也必须在历史叙事中展开”。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46页。
[30][31][32][33][34]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8,57、60,67,68,69页。
[35][36][37]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77,77、79,78页。
[38][39][40][41][42]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408,88,460~461、464,19,163页。
[43][44][45]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33、20、31页。
[46]参见王晓平《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和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以王德威的研究为中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47]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48页。
[48][50]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34、39页。
[49]作者谈到“以空间因素消解张爱玲小说中的时间感和历史意识,是近来张爱玲研究中的问题所在”,因此需要纠正张爱玲研究中的去历史化倾向所带来的问题。作者由此从“空间的时间化”的角度,指出“摩登上海中不止是光怪陆离的空间图景,也有记忆、历史、时间”,而“时间意识的背后还牵涉着文化历史传统与民族国家理念”。这种充分语境化达到了历史化的程度,使得作者深刻认识到“在战争这个总体背景中,张爱玲发掘的个体记忆以及所谓的‘大记忆’最终则把我们引向沦陷空间中的国族问题以及历史记忆问题”。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281页。
[51]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123~124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引的作者的相关语句在文中只是一笔带过,作者未对此展开阐述,因此不影响其整篇论文的主体论述。
[52]这是2016年暑期王斑与笔者在厦门大学会面时提及的。
[53][54]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381、381~382页。
[55]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第8~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