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歌《平乐县志》,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春卷,同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
内容提要
作为“平乐镇”系列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平乐县志》延续了方言文化和县城叙事特质,并赋予了小说更复杂的形式、更驳杂的情感。《平乐县志》创造性地将传统说书体融入现代叙述,生成了一种能够接纳更多层次读者、生成更多维度阅读效果的叙事伦理。同时,《平乐县志》的叙述也内含着世界的目光,世界与地方的关系构成了小说最内在的精神结构,小说结尾的开放性也表征着一种徘徊在“家”与“世界”之间的情感矛盾。《平乐县志》是“平乐镇三部曲”的终结篇,这一系列小说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平乐镇”文学地图。颜歌“空时性”思维性质的绘图方式,也为“后全球化时代”重建地方叙事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 键 词
《平乐县志》 古典形式 叙事伦理 中国叙事 后全球化时代
导 语
2023年,颜歌完成了“平乐镇”系列第三部长篇小说《平乐县志》。出版后,颜歌直言:“《平乐县志》以后,写方言和写平乐镇都应该是暂时画下了句号。”[1]“《平乐县志》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对明代话本小说叙事腔调的拟仿。”[2]《平乐县志》直接借鉴古典拟话本文体,小说叙事者就像古代说书人一样,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时不时地站出来发表感慨、评论世事。可以说,《平乐县志》创造性地融合拓展了“平乐镇”系列小说《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所探索实践的文体形式。文体形式层面的集成,意味着相比于之前的“平乐镇”故事,《平乐县志》容纳了更丰富的经验、更复杂的情感。
在“平乐镇”系列小说里,《五月女王》的叙事人是以孙辈的视角讲述南街上“巨人”袁青山的人生,这是爷爷辈念念不忘的、属于过去的“志怪”故事;《我们家》讲述的是西街上豆瓣厂厂长一家的荒唐闹剧,叙事是以女儿的视角言说和审视父辈的生活。《平乐县志》处理的是当下的经验,故事主要发生在东街、县政府大院,小说中陈地菊的人生遭际可以视作“我”这代人的故事。但为了把陈地菊的生活处境和情感选择写通透,小说用了大量笔墨写她身边的人,如叶小萱、傅丹心、傅祺红,这三个人也可以视作小说的主角,写他们的时候又关联叙述了更多的人。相比于《我们家》《五月女王》,《平乐县志》呈现了更多层面的平乐县生活圈,触及了平乐县官场内部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关系网。当下的经验和属“我”的情感,使得《平乐县志》不只是在空间层面补充拓展“平乐镇”文学版图,更是以新的情感立场和文化理念重新讲述“平乐镇”。颜歌所谓“暂时画下了句号”,意味着她心目中的“平乐镇”文学地图已绘制完整,同时也暗示,《平乐县志》是颜歌对于故乡情感、对于平乐镇生活经验的总体性交代,完成了一出“漫长的‘出平乐镇记’”[3]。

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三部“平乐镇系列”作品:《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一 “说话体”:古典形式的现代转化
文学如何才能讲好当下?“用文学的表达来写当下一直是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毕竟,‘当下’太庞杂纷繁,而我们自己也是依然身在此山中的处境,无法找到一个妥当的叙事角度。后来我想到其实我想写的这个‘当下’和明朝时候的那种繁茂和多重复调的感觉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觉得可能用‘三言二拍’的方法来写当下是一种合适的处理。”[4]颜歌乐于在文体上拟古求新。《关河》讲“史”,《异兽志》说“怪”,《声音乐团》用“套盒”,“平乐镇”系列的《五月女王》围绕一个女巨人写“地方怪事”。但此前探索的文体形式,主要还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或是为表现一些难以言说的青春情绪。《平乐县志》对明代拟话本文体的借用,是希望更好地表达庞杂纷繁的当下经验。处理“我”的、还在进行中的经验,颜歌再难像《五月女王》那般以“外来者”的视角纯粹地讲述平乐镇的怪异人物,也不可能如《我们家》那样用一种戏谑的叙述腔调贯穿全文。
借鉴“三言二拍”拟话本文体来写《平乐县志》,意味着采用全知型的叙事视角,叙事者身在其中又超离现场,把控每个人物的命运走向,深入故事内部、切身入境地讲这些平凡众生的所言所行与所念。作家也需化身为传统的说书人,一边从容地讲故事,一边根据需要随时从故事中抽身出来对小说中的人和事评点议论。但《平乐县志》的全知叙事,不是回归古典小说那种平面的故事讲述和道德说教。颜歌综合现代叙事技法,激活并再造了传统全知视角的叙事功能,将平乐镇东街上显露的事迹、隐秘的人心以及被潜规则支配的官场等一并呈现,既让我们看到“平乐县”内部的罪业与悲情,同时也让读者对生活在其中的、被人世间的贪嗔痴所折磨摧残的普通人产生同情和悲悯,从而将古典的全知叙事转化成了现代的、有情的叙述。颜歌说过,自己的写作需要走进人物、把握一种“情感真相”:“有的作家可以完全把小说建立在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而对我来说,每一个故事,不管看起来和我个人的距离是近还是远,都必须有一个和我个人很贴近的情感真相。就好像如果写一部长篇是要在新的宇宙中来构建,无中生有的话,那么这个情感真相就是我构建时候的立足点。”[5]对人物有情,《平乐县志》的叙事伦理也不再是单向度的批判或说教,而是多维度的共情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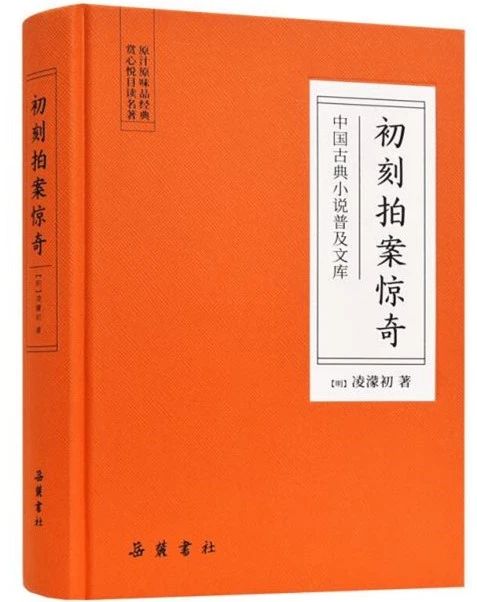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岳麓书社2019年版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明代“三言二拍”地位特殊,它们意味着中国古典小说开始由史传笔记向现实题材过渡,意味着小说家“开始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走向文人独创话本小说的道路”[6]。《初刻拍案惊奇》原序言写道:“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7]其点明要写出日常生活、当下现实中的“谲诡幻怪”。要书写当下的经验,未必就一定要用“三言二拍”文体。颜歌看重这一文体能够容纳庞杂繁复的现实生活,细究起来理由并不充分。“三言二拍”这些拟话本小说喜欢讲道理,动不动就进行道德劝诫,这对于现代以来的小说创作而言,乃是大忌讳。颜歌很清楚这一问题,为此颜歌采用“三言二拍”文体的缘由可能是:
这个说书人的声音是我从很多明清小说里面的说书人的声音中概括出来的一个通用的说书人声音。我想把它用一种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一直在背景里回响着的,所谓的“说公道”的声音,表达这声音的偏颇、狭隘、自相矛盾和厌女——这是我们作为读者和听众应该去听从和相信的权威声音吗?这是我想留下来的一个问题。[8]
《平乐县志》里“说书人”的声音,并非简单用来评点故事人物和议论世道人心的“说公道”的声音,小说插入的各种道德话语和引经据典的“生活哲学”,是颜歌要反思和剖析的对象。小说中“说书人”所讲的各种道理,就类似于傅祺红训斥他儿子傅丹心时总要念叨的那些“生活道理”。傅祺红是个读书人,自视甚高,时不时吟诗赋词、引经据典,说起事来是一套又一套的道理。但如此多的道理、经典,却并没有让他走出偏执,反而是越走越偏,他那些“道理”甚至成了导致傅丹心幻听的梦魇之声。比如,傅丹心决心要去掺和赌球活动时,他对妻子陈地菊保证说这是稳赚不亏的活,发誓自己会保持头脑清醒,这时“说书人”来了一段“道理”:
傅丹心提的这门生意听起来有点陡,但它背后的道理还是实在的,也就是说无险不生财,无变不成功。毕竟《周易》里面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后来又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都是在跟你说,人呐,过就要过个活套。[9]
其反讽意味一目了然。“说书人”“不公道”的“道理”并非劝诫之文,颜歌将“说公道”的声音填充到“平乐镇”的故事当中,让这些“道理”与故事、与人物命运遭遇形成悖反效果,她借着传统“说书人”的口吻讲民间的“道理”,同时又用现代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去解构那些“道理”,总体而言形成一种戏仿意义上的反讽叙事。戏仿不同于一般的模仿借鉴,它是通过变形和夸张的方式来引起读者的思考。将古典的全知叙事化为现代的有情叙述,用当下的经验解构传统“说公道”的声音,这是《平乐县志》在文体形式层面所完成的现代转换。

戴树良作品《讲评书》(成都风俗画)
图片来源:“成都方志”微信公众号推文《他画活一座老成都》
《平乐县志》的全知视角,引导读者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同情作品中的某个人、某些事,让我们对人物和故事有更多视角的观察、更复杂的伦理判断。同时,《平乐县志》中借“说书人”“说公道”的声音,呼应或阻断阅读进程中可能浮现的情感反应,但作家又通过故事的推进拆解了“说公道”的声音,形成多层次的、辩证式的叙事。预设读者的情感反应,给出“说书人”的判断,同时又拆解它,这个过程意味着《平乐县志》有着相对复杂的叙事伦理,这不是古典小说说教型的叙事伦理,也不同于追求零度情感和客观叙述的现代叙事伦理。詹姆斯·费伦讨论修辞叙事体验时认为:“正如有一个事件的进程一样,也存在一个读者对这些事件的反应进程,这一进程根植于观察和判断的双重活动中。因而,从修辞的角度来说,叙事性涉及这两种变化的相互作用:人物经历的变化以及读者在对人物变化不断做出反应的过程中经历的变化。”[10]借助詹姆斯·费伦这一“修辞叙事”论述,可以帮助发现《平乐县志》可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综合了小说叙事进程和读者反应的叙事伦理探索。“说书人”评价故事中的人和事,更瞄准读者阅读相应情节时可能出现的情感反应,“说书人”同时在评价读者的阅读体验。小说经常借用话本小说中的表述——“各位看官”“在座诸位”等,由此向着“看客/读者”说“公道话”。由“说书人”直接发出的“说公道”的声音,针对故事中具体的情节事件发出人生感慨,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伦理。现代意义上的叙事伦理并不需要作家直接给出伦理判断,作家只需要讲好故事,通过叙事呈现人物的命运、伸展个体生命的感觉,读者通过阅读跟随叙事获得一种生命体验,这生命体验本身即是一类伦理感受。《平乐县志》的现代叙述艺术引导读者多维度地理解陈地菊、傅祺红、傅丹心等人的生活变故和精神处境,读者对人物产生共情之时,也意味着体验了一种生命存在,这是典型的现代叙事及其伦理反应。融合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的叙事伦理类型之后,小说所能引发的伦理效果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如果读者既能关注到“说书人”形式的独特性,也能理解故事人物的生命境遇,可以打通小说中的“生活道理”与“生命经验”,这就意味着把握了小说的反讽叙事及其敞开的意义结构,可以收获更复杂的阅读感受和伦理判断——包括人物的复杂性、情感的复杂性、“说公道”声音的复杂性等等。总而言之,《平乐县志》激活了传统话本小说的说教型叙事伦理,将其与现代叙事伦理融合之后,创造了一种能够接纳更多层次读者、生成更多维度阅读效果的叙事伦理。

詹姆斯·费伦:《体验小说:判断、进程与修辞叙事理论》,唐伟胜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二 “世界”的目光:地方、家庭及其文化反思
《平乐县志》小说主线是讲述陈地菊的爱情和婚姻变故,副线是县志办领导傅祺红的“县志”编撰日记。主、副线背后,还可以划分出更复杂的“多线”:主线并非只写陈地菊这一个人的情感故事,而是呈现陈地菊背后一大群不同身份、不同角色人物构成的最世俗、最真实的县城生活;副线的“傅祺红日记”,既是关于“平乐县志”和官场事迹的笔记,更是个人日常生活和情绪感触的记录。故事线的繁复,意味着小说可以延伸出很多主题。《平乐县志》不只是“县志”,更是关于地方文化、家庭情感、女性觉醒、官场腐败、市民生活等多种主题的故事。《平乐县志》的审美层次,可通过叙事艺术分析读者审美反应和伦理判断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也关联着文本本身的多义性。
傅祺红的十三则“日记”逆着故事时间,由2010年1月13日倒叙至1980年6月25日,向前延长了《平乐县志》的故事时间,也彰显了小说之为“地方志”的叙事特征。“日记”的内容,与陈地菊、傅丹心的情感故事,并非简单的内容层面的“互补”“呼应”关系,它更是补齐了傅祺红、傅丹心的人生。这个倒叙的“日记”,可视作傅祺红的“人生录影带”[11],也可作为一种“县城人生”的隐喻,以此与陈地菊的人生形成对照。主线故事是从叶小萱找女婿、陈地菊与傅丹心闪婚开始,副线的“日记”是倒回到傅祺红与汪红燕相亲的时间,这一头一尾的“相亲”衔接必然不是随机的。傅祺红大学毕业后回到平乐县,经历了政府办的高光时刻,后来被调去县志办做了几十年的副主任,在即将退休的年龄被提为主任,但很快就陷入了腐败旋涡、走向了绝境,这是一个悲剧人生。陈地菊也是大学毕业,在大城市工作多年后因情感变故回到平乐县,做了多年银行前柜,后来在傅祺红的走动下,经历了一段“要去政府办”的风波,最后对婚姻、工作都彻底失望,下定决心要离开“平乐县”、出国开始新生活……两个“读书人”都是回到“平乐县”,最后是两种走向:一是进入体制内,在官场默默无为,最后被卷入名利旋涡,身败名裂;二是放弃地方上的一切,去往世界,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两条线索所呈现的两种人生选择及其命运走向,暗示《平乐县志》的叙事结构背后,还有着更内在的精神结构,即由县城叙事关联起来的“地方”与“世界”这一二元关系。
《平乐县志》中的“地方”书写是一种文化反思和情感追述,“世界”想象则是作为一种拯救性的力量来想象和书写。因为有“世界”这一远方的、可供想象的空间,陈地菊才不至于重走傅祺红的老路。《平乐县志》的所谓“世界”,不只表现在人物最后选择了出国留学,更是作为一种文化和思想的“目光”在审视和照亮着人和事;“世界”不只是与地方相对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世界,也作为一种超越地方经验的文化视域、思想格局。《平乐县志》中的陈地菊形象,是直接彰显“世界”的精神存在。这个能让人联想到颜歌自身经历的小说人物,自小就与身边的“平乐县人”格格不入,成人后也经常处于“离皮离骨”的精神状态,这一性情与她喜欢读文学书、能够通过阅读想象一个与平乐县不一样的“世界”相关,但这更是作家赋予她的“文学性”特征。[12]陈地菊还经常追问死亡、活着的意义等问题,这些“心思”都超出了“县城经验”的理解范围。叶小萱的人生故事,代表的是典型的县城经验,她了解到女儿要辞职后追问:“你现在也是嫁出去了,成家了,就该清楚过日子不可能是简单的——你看看你妈我,这么多年有哪天不是在熬,不是在忍?”[13]熬、忍,这是县城普通人的“过日子哲学”。有文学性情、被“世界”点燃了内心之火的陈地菊,岂能轻易遵从?“文学化”的性格、超越地方经验的视野,这是陈地菊身上的“世界”品质。“世界”维度的存在,让陈地菊的人生经验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性。在卖完房子、处理完身外之物后,陈地菊彻底解脱了一般,她走在平乐县街道上,体验了一种“魂魄飞升”之感。
冷湿湿的风吹在陈地菊的脸上,使她觉得自己的脑壳里头前所未有地清醒。她的魂魄像是升腾了,飞到了一个高高的地方,俯瞰着这街道上的熙攘,三姑六婆、尘垢秕糠——曾经,她自己也在这些人中间,苦痛和愧疚都长在身上,迟疑和自责也坠在心头,真切切、沉甸甸;而现在那所有的一切却忽然变得轻巧又荒唐,像是哪个随口编出来的一则故事。[14]
随着故事进展,陈地菊内心意识中“世界”的轮廓变得清晰之后,她也豁然开朗。街道上的熙攘人群,县城里的肮脏尘垢,包括陈地菊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苦痛、愧疚和不甘,都变成了一种“对象化”的、供人审视和回味的“故事”。

张楚:《云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冬卷,首发时题目为《云落图》)
颜歌笔下的“平乐县”是需要逃离的“地方”,这与同年出版的张楚的《云落图》中的“云落县”有一定的可比性。张楚笔下的“云落县”塑造了有情有义的万樱和来素芸。[15]如果一个“县城”有很多万樱、来素芸这样的普通人,这“县城”将不再是让人绝望、使人逃离的“地方”,那些从外面回到“县城”的人,更有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归宿感。但在颜歌的《平乐县志》中,小市民身上只见斤斤计较、嫌贫嫉富、自私狭隘;县城官场只有无处不在的腐败,人与人之间只是相互利用,为了一点利益可以构陷污蔑、落井下石;县城商界更是在黑社会势力的掌控之下;“女性情谊”也是被身后的丈夫/男性关系所主导。“平乐县”人大多陷于贪痴嗔泥潭,人物之间难见超越世俗利欲的情和义。这里的“地方”需要有“世界”这一出口,才能看到希望。
虽然“平乐县”里找不到似“云落县”里的可信、有情的“附近的人”,但是颜歌把她对故乡、对地方的“情感”赋予了“平乐县”的“家”。让陈地菊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的因素,不是“附近的人”,而是“家人”。《平乐县志》写了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的主要人物傅祺红、叶小萱虽不是道德上无瑕的“绝对正面形象”,但他们对家人尤其对陈地菊是有真情的。叶小萱是斤斤计较的市侩刁民,作为母亲,对于女儿陈地菊很多不寻常的选择尽管不理解,但最终也都能给予经济上、情感上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包含了很多非理性的、一厢情愿的、可能导致恶果的行为。傅祺红作为县志办的小领导,在官场上窝囊、见利忘义,在家庭内部,作为父亲对儿子傅丹心是“爱之深、责之切”,这导致了很多不好的后果,但他对儿媳陈地菊却是真正的欣赏和关心。傅祺红没能坚守原则,最终沦为官场上的棋子,也是想着能为儿媳陈地菊谋一个“稳定”的公务员身份。陈地菊与她的家人之间有着最传统的情感,他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希望他们的“小家”变得更好,即便很多时候事与愿违。颜歌对“家”的书写,虽有审视和反思的思想基础,但“情”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项飙相信“密切关注附近,包括其中的多重裂缝,将有助于更现实、更细致入微地理解世界。毕竟,附近本身就是一个世界”[16]。《云落图》所谓对“附近的人”的关注,是希望回到地方、回到生活世界去“更细微地理解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民族-世界意义上的“大世界”,而是个人生活层面的“小世界”。颜歌的目光,不是要回到地方“小世界”,而是要去往海外“大世界”。颜歌对“家”的重视,是身在异国对于故乡故国的情感表现,在这份情感内部,也潜伏着“世界”的目光。颜歌对“家”的书写兴趣,尽管在之前的《我们家》中已有了清晰的表现,但《平乐县志》的“家庭叙事”更添了世界性的文化视野。在《我们家》里,“家”是纯粹的、客观的书写对象,叙述者“我”以一种轻松揶揄的口吻讲述着父辈生活中的隐秘事情,有审视,也有同情,但这里面还没有文化比较的意味。在《平乐县志》里,虽没有直接写到西方的“家”,但作家赋予陈地菊身上的那种犹豫,尤其结尾处陈地菊“回家”后选择“个体获救”还是“守护家庭”这一悬置,就很清晰地意味着一种“世界”的目光:“陈地菊一个人往前走,想着自己即将要踏上的路,要去到的地方。她似乎还没有听到那尖锐的悲鸣,心里面依然充满了希望。”[17]陈地菊处理完一切,充满希望地准备回家摊牌离婚时,傅祺红已身败名裂、服药自杀。回到家、“听到那尖锐的悲鸣”之后的陈地菊还能一走了之吗?她真的能够无视傅家的悲惨遭遇、单纯为个人的前途而去吗?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叙事设置,每种选择都朝向不同的伦理判断:留下,是对家、对家人的深情守护;离开,是解脱,是个体的获救。留在地方上的“小家”?还是去往世界寻找新的希望空间?现实的选项只有两种,但作为审美对象,这一不确定的结尾就是第三个选项。每一个从地方去往世界的人,身体都会作出最现实的选择,但心灵、情感或许永远都摇摆在去与留之间。
“家”是构成《平乐县志》“地方-世界”精神结构的核心所在。就小说内部的叙事来看,陈地菊“漫长的”去往世界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成家”与“离家”之间徘徊的情感历程。回到平乐县工作之后,陈地菊在母亲的催促之下多次相亲,但最后还是顺着自己的心意选择了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甚至以一种“先斩后奏”的方式草率地“成家”了。通过两个人的爱情实现自立自主是第一重的“离家”,这是离开“传统之家”。但因为经济能力,他们还得继续住在父母家里,各方面都受到傅祺红的约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家”、“立家”和“离家”。结婚后的几个月内,陈地菊更进一步地体验到了爱情意义上的“夫妻之家”也不可靠。婚后情感关系、家庭生活上的委屈与不堪,直接将陈地菊推向世界,这是第二重的“离家”。

颜歌:《我们家》,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经历了走出传统家族、家庭,追求个体自由与独立的“现代化”过程,但无论如何“走出”,中国人心目中的“家”依然不等于“契约”意义上的关系。陈地菊“去往世界”过程中所有的徘徊、犹豫与困惑,都是突出法律关系之外的“情”的牢固性。“家”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着割不断的“情感”,而非简单的随时可解约的“契约”。有情感牵连的“家”的存在,作为故乡的“平乐县”才值得身在海外的作家去怀念、去想象、去书写。当然,“情”只是《平乐县志》的一个出发点、一种基调,颜歌的“世界目光”,不是直接的怀乡、恋家,而是通过重新审视“家”及其内部的情感含量,对以“平乐县”为典型的中国更多地方的生活传统和人性状况进行文化反思。《平乐县志》对中国传统家庭理念的伦理反思都是通过表现陈地菊的“去往世界”来完成的。陈地菊的“离家—去往世界”要摆脱的并非“家”,而是逃离“家”所在的那个遍布着文化痼疾的“地方”。其所谓“离家出走”是离开那个有着无数痼疾的“地方”,而不是离开“平乐县”那个生养她的、有亲人的“家”。
三 “生产地方性”: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叙事”
古典与现代,叙事与抒情,地方与世界,个体与家庭……《平乐县志》携带了丰富的文化议题和审美可能性,它以现代的精神有效地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和抒情传统,也以“世界”的目光重新唤醒了地方书写、家庭叙事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可能及其文化意义。《平乐县志》作为颜歌移居海外之后创作的汉语小说,其清晰的中国小说的外壳、清醒的现代叙事精神以及超越地方的“世界性”文化视野,多维度地彰显了“中国叙事”的美学魅力。
21世纪以来,很多中国作家、评论家开始探索实践“中国叙事”、建构“中国叙事学”。2001年莫言推出新长篇小说《檀香刑》,一改之前的西式魔幻风格,融合古典“说书人”以及民间“猫腔”等很中国、很本土的文体形式来讲故事。李敬泽曾以札记的形式点评《檀香刑》的“中国小说”特征:
《檀香刑》是21世纪第一部重要的中国小说,它的出现体现着历史的对称之美。
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学会了在全球背景下思想、体验和叙述,同时,我们欢乐或痛苦地付出了代价:斩断了我们的根,废弃我们的传统,让千百年回荡不息的声音归于沉默。
而《檀香刑》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向,同样是在全球背景下,我们要接续我们的根,建构我们的传统,确立我们不可泯灭的文化特性。[18]

左图: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封面
右图:改编自莫言小说、莫言和李云涛共同编剧的《檀香刑》歌剧海报
《檀香刑》开启了21世纪中国作家探索实践“中国叙事”的新里程,此后越来越多的作家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通过借鉴说话体、史传体、编年体、章回体以及世情、志怪、传奇、笔记等传统笔法,不同维度、不同程度地实验和拓展着中国古典叙事资源当代转化的可能性。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品有林白的“纪录体”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2003)、莫言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生死疲劳》(2006)、金宇澄的“话本体”长篇小说《繁花》(2012)、格非的“说书体”长篇小说《望春风》(2016)、贾平凹的“方志体”长篇小说《秦岭记》(2022)、叶兆言的“史传体”长篇小说《仪凤之门》(2022)、魏微的“编年体”长篇小说《烟霞里》(2022)等。这些小说对相关古典文体形式的借鉴,内化于更具艺术感的现代性叙事和地方性语言腔调中。颜歌的《平乐县志》在运用中国古典小说文体形式方面,比之大多数借鉴古典叙事资源的中国小说而言,表现得更为大胆、清晰、深入。
在创作《平乐县志》之前,颜歌已开始从事英文创作,这种经验让她领悟到不同语言的写作意味着遵循不同的文化传统。“她越发渴望在中文写作中,体现中文性与中国文化里的文学传统……”[19]基于一种世界文学视野和比较性的文学创作经验,颜歌意识到汉语写作也需要凸显中国文化传统。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初版于1996年3月)
颜歌《平乐县志》的成功实践可以为当下的“中国叙事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开拓方向。傅修延曾呼吁:“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理论,让中国叙事文学在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这是我们进行叙事研究的最基本的目的。”[20]在学术界,通过理论研究的途径强调“中国叙事文学”在世界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在浦安迪、高友工等汉学家那里已经基本完成。对于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叙事理论研究者而言,最值得开拓的或许是中国古典叙事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是其如何更有效地作用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让更多蕴含“中国叙事”品质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丛林中获得瞩目。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尤其是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演讲,直接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文学“讲故事”传统的伟大与悠久。但这还不够,需要更多能够彰显“中国叙事”品质的作品获得世界影响力。“中国叙事学”的理论话语建构,也需要回到这一基本的目标上来,助益更多的“中国叙事”作品走向世界。《平乐县志》所蕴含的“中国叙事”品质,不只是它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也不等于小说讲述的“平乐县”版图内的地方故事及其使用的四川方言等,这些古典性、地方性元素是很多“中国叙事”作品的共性。《平乐县志》的独特意义,是相对于“后全球化”时代而言,它以彰显“中国叙事”的方式拓展或重建了地方叙事新的可能性。21世纪已进入“后全球化”阶段。从全球化到后全球化,其文化层面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后全球化”时代是去中心或多中心的全球化;二是在新技术、新媒介的影响之下,全球化进程已走出了空间意义上的“跨文化”阶段,导向了时空并置性质的“超文化”状况;三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意义上的“后全球化”。《平乐县志》的故事时间,正是世界由全球化滑向“后全球化”的阶段。它不仅仅是讲述中国“平乐镇”的故事,更是以“中国叙事”的面目综合性地表现了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并以中国的地方经验回应了“后全球化”时代如何生产地方性知识的历史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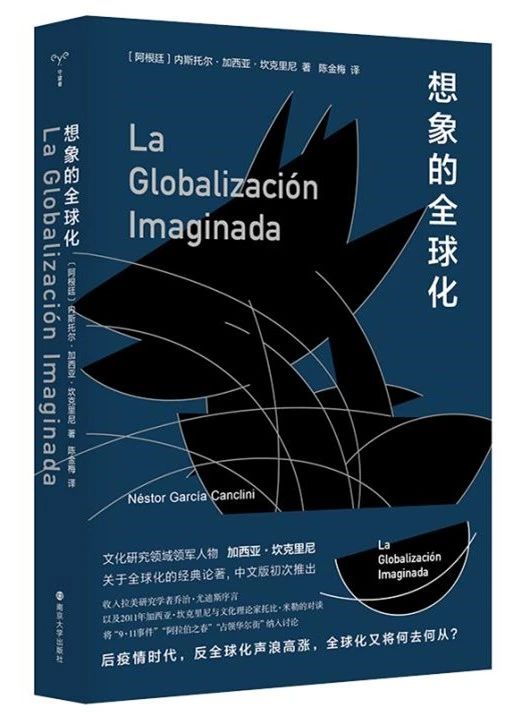
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想象的全球化》,陈金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阿根廷学者坎克里尼指出21世纪出现了“去中心化的全球化”现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新自由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宣告破裂,世界各地同时涌现出多种新的样态和可能。”[21]在之前的以西方为世界中心、全球化等于西方化或美国化的阶段,很多“第三世界”作家想象的“去世界”往往等同于“去往西方”。这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迁移,更是文化认同上的“奔向西方世界”。这一阶段的文学对于故乡、故国的书写,都以否定和批判为主,情感都相对决绝。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新自由主义性质的、西方中心意义上的全球化,而是多中心、多层次、多结构的全球化,“第三世界”的作家也不再迷恋某个中心,他们对故乡的表现、对世界的思考可以更客观、更复杂。《平乐县志》对“平乐县”的书写,有很清晰的针对地方上腐败、虚伪、势利等社会问题和文化痼疾的批判,也有对于普通人的深情与悲悯,作家对故乡的情感极为复杂。情感的复杂、悬置的结局,都意味着一种客观、冷静的地方书写和家庭叙事,这是“后全球化”阶段才更可能出现的情况。颜歌有意识地借鉴和发扬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精神和抒情传统,这一文学选择也是“去中心”“反英语文学霸权”的表现。全球化阶段,“第三世界”的作家普遍在学习西方、以西方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创作;但“后全球化”时代,作家能够更客观地看待不同民族文学传统所包含的不同价值,这使得他们在文学风格的选择、叙事资源的征用上更自主、更自由。
仅仅从“去中心”“反英语文学霸权”维度来讨论《平乐县志》的“中国叙事”价值,这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思维,很容易将“中国叙事”背后的“中国元素”奇观化、符号化,很难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在审美和思想上收获影响力。《平乐县志》不单纯是一部相对于英语文学而言、彰显了“中国叙事”的汉语文学作品,它也是“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了地方性文学魅力的中国小说。全球化没有带来理想意义上的“地球村”,但借着新技术、新媒介的作用,地球上的各种“村”的确已经不再“与世隔绝”,地方与世界的关系也不再是距离的远近、空间的隔绝;因各种文化的重叠和融合,地方上独特的“时间感”“历史感”也逐渐淡化,甚至导向了韩炳哲所谓的“去除了自然性”“摆脱了血缘和土壤”的“超文化化”状况。[22]“超文化化”意味着“文化的去事实化”,对于“地方”而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属性。雷尔夫曾感慨:“今天,有一种氛围正在四处蔓延,那就是前工业社会与不自觉的手工艺文化所代表的地方与景观,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地方性和多样性正在不断减少,以至于完全消失。”[23]“后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是丧失了时空感的地方,如此背景下的“地方叙事”如何可能?颜歌“平乐镇”系列小说正是在丧失了时空感的“地方”重建一个“空时性”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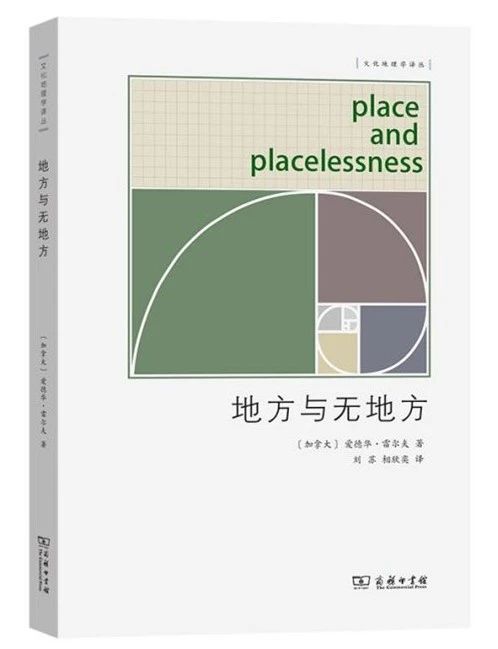
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颜歌对“平乐镇”写作计划有一个解释:“平乐镇是虚构的一个川西小镇,是从很多川西小镇里概括出来的一个理想版图。我可能也有这样一个野心,让平乐镇的世界更清晰,从时间线上、空间线上,多角度去阐释和完善。我希望最后出来的东西能打下时代的烙印,能在一系列的作品中,呈现小镇一个宏大的风貌。”[24]这一自述说明颜歌创作“平乐镇”系列小说时有很清晰的“绘图”意识,试图建构一个能够容纳自身情感记忆和生活经验的“文学空间”。文学叙事意义上的地理绘图,并非要还原或纯粹地反映某个真实空间。罗伯特·塔利说文学绘图是打造一面“空间性的镜子”:“故事叙述者像制图师一样,在作品中创造出对世界的表征,但这种表征并非以更具比喻性的形式纯粹反映那个‘真实’的世界。”[25]颜歌记忆中的那个作为“故乡”的“地方”,或许早已消逝,颜歌在“平乐镇”投射了她对故乡、对时代、对现实、对世界的情感、记忆和理解。
颜歌绘制的“平乐镇”文学地图,首先铺下的是空间维度的街道规划,然后才是街道内部人物、家庭的成长故事和历史事迹。《五月女王》讲述南街上袁青山的人生;《我们家》通过揭示父辈的家庭生活,围绕豆瓣厂串联起了西街上的人情和生意;《平乐县志》则把目光转移到东街。东街、西街、南街,加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的“江西巷”“宝生巷”等等,将这些街道上的故事展开,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平乐镇”文学地图。
绘制地图看似是在空间层面横向地讲述“平乐镇”的人物故事,但“三部曲”的每一部又融合了历史的线索。比如《五月女王》主线故事交代了袁青山完整的一生,副线故事又以“小小说”的结构缩略性地交代了“平乐县”无数个神奇人物的人生。《我们家》故事时间很短,但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关联着豆瓣厂的历史,豆瓣厂的历史也就相当于平乐镇的过往。《平乐县志》里傅祺红的日记也是直接呈现平乐县的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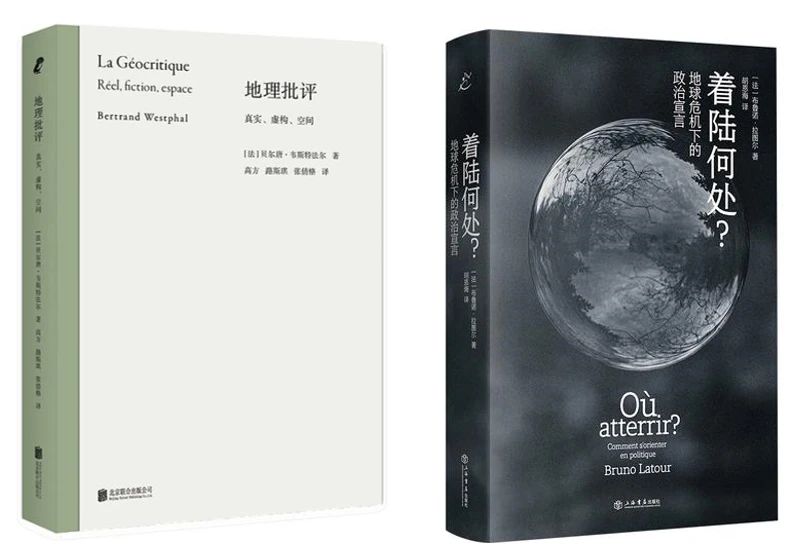
(左)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高方、路斯琪、张倩格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
(右)布鲁诺·拉图尔:《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胡恩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版
韦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中阐述了二战结束至今空间思维逐渐支配时间观念的历史过程,提出了“空时性”概念:“至高而又独立的时间性的统治已经终结;空间的反击创造了势均力敌的全新局面。从今以后要把时间倾注在空间里并让位于空—时。”[26]“空时性”强调空间的重要性,意味着时间、历史问题将通过空间获得表达。传统的地方叙事,多指向个人成长史或家族史意义上的“地方史叙事”,这是时间观念主导的历史叙事。颜歌“平乐镇三部曲”与之不同,这“三部曲”虽有主要人物的成长事迹,但也有与主要人物同等重要的“平乐镇”人物群像。相比于时间性质的“地方史叙事”,“平乐镇三部曲”更是空间性质的、重在表现“平乐镇”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地方性叙事”。《五月女王》在讲述袁青山成长经历的同时,更浓缩了“我爷爷”、高木匠、何胖娃、张仙姑等十几个平乐镇人物的生命事迹,而且小说后半部分袁青山进入仓库之后,主要人物已转变为袁清江、张沛等人;《我们家》的叙事虽聚焦在薛胜强身上,但小说更是借用薛胜强这个唯一还留在平乐镇、继承了家族企业、作为豆瓣厂厂长的独特身份,关联讲述整个薛家及与豆瓣厂有关的一大群人的人生状况;《平乐县志》更为典型,陈地菊只是连通两个家庭的关键角色,小说更大篇幅其实是写傅祺红、傅丹心、叶小萱等一大群“平乐县”普通市民的生活情状。较之于塑造经典人物形象,颜歌的“平乐镇”绘图更像是描摹和呈现一个地方的人性状况和生命状态。兼顾空间层面的地理广度与时间方面的历史纵深度,“平乐镇三部曲”呈现了“平乐镇”内部及其背后更广阔的中国县城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罗伯特·塔利讨论“文学绘图”认为:“在世界文学具有无限反射性和投射性的叙事中,读者找到了无数种方式,可以运用想象理解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中的空间和地方,毕竟,这就是绘图的意义所在。”[27]颜歌绘制的“平乐镇”文学地图,为读者敞开了想象中国的空间,同时作为“世界文学”文本,也让我们看到了“后全球化时代”重建“地方叙事”的可能性。
回到地方,重建“地方叙事”,是后全球化阶段的世界性文化现象。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出现很多极端化的反全球化事件,这些现象背后,是更广泛的、全球范围的重新“本土化”浪潮。后全球化时代的回归地方,必然与全球化初期阶段的“地方主义”不同。尚未经历全球化的“地方主义”,普遍是保守意义上的、拒绝异质文化“侵入”的地方保护主义;但经历了全球化的影响之后,所有的地方性矛盾,可能都“同时蕴含着全球性的意义”[28]。今天讨论回到地方、重建地方叙事,并非拒绝世界、否定异质文化,而是探讨如何在传统的本土化与抽象的全球化之间找到一块具有中间属性的“飞地”。正如拉图尔探讨全球化去向问题时所追问的:“我们一直在朝‘全球’演进,把自己投射到一种无边际的全球化愿景里(此处有一种反作用,为了逃避这种看上去不可避免的命运,本土性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但所有这些从来没有任何可以根植的土壤,也没有任何的现实和物质基础。”[29]拉图尔在传统的“本土”与抽象的“全球”之间设想了一个新的着陆方向:“在地”(terrestre)。“在地”继承了世界,但又不把自己限制在“本土”,“在地”意味着与土地、土壤联系在一起,“但它也是世界性的”。[30]拉图尔的“在地”概念或许抽象,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回归地方,但又不是简单地认同地方,而是带着世界的目光重新发现和确认我们生活的真正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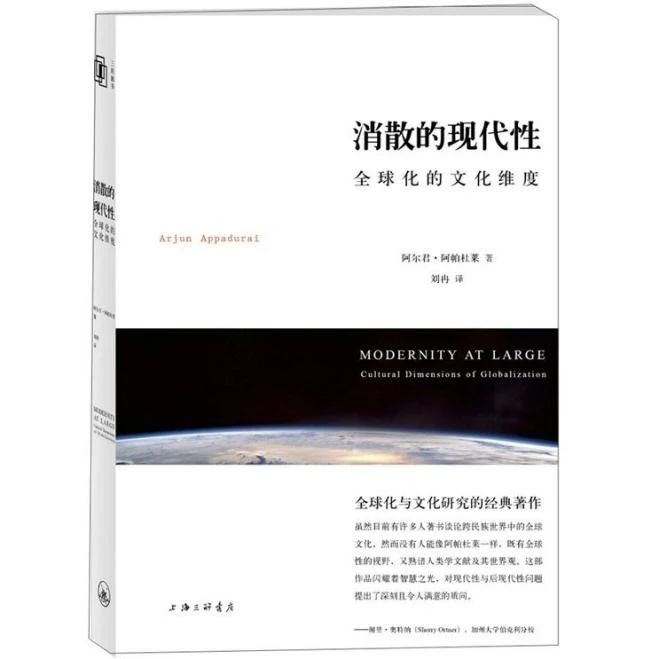
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颜歌绘制的“平乐县”文学地图,就是一类具有拉图尔“在地”属性的“文学飞地”。当作家以世界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和表现“平乐县”时,一方面是在反思和拒绝那些保守的、已成痼疾的传统观念和“地方知识”(“说公道”的声音、傅祺红的“道理”等),另一方面又通过陈地菊形象去重新感受和发现一种现代人需要但又缺失的情感和家庭。以“世界”的目光来看,回到中国的“地方”,并非如当前很多“返乡”小说般重新去体验某个地方上的风景或物质,而是回到最具人情味、最具中华文化属性的“家”。“家”是地方上最本真的经验——“家,在本真的经验之中,‘家’——不管是一栋房屋、一座废墟、一个区域,还是一个国家,它都位于存在的中心,是个人认同的中心点,人们从此出发去观看周围的世界。”[31]《平乐县志》念念不忘的,正是那个让人爱怨交织的“家”。颜歌投射在小说人物陈地菊身上的情感和经验,也是以文学的方式回到故乡的“家”重新出发。小说安排陈地菊回家再离家、去往世界,这一过程充满了绝望与犹豫,“漫长”得令人发慌。陈地菊的心理历程,是检视作者自身的“去国”经验,也是审视一代人的“离家出国”情结,它凝聚了“家”之于中国儿女的爱与痛、情与殇。
在全球化开始转向“后全球化”的1990年代,人类学家阿帕杜莱曾追问:“在全球文化流的框架内,地方性的位置在哪里?既然在这个世界里,地方性似乎已失去了其本体论的停泊点,那么人类学还有任何修辞上的特别优先权吗?人类学和地方性之间相互构建的关系,在地方性消解得如此剧烈的世界中是否还能存续?”[32]这是人类学视角的提问,阿帕杜莱也给出了人类学视角的“生产地方性”方案——去直面“民族国家、不稳定群体、全球电子媒介”等新兴要素及其互相结合产生的变体所带来的挑战。把这个人类学视角替换为文学视角,我们又能提出怎样的“地方性再生产”策略?颜歌的“平乐镇”系列小说,尤其是《平乐县志》,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古典形式、世界的目光,以及“空时性”思维的文学地图绘制,当然也包括方言的运用、人物群像塑造以及“家”的重建……

颜歌作品的英文版图书封面
左图:White Horse,HopeRoad于2019年10月出版;
中图:The Chilli Bean Paste Clan,Balestier Press于2018年 5月出版;
右图:Strange Beasts of China,Melville House于2021年7月出版,获得2021年度《华盛顿邮报》最佳科幻、奇幻和恐怖类小说
余 话
《平乐县志》最末,陈地菊办完房产交易手续,着急回去跟傅家摊牌离婚、宣布出国计划,于是抄近路闯入了未来城和创新公园。“未来”与“创新”,这是“平乐县”的新版图、新空间,但年轻的陈地菊却对这些新事物无感——“她有点后悔自己走这一头钻进来了”。陈地菊有感情的地方,是有生活气息的、人声鼎沸的老街:“……加快了步子朝公园外面走,过了人工湖,又过了梅花道,便涌过来那熟悉而鼎沸的声音:街上的杂谈、闲话、叫卖,三轮的吆喝,自行车的铃铛,汽车的喇叭,还夹杂着救护车的鸣笛——也就是一眨眼,平乐镇东街就在她的面前了,或者应该说,是老平乐镇的老东街。新的平乐镇已经在她的身后起来了,一栋栋有的刚刚打好地基,有的马上要封顶了,日新月异,节节高升,像是平原上春天里的竹子。”[33]“一眨眼”的时间,“平乐镇”升级成了“平乐县”。“新的平乐镇”没有记忆,不是作家心目中的故乡。“平乐县志”所谓“志”,其实是记述“平乐镇”的终结,是作家与自己记忆中的故乡的一种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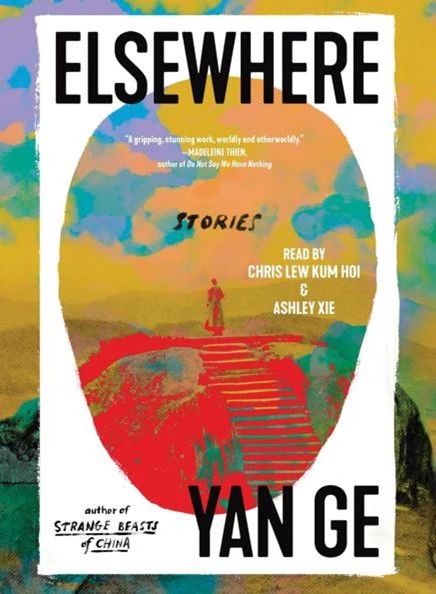
颜歌的第一部英文小说 Elsewhere: Stories,Scribner 于2023年7月出版
《平乐县志》标志着“平乐镇”文学地图已绘制完毕。颜歌说完成《平乐县志》相当于一次“自我斩断”,接下来她只想进行英文写作。但无论未来颜歌会推出多少英语文学新作,我们再谈及作家颜歌时,她的“平乐镇三部曲”以及她那独特的、四川方言化的文学语言必然会继续浮现心头;其中,凸显“中国叙事”的《平乐县志》,也会是我们探讨颜歌转型以英文写作继续“Writing Against English”的分水岭之作。
唐诗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
51063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6期)
注 释
[1[颜歌、赵依:《“很有挑战性的部分也是我最喜欢去写的部分”》,《广州文艺》2023年第8期。
[2]张定浩:《颜歌与我们的小镇》,《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夏卷。
[3]刘欣玥:《我们与小镇的距离——〈平乐县志〉与颜歌的“出平乐镇记”》,《文学报》2023年8月31日。
[4][5]颜歌、赵依:《“很有挑战性的部分也是我最喜欢去写的部分”》,《广州文艺》2023年第8期。
[6]谭帆等:《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844页。
[7]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岳麓书社2019年版,“凡例”第2页。
[8]颜歌、赵依:《“很有挑战性的部分也是我最喜欢去写的部分”》,《广州文艺》2023年第8期。
[9]颜歌:《平乐县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274页。
[10]詹姆斯·费伦:《体验小说:判断、进程与修辞叙事理论》,唐伟胜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16页。
[11]刘欣玥:《我们与小镇的距离——〈平乐县志〉与颜歌的“出平乐镇记”》,《文学报》2023年8月31日。
[12]颜歌:《平乐县志》,第422页。
[13][14]颜歌:《平乐县志》,第382、452页。
[15]颜歌的《平乐县志》与张楚的《云落图》(《收获·长篇小说》2023年冬卷),有很多可比之处,如故事时间的当下感(《平乐县志》的故事是从2009年秋到2010年夏,《云落图》的故事则是从2015年的春到秋)、叙事结构上的双线与复调(《云落图》用注释的形式交代小说人物过去的生活,与《平乐县志》傅祺红的日记交代傅祺红、傅丹心的过去,两者很近似)、小说所表现的县城世俗生活和腐败情况(如小市民的生活习性、地方上官场的腐败、房地产等商界的阴谋等)、主要人物的最后选择(《云落图》天青要出国读博、《平乐县志》陈地菊下决心去国外读研);另外,这两部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中国传统市民小说,用了很多古典文学的笔法,这些相似性都值得做更多探讨。徐刚在评论《云落图》时指出:“张楚把‘自己’作为方法,意味着以个人的县城经历切入,把个体经验问题化,将了解自己作为了解世界的开始。以‘自己’为方法,也意味着以‘附近’为方法,从‘自己’出发不断延展到社会网络中更多的节点,从而让更多的‘附近’之人现身,并完成他们的讲述。由此,我们得以看到《云落图》中普通却不乏光彩的‘万樱’们,以及他们有趣而悲伤的故事。……只是在张楚这里,县城的面目会更显温情,县城人物也更具人性的亮色,这也正是其‘县城叙事学’更具启示性的意义所在。”见徐刚《“县城叙事”:附近空间与切身的人——论张楚〈云落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16]项飙:《作为视域的“附近”》,《清华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7辑。
[17]颜歌:《平乐县志》,第474页。
[18]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19]看理想编辑部:《她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留下一个自己的版本》,“理想国imaginist”微信公众号,2023年12月15日。
[20]傅修延:《叙事:意义与策略》,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21]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想象的全球化》,陈金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1~332页。
[22]韩炳哲:《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
[23]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26页。
[24]胡子华、颜歌:《颜歌:我写一人炒股会同时写一头猪会飞,只要我觉得OK》,“腾讯文化频道”微信公众号,2015年5月19日。
[25]罗伯特·塔利:《空间性的镜子:对文学绘图的思考》,方英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26]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高方、路斯琪、张倩格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第49页。
[27]罗伯特·塔利:《空间性的镜子:对文学绘图的思考》,方英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28]安东尼·吉登斯:《逃逸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郭忠华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86页。
[29][30]布鲁诺·拉图尔:《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胡恩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版,第97~98、132页。
[31]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第132页。
[32]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9页。
[33]颜歌:《平乐县志》,第47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