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孽海花》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
小说林社1905年初版封面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历史小说”接替“演义”而创生,梁启超《新小说》杂志将“历史小说”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载于此刊的吴趼人《痛史》即是代表作。吴趼人的《历史小说总序》、《月月小说序》和《两晋演义序》对“历史小说”的诠释,标志着现代“历史小说”观念的正式登场,但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观及创作有其不足。曾朴《孽海花》突破“演义”的陈规,成为中国“历史小说”创生期的代表作。《孽海花》的成功与曾朴对西方“历史小说”的翻译不可分。西方“历史小说”的引入在清末民初成为一个潮流,其中德龄《清宫二年记》的中译充分行使了“历史小说”的主体性功能。“历史小说”替代“演义”终究成为现代文学的定势。
关 键 词
历史小说 演义 吴趼人 曾朴 德龄
“历史小说”概念在晚清才生成,《三国演义》等传统小说只可称之为“演义”或“历史演义”。对“演义”有专门研究的学者认为:“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盛极一时的历史演义,却随着其他小说类型的繁荣而走向了衰退”;“到了晚清,历史演义创作曾有过小小的回潮,出现了吴趼人、黄小配等人的新型历史小说,但其影响无法与早期的历史演义相提并论。到了民国前期,蔡东藩新编历朝演义,要求自己‘语皆有本’,不过是历史的通俗化。到这时候,可以说历史演义的文学生命已经结束了”。[1]如果清末民初“演义”的“文学生命已经结束”,那么“历史小说”是否在此时接替了“演义”而兴起?晚清吴趼人等作家的“新型历史小说”与传统的“演义”有何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对现代历史小说的研究,关注多在五四以后,而在“历史小说”创生、“演义”逐渐退场的过程中,清末民初实在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
一 作为“新小说”的《痛史》
“历史小说”称谓在中国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梁启超1899年在《清议报》上连载《饮冰室自由书》中之所言,“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2],谈的是日本明治时期翻译西方小说的情况。梁启超的“历史小说”称谓便和日人翻译英国小说有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幅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介绍了即将出刊的《新小说》杂志的主要内容。其中介绍“历史小说”道:“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奇俶诡之笔,代庄严典重之文。”[3]在这则著名的广告中,梁启超对“历史小说”做了一个界定,即以史实为题材,用演义体叙事,《三国演义》是范例。梁启超的这一界定,还不出传统“演义”的范畴,只是以“历史小说”称谓替换了“演义”。尽管如此,“历史小说”观念已然萌发,具体的小说实践也与传统“演义”产生了不同。
(一)《新小说》上的“历史小说”

刊载《痛史》第一回至第三回的
《新小说》1903年第8号封面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广告列出了《新小说》将要刊载的几部“历史小说”:《罗马史演义》是译作,《十九世纪演义》“乃采集当代大史家之著述数十种镕铸而成”[4],《自由钟》叙美国独立史,《洪水祸》讲法国大革命史,《东欧女豪杰》谈俄国革命党人故事。对这几部小说,广告都做了简略的内容介绍。另外还列出了几部“历史小说”的书名:《亚历山大外传》《华盛顿外传》《拿破仑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叙述国外历史,且具有革命革新价值,是这些“历史小说”的共同处,这也当是梁启超构建“历史小说”的理想。仅从取材看,与中国的“演义”已大为不同。
《新小说》创刊号上即设有“历史小说”的门类。创刊号的“历史小说”栏紧跟着发刊词性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其中刊载了两部长篇:雨尘子《洪水祸》的第一回至第三回,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的第一回和第二回。在“历史小说”之后才是梁启超特别推崇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科学小说”“哲理小说”更在其后。[5]在广告所列各类小说中,“历史小说”排在“图画”“论说”之后,是第一类被推出的小说,之后才是“政治小说”三种:《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新桃源》。在广告预告的小说数量上,“政治小说”也不如“历史小说”。
为何“历史小说”被梁启超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从刊登情况来看,《新小说》对‘历史小说’和‘政治小说’的界限划分不是非常严格。《洪水祸》和《东欧女豪杰》也都讲述政治革命故事”,而“‘政治小说’的来源本身就和各国的历史变革息息相关”。[6]就梁启超的“新小说”言之,两种小说功能类似,区别不大。《洪水祸》开篇,叙述者先分析了“人种的感情”和“政治的感情”,然后谈“竞争”:“大凡各国史书上的事业,不外两种:一是国内之竞争;一是外国之竞争。西洋史上的国外竞争,多半是人种的关系;国内竞争,多半是政治上的关系。这个看过西洋史的,便可领略,不必多说。于今单说西洋数十国内的一国,西洋数千年史上的一种事情,这事情不是国外竞争,便是国内竞争,也无非出乎政治上一层魔业。”[7]“内竞”和“外竞”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强调的两个概念,也是进化论思想在晚清知识界所激起的反应。“历史小说”《洪水祸》谈论此类问题,足以显示其政治关怀。和“政治小说”相区别,“历史小说”只在取材上或有不同。《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所列“历史小说”均述国外史事,而“政治小说”“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8]。叙述国外史事,目的是给国内政治革新以借镜,于启蒙读者或“群治”方面,“历史小说”不妨作为“政治小说”的先导。
但就《新小说》所刊作品来看,“历史小说”和“政治小说”的取材并不全然区分中外。《新小说》所刊“政治小说”仅有两种,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和玉瑟斋主人《回天绮谈》。《回天绮谈》叙述的是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史事,而非中国之事,很可以归入“历史小说”栏。可见“新小说”观念中的“历史小说”和“政治小说”之间的边界实在不明显。《新小说》并没有如之前广告所言,刊登《罗马史演义》等“历史小说”,而仅连载了《洪水祸》《东欧女豪杰》《痛史》三部作品。与前两部“历史小说”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痛史》叙述的是中国的历史故事。
在《洪水祸》、《东欧女豪杰》、《新中国未来记》和《回天绮谈》的连载均告一段落后,列于“历史小说”栏的吴趼人《痛史》于《新小说》第八号(1903年10月)登场,同时刊出的还有吴趼人的“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此后,吴趼人成为《新小说》杂志的主要撰稿者。《痛史》连载到《新小说》的最后一期(1906年1月),至第二十七回,未终篇。和《洪水祸》等小说一样,《痛史》也用章回体的形式来演义历史,同样别有寄托。邱菽园评吴趼人《痛史》道:“《痛史》,如宋儒为诗,号击壤派。”[9]所谓“击壤派”得名于宋代邵雍《伊川击壤集》。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10]《击壤集》的特点是“平易近人”“觉世唤醒”,邱菽园说吴趼人的《痛史》是“击壤派”,指《痛史》虽写历史,其实并不措意于史事的准确可信,而是以历史来表现意图,将讲史作为载体,来传达反清、维新的思想。吴趼人在《两晋演义序》中谈《痛史》,表示:“吾将一变其诙诡之方针,而为历史小说矣,爱我者乞有以教我也。旋得吾益友蒋子紫侪来函,勖我曰:‘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剌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贻误阅者’云云。末一语,盖蒋子以余所撰《痛史》而发也。余之撰《痛史》,因别有所感故尔尔。”[11]吴趼人明确交代《痛史》是“别有所感”而作的。
(二)吴趼人《痛史》的写作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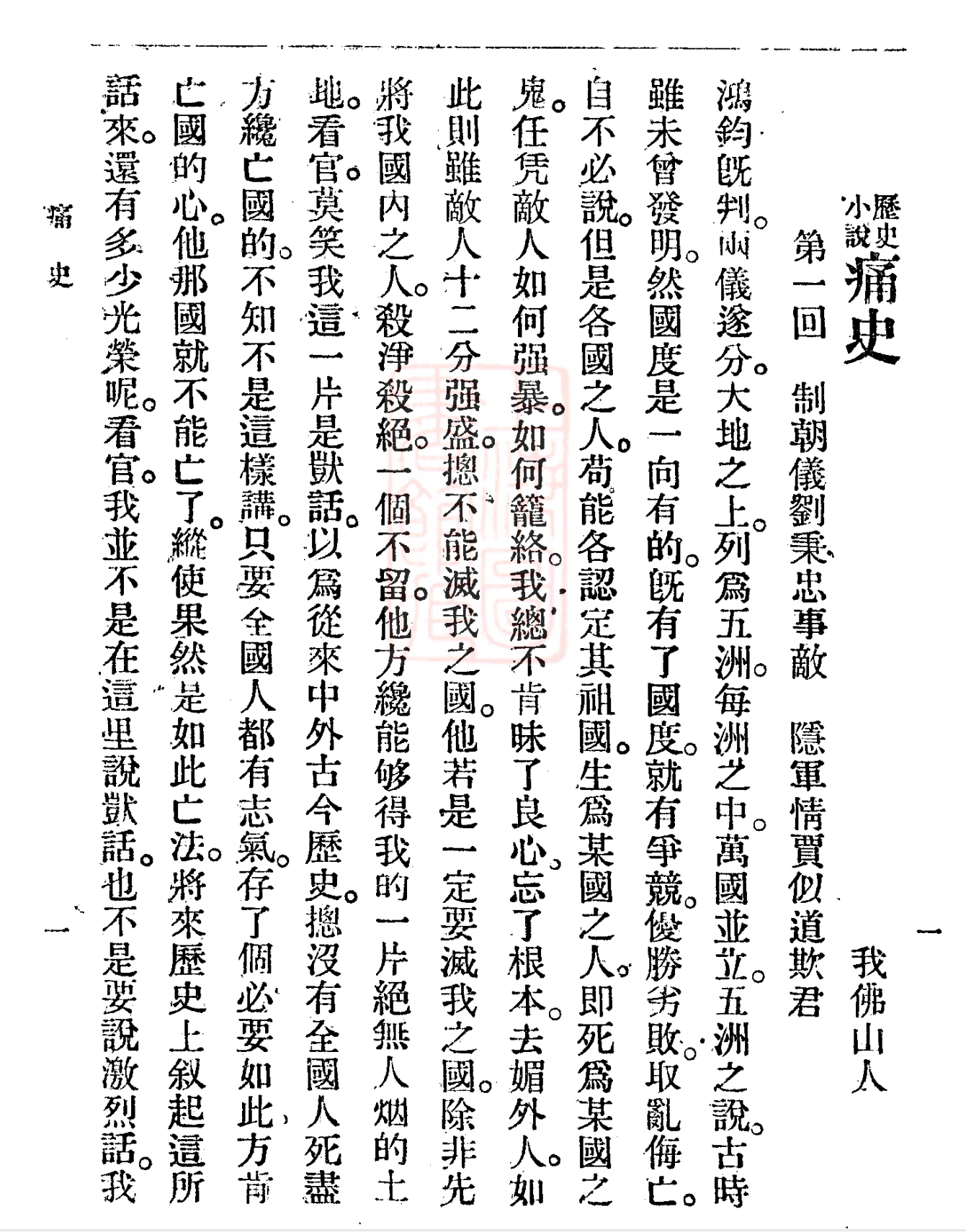
《痛史》第一回
《痛史》是吴趼人以严肃态度创作的第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主要叙述南宋末年的故事。《痛史》与《三国演义》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第九回写众义士在仙霞岭相遇,彼此见解主张一致,遂结盟:“当下商量要起个会名。宗礼道:‘我们就学《三国演义》上周瑜的“群英会”如何?……’”[12]第十回宗仁、胡仇初到仙霞岭,金奎介绍山上的布置说道:“这山上树木很多,这都是岳兄指点着移种的。这是按着‘八阵图’的布置,虽然不似《三国演义》说那鱼腹浦的‘八阵图’的荒唐,然而生人走了进来,可是认不得出路呢。”[13]无论是“群英会”还是“八阵图”,都成为可以自然比附的《三国演义》的遗产。另如战阵中绝粮道、赚城池、诈降等,都是对《三国演义》军事智谋的明显运用。
在小说“起结”方面,《痛史》也继承了传统“演义”小说的体例。毛宗岗总结《三国演义》道:王朝兴衰、事件过程、人物命运“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14]。《痛史》第一回至第五回度宗驾崩,遗命贾似道带兵出征,贾似道兵败逃跑被革职,第六回贾似道死,是一起一结,这一段落是以贾似道通敌弄权卖国为中心。第七回三个重要人物,文天祥、谢枋得、张世杰,先后登场。张世杰在第一起结中已经出现,这即是似断还续的结构经营。文天祥与张世杰在后文的南逃小王朝故事中构成两条线索,第十回文天祥登坛拜为大元帅,张世杰拜将,此后二人的故事时而交汇,时而明暗互补,终于一战死,一被俘就义。这是人物的起结。“演义”之体就是要将大事本末和人物列传妥为安排,穿插连络,成为统一的艺术整体。
虽然受《三国演义》影响明显,《痛史》终究是一部具有现代性质的“新小说”,怀抱“别有所感”的意旨。阿英说:“吴趼人写作这部小说时……是如书中人张世杰说的话一样:‘我实在恨这班畜生,时时都想痛骂打他一番,我骂他畜生还嫌轻,不知要骂他是个什么才好呢!’这真的是吴趼人对于宋代当时人物的愤慨么?是在宋代的一些卖国汉奸以外,兼咒诅那些清朝的汉奸的。是对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几十年事件愤慨的总发泄,总暴露。”[15]吴趼人的“愤慨”源于他对历史趋势和中国面临危机的认识。《痛史》第一回开宗明义,描绘了一个万国争竞、“优胜劣败”[16]的世界。在竞争中,何以自存?吴趼人认为首先是国人要有爱国心:“但是各国之人,苟能各认定其祖国,生为某国之人,即死为某国之鬼,任凭敌人如何强暴,如何笼络,我总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血性的太多”,“所以我要将这些人的事迹记些出来,也是借古鉴今的意思”。[17]这一“别有所感”的意图,决定了《痛史》的写法。
小说从南宋王朝末路展开叙事,目的在于凸显危难之际朝廷人物的忠奸。吴趼人为了表达惩奸除恶的“历史正义”,不惜违背历史事实。奸臣贾似道被革职后,《宋史》记载:“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绵庵,虎臣屡讽之自杀,不听,曰:‘太皇许我不死,有诏即死。’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拉杀之。”[18]贾似道死于郑虎臣之手,于史有据,只是吴趼人似不解恨。《痛史》第六回中贾似道也死于郑虎臣之手,却是被郑虎臣推入粪缸而死,这是吴趼人特意虚构的。私刑处死贾似道后,据史载,郑虎臣亦被逮,瘐毙狱中。但如果这样叙述,似不足以伸张正义,所以吴趼人给郑虎臣另外安排了结局:“于是等到更深时,悄悄地开了山门,牵出马来,扳鞍踏蹬,加上一鞭去了。”[19]对历史人物结局的这一改写,吴趼人振振有词:“下文方有得交代,他还建了许多事业呢。据正史上说起来,是陈宜中到漳州去把他拿住了,在狱中瘐毙了他,算抵贾似道的命的。但照这样说起来,没甚趣味,我这衍义书也用不着做,看官们只去看正史就得了。”[20]对“衍义书”的辩护实际上是吴趼人不拘“演义”规范的说辞。
据元史,《痛史》中贯穿前后的重要人物之一张弘范,出生于元太宗十年(1238),此时金朝已亡四年,所以不能说张弘范是金朝的臣民。但在吴趼人笔下,张弘范是从金朝投降蒙古的。就张弘范个人历史而言,他生于元,长于元,是元朝人,他效忠于元未见得有历史的悖谬。但是,在中国历史易代之际,种族是最容易被操作的符号,正因此,张弘范被贴上了卖祖求荣的标签。《痛史》第十八回,借人物之口,痛斥清朝的汉人官僚,“弘范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往后便倒”[21],小说这一情节不合史实。在历史上,张弘范生病期间,元主极为重视:“未几,瘴疠疾作,帝命尚医诊视,遣近臣临议用药,敕卫士监门,止杂人毋扰其病。病甚……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略。”[22]为了严华夷之辨,讲忠奸之分,尊汉家正统,《痛史》以观念驱遣史事,实为“别有所感”的。
《痛史》中最具有虚构性的部分是宗仁、胡仇为给三宫请安而北行,由此串连起仙霞岭故事。仙霞岭地理险要,在历史上是重要关卡,小说叙述金奎占山为王,把仙霞岭发展为反元的基地,则全出于想象,由此《水浒传》的影响渐趋显著。小说第二十七回,山东起事失败,元兵集结攻打仙霞岭,小说至此而止。大约从《三国演义》向《水浒传》的笔法转换间,吴趼人无所措手了。
以古写今是对“演义”规范的调整和发挥,当正史不足以表达作者写史的主观意图时,不妨虚构创作。梁启超把“历史小说”作为“新小说”的重要门类,目的在于“群治”或“新民”,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观与梁启超的“新民”是一致的。这是《痛史》成为“新小说”而非传统小说的因由,虽然在形式方面,还是运用了“演义”体。这也是《新小说》上“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
二 “历史小说”观念的正式登场
吴趼人认为《三国演义》之后的小说每况愈下,原因是失真“无稽”。[23]到了晚清,“演义”之体渐趋涣散,“历史小说”由此而兴。《痛史》是吴趼人正式提出“历史小说”之前的创作实践。虽然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观想纠正《痛史》的“别有所感”,但是“历史小说”一旦登场,其创作之途,便与“演义”渐趋分道。
(一)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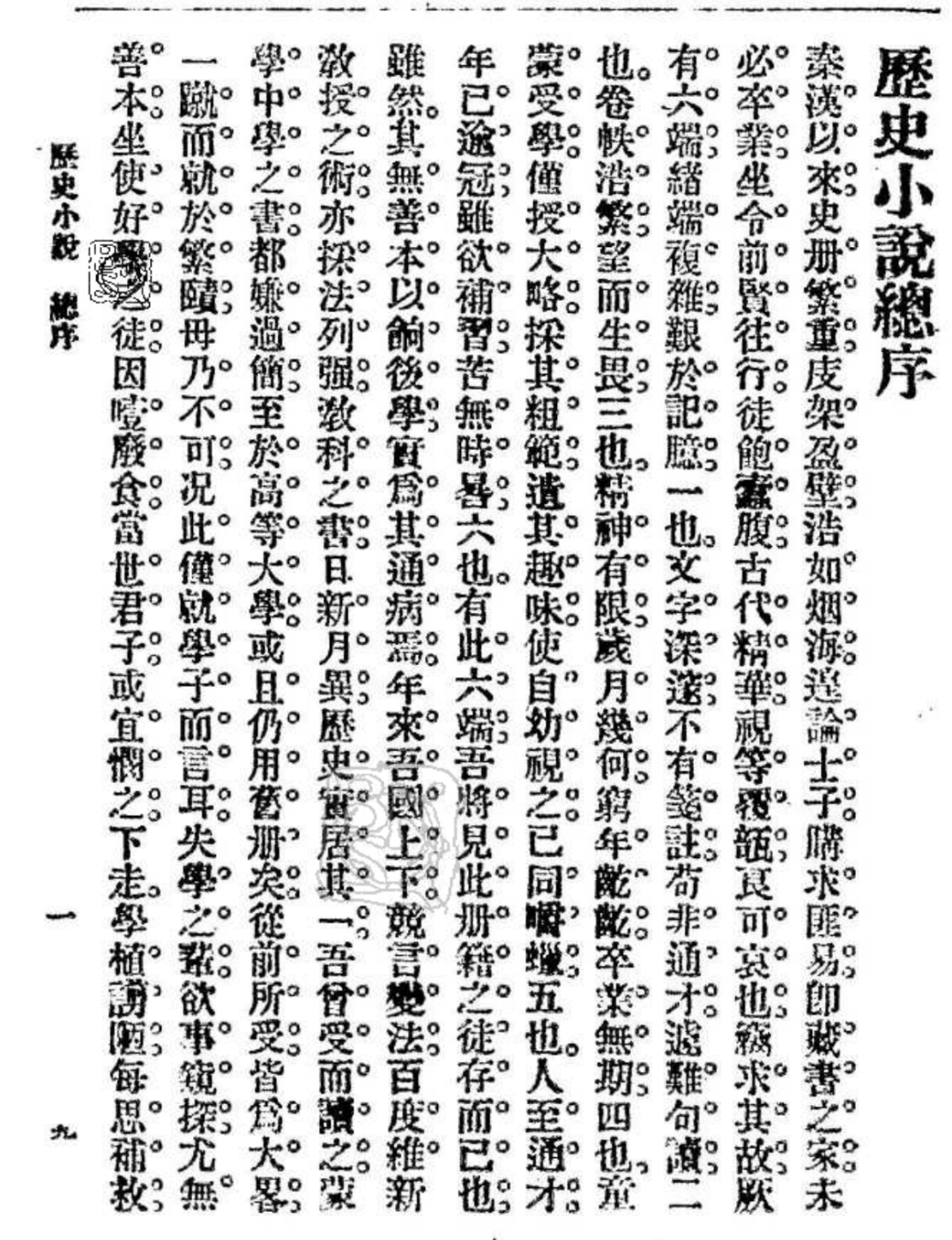
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
现代性的“历史小说”观念和传统的“演义”所体现的朝代兴衰观念不同——“历史小说”是现代人用一种“新小说”观来寻绎过去之事。
吴趼人以“历史小说”的眼光来看《三国演义》。他在《历史小说总序》一文中说:“是故等是魏、蜀、吴故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至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历代史籍,无演义以为之辅翼也。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24]这与《新小说》杂志关于“历史小说”的广告取义一致。吴趼人以“历史小说”代换“演义”的称谓,这不是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要用“历史小说”来诉诸“今日读小说者”,具有现实功能的指向。于此,要“编撰历史小说”,使之成为“今日”之作。
1906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创刊号上发表《历史小说总序》一文,可以看成是现代“历史小说”观念的正式登场,杨世骥说:“此文颇足作为当时一切历史小说的理论。”[25]在这篇文章中,吴趼人先陈列了古代史册被“视等覆瓿”的诸多原因,接着谈到维新以来,西学引入,教学科目中也有“历史”一门。中小学的历史书“都嫌过简”,大学的历史教材还有用古代史籍的,学历史,而“无善本”,殊非理想。吴趼人很想寻得一种“补救”之法。一日他听得窗外有二人在谈“三国史事”,“虽附会无稽者,十之五六,而正史事略,亦十得三四焉”。这不就是“演义之功”吗?于是就有了“编撰历史小说”的“大誓愿”。在文章最后吴趼人提及了“小说”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小说附正史以驰乎?正史藉小说为先导乎?请俟后人定论之。”[26]小说因为叙述正史故事以获得价值,正史通过小说更易于被接受。在吴趼人的理解中,“历史小说”之“历史”便是正史之内容,“历史小说”之“小说”便是“新小说”之功能,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体现了传统至现代转换之间的观念意识,奠定了之后现代“历史小说”写作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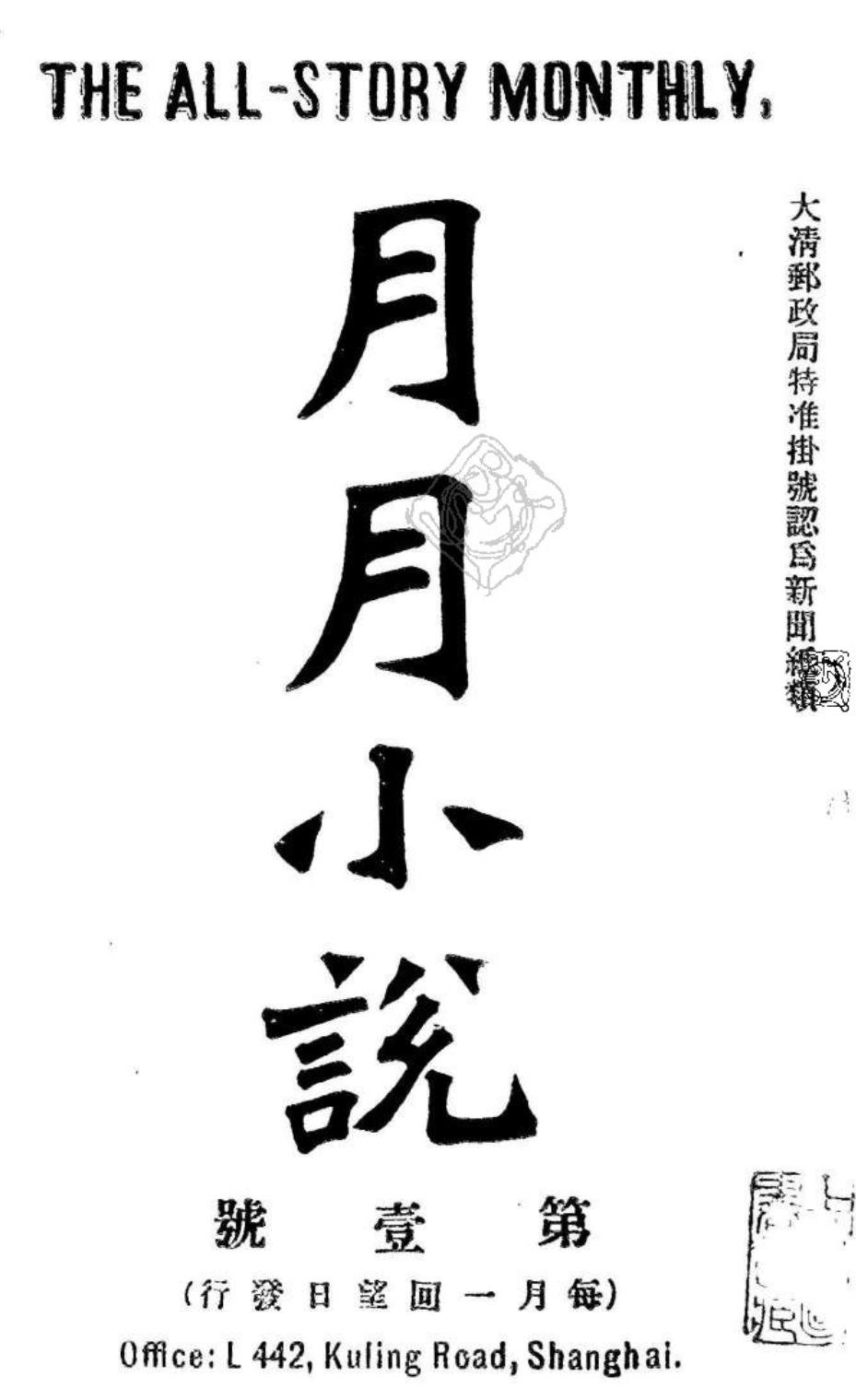
《月月小说》
《历史小说总序》显现出吴趼人对“历史小说”的特别关注,也代表了《月月小说》乃至晚清文坛对“历史小说”的看重。《月月小说》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是《月月小说出版祝词》,其次是《月月小说序》,第三篇即为《历史小说总序》。事实上,作为《月月小说》发刊词的《月月小说序》也是一篇提倡“历史小说”的文章。《月月小说序》先谈“群治”,呼应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要“改良小说”。小说可以“补助记臆力”,可以“输入知识”,但当时的小说创作却“杳乎其不相涉也”。于是“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历史云者,非徒记其事实之谓也,旌善惩恶之意实寓焉。旧史之繁重,读之固不易矣,而新辑教科书,又适嫌其略。吾于是欲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焉。他日吾穷十年累百月而幸得杀青也,读者不终岁而可以毕业,即吾今日之月出如干页也,读者亦收月有记忆之功。是则吾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者也”。这篇发刊词突出“历史小说”,并且强调了其“教科之助”的功能,即“历史小说”具有启迪民智的作用。作者在文末感叹道:“呜呼,吾有涯之生,已过半矣。负此岁月,负此精神,不能为社会尽一分之义务,徒播弄此墨床笔架,为嬉笑怒骂之文章,以供谈笑之资料,毋亦揽须眉而一恸也夫。”[27]《月月小说序》虽没有注出写作者,但可以肯定文中之“吾”即为吴趼人。时年吴趼人四十岁,哀乐中年,颇有一番人世感慨。“历史小说”乃吴趼人“为社会尽一分之义务”的寄托。
在《月月小说序》和《历史小说总序》二文之后,便是吴趼人的《两晋演义序》。此文和《历史小说总序》、长篇小说《两晋演义》一同刊载于“历史小说”栏。吴趼人道:“然《月月小说》者,月月为之。使尽为诡谲之词,毋亦徒取憎于社会耳。无已,则寓教育于闲谈,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仍可获益于消遣之际,如是者其为历史小说乎。历史小说之最足动人者,为《三国演义》,读至篇终,鲜有不怅然以不知晋以后事为憾者。吾请继《三国演义》以为《两晋演义》。”[28]吴趼人撰《两晋演义》是直接为《三国演义》续之后的历史,即使《两晋演义》仍以“演义”名之,但其已是“今日”之作,可归于“历史小说”,行使“寓教育于闲谈”的功能。阿英认为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这两篇叙文,不仅可以作为吴趼人对于讲史之理解看,在晚清的论讲史的文字里,也是最重要的。当时所谓新的讲史的写作,是企图正确的叙述史实,使成为通俗的历史教科书”[29]。吴趼人在《两晋演义序》中谈到《痛史》的写作“因别有所感”而有违史实,此次作《两晋演义》要归乎正。《两晋演义》刊载时,标明“甲部历史小说第一种”[30],可见吴趼人是要把《两晋演义》作为“历史小说”写作的范本。

《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号吴趼人像
总体来看吴趼人对“历史小说”的解释,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要叙述正史故事;二是有助于教育。寓教育于讲史,这便是吴趼人及晚清新小说家提倡“历史小说”的主要意图。而教育为何?当然不仅仅是丰富国民的历史知识。阿英在谈“通俗的历史教科书”之后,便论述了晚清“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吴趼人的作品,写南宋的偏安,写两晋的混乱,是针对着晚清的政治而说教。内如光绪慈禧的冲突,外如列强的侵略,与两晋、南宋是有共通性的。”[31]阿英认为晚清“历史小说”都有这一共同特点,即通常所谓的“借古讽今”,也就是吴趼人所说的“别有所感”。而当正史故事不足以讽喻现实时,或可对正史稍加改写。就此言之,《痛史》只是比《两晋演义》的现实教育功能更为明显罢了。
(二)《孽海花》:“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痛史》《两晋演义》之外,吴趼人还著有“历史小说”《云南野乘》,于《月月小说》第1年第11号开始连载,只见三回。这与史料缺乏有关,也折射出吴趼人“历史小说”的局限。杨世骥对吴趼人小说的拘于史有一个批评:“历史小说应该一本于历史(官史)上的真实故事,不可有所剌缪,完全忽略了小说的文学的技巧与价值。晚清历史小说自沃尧所撰《痛史》以后,一时风起云涌,然而没有一部特别生色的作品,主要的原因就是太注意情节的真实性,缺乏剪裁或点染,这当是受了沃尧《历史小说总序》一文的影响罢。”[32]杨世骥是在四十年之后来评论吴趼人“历史小说”的,当然有后见之明。但无可讳言,就小说本身的“文学性”来看,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还不能成为晚清小说的代表作。
对“历史小说”有专门研究的卢卡奇在谈“小说”问题时说道:“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小说则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建构隐蔽的生活总体。”[33]“小说”具有主体性,“历史小说”具有“塑造”而非仅是“演义”历史的能力。在无正史可据的情况下,例如要演述当代历史,只能依靠笔记等非正史资料,或参考报刊新闻,这就需要小说发挥“塑造”历史的功能,晚清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便属于这种情况。另一部不容忽视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不仅是晚清人写晚清史,同时突破了传统“演义”的写法,能够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取得平衡,是《痛史》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晚清“历史小说”。
1905年,《孽海花》前二十回由小说林社刊印,被标为“历史小说”。[34]1907年《小说林》创刊号在两篇“论说”之后的“社会小说”栏,从第二十一回开始刊登了两回《孽海花》。[35]有意思的是,在正文里,《孽海花》不被标为“社会小说”,而被标为“历史小说”。鲁迅把《孽海花》归为“谴责小说”,称其“杂叙清季三十年间遗闻逸事”[36]。之所以也被称为“社会小说”,可能是因为小说所记述的是晚清故事,故事发生时间离作者曾朴并不遥远。小说主人公原型洪钧是同治年间的状元,虽是长曾朴一辈的人物,但和曾朴相识并多有往来。可以说,小说记述的是作者同时代的故事。《孽海花》之所以应被归为“历史小说”,主要原因是小说的人物故事在历史上真切存在过。1916年出版的《孽海花》附有署名“强作解人”对小说做的“阐旨兼考证”,把小说和历史相对应。[37]清末,《孽海花》完成至第二十五回。此后曾朴修改了之前的写作,并续至第三十五回。1928年,当曾朴为《孽海花》单行本撰写《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时,《孽海花》已成前朝故事,确实可以做“历史”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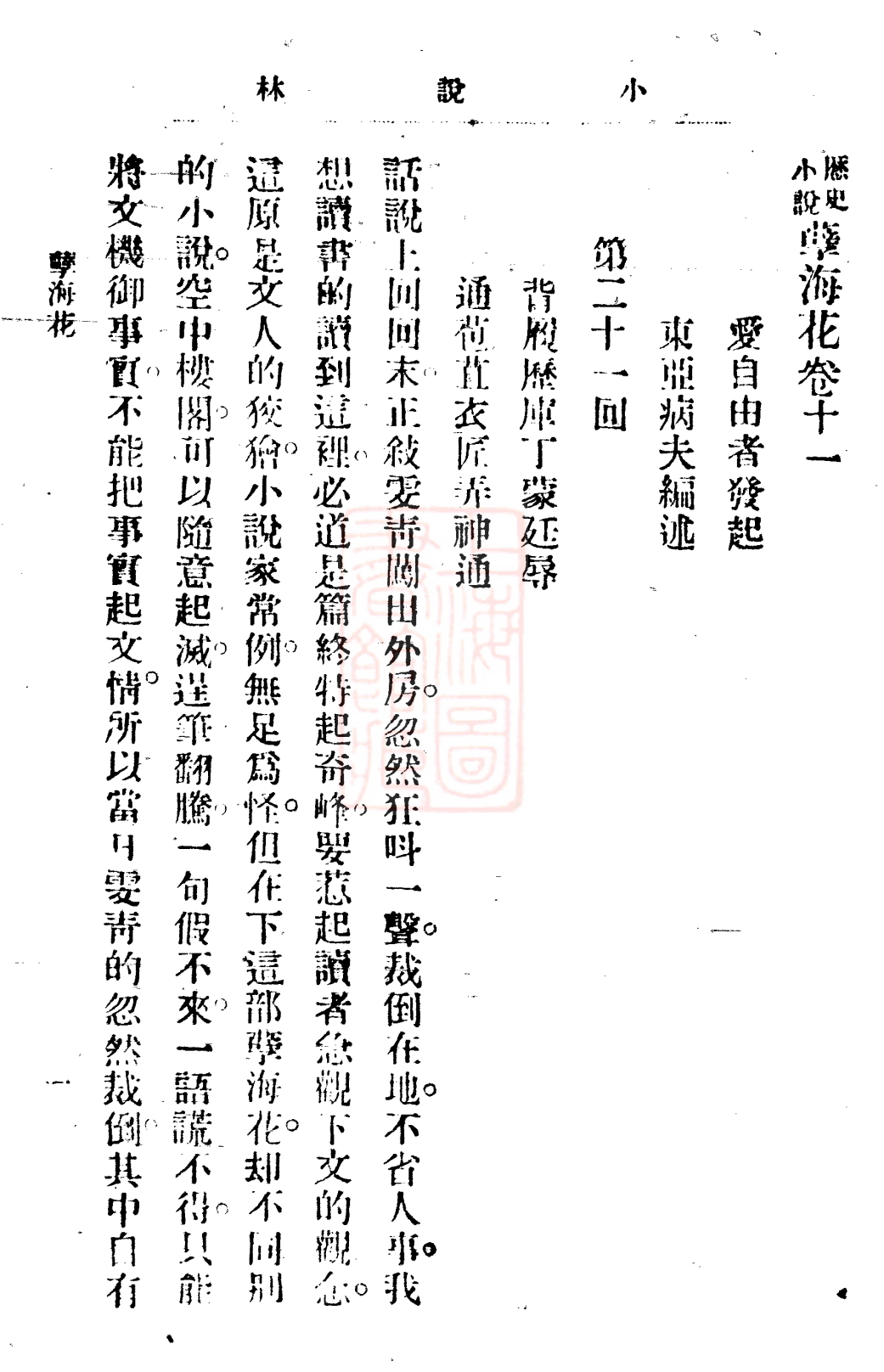
《小说林》1907年创刊号上连载的《孽海花》
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曾朴称“这书还是我二十二年前”“一时兴到之作。那时社会的思潮,个人的观念,完全和现时不同”,“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38]文化和政治是《孽海花》叙写三十年晚清史的主要内容,作为“历史小说”的《孽海花》和梁启超、吴趼人等人推崇“历史小说”的意图是一致的。《小说林》把《孽海花》列为连载的首篇小说,也是突出了其中的政治文化价值。

《孽海花》1905年初版本扉页,小说女主人公原型图像
对于翻译了大仲马《马哥王后佚史》《血婚哀史》等“历史小说”的著名翻译家曾朴来说,《孽海花》的写作明显受到了西方历史小说的影响。在《血婚哀史》的“译者附识”中,曾朴言道:“以显理四世及查尔斯妹马奇公主,为书中之线索,兼写当时暗主骄后、权臣悍卒,种种奇瑰之行,秘密之谋,情节复杂,局段谨严。翔实似《三国演义》,调侃如《儒林外史》,细腻如《红楼梦》,豪迈似《水浒传》,实泰西小说中淹有中国说部之长者杰构也。亟译之,以饷读者。”[39]西方小说可以有中国小说的长处,中国小说也可汲取西方小说的优势。《孽海花》把洪钧和赛金花的现实故事纳入了小说的主体结构,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婚姻故事“为书中之线索,兼写”官场沉浮、宫闱秘史、中外战争、维新革命等等,金雯青出使西方的详细经历,傅彩云放诞绮丽的生活情致,均是“借男女情事写历史事变”[40],这种以主人公故事“塑造”历史的方式,为之前全知全能敷陈历史的“演义”所少见,《孽海花》是“演义”转换为“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受西方历史小说影响,融合中西说部之长,是中国“历史小说”创生期的一大特点。
三 被译介的历史小说
清末民初,西方历史小说的引入是一个潮流。法国大仲马、美国华盛顿·欧文、英国柯南·道尔、日本押川春浪等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潮流中被译介。曾朴在《小说林》上连载翻译小说《马哥王后佚史》,即被置于“历史小说”栏。陈鸿璧翻译的“历史小说”《苏格兰独立记》则和《孽海花》同时连载于《小说林》创刊号。在《月月小说》创刊号上,与《两晋演义》同时开始连载的还有被标为“乙部历史小说第一种”[41]的《美国独立史别裁》,也是翻译小说。英国小说《卢宫秘史》(《小说月报》1912年)、日本小说《拊髀记》(《小说月报》1913年),林纾《恨绮愁罗记》《大食故宫余载》(商务印书馆1914年)等,均被作为“历史小说”翻译引入。这些翻译小说很多以“章”或“节”标目,和“演义”体式显出不同。
刊载于《新小说》上的“历史小说”《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不注明是翻译小说,却演述西方史事。这类“历史小说”在清末民初也数量众多。《磨坊主人》(《小说月报》1912年)、《玛瑙英雄》(《礼拜六》1914年)、《西班牙宫闱琐语》(商务印书馆1915年)、《法国拿破仑》(商文图书馆1916年)等“历史小说”都叙述国外历史人物故事,但不注明是译作,很可能是中文作者根据国外作品改编的。周瘦鹃在《铁血皇后》文末有一段说明:“美国文学家摩尔拔克氏,著有世界历史小说大成。全书共二十卷,其首卷即普罗士皇后与拿破仑事。原书至长,约有八九万字。余得其崖略,节之使短,名之曰‘铁血皇后’。后虽未竟其志而死,而今日德意志之得以称雄于世界,未始非后之功也。”[42]周瘦鹃对历史小说的关注与翻译改编,足见西方历史小说在清末民初文坛的被重视。而无论是翻译还是改编,都能影响中国“历史小说”突破传统“演义”的写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创作。
(一)德龄与《清宫二年记》的翻译

《清宫二年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西方历史小说叙述的是西方历史故事。中国作家的翻译和改编即使让一些细节乃至叙事文体中国化,但总体保留了西方史事,并以西方史事来比照或激励中国的政治变革。这也是清末民初编译西方历史小说的主要原因。在这些编译中,有一部小说颇为与众不同,它是一位中国人在国外用英文写作中国史,再被国内译者翻译成中文并引起轰动的“历史小说”。这便是德龄的《清宫二年记》。
《清宫二年记》1911年在纽约出版,共二十章,[43]民初由陈冷汰、陈贻先翻译成中文,分七次连载于1913年《东方杂志》,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15年再刊印时,封面上标明“历史小说”[44]。商务印书馆用“唯一无二之奇书”为《清宫二年记》做广告,并介绍其内容道:“记为前清驻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璘女士所撰,女士入宫侍慈禧太后二年,故知宫闱事甚详。慈禧于近年国事之关系,可谓重要。书中所记,凡庚子后变法之真相、外交之实情,与夫德宗末年之幽废、端肃诸人之被诛,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其实际为外间所不能知者,均时时由慈禧口内流露而出。至于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见之卑陋、游嬉之荒纵,又如宫中礼俗之奇异、服色之奢诞、宫眷之童、阉宦之险毒,皆为吾辈脑筋万想所不到者。女士身历目睹,一一记载无遗。则此书实合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神怪小说而兼赅之,可谓无奇不备,有美必臻,阅之令人目迷五色。”[45]晚清“历史小说”叙述政治史事,本来就和“政治小说”区别不大。商务印书馆为《清宫二年记》做大幅广告,很可见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影响。

1911年英文版《清宫二年记》作者像
与《孽海花》类似,《清宫二年记》也是晚清人写晚清事,并都是在历史变革之际出现的作品。《清宫二年记》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作者德龄。在小说的英文初版本上,作者署名为“The Princess Der Ling”(德龄公主),很能引起一种阅读兴趣。德龄是清末外交官裕庚之女,早年随父出使英法等国,受西式教育,通英法文。回国后在慈禧身边任事,后嫁美国人T.C.White,赴美生活,用英文写了一系列清宫故事,被译介入中国,引起很大反响。1930年代德龄曾短期回国,1944年在国外车祸身亡。她的回国和身亡在国内多有报道。她作品的另一位重要译者秦瘦鸥记述道:“当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她也曾在祖国有过较长时间的逗留,甚至还在上海跟李时敏君伍爱莲女士等演过几天英文戏,地点是博物院路时代的兰心大戏院,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宫秘史一类的剧本,由她自己扮演‘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西太后。”按身份,德龄在晚清是郡主,“在上海演戏,广告里少不得要写她的大名,她也就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46]
德龄《清宫二年记》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反响。这是德龄写清宫故事的第一部作品,以第一人称叙事。民初的中译本用浅近文言,讲述“余”侍奉慈禧两年的故事。从1903年3月随父回国入宫到1905年3月出宫至上海,两年的宫廷生活被“余”认为是“闺女时最乐之日也”[47]。因此小说所描述的慈禧和对慈禧通常的历史概括并不完全一致。译者在引言中说道:“其中所载,一得之身历目睹之余,日常琐碎,纤悉必录。宫闱情景,历历如绘。不独阅之极饶趣味,而隐微之中,亦可以觇废兴之故焉。至于一支一节,足备掌故之资者,更复不鲜。间尝窃叹昔在帝制之世,宫府隔绝,吾民之视皇宫,若瑶池琼岛之可望而不可即。虽或传闻一二,亦惝恍而莫得其真。今得是书,一旦尽披露于前,不亦快欤。”[48]德龄以亲历者的身份回忆了已逝去的清宫故事,与一般历史小说不同,《清宫二年记》写的是个人记忆,诠释了个人之于历史的关联,通过富有个性的小说叙事者与主人公,充分行使了“历史小说”的主体性功能。

《东方杂志》1914年第7期《清宫二年记》照片
“余”和母亲、妹妹被慈禧召进宫,成为最得慈禧宠爱的女官。小说由此详细叙述了慈禧的日常生活故事,慈禧的脾气心境在“余”的感受中变得生动而真实。第十三章写慈禧喜欢在雨中步行,喜欢拍照,还扮成观音照相。中译文道:“碰着我发气的时候,或有事烦恼,我装扮观音,气就平些。心里坦然,自己觉得我是个慈悲的面貌。我要装扮起来,照一个像,时常看看,可以勉励我永远为慈悲和悦的像。”[49]慈禧在“余”的叙述中是有喜怒哀愁,心怀良善,甚且博闻强识的女王。“余”对慈禧的好感渗透于字里行间。
小说第二章交代,“余”到宫中,并不只想当个宫眷,而是“当设法劝太后回心转意,使中国变法自强”,“当尽余之心力而为之”。[50]所以,在清宫的二年,“余”除了侍奉慈禧,当慈禧的御用翻译外,也在尽力说服慈禧“变法自强”。“余”引导慈禧接受照相技术,就是引入西法的一个例子。还是第十三章,再谈“西法”:“余志在使太后审知西法之美。太后并非顽固,常与余言欲将余等所陈,与大臣商量行之。有一事可以证明。一日余以在巴黎时所见之海军大操像片,与太后看,太后甚为动心,说也可以叫中国照这样做。后即以此事商之大臣,彼等乃用其稽延之惯技,答言须缓图之,不可急遽。读者诸君,当知太后即心思改革,亦不能一人独断,必须与大臣商量,而为大臣者,亦并不显然反对。但言事宜缓图,为时甚长,而天下事遂堕废于无形矣。”[51]慈禧在“余”的影响下“心思改革”,她并不顽固,可是势不遂愿。小说所叙大量情节是关于“西法”的,如招待外国使臣、欧洲服装、西洋画像、外国药品、巴黎家具等等,都为慈禧接受。清末“新政”便在这种宫廷日常变化中徐徐展开。
(二)从“演义”到“历史小说”
比较《孽海花》对慈禧“扰乱江山”[52]的描述,《清宫二年记》叙写了“另一个”慈禧。在民初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西太后演义》这类演义小说中,所叙德龄和慈禧故事,与《清宫二年记》或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地方也很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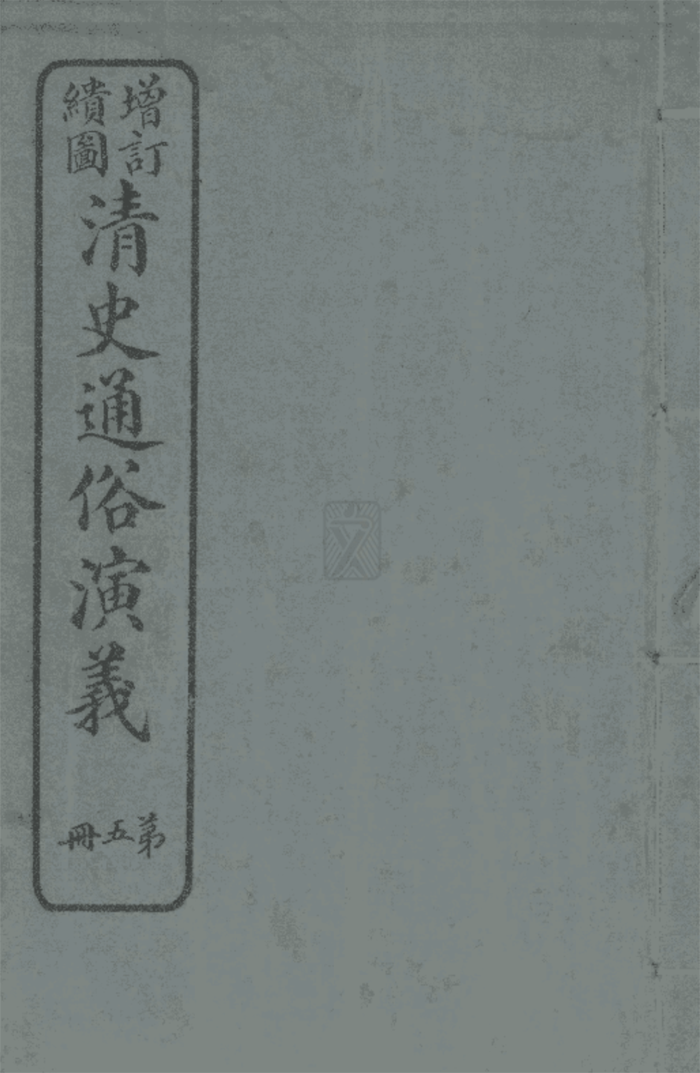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会文堂新记书局1925年版
在民初,蔡东藩以一己之力,在十年中编撰了多部“演义”体小说,叙述从上古至中华民国的全史。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小说史上‘正史演义’创作的集大成者”[53]。《清史通俗演义》出版于1916年,其中对慈禧的叙述主要在于执政方面,第九十一回和第九十二回叙述德龄进宫至日俄交战之事,这两回对慈禧日常生活有所涉及。第九十二回回末附言道:“慈禧后之喜谀好奢,曾见近今印行之《清宫五年记》,原书即德菱女士所著。本回第节录一二,而慈禧后之性情举止,已可概见。”[54]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宫二年记》中译本已出,它成了蔡东藩写作清史故事的一个来源。德龄给慈禧当翻译、慈禧接见公使夫人、慈禧的珠宝等等,这些《清史通俗演义》都采自《清宫二年记》,但叙述有所不同,不如《清宫二年记》细致有味。第九十二回叙克姑娘给慈禧画像事,仅用两节,“每日临绘一小时,绘至两星期才罢”[55]。画像一事在《清宫二年记》中有非常详细的叙述,且此事时间跨度很长,并非“两星期才罢”。第十二章末《清宫二年记》开始叙画像之事是1903年5月,直到第十九章密司卡尔完成画作已是1904年4月19日,小说明确交代了这一时间。其间叙述乞巧、中秋、元旦、正月、花朝等节庆故事,日俄战争等国事,也谈论了密司卡尔的家事、住处安排、酬谢事宜等。画像之事持续近一年,和《清史通俗演义》的记述很不相同。
如果说画像事就《清史通俗演义》而言仅是很微末的细节,概要叙写很平常,那么在《西太后演义》中仍有相似处理,便值得关注。《西太后演义》1919年初版,是继《清史通俗演义》后蔡东藩写的第二部历史演义,详细演述了慈禧的一生。对于这位主人公,叙述者的评价与一般看法不同。小说第一回论道:“前歌谁嗣?后诵孰杀?一片诽谤声,喧腾全国,甚且肆口讥评,捏词诬蔑,说得慈禧一钱不值,且目为中国罪人。其实往时的称颂未免过情,晚来的谤毁也不无太甚。倘使慈禧太后今日尚存,吾华的革命恐没有这般迅速,就令推位让国,也要弄得筋尽力疲,那里肯不战而退呢。看官不信,试想慈禧自西安回銮,途中并没有出险情事,到京后,依然手握大权,莫敢指斥。由辛丑至戊申,其间又经过八年,并没有损动分毫。到了光绪宴驾,宣统入嗣,宫中仍肃静无哗。及至自己病剧,犹且从容不迫,嘱咐得井井有条,自王公以下,统恪承遗训,安而行之。若非慈禧平日有强忍果毅的手段,笼罩得住,难道有这样镇静么?”[56]《西太后演义》对慈禧的评价不是否定的,“强忍果毅”和《清宫二年记》中“余”对慈禧的印象相似,因此这两部小说塑造的慈禧形象可以放在一起对读。
《西太后演义》共四十回,第三十三回“二慧女随母入宫”至第三十七回“划战域中立布条规”与《清宫二年记》的内容相合,《西太后演义》对德龄故事的叙写比《清史通俗演义》要详细,但对密司卡尔画像事叙述得仍很简略。第三十六回末慈禧接见密司卡尔,第三十七回开首画像就完成了。“却说克女士应召入绘,为西太后画油像,形容态度,很是相似。约数日即已告成,呈诸西太后。”[57]“约数日”似乎比《清史通俗演义》中的“两星期”还要短。可见画像事在蔡东藩的笔下不值多费笔墨,但却是贯穿《清宫二年记》后半部的主要事件,从中或可见出小说记述历史的差歧。画像事到底如何,虽然蔡东藩所记草率,但德龄的个人记述也不可全信。可以辨析的是“演义”和“历史小说”的区别。“演义”多行动叙写,少细致描摹,众多事件只是呈现经过轮廓,这是《三国演义》而来的叙事传统。“历史小说”就不同了,它是现代小说,融合了西方小说的叙事特征。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德龄,在西方语境中写下《清宫二年记》,其对历史的个人性叙述必然突破“演义”的规范传统。
清末民初的“历史小说”和“演义”虽然同时演述着历史故事,但“演义”的写法因现代观念的介入而渐趋势弱,“历史小说”替代“演义”并非只是概念的更迭,更有着历史观念和叙事方法的变更。就现代小说而言,“演义”不可挽回地衰落了,因为“演义”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已经不存在。“演义”要据正史,就“正史”而言,中国传统的正史叙事是二十四史的体例,包括纪、表、列传等。到了现代,史书的纪事体例已被欧美写作模式取代,《清史稿》之后,不再有传统体例的史书问世,这是一方面的文化条件的消失。另一方面是私史的渐趋消失。在古代中国,与正史相辅相成的是个人的野史、杂志、笔记,这些构成了中国伟大的私史传统,这一私史传统,是“演义”产生的必要条件。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后,历史撰述已被学科化,私史写作越来越少。就此,“历史小说”替代“演义”终不免成为趋势。
1930年代通俗文学家秦瘦鸥翻译德龄《御香缥缈录》[58]、《瀛台泣血记》[59]时,“历史小说”已是一种成熟的创作形态。1948年顾秋心再译《清宫二年记》,书的封面上印有“清宫中的生活写照”[60]几字,对小说内容做了大致说明。顾秋心的译本和陈冷汰、陈贻先译本的最大不同是前者完全是现代白话,而不是半文半白的语言。小说最后叙道:“在上海我交到了许多朋友,觉得在宫中二年的生活,仍不能铲除我在欧洲的一切习惯,我本来生长在外国,在外国读书,遇见了我的丈夫后,益发使我注定为美国人了。然而回视宫中二年跟太后一处的生活,仍然使我神往,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最有为的时期。”[61]可以说,顾秋心版《清宫二年记》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回忆叙事来装置历史的现代小说。
张蕾
苏州大学文学院
21512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3期)
注 释
[1]楼含松:《从“讲史”到“演义”——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历史叙事》,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35页。
[2]任公:《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1899年9月第26册。
[3][4]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8月第14号。
[5]见《新小说》1902年11月第1号。
[6]张蕾:《新小说与旧体裁:〈新小说〉著译作品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7]雨尘子:《洪水祸》第一回,《新小说》1902年11月第1号。
[8]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8月第14号。
[9]邱菽园:《新小说品》,转引自卢叔度《我佛山人文集·前言》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0]朱国桢:《涌幢小品》,司马朝军编:《四库全书总目精华》,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2页。
[11]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12][13]我佛山人著,王俊年校点:《痛史》,《我佛山人文集》第5卷,第91、102页。
[14]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罗贯中:《三国演义》毛宗岗批评本,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4页。
[15]阿英:《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页。
[16][17]我佛山人著,王俊年校点:《痛史》,《我佛山人文集》第5卷,第3,3、4页。
[18]《宋史·列传第二三三·奸臣四·贾似道》,《二十五史》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6733页。
[19][20][21]我佛山人著,王俊年校点:《痛史》,《我佛山人文集》第5卷,第59、59~60、184页。
[22]《元史·列传第四十三·张弘范》,《二十五史》第9册,第7660页。
[23]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24]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25]杨世骥:《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文苑谈往》第1集,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85页。
[26]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27]《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28]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29][31]阿英:《晚清小说史》,第228、228页。
[30]我佛山人:《两晋演义》,《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32]杨世骥:《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文苑谈往》第1集,第86页。
[33]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3页。
[34]东亚病夫:《孽海花》,小说林社1905年版。
[35]见《小说林》1907年2月第1期。
[3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37]强作解人:《孽海花人名索隐表》《孽海花二十四回中人物故事考证》《孽海花二十四回中人物故事考证续》,东亚病夫:《孽海花》,望云山房1916年版,第87~143页。
[38]东亚病夫:《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第1编,真美善书店1928年版,第6页。
[39]大仲马:《血婚哀史卷一》,病夫译,《时报》1912年9月16日。
[40]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41]《美国独立史别裁》,清河译,《月月小说》1906年11月第1年第1号。
[42]瘦鹃:《铁血皇后》,《妇女时报》1912年9月第8号。
[43]The Princess Der Ling: 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Moffat, Yard and Company, 1911.
[44]德菱女士:《清宫二年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单行本译者署名为“陈冷汰”,《东方杂志》连载本署名“冷汰”。
[45]《唯一无二之奇书 清宫二年记》,科南达利:《恨绮愁罗记》上卷,林纾、魏易合译,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封底整页广告。
[46]秦瘦鸥:《介绍原著者》,见德龄《瀛台泣血记》,秦瘦鸥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47]泠汰、贻先译:《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914年1月第10卷第7号。
[48]《清宫二年记》引言,未加标题,署“陈贻先识”。《清宫二年记》,泠汰、贻先译,《东方杂志》1913年7月第10卷第1号。
[49][51]泠汰、贻先译:《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913年11月第10卷第5号。
[50]泠汰、贻先译:《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913年7月第10卷第1号。
[52]曾朴:《孽海花》,苗怀明主编:《曾朴全集》第1卷,广陵书社2018年版,第288页。
[53]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54][55]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第4册,会文堂新记书局1935年版,第639、637页。
[56]古越东帆:《西太后演义》第1册,上海会文堂书局1921年版,第3~4页。
[57]古越东帆:《西太后演义》第4册,第70页。
[58]Imperial Incense(1933年英文版),秦瘦鸥译为《御香缥缈录》,《申报》1934年4月1日开始连载,有容龄序言和秦瘦鸥《介绍原著者——清德龄公主》,申报馆1936年版,春江书局1940年版,百新书店1945年版。
[59]Son of Heaven(1935年英文版),秦瘦鸥译为《瀛台泣血记》,《新闻夜报》1937年2月14日开始连载,春江书局1940年版,百新书店1945年版。
[60]德龄女士:《清宫二年记》,顾秋心译述,百新书店1948年版。
[61]德龄女士:《清宫二年记》,顾秋心译述,第15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