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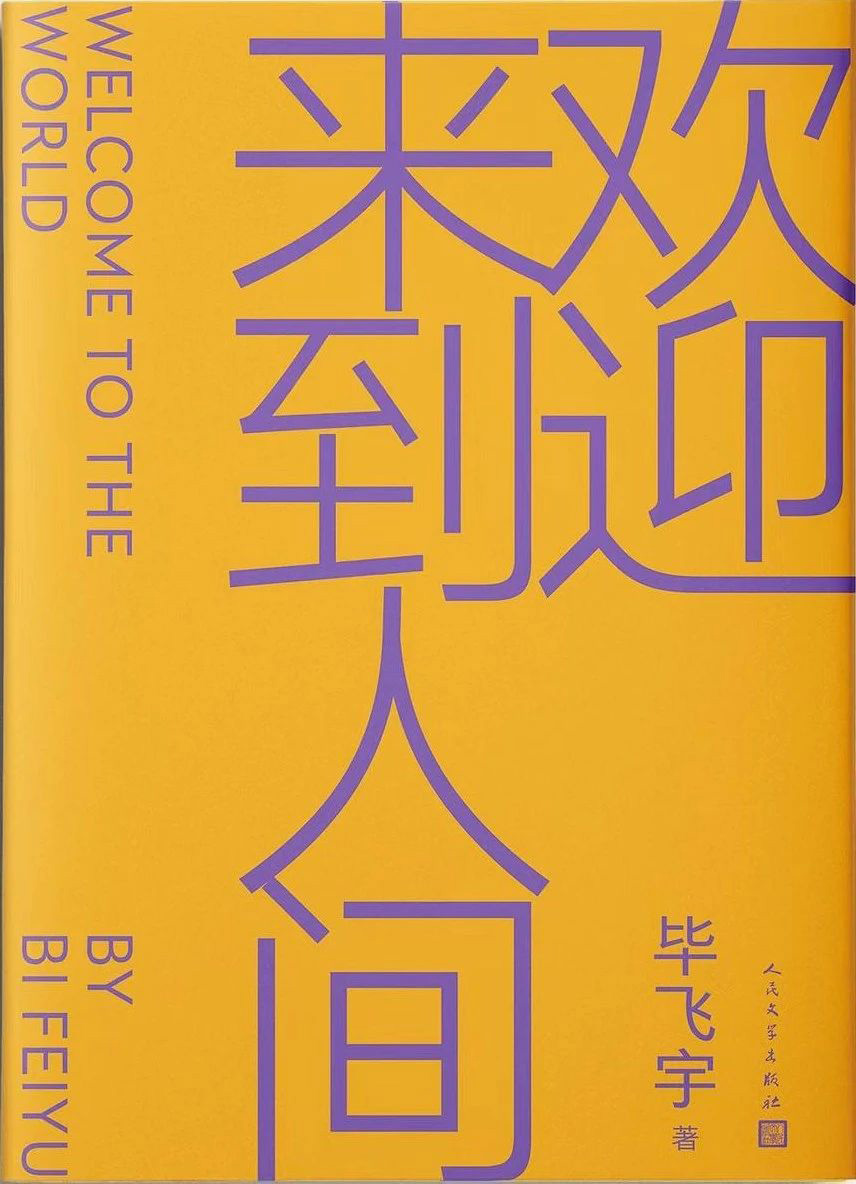
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
内容提要
长篇新作《欢迎来到人间》是毕飞宇切入当代、观照当下的突破性作品。围绕着主人公傅睿“医者”“患者”“解放者”的三重身份,作者呈现了微观权力笼罩下当代城市生活的现实图景,摹写了城市人群弥散性的“神经症人格”,并试图以“非理性”作为冲破压抑、争取自由的力量。小说以“非暴力”的叙事方式,真切地贴近了当代都市人群波澜不惊又日复一日的精神困苦,从而在当代小说中获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关 键 词
毕飞宇 《欢迎来到人间》 非理性 神经症人格
暌违十五年,毕飞宇推出长篇新作《欢迎来到人间》。毕飞宇寄予了这本小说厚重的使命:“一个作家没有理由到他死的时候,对他的家人和读者说,‘我’的一生跟当代无关。从文化结构上讲,我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东西嵌入当代。”[1]
小说原定的题目是《傅睿》,毕飞宇要通过主人公傅睿切入、书写、表达当代中国,“去展望新世纪之后整个族群的生活”[2]。
医者傅睿:人间图景中的“天使”
《欢迎来到人间》的主人公傅睿是一名外科医生。医生是“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3],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对医生还有悬壶济世、普济众生的道德要求。因此,医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负载意义的职业,至少包括三种属性,治病救人的拯救者、掌握知识的社会精英、舍己为人的白衣天使。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医生的形象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结合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建构的。

中国现当代医疗题材文学作品举隅
晚清时期的中国,日薄西山、危机四伏,而革命救亡的脚步正在逐渐迫近,革命者将民主科学视作挽救国家的良方。于是,“国家-积弊-志士-救亡”的关系,相当自然地被转化为“患者-疾病-医者-治疗”的关系。《老残游记》中,老残为大户人家黄瑞和治疗溃烂病的隐喻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这类模式的开端。到了抵抗日本侵略的1940年代,“医生-社会/国家”这一关系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达。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研究戏剧的医学家俞实夫为主人公,直接将法西斯才是破坏中国人生活的最大细菌这一主题彰显在题目上。在陈白尘的《岁寒图》中,黎竹荪行医和编制《防痨计划》的经过,既是履行医生使命的过程,更是认识并暴露社会黑暗,逐渐承担起为国家“诊病治病”的责任和使命的过程。家喻户晓的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更是极大地巩固了“医生-社会/国家”之间的关联性,使其几乎成为现当代文学中涉及医生形象时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救亡图存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医生形象的塑造偏重于强调其道德属性。“医生-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对国家的疗救,转为对不合理的社会潮流的拒斥。在丁玲1940年代的作品《在医院中》里就出现过的,在不理想的现实环境中坚持自我的医者形象,在新时期以后的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80年代,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大夫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对人性的坚守;1990年代,池莉《霍乱之乱》中的闻达大夫则代表着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自持与坚定。
《欢迎来到人间》继承了百年文学的这一书写传统。小说伊始,作者便以相当精致的笔墨绘制了一幅城市景象,表明这部小说并不止于讲述一个医生的故事,而是要为人物创造一个仿真的世界,借人物的视角观察城市、观照当下、摹写时代。
小说从一尊“千里马雕塑”开始:
为了体现时代的速度,一尊城市雕塑很快矗立在了椭圆形广场的中央。是一匹马,坐北朝南。绛红色,差不多像人一样立了起来,像跑,也像跳,更像飞。马的左前腿是弯曲的,右前腿则绷得笔直——在向自身的肌肉提取速度。马的表情异样地苦楚,它很愤怒,它在嘶鸣。[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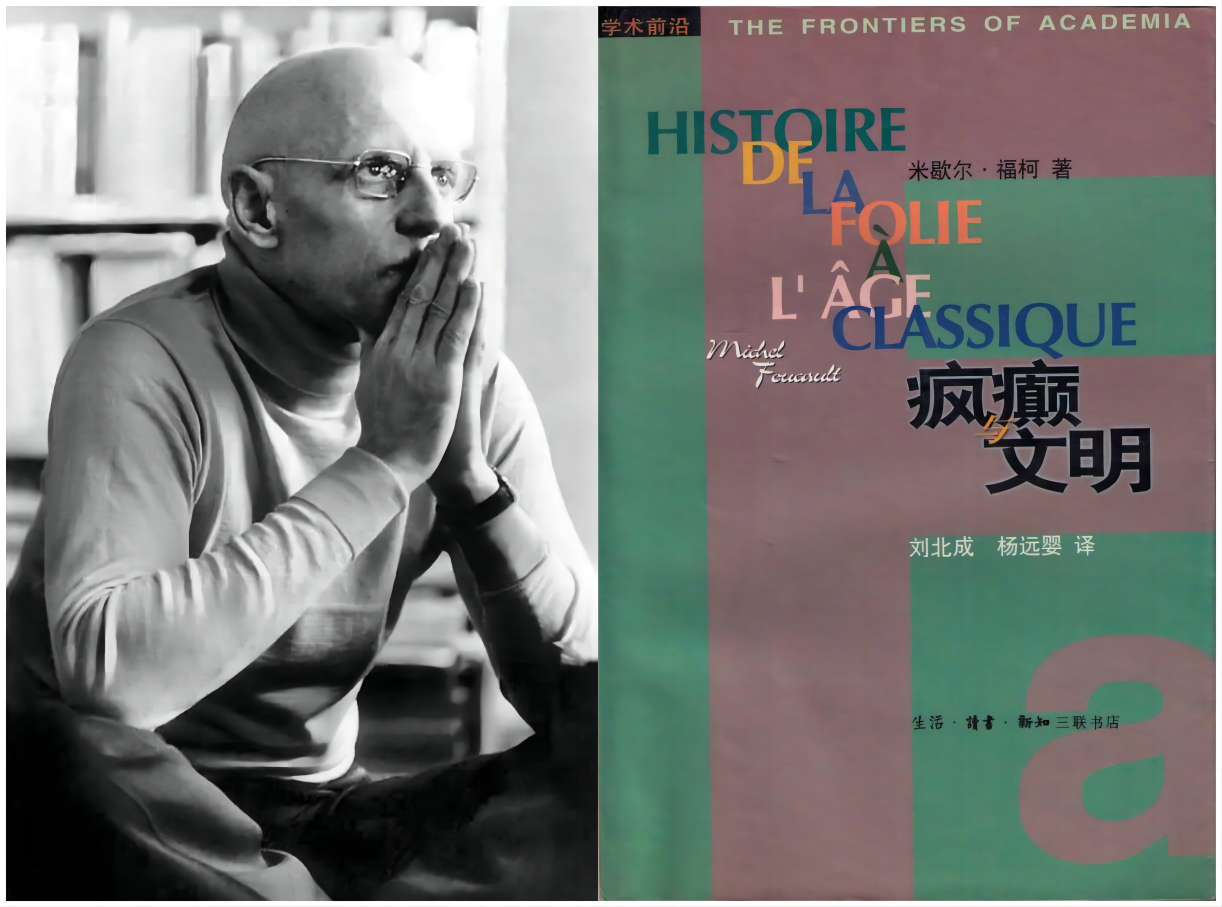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恍如《子夜》一开篇,茅盾就用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所射出的“Light, Heat, Power”来标识1930年代的上海, 毕飞宇用这座千里马雕塑直指时代的要害与症结——速度,以及速度带来的痛楚。城市围绕着“千里马广场”向我们铺开,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两条道路,隐含着这个城市过往的历史。不过,在滚滚的经济洪流面前,历史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气息”的残留。路两侧高大的梧桐被砍光了,明朝的铺路石换成了沥青,一切都是快速、现代的样子。就连道路的名字也被改成了“南商街”“东商街”,“商”的逻辑简单粗暴地盖过了一切。在对城市景观进行“航拍”之后,作者将镜头对准了主人公傅睿工作的地方——位于黄金位置的市第一医院。绕过最为显眼的门诊大楼,作者的镜头推进到第一医院“真正意义上的主要建筑”外科大楼,然后进入门诊楼内部,聚焦到第一医院的王牌科室泌尿外科。通过类似一组电影慢摇镜头般的描写,毕飞宇清楚地刻画了医院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医院非但不是世外桃源,反而是商业的中心、各种利益的交汇点。正如第一医院的书记傅博在市人大的报告中强调的,“我们去年的营业额超过了十个亿”。这里不只是救死扶伤的医院,它更是一个盈利的单位,是这城市的交汇点,“人间”的样板间。然而,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的主刀医生傅睿却是这“人间”的一个例外。
小说中“人间”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正是在傅睿与敏鹿相亲的时候。从敏鹿的视角观察到的傅睿:
傅睿的眼睛是多么地好看哦,目光干净,是剔透的。像玻璃,严格地说,像实验室的器皿,闪亮,却安稳,毫无喧嚣。这样的器皿上始终伴随着这样的标签:小心,轻放。敏鹿会的,她会小心,她会轻放。敏鹿就那么望着傅睿,心里说:傅睿,欢迎来到人间。[5]
小说的题目据说正是编辑程永新从这里摘取的,可以看作是整本小说的题眼。毕飞宇将“白衣天使”拆分开来,放大了傅睿的“天使”属性。“欢迎来到人间”,即他虽然在人间,却不属于人间,不熟悉人间。小说不断地强调傅睿的“非人间性”。当傅睿偶尔端详车窗外,他发现:
今天的空气特别地脏,黏稠得很,都有些发黄了。实际上,空气一直都是这样的,傅睿没有留意过罢了。傅睿很少注视二十米之外的远方,更不用说天空了。傅睿一直待在室内,基本处在灯光的下面,空气总是那么干净,它透明,接近于无。这一切原来都是假象,空气结结实实的,固体一样凝聚在一起。
作为天使,傅睿与“人间”最大的格格不入之处在于他的寡欲。他不慕钱财、不谙官场之道、不享口腹之欲、不善社交、没有特别的爱好,甚至已经没有了性生活。在这个热气腾腾、充满欲望的城市里,傅睿显得鹤立鸡群。
作者为傅睿设置了一个“参照系”,郭栋。郭栋是傅睿的同事,也是博士期间的同学。同样是大夫,郭栋却在各个方面都几乎是傅睿的反面。傅睿是“官二代”,郭栋是“凤凰男”;傅睿孤傲,郭栋随和;傅睿瘦弱,郭栋强壮。而最为重要的是,傅睿寡欲,而郭栋可以说是纵欲。小说用一道令人口角生津的菜诠释了郭栋的人间性:
铁锅里的铁生烟了。大爷把事先预备好的大葱、姜、桂皮、花椒、八角扔在了油里。炝完了,厨房里芳香四溢,未成曲调先有情哪。——油锅就是在这个时候燃烧起来的,它的火苗蹿得比大爷的脑袋还要高。大爷瞅准了这个时机,倒进了羊杂。油锅“嗞啦”一声,既像疼,也像高潮。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所有的羊杂当场就改变了它们的颜色与造型……香啊,香。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香,像命运的撞击。……它伴随着致命的诱惑,惊为天人。天上人间,不枉此生。
这道菜的名字就叫“天上人间”。这样诱人的甘旨肥浓,这样热闹的人间烟火气,恰与傅睿清冷寡淡的“非人间”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用敏鹿的话说,郭栋“跟上这个时代了,整个人都蓬勃,正享受着这个享受的时代”,而傅睿“吃力得很,说受罪也不为过”。[6]
傅睿寡欲,也就与人间拉开了距离,他得以“悬浮”着,以一种高半等的姿态微微俯瞰着这个人间。透过傅睿的视角,作者呈现了一幅“人间”的众生相。这里有捞金无数,如今却因病幽闭丧失自由,只剩下基本求生欲望的前报社领导老赵;有靠点钞票起步,一步步发达的银行行长郭鼎荣;有谈了七次恋爱,如今甘当胡先生情妇的护士小蔡……情感与欲望、父母与子女、媒体与公众,现代社会的诸多议题都可以在这个浮世绘中找到踪迹。这个“人间”既是复杂的,又有着清晰的逻辑,作者在一开始就言明了:“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不是买就是卖。”[7]理解和认可它,便能在人间怡然自得、翩翩起舞。小说里有个“观自在”会馆,在这个会馆里,权钱交易、假凤虚凰天天上演,这里是“人间”的极致形态,也是作者对“人间”的极致讽刺。作者说,看呐,那些名利场中的人,他们多么自在!然而这种自在,却都带着某种病态。郭栋是病态的贪婪:“每一顿饭都像玩命儿。是争分与夺秒,是强取与豪夺。是落荒。是饿狗遇上了新鲜屎。”[8]胡先生是病态的情欲:“他不是来过夜,不是,是遭到了意外的暴击,奄奄一息了。”[9]老赵是病态的被控制欲:“只要能跪下去,膝盖的缝隙都会微笑。”[10]个体的无意义感、道德标准的消散、自由的丧失,查尔斯·泰勒提出的现代性的种种隐忧在这里皆可对号入座。[11]
患者傅睿:神经症人格与“非暴力”
作者赋予了傅睿近乎完美的天使般的形象,他聪慧帅气、正直善良。但天使终要与人间遭遇,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这时的傅睿便成了一位处于焦虑和压抑之中的典型现代人。
尽管毕飞宇一直以擅长心理描写著称,但与他的早期作品相比,近年来的创作无疑更加鲜明地呈现出一种开掘人物内心深处世界的趋势。他如同手持采铲、头戴矿灯帽的工人,用力而耐心地向人性的最幽微处掘进。《欢迎来到人间》其实与《推拿》有着相通之处。它们写的都是“病人”,但都不是以“正常人”的视角去观察“病人”的“异态”,而是去体贴“病人”的内心世界,去书写他们的“常态”,他们内心深处的爱、痛与怕。《推拿》是从盲人的“视角”,让作为健全人的读者了解“他们所建构的客观世界是怎么样的状况”[12],了解盲人的心脏里“彪悍的马力”[13];而《欢迎来到人间》则是从有心理问题的傅睿的视角,去呈现他的精神世界,带领读者去体悟那里的细致逼仄、澎湃丰盛。所不同的是,盲人的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徐泰来对金嫣说的那句“你比红烧肉还要好看”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正是以一种陌生化的体验打动了我们,类似于修辞学上的“通感”。而《欢迎来到人间》打动读者的,则恰恰是熟悉,是“同感”。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杨佳慧译,北京时代文化书局2018年版
卡伦·霍妮在她那本著名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指出,焦虑实际上是一种恐惧感,“但导致恐惧的危险更明显更客观,导致焦虑的危险则往往是潜在而且主观的”,甚至“表现者自己本人基本上也不知道”。[14]于是我们不难发现,焦虑是现代性的必然伴生品。现代性要求人们不断向上、向前、尽善、尽美,于是就带来了模糊的对未知的恐惧、对不完美的担忧,焦虑就此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弥散性症候。而为了抵抗焦虑而产生的自我防御机制、试图找出缓和冲突倾向的妥协方式又与焦虑本身一起导致了现代人心理的紊乱,共同构成了“神经症”的组成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经症”确乎已经是我们的时代人格。
傅睿的焦虑首先来自他的完美和他对完美的执着。上小学的傅睿就曾因为担心在考试中写错了一个标点符号吃不下饭。成年以后,作者则用“洁癖”外化了他的焦虑:“他的西服干净。衬衣干净。领口、袖口干净。牙干净。指甲干净。面部的皮肤干净,找不出一块斑点。眼镜的镜片干净。瞳孔和目光干净。干净的镜片和干净的目光原来是相互呼应的,那样地相得益彰。头发。耳廓。脖子。还有他的气味。”[15]毕飞宇用“实验室器皿”来比喻傅睿的干净,同时也暗示着危险——这样的完美容不得一个小小的污点、经不住一次轻微的磕碰。
傅睿的“磕碰”是田菲的去世。“非典”过后,作为泌尿科王牌大夫的傅睿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经他手术的病人一连出现了八例术后死亡的情况,而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小女孩田菲。田菲的活泼可爱让傅睿一时心软,违背医生的原则,向她保证能治好她的病,这个没能兑现的承诺从此成了完美主义又道德洁癖的傅睿的心结。随后,两次表扬大会把傅睿推向了深渊。田菲死后的“医闹”事件不但没有对傅睿造成不良影响,以表扬傅大夫为主题的“老赵日记”还使得傅睿成了先进人物,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进入“骨干培训班”。在骨干培训班里,他深夜拖地,又成了“好人好事”。对傅睿而言,这是两次严重错位的表扬。“老赵日记”颂扬他半夜去探视病人,其实是他在田菲死后,无法遏制内心的焦虑,要去确认其他病人的情况;培训中心拖地,也只是他在极度焦虑之下的夜游。于是,对于傅睿而言,“表扬”恰恰是将他内心的脆弱与隐秘示众,他不过是一个被展示的工具,被选定、被赋予意义、被索要价值,他既难以招架,也无力制止。
在第二次表扬大会上,傅睿在心里进行了一台手术:
讴歌是多么地残暴,傅睿是患者,被捆好了固定带,他已经被推上了手术台。灯火通明,无一阴影。这一台手术要切除的不是肾,是傅睿脸部的皮,也就是傅睿的脸。傅睿很清醒。傅睿知道了,麻醉师没有对他实施全麻,是局部麻醉。稍后,中心主任、雷书记、老傅,他们齐刷刷地站在傅睿的身边。傅睿的父亲,老傅,终于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手术刀。他主刀。他要亲手剥了傅睿的脸皮。傅睿亲眼看着父亲手里的刀片把自己的额头切开了,中心主任和雷书记一人拽住了一只角,用力一拽,傅睿面部的皮肤就被撕开了,是一个整张。傅睿的面目模糊了,鲜红的,像一只溃烂的樱桃。却一点都不疼,只是痒。生命显示仪就在傅睿的身边,血压正常,心率正常,呼频正常,血氧饱和度正常。
现在,中心主任就拿着傅睿的脸皮,高高举过了头顶。[16]
作者赋予了傅睿的“神经症”更加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对于“脸皮”的焦虑。脸皮,也就是尊严。傅睿逐渐崩溃的过程,也正是尊严被破坏、被损毁的过程。如果说七位病人以及田菲的死亡挑战的是傅睿作为医者的尊严,那么两次表扬大会损毁的则是傅睿作为人的尊严。尊严的挑战与毁灭一直是毕飞宇小说创作中的关键词之一,《玉米》里的玉米、《推拿》里的都红、《平原》里的吴蔓玲……毕飞宇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以强烈的尊严感作为人物的核心特性的,而侵犯人的尊严的,往往是或隐或显的权力。
权力的施行,在《玉秀》里是一场性暴力,在《雨天的棉花糖》里是漫天的流言,在《推拿》里是视觉正常的人对盲人的同情,在《欢迎来到人间》里,便是傅睿父亲、雷书记、中心主任传承有序的神情语调。通过对傅睿精神世界崩塌过程的书写,毕飞宇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他将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来源,归结为无处不在的权力。不过,在以往的作品中,毕飞宇着力于向我们展示权力如何以历史暴力的方式加诸个人、带来人物命运猝不及防的转折,而从《推拿》到《欢迎来到人间》,随着作家的目光转向当代,权力更呈现为一种关系,接近于福柯所谓的“微观权力”,它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杂综合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综合性力量。这里鲜有显而易见的暴力,但人人都处在权力关系的宰制性笼罩之下,它浸透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平缓而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机制和心理结构,最终让焦虑成为生活的常态。毕飞宇写道:“傅睿的脸算是丢尽了。”这或许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玉秀》那个似乎有点突兀的结尾:“玉米捂上脸,在巴掌的背后咬着牙齿说‘脸都给你丢尽了。’”[17]权力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从显性的变成了隐性的,但个体面对权力关系时无奈的喟叹却是共通的。

电影《推拿》海报
如同在《推拿》中,毕飞宇在尝试问询每一个盲人,他们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盲的时间、盲的原因、盲的程度是怎样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在《欢迎来到人间》里,毕飞宇也并没有止步于对傅睿精神世界现状的刻画,而是去追溯了他的前史。毕飞宇曾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老话因为被重复的次数太多而差一点骗了我。写完这部小说(指《青衣》),我想说,命运才是性格”[18]。在《欢迎来到人间》里,毕飞宇探索着傅睿性格的来路。小说用插叙的方式,不断回溯傅睿的人生经历。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傅睿的人生一直是“被按揭”的,他有一对有着极强控制欲的父母。作者以插叙的方式多次回溯了傅睿的人生经历。幼年时期,他分分必争,为的是替母亲压过她的女同事;他在母亲的安排下先后学习了二胡、小提琴、钢琴——为的是一次文艺会演可以上台表演三次,被人当成音乐天才;长大以后,父亲为他选择了医学专业,为的是帮父亲圆他的医生梦。再之后,他的导师、他的研究方向、他的工作单位,都是早早安排好的,妻子敏鹿则是母亲为他挑选的能照顾他的“贤内助”。而傅睿,他“不争辩,不抗拒,你安排什么他就是什么”[19]。
毕飞宇对于傅睿“前史”的讲述,同样聚焦于权力关系,并且具体到了一个微观场域——家庭关系当中。父辈权力阴影下孱弱的子辈形象可以构成毕飞宇小说中的一个形象序列,《哥俩好》中的图北、《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的耿东亮、《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都与傅睿有着相似性。不过,在以往的作品中,毕飞宇往往以激烈的冲突来呈现父辈的强权和执着的自我意识拉扯下人物的内在分裂性,以强烈的悲剧性去反思父子这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哥俩好》中原本“一心想读金融”“套上著名的黄马甲”的殷图北,却背负着继承“教书世家”、成为一名教书匠的使命。在性意识觉醒之后,他“下海”了,彻底走向了父亲和哥哥期待的反面。《雨中的棉花糖》中的红豆,明明是女孩子一般的性情,却在朝鲜战争归来的英雄父亲引导下走上战场,最后在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和因为曾经做过战俘而被周围人鄙视的偏见中结束了生命。
“我不会做另一个你的。”[20]《哥俩好》结尾处图北的这句宣言几乎可以看作是《欢迎来到人间》之前毕飞宇代际书写的核心主题。而在《欢迎来到人间》中,毕飞宇没有将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冲突处理成表面的激烈对抗关系。对于父辈们的期待和安排,比起红豆们的不适合,傅睿是适合的。他是天才的外科大夫。他思维缜密、记忆力超群,还生就了一双“天生就该是一个外科大夫”[21]的手,他也的确成了医术精湛的大夫。到傅睿这里,毕飞宇其实将代际冲突的思考和描写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亲情并不是微观权力的化外之地,恰恰相反,微观权力可以通过个体渗透到由个体组成的家庭,再以代际传递的形式继续扩大它的影响。
小说通过一场傅睿缺席的傅睿专访,生动地表现了微观权力是如何在傅睿的原生家庭中运转的。老傅替傅睿应承了一场电视台的专访,采访的人来了,傅睿却失联了。然而傅睿的不在场并没有影响采访的进行,专访变成了他父母的“秀场”:母亲闻兰拿出了她的播音员做派,在镜头前喋喋不休地展示她完美的普通话;父亲傅博则端出了书记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夸耀自己对第一医院的贡献。这当然是作者的一个隐喻:在母亲眼里,傅睿是她可以炫耀的“别人家的孩子”;在父亲口中,傅睿是他值得赞许的下属。作为儿子、享受父母之爱的傅睿在他的原生家庭里一直是“缺席”的。毕飞宇不动声色地暗示着家庭温情的缺失给傅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小说中有大量傅睿的内心独白,却几乎从未出现过他的亲人,母亲闻兰、妻子敏鹿甚至儿子面团,唯一出现过的老傅,也是以领导而非父亲的身份出现的,而且还是撕毁他脸皮的刽子手。母亲闻兰这样认识傅睿:
知子莫若母。傅睿这孩子打小就这样儿,他热衷于额外的承担,他满足于额外的承担。然而,这承担并不针对任何人,相反,他针对的仅仅是他自己。在骨子里,这孩子却冷漠,很冷,尤其是和他亲近的人。在他所认定的承担之外,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恰恰又很难走进他的内心。[22]
但我们知道,傅睿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恰恰相反,他善良、敏感、博爱。与其说傅睿的承担仅仅针对他自己,倒不如说傅睿的冷漠仅仅针对他的亲人,他的冷漠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抗争,只是他的抗争并不是外向的针锋相对,而是内向的自我消耗。
当毕飞宇把对权力的理解从宏观权力转移到了微观权力,小说也就变得温暾了起来。作者将权力与个人的冲突、权力带来的代际问题都处理成了“去暴力”的,规避了死亡、性、离家出走这些小说中常见的,也是他过去常常使用的暴力反抗形式,最大程度地遵循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和现实生活的逻辑。配合傅睿作为大夫的身份,整部小说起承转合的关键节点,都落在“伤害与拯救”上。不断被外部力量损伤尊严的傅睿,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拯救欲。拯救小羊、拯救独角仙、拯救哥白尼、拯救小蔡。拯救“哥白尼大夫”是这一系列拯救行动的高潮。装修中从天而降的水泥包裹住了培训中心哥白尼的雕塑,“透过搅拌物,他(傅睿)看到了哥白尼窒息的表情。哥白尼已不能呼吸了,他的瞳孔里全是求助的目光”[23]。无法“呼吸”、无法“言说”的哥白尼大夫,让傅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他想要清除掉水泥,就如同他想要清除掉那些包裹着他、禁锢着他、令他窒息的空气。但是,水泥早已凝固,岂是傅睿能够撼动的,他的钢錾只能划下淡淡的痕迹,不但没能拯救哥白尼,反而使他身首异处。傅睿不断地尝试拯救,而每一次拯救都以失败告终,对他来说不啻于又一次的伤害,再次将他推向深渊……通过这种“非暴力”的螺旋式下坠,小说抵达了一种格外压抑的真实感和一种无法逃离的悲哀——驯顺而无措,不满又无从表达,这大约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或有形或无形的权力时最为真实的情态。作者没有选择去制造激烈的矛盾冲突,主人公也就失去了发泄的途径,于是不得不堕入无休止的精神内耗之中。他“陷入机械轮回般的自我抗争。只要傅睿的油箱里还有一滴油,傅睿就会永不停息地抗争下去”[24]。
解放者“free”:拯救他人与释放自我
不知毕飞宇是有心还是无意,傅睿的发音非常接近英文的“free”。与傅睿精神世界的螺旋下坠互为对照又相互交织,小说中另有一条螺旋上升的线索,即傅睿不断寻求精神自由,试图冲破束缚的过程。当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如水泥般禁锢住现代人的精神自由,我们能做的是否只有缅怀?毕飞宇显然并不甘心。在小说前半部分的极度压抑之后,叙事变换了风格和节奏,傅睿开始了他的反抗,他精神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被召唤出来,成为突破压抑的力量。在谈论这本书的创作时,毕飞宇谈到了他对书写“非理性”的渴望:“你如果问我脑袋里面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充分地呈现我们的非理性。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艺术家关注非理性都是必须的。新世纪之后,我们似乎把这个事情忘了。我们力图从二十世纪的非理性,缓慢地建立理性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理性的建立是有成效的,但是内心的那种非理性究竟有可能是怎样的一个局面,最起码我们的文学没有呈现它,我甚至都不认为我们的文学是完整的。”[25]巧合的是,卡伦·霍妮也曾论及非理性,她认为,焦虑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非理性,但这种非理性因素,往往是受到压抑的。“对于某些人来说,允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简直是一件不堪忍受的事情。这些人心中会隐隐觉得自己正处于被一股异己力量吞噬的危险境地中,由于坚信理性的力量,他们已经在无意识中将自己训练成了严格服从理智支配的人,因而对这群人而言,他们坚决无法自觉接纳非理性因素。除了种种个人动机外,后者的反应还涉及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极力推崇理性思考、理智行为,对于那些非理性或类似非理性的东西,我们将其一律认作低级之物。”[26]显然,毕飞宇与卡伦·霍妮达成了某种遥远的共识,即,我们需要去正视被现代理性所压抑着的自身的非理性、时代的非理性。

作家毕飞宇
小说多次强调,傅睿“寡言”。事实上,在小说前半部分理性占据主动时,傅睿不只寡言,甚至几乎是“静音”的;而后半部分,傅睿开始有声音了,他一旦出声,便多半是喊、是叫,前半部分里被压抑着的、影影绰绰的非理性以狂欢的形式大张旗鼓地走上了前台。
小说中出现了三次傅睿的叫喊。第一次叫喊,是他从老赵家出来,对着所有的建筑物大喊:“我保证你们都能活下来!”[27]在他眼里,所有的建筑物都跪立在他的面前,请求着他的承诺。此前,他刚刚向老赵做出了“我保证你能够活下来”的许诺。他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老赵的跪拜,在老赵“只有被拯救的人才会有”的泪光中获得了强烈的、“接近于幸福”的自我满足。在爱秋的见证下,这个小小的场域充满了仪式性。老赵的“跪”和“磕头”,使得现实社会的规则、秩序和身份被打破了,傅睿不再是不能做出允诺的大夫,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他被“加冕”了。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作为狂欢式中的核心仪式,加冕更具有“两重性”[28],加冕就是脱冕,国王即是小丑。在这个加冕时刻,傅睿的身份也是“双重”的,他是医生,也是病人,既是拯救者,也是被拯救者。他感受到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在田菲那里产生的自我怀疑,在两次表扬大会上被损毁的尊严,在这一刻被修复了,他获得了内心暂时的宁静。
傅睿的第二次大喊是在拯救小蔡的行动中。傅睿有一个疯狂的设想,他要用汽车的离心力重组人的灵魂,“只需一次呕吐”。整个行动中,作者一直在强调傅睿内心的理性和冷静,与行为的非理性和癫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直沉静的、恹恹的傅睿,在这次拯救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亢奋:“傅睿一上直道就减速,一旦冲上了弯道,他就拼命地抽帕萨特的屁股,驾!——驾!”“傅睿无比地亢奋,他大声地喊道——吐,吐干净!吐,吐干净!”[29]这是又一场“狂欢”。“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正是从这种郑重其事的官腔中把人们解放出来。”在与帕萨特的肉搏中,那个儒雅的、矜持的、理性的傅睿消失了,从一直规训他的成规中解放了出来。与其说这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发疯,不如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越轨行动,是“一种自由意识的突然放纵”,“心理的一种解脱,一种心灵的松弛,一种压迫被移除的快感”。[30]因而,这场不可能的拯救虽然无法拯救小蔡的灵魂,却救赎了傅睿自己,甚至也救赎了作家本人,毕飞宇说:“在描写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但我的手不能等,只有一个字一个字把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状况交代的清清楚楚,我的噩梦才能结束。”[31]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上岛咖啡里的那个狂欢时刻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个拯救了傅睿的光头是谁?他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仅仅存在于傅睿的幻想之中?或者,就是傅睿自己?完成了对小蔡的拯救之后,在光头狭小的地下室里,上演了令人惊异的“变形记”,他狂笑,他吼叫。他变成羊、变成狗、变成蛇。那个冷漠孤傲的傅睿变得乖巧、忠诚、讨好,他蹭、他舔、他依偎、他要抱抱,他毫无尊严。最后,他变成了蚕,吐干净了,睡着了。在帕萨特里,他曾高喊着让小蔡“吐!吐干净!”而此刻,吐干净了的不正是傅睿自己么?或者,是另一种可能让我们哑然失笑的答案:毕飞宇本人,不正是一个“光头”么?毕竟,从《虚构》中的马原到《褐色鸟群》中的格非,打破现实与叙事的界限不过是先锋派惯用的伎俩,而毕飞宇本人,早年也正是博尔赫斯的信徒。
三次狂欢,是小说中的越轨时刻,是傅睿最为疯癫的时刻,却也是他精神得到安宁和救赎的时刻。福柯认为,疯癫作为近代文明社会的产物,其罪魁祸首就是人的理性话语和理性权力。“作为起点的应该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由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32]理性通过其拥有的权力及各种微观权力,对非理性进行着绝对的统治。因而,在福柯看来,疯癫并不会使人失去本质或本性。恰恰相反,在人人相互欺骗的时候,疯癫构成了“欺骗之欺骗”,成为真理、正义、直言和诚实的化身,成为人的底线和本真,从而构成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有力批判。傅睿以非理性的方式寻求自由,正是对理性的挑战、对微观权力的挑战、对“人间”的挑战。傅睿的疯癫,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福柯所提到的“愚人船”,其上所装载的不是后来被混同于麻风病、罪犯、妓女和贼盗一类的精神病人,而是一船颇受欢迎的“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和社会的典范”[33]。他们比普通人更加直接地“向恋人谈论爱情,向年轻人讲生活的真理,向高傲者和说谎者讲中庸之道”[34]。因此,他们也往往会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傅睿是强大的,尽管各种权力关系让他不堪重负,但他不但拒绝了“人间”秩序对他的改造,还主动以非理性向“人间”宣战,他是勇者、也是英雄。由此,我们可以再次理解傅睿对哥白尼的共情:“和排列在图书馆门前的其他塑像不同,哥白尼医生并没有紧闭他的嘴巴,这是绝无仅有的。在他的上嘴唇和下嘴唇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缝隙。显然,那是言说的欲望。”[35]我们都知道,哥白尼是没有屈服于“地心说”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日心说”的人,傅睿对他,有一种同为逆行者的惺惺相惜。在拯救小蔡之前,傅睿曾与哥白尼有过一段“对话”:
哥白尼的脑袋埋在了草丛中,面朝下。哥白尼的嘴巴陷在泥土里说:“你要挽救她,你是医生。”大地的表层泛起了涟漪,把哥白尼的嘱托一直传递到了傅睿的脚下,傅睿的双脚听见了,哥白尼在说:“你要挽救她,你是医生。”
傅睿郑重了。夜色是使命的颜色,笼罩了傅睿。傅睿说:“我会。”[36]
这是傅睿的出征仪式。福柯引用德尚的诗说:“我们胆怯而软弱,贪婪、衰老、出言不逊。我环视左右,皆是愚人。末日即将来临,一切皆显病态。”[37]面对这个“病态”的人间,傅睿决定出征。他是“天使”,他观察“人间”,遭遇“人间”,现在,他要拯救“人间”。非理性的傅睿显然寄托了作者的某种理想,虽然这种理想带有显而易见的悲壮,以至于作者自己似乎也无法十分笃定,小说最后结束在了敏鹿苍茫一片的梦境里。
小说中一直并行着两个傅睿,一个是作为被观察的客体存在的“傅睿大夫”,他优秀幸运、风度翩翩;另一个是内心世界里作为主体存在的“傅睿”,他百病缠身、奋力挣扎。毕飞宇以傅睿来代表“新世纪以后”的族群生活,就是在摹写看上去非常幸运,踩着时代的风口起飞的这一代人,在物质生活基本实现自由之后的精神状态。这也构成了《欢迎来到人间》在当代小说中的独特位置。通过傅睿,毕飞宇突破了现实主义对琐碎生活细节的复现、对性的习惯性书写、对戏剧化冲突的依赖,真正抵达了微观权力下城市人群波澜不惊又日复一日的精神困苦。毕飞宇给了这种痛苦一个外化的症状——“痒”。每个人都体验过“痒”,它没有伤口,却无孔不入,它不致命,却无休无止。“你很难从临床上解释这样的征兆,那是千真万确的感受。”[38]痒是“活的”,它可以从一点抵达全身,甚至深入骨髓。当代人也许与傅睿有着不一样的境遇,但是,单调高压的工作,缺乏温情的家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道德与尊严的挑战,权力与利益的压迫……总有一样,或者几样,是我们每天正在面对的,是我们每天都在感受的“痒”。从这个意义上说,傅睿又是属于“人间”的,他“在‘这里’,也不在‘这里’;他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我们’”[39]。
刘月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0010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注释
[1]徐鹏远:《毕飞宇:重新回到人间》,《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9期,第73页。
[2]徐鹏远:《毕飞宇:重新回到人间》,《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9期,第72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42页。
[4]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
[5]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39页。
[6][7][8][9][10]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127、4、135、233、307页。
[11]参见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2]贺绍俊:《盲人形象的正常性及其意义——读毕飞宇的〈推拿〉》,《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13]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14]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杨佳慧译,时代文化书局2018年版,第33页。
[15]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59页。
[16]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218页。
[17]毕飞宇:《玉秀》,《玉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18]毕飞宇:《〈青衣〉问答》,《沿途的秘密》,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19]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257页。
[20]毕飞宇:《哥俩好》,《轮子是圆的》,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21][22]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29、165页。
[23][24]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254、262页。
[25]徐鹏远:《毕飞宇:重新回到人间》,第75页。
[26]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35页。
[27]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346~347页。
[28]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8页。
[29]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346~347页。
[30]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31]徐鹏远:《毕飞宇:重新回到人间》,第75页。
[32][33][34]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0、16页。
[35][36]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255、305页。
[37]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19页。
[38][39]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第247、3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