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
内容提要
鲁迅作品虽普遍存在戏剧性,但如果从戏剧文体本身来看,最接近完整戏剧体例的只有《过客》和《起死》,关于这一点目前已引起学界关注,但尚未展开充分讨论。本文首先从叙事文体的角度对这两篇文章进行深入辨析与阐释,并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话剧在中国本土的生存前景虽并不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依然身体力行地支持着中国新兴话剧的发展。《过客》和《起死》既为他的文类创作延展了美学可能性,也为中国早期的戏剧现代化提供了“鲁迅式”的思想参数。这两次戏剧实践所折射出的鲁迅之文体意识的核心指向正是他“精神界之战士”的立身态度和价值定位。
关 键 词
鲁迅《过客》《起死》戏剧形态 文体意识
鲁迅与戏剧这一话题在学界早已引起了关注,比如王富仁曾指出鲁迅的创作很多都可以认为近似独幕剧或多幕剧的结构[1];他还提到鲁迅的不少作品在叙事方式上是“有戏剧性的”[2]。王富仁在这里所说的戏剧结构与戏剧性显然指向现代戏剧(话剧)而非传统戏曲。后来也有其他学者进一步论述了鲁迅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戏剧性要素。[3]如果从戏剧文体本身来看,鲁迅所有作品中最接近完整话剧体例的要数《过客》和《起死》,关于这一点目前虽也被提及过,但尚未展开充分讨论。那么,《过客》和《起死》到底只是具有戏剧性要素,还是可以试图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话剧?此外,这两篇文章的写作体例明显分别与它们所在的两部文集《野草》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篇章“格格不入”。既然如此,鲁迅在创作这两篇文章之时为何要特别采用这种形式,而非常规的散文诗或小说体,这是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是否也透露出了鲁迅对于当时在中国本土刚兴起不久的新兴话剧所持有的某种态度,而这背后又折射出作者怎样的文体意识?
一 《过客》《起死》的叙事文体辨析
鲁迅曾致力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戏剧作品的翻译集中于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至1920年代早期,其先后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剧《一个青年的梦》和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另一个是在1930年代前半叶,鲁迅先后翻译了俄国卢那察尔斯基的话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第一幕以及西班牙巴罗哈的《波希米亚者流的离别》(又名《少年别》)。而《过客》和《起死》也正是分别创作于这两个时间阶段。
上文提到的“戏剧性”这一概念最早是对戏剧本质属性的概括,其目的是为了把具有戏剧性质的各种戏剧要素揭示出来,从而呈现出戏剧形态。后来“戏剧性”这一表述延展到了谈论小说和诗歌等其他叙事体式,虽脱离了戏剧艺术自身,但“亦颇能道出戏之为戏的某些特性”[4]。小说中的戏剧性更多的是关于其叙事结构、叙事时间、情节设置等某种特点,这也正是王富仁和其他学者基于小说这一文体定位所讨论的鲁迅作品的戏剧性要素所在。但如果能够将其作品从叙事文体的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辨析与阐释,或许对于进一步讨论和理解鲁迅作品的戏剧性这一命题会有些许助益。而要想深入剖析鲁迅这两篇文章的思想内涵以及作者背后的创作意图,亦先要对其所含的这种戏剧性进行明确的叙事文体辨析。
话剧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其最基本的是人物塑造,此外还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戏剧冲突、舞台说明和戏剧语言。如果把戏剧文本作为一个叙事文本来看,那么其叙述方式应是“展示”而非一般小说的“单纯叙述”。[5]罗钢曾提出,在这样的“展示”中,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个“反映者”的人物角色,他所做的只是反映自身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及思考,并非主动向读者讲述[6]。《过客》显然是在“展示”而非“单纯叙述”。他们在完成“展示”前,还需要先对戏剧叙事设置一系列成规。第一,“展示”必须在对话中进行,只有通过对话,“剧中角色才能互相传达自己的性格和目的”[7]。《过客》很明显是由老翁、女孩和过客之间的对话所构成的叙事文本,通过对话展现出了人物各自的性格与行为特征。第二,“展示”在戏剧中展开的前提是要有动作,而动作本身也是对话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叙事语言。戏剧就其本质来讲就是动作的艺术。所谓“戏剧动作”这个概念,最早可联系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及的“行动的摹仿”。在《过客》一文中,最明显的戏剧动作就是过客的“走”这一行为。“走”作为戏剧动作,是过客有意识的行为选择,也是其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作者在文章开头所安排的场景介绍为我们说明了过客来路的周遭环境,在如此晦暗荒凉的戏剧背景中,过客身着破衣裤拄着竹杖一刻不停地往前走,行走的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8]。因此《过客》除了具有显著的对话性之外也具备一定的动作性,基本符合适用于直接演出的独幕剧结构。其时间、地点及人物行动的一致性也符合传统“三一律”的惯常技巧。第三,“展示”还要在一定的戏剧情境中方能展开,即用以表现主题的情节及境况。《过客》的整体情节安排张弛有度,对于“坟那边是什么”的回环往复的叙事结构使得作品呈现出一唱三叹的美学效果与诗学意境。苏珊·朗格说,“戏剧就是一首可上演的诗”,在她看来,戏剧就是“以动作为形式的诗歌”。[9]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话剧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这主要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有关。朱栋霖也专门论述过关于戏剧的诗本体这一命题。[10]从这个角度讲,《过客》的诗剧定位也可以作相应解释,但这并不影响它在舞台上呈现出的话剧形态。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如果说《过客》是一场完整的适宜演出的独幕剧,那么《起死》可以看作是鲁迅创作的一出“案头戏”。当进入文本,我们会发现该文实则也具备了戏剧文体的基本要素,包括显著的戏剧冲突,清晰的人物台词,以及完整的舞台提示。鲁迅于1934年翻译《少年别》后的译者附记,他在其中提及这是一篇“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形式的小说”,而他之所以选择翻译,是因为“这种新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11]因此有些研究者推断《起死》也是仿《少年别》的所谓“戏剧体小说”。但鲁迅译后的《少年别》从体例上来看已经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戏剧文本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所界定的文体其实是具有模糊性的。
回到文本,整个故事情境主要围绕庄子展开。庄子途遇骷髅,请求司命大神将其复活,但是复活的汉子却以为庄子偷盗了他的衣物而与他争论不休,庄子无奈将巡士喊来解围得以逃脱,汉子则继续与巡士纠缠。[12]场景设置于荒地,主人公来自三个不同时空,在文本内部创造出了人物思想的交锋。从人物对话到人物动作均符合戏剧的程式,这种高度个性化的人物塑造也是戏剧文本叙述和舞台叙述在艺术上的契合点。但必须承认的是,《起死》的动作性要明显弱于《过客》,戏剧动作并不突出,在实践过程中舞台叙述的考量弱于文本叙述,《起死》因此呈现出案头戏的叙事模式和审美效果,或者说,更倾向于表现出了王富仁他们所说的“戏剧性”。
荆有麟在回忆鲁迅时说道:“《野草》中的《过客》一篇,在他脑筋中酝酿了将近十年。但因想不出合适的表现形式,所以总是迁延着,结果虽然写出来了,但先生对于那样的表现手法,还没有感到十分满意。”[13]《过客》确实与《野草》中其他某些记录“随时的小感触”的作品不同,同时也说明戏剧之于鲁迅创作的难度与复杂性,这在他的写作经验中并不多见。荆有麟的说法,也正说明了鲁迅对于《过客》的表现形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样,《起死》的写作体例也明显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篇章不同。那么,鲁迅为何要将这两篇文章以类似话剧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又透露出了鲁迅对于当时在中国本土刚兴起不久的新兴话剧的何种态度?
二 鲁迅为何“不看好”话剧?
鲁迅一生中所从事的戏剧活动涉猎广泛,除了上文提到的对外国戏剧作品的翻译之外,鲁迅长期热衷于观看话剧演出并开展戏剧批评。1937年一位名为恭勉的作者公开发表了《鲁迅和〈钦差大臣〉:作家和戏剧的姻缘》一文,在他看来,鲁迅对于话剧的爱好比当时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14]除了翻译剧本之外,他还经常介绍其他作家写的剧本。作者此外重点记述了一件事,在社会业余剧人演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的时候,鲁迅专门偕许广平和周海婴一同去剧场看剧。最重要的是,鲁迅观看话剧后特地托丽尼先生转达了他的几点意见。他从舞台设置,演员服饰、化妆、表演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鲁迅这一剧评行为后来也被欧阳予倩撰文提及,且就连欧阳予倩都觉得鲁迅比自称“行家”的人还要“内行”。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当时对于话剧极其专业且饱富热情的真实态度。
既然如此,他为何鲜少进行现代戏剧创作?以他在其他文学体式上的修养和造诣,他也完全有可能创作出成熟的戏剧作品。这似乎形成了一种矛盾。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与他对于中国传统戏剧及看戏观众的态度与看法是有关的。鲁迅深刻地意识到戏曲在中国的流毒之深,以及麻木的“看客”这一国民劣根性问题,严重阻碍着新兴话剧的发展。在话剧引入中国之前,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戏剧已然有了自己明确的态度,比如在《社戏》中他就表现出了对于戏曲的腻烦心理。鲁迅对于家乡目连戏情有独钟,但综观他有关绍兴旧戏的具体描述,鲁迅更多的是旨在对于乡土的眷恋,而非旧戏本身。1920年代初鲁迅开始公开批判京戏,彻底地将矛头指向旧戏中承载的落后思想和封建文化,并将其总结为“瞒和骗”的文艺传统。在这条“瞒和骗”的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15]。而在旧戏中,鲁迅对于京戏的批评最甚。他曾针对京戏中的性别反串表演强烈斥责,最早可见于他《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对于梅兰芳的批判。鲁迅认为梅兰芳饰天女、扮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极端不美”。值得提到的一点是,《论照相之类》刊于1924年11月,而就在此半年前,周作人刚发表一篇主张旧戏曲的文章,他指出“新剧当兴而旧剧也绝不会亡”[16]。在他看来,中国旧剧有长远的历史,其中“存着民族思想的反影”,且如果可以完全保存下来,“只当为少数有看这戏的资格的人而设”。鲁迅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也或多或少掺杂着周氏兄弟之间的个人恩怨与情感宣泄,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另一推测的原因。与此同时,胡适、刘半农也开始从“五四”初期对传统戏曲的大肆鞭挞转为拥护支持,且与梅兰芳有着密切交往,纷纷“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鲁迅虽同属于“新青年派”,但在对于旧戏曲尤其是对待梅兰芳的态度上,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鲁迅于1934年11月5—6日连续两天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猛烈抨击梅兰芳京剧艺术的题名为《略论梅兰芳及其他》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道:“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17]梅兰芳曾经认为中国戏剧是象征主义,而鲁迅敏锐地指出,中国戏剧和西方真正的象征主义实在天差地别,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梅兰芳认为的“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也同样不被鲁迅所认同。鲁迅在这里除了批判梅兰芳及其旧戏之外,其实也传递出了他对于西方戏剧的某种认识,他显然是熟悉象征主义的。而就在鲁迅连续发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之后不到一个月内,他创作出了《起死》。

鲁迅:《论照相之类》,《语丝》1925年第9期
除了对于中国旧戏文化本身的批判,鲁迅对于作为“看客”的中国观众也常抱有失望态度。1922年4月初,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的一个艺术团体“俄国歌剧团”经由哈尔滨、长春等地来到北京第一次演出,鲁迅去现场观看歌剧演出后,作了《为“俄国歌剧团”》一文。他看到楼上四五等座位还有三百多“看客”,但现场环境却如同“沙漠”般,观众既没有好奇心,也缺乏西方戏剧常识,只懂得在台上演员接吻时拍手欢呼。[18]鲁迅对于中国演戏场所的传统也向来不满。在《社戏》里他有这样的表述:“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应于剧场。”在他看来,这样的“中国戏”和“看客”很难与西方剧场适配,更不用说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话剧。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宿命论也是导致鲁迅不太看好西方戏剧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前景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普遍担忧而存在的。费迪南尔·布伦退尔(Ferdinand Brunetière)曾经有过关于戏剧规律的极富影响的经典论说:“东方人没有戏剧,他们只有小说;这是因为他们是宿命论者,或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定数论者,至少在今天看来是如此。”[19]这也会让我们自然想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中国的表述:“中国人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20]鲁迅也曾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所具有的这个根本性问题。而《过客》的出现,就是对所谓“听天由命”的挑战。过客的根本精神在于拒绝宿命,在于“反抗绝望”,反抗的实质又在于做出选择。作为一个在路上的过客,他最重要的就是不顾阻拦听从内心且勇往直前,同时要拒绝他人的帮助与施舍,在情感上做出极限选择。《起死》同样如此,“宿命”和“虚无”实乃一体两面。鲁迅在批判宿命论的同时,也否定了虚无体验的积极价值,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是非”观,既要反抗绝望,更要克服虚无。

费迪南尔·布轮退尔(Ferdinand Brunetière)
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鲁迅虽然对于西方戏剧持有积极热情的态度,但是对于话剧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前景实际并不看好的这一事实,而这也正是基于他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深刻认识。萨特曾言,“戏剧含有哲学意味,哲学又带有戏剧性”[21],戏剧形式也往往是可以用来把抽象的哲学思想中某些具体含义表达出来的唯一方法[22]。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再反观鲁迅的这两篇作品,就意识到他对于话剧文体的实践,实则是一种对于宿命论及消极避世思想的挑战,也是一种指向国民性的深层批判。这既是他对于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的态度,更是他对于话剧这种文艺形态的深刻理解。从这个角度讲,鲁迅的这两次现代戏剧尝试实乃良苦用心且弥足珍贵。
三 “到戏场去”的文体自觉
鲁迅用类似话剧的形式创作,这是他做出的文体选择,而这自然也渗透着他的文体意识。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他对于话剧的文体意识是彻底自觉的。在笔者看来,鲁迅在进行戏剧创作时的文体意识与他在杂文创作时的文体意识还是不同的,这自然和话剧的舶来属性不无关系。鲁迅对杂文文体的选择是他追求时代性与文学性相统一、功能意识与文体意识双重价值实现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他愿意倾注巨大精力于杂文的实践中并将之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至少在创作后期可以看作绝对自觉的行为。但反观其戏剧创作则是完全相反的局面。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猜测:他一开始并不打算介入戏剧文体,正如他对自己“戏剧的外行”的评价,而在构思《过客》和《起死》时发现戏剧的文体形式更适合表达他的主题思想,承载他的精神内涵。暂且不论他文体自觉的程度到底有多少,但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然可以判断出鲁迅着实意识到了话剧这种文学体式的客观存在,同时也吸收了话剧这一创作体例。但是,鲁迅向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自然也绝不会为了话剧而写话剧。与其说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文体意识是完全自觉的,毋宁说鲁迅在创作中延续的是他的精神自觉。他的文体选择的核心指向应是他的思想根基与精神脉络。
首先来看《过客》。剧中过客的核心行为就是“走”,而要想凸显动作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最好的叙事形态往往是使其作为戏剧动作而存在。对于过客而言,生的意义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而是要演绎出生命的鲜活价值,“走”即是对生命意志的深度开掘与深刻界定。鲁迅以这个戏剧动作赋予了过客对生命意义的形象性表达,他的“走”由此获得形而上的哲学诠释。鲁迅深知宿命论,洞悉了中国人关于命运循环与轮回的症结,于是他笔下过客的“走”更体现为对于生命意志的一种挑战。对于过客而言,他全然不顾前面有无坟墓,他的生命价值就在于“走”这个过程本身,即便一切最终归于“无”的境地,他也不在乎。这看似过客的选择,实则也是鲁迅一向追求的生命的本真所在——“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其体现出了鲁迅“中间物”的历史角色定位,实现了对于生命的肯定与超越。胡风于1929年10月撰写了《〈过客〉小释》一文,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过客’实在就是先生自己”[23]。过客的“走”以及在绝望中的抗战是鲁迅的生命体验,过客也是鲁迅一生沉郁又高昂的主旋律,是他所赋予人生以戏剧的悲壮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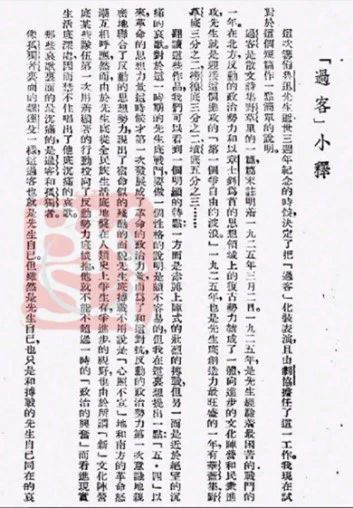
胡风:《〈过客〉小释》,《胡风文集》,春明书店有限公司1948年版
不同于《过客》通过戏剧动作的重复演绎表现对“生”之意义的显性呼唤,《起死》则是用戏剧中怪诞讽刺的手法重申了鲁迅对于道家无为,缺乏反抗精神的批判。纵观鲁迅的基本思想脉络,他对于老庄向来持否定态度。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尤其鞭挞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人群体。鲁迅认为,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类选择消极避退的文人只是“枭雄”,毫无社会责任感,并不利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与进步。在他看来,老庄的“无为”哲学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也是国民劣根性之所在。他把道家思想视为“不撄人心”[24],“不撄”就是不去正视黑暗,不敢面对强权。他公开表达对道教的憎恶,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起死》借由戏剧形式凸显出的油滑元素和荒诞境界,正和庄子的“荒唐的,放浪的,没头没脑的,不着边际的”[25]相呼应,这也是鲁迅在创作中重要的思想支点。在剧本一开始,庄子以道士的扮相出场,“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布袍,拿着马鞭”,他可以利用道力呼唤鬼魂,甚至将死人复活。这一系列舞台提示及戏剧动作无不是对于道教文化荒谬性的讽刺。此外,庄子一出场就开始使用庄周梦蝶的典故,随后再次重复“我庄周曾经做梦变了蝴蝶,是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成了庄周,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庄周”。众所周知,庄周梦蝶是《齐物论》中的一个寓言,代表了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个无解的问题在《起死》中依旧被重复着:“要知道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当庄子请司命大神把骷髅变成活人而司命拒绝之时,庄子又搬出了他的哲学观“其实那里有什么死生”,这种油滑之感正是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人价值观的排斥,是他针对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和“无是非”观所进行的绝妙的反讽与彻底的否定。正如刘剑梅将鲁迅的这种从现代语境出发对古代哲学寓言进行的改写,视为其从现代启蒙者的立场对中国国民性和文化积淀所进行的一次“大审视”和“大批判”。[26]在这个过程中,戏剧的叙事方式所形成的冲突感无疑是最有效且最具有冲击性的。

庄子
回到《过客》中,过客问老翁,前面是怎样的所在?老翁明确告诉他,前面是“坟”。通常意义上来讲,坟墓是死亡的象征。过客接着又问,那走完了坟地之后呢?老翁说,“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老翁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过客,他去过南边北边东边,唯独没有去过西边。众所周知,西边即西天,是人死后的去向,常常用作死亡的代名词。老翁出于善意劝告过客“转去”,其实也是对于死亡的逃避与拒绝。这是人之常情,是大多数人对于死亡的态度。然而过客并没有接受老翁的好意,他拒绝“转去”。而再往前走,只有死亡等在那里,这是已被预知的结局。面对死亡,常人的态度是恐惧,是拒绝,是躲避;与之相反,过客的态度是向前继续“走”,即便他很清楚前方是坟墓,是西天,是死亡的境地。他之所以能做出如此选择,源于他对死亡的不畏惧;相较于“死”,他更怕无意义的“生”。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27]。当在看清一切社会现实的虚无本质后,他便可以义无反顾地“走”,最终如同战士一般向死而生。
在《起死》中,鲁迅通过戏剧性手段将“死”这个终极动作指向了“复活”的可能性。庄子因为同情而复活了一具路旁骷髅的生命,他的尝试很快变成了一场充满误会的闹剧。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是对生死界限的戏剧化的超越,这个过程是对死的虚无本质的又一次指涉。由此一来,死不再是严肃而可怕的存在,他指向复活的可能,这也是对虚无意识的搏击。鲁迅倚仗戏剧的力量,得以跨越了生与死的界限。通往阴间的旅程因舞台独一的、阈限性的空间而得以存在,而同时又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是虚无世界的根本特质的倒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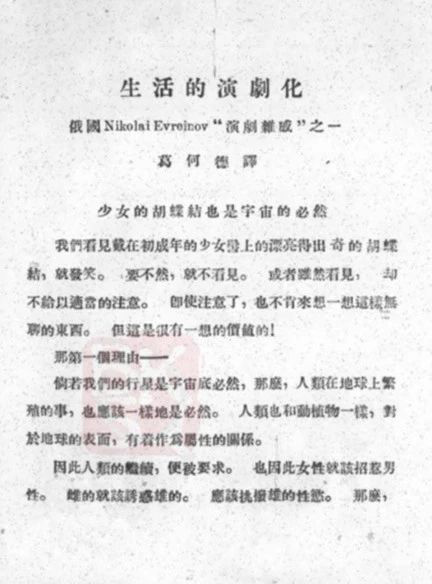
Evreinov,N.著,葛何德(鲁迅)译:《生活的演剧化》(“演剧杂感”之一),《奔流》1928年第1卷第2期
在新文学体式中,话剧当属晚熟,但鲁迅敏锐地看到了话剧本身所蕴含的力量。鲁迅曾在他翻译过的叶甫列伊诺夫《生活的演剧化》一文中大呼:“到戏场去,换一换心情!”“褪色的你们,便要成为绚烂的人!灰色的你们,便会明亮!懦弱的你们,便要成为强者!”[28]虽然无法确定鲁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对于叶氏的理论全盘接受,但起码他切实看到了这位俄国剧作家在文中所展示的“真的戏场”的变革力量,看到了戏剧性这一理念为社会的现代变革提供了一条出路。他虽无法完全预知话剧在中国的未来,但他依然勇于承担起了社会责任赋予他的人生角色,将自己“反抗绝望”与“克服虚无”的核心思想嵌入舞台上这一超越生死的循环旅途。这个逻辑渗透于他的这两次戏剧实践中,决定了他在文艺创作中的精神底色,同时也可以看作他将诗学理想与人生哲学相结合的先锋文艺思想的一帧截面。鲁迅一向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9]。鲁迅文体意识的根本是他对于文学特性的深切体悟,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持久介入和在创作上保持的精神自觉,而其核心指向也正是他“精神界之战士”的立身态度和价值定位。
刘一昕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9期)
注 释
[1]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页。
[3]参见孙淑芳《鲁迅小说与戏剧关系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4]董健:《戏剧性简论》,《戏剧艺术》2003年第6期。
[5] “单纯叙述”和“展示”是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单纯叙述”可以是当事人的直接叙述,也可以是别人的转述,而“展示”只能是当事人自己在叙述,就是通过角色之间的对话,将角色的动作和情境都展示出来。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6]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7]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9页。
[8]鲁迅:《野草·过客》,《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9]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10]参见朱栋霖《论戏剧的诗本体》,《学术月刊》1991年第10期。
[11]鲁迅:《〈少年别〉译者附记》,《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12]鲁迅:《故事新编·起死》,《鲁迅全集》第2卷,第485页。
[13]荆有麟:《鲁迅回忆(素笔忆鲁迅)》,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
[14]恭勉:《鲁迅和〈钦差大臣〉:作家和戏剧的姻缘》,《中国电影》(上海)1937年第1卷第4期。
[15]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
[16]周作人:《中国戏剧的三条路》,《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期。
[17]鲁迅:《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鲁迅全集》第5卷,第609~610页。
[18]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第1卷,第403页。
[19]费迪南尔·布伦退尔:《戏剧的规律》,罗士鄂译,收入罗晓风选编《编剧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20]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21]萨特:《萨特自述》,黄忠晶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22]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罗婉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23]胡风:《〈过客〉小释》,《胡风文集》,上海春明书店1948年版,第28页。
[2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页。
[25]钱穆:《庄老通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9页。
[26]刘剑梅:《鲁迅对庄子的拒绝》,《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8期。
[27]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
[28]尼古拉·叶甫列伊诺夫:《生活的演剧化》,《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29]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