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达夫:《屐痕处处》,现代书局1934年版
内容提要
旅游业及旅游印刷媒体在中国的兴起,构成了郁达夫1930年代游记写作的时代背景。这些风格鲜明的游记与当时的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流行话语存在着联系与冲突,反映出郁达夫对现实的敏锐感知。在文章体式和行文笔法上,它们部分继承了中国古典游记的书写传统,通过对作为中介的传统象征秩序的接纳与重构,迂回地切入现实。在这些游记中,风景书写不再只是个人主观情思的直接投射,而成为个人实现自我的延展并重建与现实、与历史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
关 键 词
郁达夫 游记 旅行 旅游 风景
1980年代以来,游记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1]游记研究在欧美学界备受关注,是因为游记——特别是在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大量出现的异域旅行记——在现代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尔·汤普森认为:“从15世纪到20世纪,(游记)这一文类在欧洲的帝国扩张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时期的游记所高度揭示的,不只是欧洲旅行者在国外的各种活动,还有那些推动了欧洲扩张主义的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同样,现代游记也能提供对于维持着当前世界秩序的各种意识形态与实践的重要洞察。”[2]旅行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现代性经验,无论是远赴异国他乡,还是云游国境之内,这些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群的接触,对各地风土人情的近距离观察,欣赏自然美景,乃至包括身体的运动,都会对旅行者的自我认知与主体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记游文学不仅例证了现代身份认同的多面性,而且对于文艺复兴以来现代身份认同的发展,也是最重要的文化机制之一,甚至是一个关键的原因”[3]。
中国现代游记的产生,虽然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欧美游记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和理论意识,仍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游记作品及其包含的现代经验。郁达夫的游记向来被誉为中国“现代游记的一朵奇葩”,“代表了现代游记文学的最高成就”[4],本文试图在新的问题视域中重新考察郁达夫1930年代的游记,揭示蕴含其中的丰富的文化意义。
一 旅行、游记与民族国家想象

郁达夫:《达夫游记》,文学创造社1936年版
1933年4月,郁达夫移家杭州。杭州的山水胜景让他有了爬山涉水的兴趣,即便只是半日的游程,在他看来亦可“聊以寄啸傲于虚空”[5]。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4月,郁达夫先后应杭江铁路局和东南交通周览会的邀请,周游两浙与皖南,写下一批脍炙人口的游记,于1934年6月结集为《屐痕处处》出版。1936年,编入更多新作的《达夫游记》问世,郁达夫于是更被看作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6]了。
郁达夫转向游记写作并大获成功,这既是机缘凑巧,也是时势所然。吴晓东指出,1930年代中国风景游记的生产与当时的旅游热以及政府的推动有极大关系,而出版界的闻风而动与主动出击,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7]这提醒我们,郁达夫的游记与1934年前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紧密相关。
1933年11月,杭江铁路全线通车在即,杭江铁路局希望借铁路沿线的山水形胜来吸引游客,提高客运收入,遂邀请郁达夫和摄影家陈万里、郎静山同游铁路沿线诸名胜,为拟将出版的旅行指南和导游丛书增色。《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即是此行记游之作,它们与陈万里的《杭江琐记》以及陈、郎两人的摄影作品,均被收入1933年12月出版的《浙东景物记》[8]。1934年春天,郁达夫又应浙江省建设厅筹办的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之邀,与林语堂、全增嘏等好友结伴,从杭州出发,经玲珑山、天目山,出昱岭关入皖,至休宁屯溪,游白岳齐云,写下《西游日录》《出昱岭关记》《屯溪夜泊记》《游白岳齐云之记》等多篇游记。东南交通周览会的举办,有明显的政治背景。从1932年5月起,连通苏浙皖三省的沪杭、杭徽、京芜、苏嘉、长宣、京杭六条公路相继开工,至1933年11月工程最艰巨的杭徽公路建成,三省六路遂实现了全线通车。而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五省筑路特别是五省交界地带军事公路的修筑,即为此准备。1934年2月,蒋介石下令筹办东南交通周览会,名为显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成就,实是要借此检验围剿红军的联络公路是否畅通。[9]“促进交通事业、开发东南名胜地区、引起中外人士游览兴趣”[10]云云,只是表面文章,而广邀社会各界名流为此撰写、创作各类诗文、书画、摄影作品,无非是想借助文化来为南京政府的国家建设背书。
1930年代的中国旅游业及相伴而来的现代游记的兴起,不仅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密不可分,而且也参与并促进了当时强势的民族主义政治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进程。埃里克·朱洛指出,旅游业的兴起一方面与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新的消费模式、健康观与审美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以铁路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化进程直接推动的结果。到了二十世纪,旅游更是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在政治光谱上或左或右的各派政权都试图用以实现各自的目的。[11]正是因为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以及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旅游“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经验的一个简明的隐喻”[12]。1930年代初,国内政局渐趋稳定,交通建设发展迅速,尤其是南京政权根基所在的东南五省间铁路和公路系统的初步建成,为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旅游逐渐成为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不断扩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主要休闲方式,政府机关和大中小学也时常组织集体旅游,这样就在193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13]

《槪說:東南交通周覽會路線圖》,《东南揽胜》1935年3月
有学者认为,1930年代中期各地省市政府积极推动旅游,与新生活运动有一定关系。[14]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年发布关于生活艺术化的初步推行方案,其中一条要求“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15],但很难由此断定旅游的发展得到了新生活运动[16]的推动。同样无法证实各级政府积极推动旅游,曾受到当时纳粹德国推行的“通过快乐而强大”运动[17]的启发,是要把旅游当作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尽管如此,举办东南交通周览会、筹建黄山风景区之类的举措,除了经济民生方面的考虑,的确也有与“通过快乐而强大”相似的政治目标,即鼓励民众更多地参与原先只为社会中上阶层所独享的旅游活动,借此强化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对现政权的支持。[18]漫画家王敦庆在参观东南交通周览会应征文艺作品展览后,就联想到“隆盛时罗马全赖脉络式的大道,把他们的帝国像铁一般地连锁起来”,因而认为东南五省交通网的联系成功,“不仅是旅行的便利或经济的拯救而已”,它在政治上和国防军事上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19]可见与交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的想象。旅游是对民族国家地理空间的体认和丈量,壮丽的河山和悠久的文化古迹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操,有力地重塑他们的文化记忆和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旅游业的兴起也与印刷媒体的推动分不开。旅游的发展催生了对于地图、旅游指南以及游记作品的需求,这些印刷出版物反过来又激发了人们对旅游的兴趣。与旅游和旅行相关的印刷出版物,当然不只是为了开拓商业市场,它们还给读者提供了各种现代知识,在无形中塑造了人们对于自然/文化、民族/世界、自我/他者等方面的认知。鲁迪·科沙尔研究了十九世纪后期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及欧洲出版的旅行指南,指出旅行指南很难摆脱政治发展的影响,它们常常承担着说教和宣传的功能,以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20]包括游记、探险报告和民族志在内的旅行写作,对西方人自我意识的形成有着更为巨大深刻的影响。保罗·斯梅瑟斯特认为:
跨越了数世纪的欧洲旅行写作,在生产和传播关于欧洲之外世界的知识以及助长扩张和征服的野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旅行和旅行写作,以及它们所唤起的地理想象,对帝国的话语形成至关重要,特别是它们暗示并巩固了像西方/非西方这样的粗陋的二元对立,而与其相关的则是文明/野蛮、科学/迷信等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固定表述。这种话语形成并非只是天真地提出一些分类范畴,使西方(一个可疑的同质体)得以依据一个投射的他者来定义自身。帝国主义话语即建立在一整套渗透着意识形态的不对等的关系体系之上。[21]
在现代中国,与旅游相关的印刷媒介虽然没有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话语的色彩,但同样有着民族国家政治的投影。莫亚君认为,现代中国的旅游指南和游记等大众旅行叙事,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都是细察一个正在创建中的国家的重要工具”[22]。良友杂志社组织的摄影旅行活动及后续的出版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良友杂志社组织全国摄影旅行团,足迹遍及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地,拍摄了一万余张照片,陆续发表在画报上,又从中选出二百多幅有代表性的照片,先后在上海、南京、汉口、北平、香港、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展览。[23]1934年4月,良友出版公司在摄影团所拍摄照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大型摄影总集《中华景象》,“是书以省为经,系以子目,以图为主,辅以说明”[24],全面介绍了全国各地的风貌。在书首的《发刊旨趣》中,编者明言此书出版,是希望于“方今中华命脉之危,不绝如线”之际,“扬震旦之光华,觇时代之进步”,使国民中“竺旧者知所维新,媮懦者咸思奋发”,庶几“于保国强民之业,亦容有秋毫蚁子之劳”。[25]回荡其间的正是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强音。
良友摄影旅行团主任梁得所在旅途中也写有不少随笔,陆续发表在《良友》及其他刊物上,后来结集为《猎影记》于1933年7月出版。这部游记所呈现的旅行路线图颇耐人寻味。从首都南京正式出发,第一站到孔孟故里巡礼“圣林”;之后赴华北,前出山海关,在北平拜访了胡适、蒋梦麟等学界名流,以及吴佩孚、张学良、冯玉祥等新老将军。然后至西北,深入塞外沙漠,再折返中原。虽然足迹未遍及全国,但所到之地、所见之人与所记之事,都经过了精心选择,别有寄寓。显然,旅行所穿越巡览的,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还有民族历史文化与道统。在对各地风土人情的描画中,危急的现实处境与理想化的民族历史与传统都鲜明如在眼前。读者不仅被引导着去看什么样的风景以及怎么去看,而且也被引导着去想象一个共同拥有的疆域和历史,进而形成民族认同。
摄影画册和游记这些印刷媒介深度参与了现代中国的风景生产,这些被打造为“中华景象”的风景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本质,它们不仅通过改变风景的符号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或重新定义了中国的人文的、自然的环境,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作为中国人的自我定义和自我认同的方式。可见风景的生产不仅缠绕着民族主义的思想话语,而且也深深嵌入了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政治进程。
二 现实的与历史的讽喻
郁达夫开始大量写游记,是乘了旅游业和旅游印刷媒体迅速发展的东风,但他的游记却较少受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那种认为旅游是要帮助人们“对于国家往古来今,有整个之认识”从而“油然起爱护其国家之心”[26]的论调,他未必会赞同,当然也不会认为游记应负有此种责任。他向来反感狭隘的国家主义对文艺的干涉,在他看来,“现代国家是和艺术势不两立的”,因为艺术的最大要素“美与情感”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强权、掠夺与破坏恰相对立。[27]对国民党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推行的各种政治议程,他并不认同,反而在游记中对当时的现实与时局多有尖锐讽刺。《感伤的行旅》中分明浮现着国民党“清党”的恐怖气氛,《钓台的春昼》也发抒了对“帝秦”暴政的愤怒。即使在看似名士气十足的两浙游记中,也时而露出贬刺的锋芒。《浙东景物纪略》中《仙霞纪险》《冰川纪秀》两篇更是生动地描绘了围剿红军给浙闽赣三省边界带来的动荡。1933年11月,为粉碎第五次围剿,红军进军赣东北,攻克玉山县的樟树、童家坊[28],随即成立了玉山县苏维埃政府。[29]郁达夫一行游江山和玉山,正值此时。在仙霞关外的二十八都,他看到的是一种紧张而恐慌的景象:
许许多多的很整齐的人家,窗户都是掩着的,门却是半开半闭,或者竟全无地空空洞洞同死鲈鱼的口嘴似的张开在那里。踏进去一看,地下只散乱铺着有许多稻草。脚步声在空屋里反射出来的那一种响声,自己听了也要害怕。忽而索落落屋角的黑暗处稻草一动,偶尔也会立起一个人来,但只光着眼睛,向你上下一打量,他就悄悄地避开了。你若追上去问他一句话呢,他只很勉强地站立下来,对你又是光着眼睛的一番打量,摇摇头,露一脸阴风惨惨的苦笑,就又走了,回话是一句也不说的。[30]
这种瘆人的景象把他们的食欲和游兴全都吓跑了。到了玉山城外,“那种异样的,紧张的空气,更是迫切了”,“浮桥的脚上,手捧着明晃晃的大刀,肩负着黄苍苍的马枪,在那里检查入城证,良民证的兵士,看起来相貌都觉得是很可怕”。于是他们决定不进城,只在城外的冰川溪边走走。遥望“玉山城里的人家,实在整洁得很。沿城河的一排住宅,窗明几净,倒影溪中,远看好像是威匿思市里的通衢。太阳斜了,城里头起了炊烟,水上的微波,也渐渐地渐渐地带上了红影”。[31]秀丽整洁、如梦似幻的市廛人家,却摇荡在兵荒马乱的恐怖气氛中。因为写得太真实,这两篇游记在《浙东景物记》和官方出版的《东南揽胜》中都被大幅删削了。

《旅行者的收獲》,《摄影画报》1934年第10卷第25期
郁达夫不愿在游记中粉饰太平,其家国之爱与忧却时有流露。《雁荡山的秋月》借一群旅行中的中学生的蓬勃活力和刻苦砥砺精神,喻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钓台的春昼》、《桐君山的再到》和《过富春江》三篇,则借谢翱西台恸哭的故事,提醒国人毋忘东北沦陷的国耻。在他的游记中,现实的疮痍与自然美景以及文化记忆交相叠映,赞美与贬刺、认同与揭露亦彼此交织。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郁达夫1930年代的游记,特别是《杭江小历纪程》《西游日录》等,与中国古典游记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是富于中国古典素养的文士的游记,举凡山川典籍,文化风习,名人遗事,常流入笔端”[32]。《杭江小历纪程》、《西游日录》以及《南游日记》均采用了传统的日记体游记,这种记录行旅见闻的游记,始见于唐代李翱的《来南录》而盛于有宋一代,以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为代表,美国学者何瞻称之为江河日记,其内容是高度多样化的,既有对沿途风景和历史古迹的描画,也有对当地风物民情的观察和报道,以及作者的议论、评述,甚至还穿插有作者的诗作。[33]王立群谈到《入蜀记》,也特别指出其中“文化认同意识完全超越了对自然美的鉴赏”,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往往“既舍弃了对自然美的领略,又抛开了对艺术美的欣赏,而是一味地沉湎于对某些诗句的正误判断之中,沉湎于历史掌故的考辨,碑刻佚闻的记述,甚或是绘画、民俗、茶道的叙写之中”[34]。事实上,对旅游名胜作为历史遗迹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重视,不仅是《入蜀记》而且也是有宋一代高度成熟的游记文学的一个普遍特征。史书和方志中的记载,前代文人的诗文题咏和碑刻铭勒,其数量多寡,往往决定了一个景点在文化价值上的高低,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自然山水的奇绝。张聪因此认为,宋代文人游历各地、探访名胜,本质上就是一场“文化朝圣之旅”,这也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身份标志,“通过突出旅行的道德、学问和文化功能,宋人加强了他们作为儒家君子、受人尊敬的学者和国家的文化引领者的地位”,而这种旅行活动本身又“促成了其后整个帝制时代各地地方记忆和国家文化版图的形成”。[35]
在郁达夫的两浙游记及其后的“闽游滴沥”中,都能看到中国古典游记的鲜明印记。旅游之于他,的确有着近乎“文化朝圣”的意味。每次出游前,他都很注重搜集和阅读与景点相关的历代文献。1934年的杭徽路之行,原计划要登黄山,他特地从各种方志和前代游记中抄录了相关资料,纂成《黄山札要》一篇;1935年10月,与王征共游天台雁荡之前,他向图书馆借得张联元所辑《天台山全志》,以备导游之用。在游记中,他常常信手拈来方志中的记载、野史逸闻以及前人的游记和诗作,可见事先都曾认真做过案头工作。在文章体式和风度上,这些作品也往往神肖古典游记。《杭江小历纪程》就采用了旅行日志的经典体式,其中记诸暨五泄,引徐霞客[36]、王思任等人的游记以为参照,并抄录万历《绍兴府志》中所记载的故事传说,考辨刘龙坪其名之来由。“苎萝村”一篇,前半部分谈论当地关于西施的各种传说,后面却特别提到同为义乌人的骆宾王和宗泽;前后各赋一诗,两相对比,讽喻之意毕现。游兰溪的横山和洞源,除绍介、考辨历史古迹外,又注意到当地的花船因铁路的开通而几乎断绝了生意,江边花事的盛衰,竟也暗含着世道变迁的消息。将风景描写、历史考辨、诗文引录以及对风俗民情的观察熔于一炉,这种行文笔法是对中国古典游记的伟大传统的一种致敬。
古典游记所展现的,是一个意义完整统一的稳定世界,山水草木、游鱼飞禽乃至断碑残碣,都有着明确的意义指向,它们所具有的象征力量往往确证并强固了既有的文化记忆和意义系统。而在郁达夫的游记中,古典游记中那种统一的意义系统已不复可见,虽然凭借文化记忆的绵延,山水、风物和遗迹在一定程度上尚保留着既有的符号象征力,但这些象征价值的稳定和有效只是局部性的,而且常常被各种尖锐的现实经验所扰乱和瓦解。现实人生中粗粝鄙俗、不乏残酷的一面,往往会在一瞬间展露无余,破坏山川美景给人带来的崇高感和美好想象。《杭江小历纪程》中写到五泄的永安禅寺,居然煞风景地说,寺里的和尚吃肉营生与俗人无异,千年古刹门风颓荡,只剩下啖饭之道了。《西游日录》里西天目山的禅源寺、东天目山的昭明禅院同样精于营收,广有寺产,将佛门净地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名利场。名山大刹这样的传统文化符号所传递的历史记忆和象征意义因而被破坏殆尽。
《扬州旧梦寄语堂》更有力地解构了传统的象征秩序。在中国文化中,扬州是用无数绮丽诗文堆砌而成的记忆之地。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认为,“扬州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所占据的地位,可以与其后威尼斯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媲美,这种地位正是来自财富、权力和文化生产力的结合”[37]。换言之,扬州的令人销魂就在于它代表了中国人对一个繁华而又美好的生活世界的全部想象,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达成了和谐的均衡。然而在郁达夫的这篇游记中,古代诗文中所描写的扬州的旖旎风光却已荡然无存,不仅街道狭窄、市廛低矮,而且荒凉萧条,竟与鲍照《芜城赋》中所描画的景象约略相似。能让他踯躅流连的地方,只剩下梅花岭下的史公祠了。

《郁達夫會見李太白》,《飘》1946年第2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运用现代阶级分析的方法解构了中国历史上的扬州神话。他认为扬州自唐宋直到清朝的繁华,只因其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商业云集,随之产生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奴隶阶级。扬州的风雅和淫靡只属于有钱的老爷和作为帮闲食客的才士雅人们,贫民的儿女只能被迫做婢妾和娼妓,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即基于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了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38]扬州的那些美丽的名字,如绿杨村、廿四桥、杏花村舍、邗上农桑、尺五楼、一粟庵等,在现实中“也许只有一条断石,或半间泥房,或者简直连一条断石,半间泥房都没有的”。与其将扬州旧梦的破灭归因于这座城市在历史中的沦落,倒不如说这旧梦原本就是一种虚幻的文化记忆。
沦落的其实不只是扬州,还有那个制造了扬州旧梦的传统意义系统,它以迷人的风雅掩盖了残酷的现实。如果建立在社会的巨大分化和不公基础上的扬州旧梦注定要破灭,那么作为有钱有势者的新天堂的上海或天津,它们所幻化出来的各种新梦就同样会破灭。由此可见,郁达夫并非在缅怀已失落的传统中国的风雅遗绪,而是以扬州旧梦的破灭,喻示了今日之各种新梦的虚幻不真,以及那个制造了各种新旧之梦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不合理。这些隐含着的微妙的现实的与历史的讽喻,使郁达夫的游记拥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而这是中国古典游记以及大多数现代游记所不具有的。
三 对风景的“凝视”与拟像化
游记描写各地风物,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与自然史的价值,但它也是一种包含自传性因素的文学形式,“居于其核心的是一个自我展现的人物形象,他强烈地想要理解新的经验,他的这种努力通常与其所使用的材料一样引人入胜”[39]。英国著名游记作家诺曼·道格拉斯认为,“在一本好的旅行书中,读者不仅能够进入一段外部的旅程,看到各种风景描画,而且也能进入一段情感跌宕起伏的内在旅程,它是与外部旅程相伴而行的”[40]。那些最出色的游记所展开的,不仅是外部空间中的旅行,也是混合着作者的记忆、回想等各种思绪的内心之旅。
那么,在更直接地记述了郁达夫个人生活行踪的游记中,他的自我是如何呈现的?他有意塑造或无意流露的自我形象传达了哪些信息或意义?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其中视觉经验的呈现方式来展开相应的分析。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认为,旅游者对风景的观看是一种凝视,而“凝视与‘话语决定性因素’相关,是社会建构的观看或‘视觉体制’”[41]。他区分了两种主要的凝视类型,一种是浪漫的凝视,它强调孤独和隐秘,以及与凝视对象之间的个人性的、部分带有精神性的联系,与之相对照的是始终显得兴致勃勃的集体凝视。[42]前者的代表是十八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壮游”(Grand Tour)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游,后者则是大众旅游兴起后的常见现象。
郁达夫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浪漫主义文学对孤独漫游的反复书写和颂赞,深刻影响了他对旅行和漫游的认知想象。浪漫主义者将旅行视为个人自我领悟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旅行而获得的自我认知,给人一种更强烈的真实、自主和自我实现的感觉,旅行因而被视为“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重要仪式和自我实现的过程”[43]。郁达夫同样强调旅行的快乐“第一当然是在精神的解放”[44],但他更亲近的却是浪漫主义游记书写中的另一种传统,即倾向于描写旅途中经历的各种不幸与苦难。这种书写模式把旅行看作人生的一种隐喻,对旅途中所经受的艰辛苦难以及人的孤独脆弱经验的描写,因而就是一种自我戏剧化的方式,是浪漫主义个人认知和塑造自身生命经验的一种方式。[45]
郁达夫游记文集中最早的一篇《感伤的行旅》就借用了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著名小说的题目,“感伤”既是对旅途经历的一种概括,更是对自身生命经验的一种隐喻。个人在空间中移动的行踪都被染上了浓郁的情感色彩,孤绝、屈辱和漂泊无助的受伤感构成了刺目的内心风景,他在途中所见的一切——山水草木,平桥瓦屋——似乎都印证并强化了这种主观体验。在火车上所看到的江南秋景虽然可爱,但他联想到的,却是这十余年间军阀对老百姓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江南鱼米之乡的百姓都“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在太湖之滨的龙山上,他趁着四周无人宣泄般地狂歌高叫一通之后,却又感到一种深山里的静寂的可怕的压迫,斜阳里的太湖让他生出“已经闯入死界的念头”,油然而起日暮途穷之感。《钓台的春昼》同样有这种强烈的主观情绪的晕染,无论是描写桐君山的微茫夜色,还是渲染钓台的寂静荒芜,都浸润着一腔悲哀和郁愤。四周的静,是“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幽谷中的清景则在芜杂中显现出颓废荒凉。
早期作品中这种浓重的感伤情绪在他移家杭州后所写游记中有所减弱,而代之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洒脱。创作风格的转变是否意味着内在自我有了调整与转变?我们不妨以《方岩纪静》为例来一探究竟。
这篇游记从方岩繁盛的香火说起,特别提到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进香,只因胡公时显灵异,能保境安民。方岩附近绝壁陡起的巨大岩石让他想起霍桑的小说《大石面》,提到这篇道德教谕性的作品,是为写五峰书院铺垫。五峰书院是宋代大儒朱熹、吕东莱、陈龙川等人讲学之地,郁达夫描摹了书院地势之奇险,又特别强调其“静”:
立在五峰书院的楼上,只听得见四围飞瀑的清音,仰视天小,鸟飞不渡,对视五峰,青紫无言,向东展望,略见白云远树,浮漾在楔形阔处的空中。一种幽静、清新、伟大的感觉,自然而然地袭向人来;朱晦翁、吕东莱、陈龙川诸道学先生的必择此地来讲学,以及一般宋儒的每喜利用山洞或风景幽丽的地方作讲堂,推其本意,大约总也在想借了自然的威力来压制人欲的缘故,不看金华的山水,这种宋儒的苦心是猜不出来的。[46]
耐人寻味的是,他紧接着写到胡公庙敬神社戏的热闹,许多老幼男女都“流着些被感动了的随喜之泪”,而台上所演的却无非是《杀狗劝妻》之类的“孝义杂剧”。最后回到客店时,堂上已点起大红蜡烛,“摆上了许多大肉大鸡的酒菜”,“菜蔬丰盛到了极点”,尽管味道不甚适口。至此不难领悟到,郁达夫所记方岩之“静”,即山水的幽静和证道的心平气静,原是以红红火火的世俗生活之“动”为底子的。香市的繁盛、社戏的热闹,以及大快朵颐的铺张,分明代表了普通百姓执着于俗世的人生态度,若是没有这俗而“动”的一面,所谓“静”就真是一种“死”静了。而那些看戏的老幼男女所流下的“被感动了的随喜之泪”,不也说明世俗人心中原本就有着一份向善慕贤的虔敬吗?所以,“动”和“静”虽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与境界,但它们不是相悖的,而是互为底里,并存于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方岩之“静”,是“动”中之“静”,“静”中又有“动”;证道不是为了弃世离欲,而是为了济世安民。“动”与“静”原本都基于对人世的执着。郁达夫既服膺于宋儒望峰息机、苦心证道之伟大,却也不鄙视乡野百姓对世俗生活及其享乐的沉迷,他把这两个方面都生动地描画出来,使之彼此对质,并在更深刻、更内在的层面发现了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与融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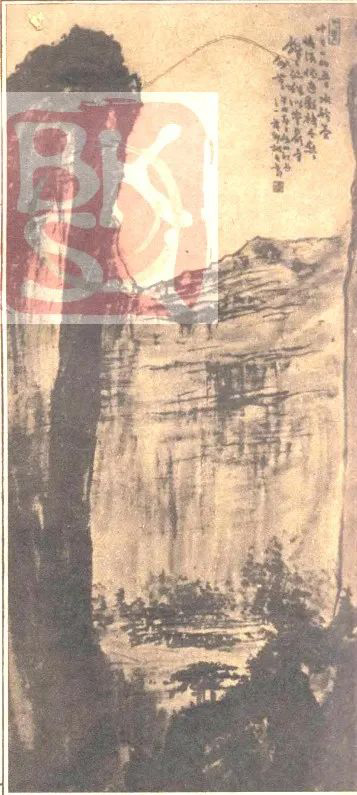
《东南交通周览会应征文艺作品·国画第一名》,《人言周刊》1934年第1卷第24期
可以说,郁达夫对风景的浪漫凝视倾注了他对世界与生命的认知和体悟,“屐痕处处”的行旅因而就是他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体悟和形铸自我经验的另一种形式。
但郁达夫对风景的凝视,在感知方式上也有着固化的痕迹。吴晓东注意到郁达夫对风景的描画,常常要借镜于西方的风景和文化,而且往往还是出现在西方书本和图片上的“拟像的风景”,即通过媒介而再现的风景。[47]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发现,因为正如吴晓东所说,如何观照风景,这与人的情感、审美、心灵甚至主体结构,都有很大关系。郁达夫描写风景实际上并非只借镜于西方,他也常常用中国书画作比,比如用中国山水画的皴法形容方岩的奇岩绝壁之苍劲雄伟(《方岩纪静》),用钟馗送妹图和长江行旅图形容杭徽路上所见古老山道上络绎不绝的行人和驴马(《出昱岭关记》),用米芾和黄庭坚的大草书屏形容天台山峭壁之奇古(《南游日记》),但这仍然不脱拟像化的手法。
形容风景美如画,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常用修辞。在十八世纪晚期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景美学,认为自然景色之所以是美的,就因为它包含了“如画美”(picturesque),旅游是为了在自然景色中寻找这种“如画美”,“并用绘画的原则来加以检验”[48]。这种审美意识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工业革命的兴起,古典世界及其文化的衰落,使得十八世纪晚期的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变得忧郁、内省而折中,他们“似乎经常处在一种瘫痪状态,对现状感到困惑,对还在眼前的过去感到不耐烦,却沉迷于遥远的过去。‘如画美’的意识正是由此而产生”[49]。“如画美”趣味对废墟的迷恋,对视觉的审美自主性的强调,以及对“参差多态”原则和低角度观景位置的注重,都透露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的主体意识的变化,这在人们对于历史、道德和自我的认知态度上都有所体现。有学者认为,“如画美”的风尚是过渡性的,“在它之前,自然是道德的象征;在它之后,自然是神秘的,代表了一切原始的和无意识的”[50]。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主体意识的嬗变,这个主体已从古典世界的象征秩序中脱落,努力在文化上进行自我定义。
这种通过视觉进行的文化重组本身却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在自然景色中寻找“如画美”,是将艺术的法则加诸自然,它因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但对自然之神秘以及低角度观景位置的强调,则表明人在自然面前“已失去了自信”[51]。“如画美”的景色所带来的愉悦绝非只是视觉性的,而且也不只是一种纯粹个人的情感,它假定“在感知的心灵与被感知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类似。美如画的景色使目光流连于对象之间,它们在复杂的思想观念中都有其精神上的对应物,激发了纷繁的思绪”[52],对“如画美”的发现因而是对存在于心智结构中的某些对应物的确认。称赞风景美如画,即承认它有着认识论上的价值。这种带有意识形态性的风景美学,会把人们观看的眼光限制在既有的参考框架中,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许多进行“画境游”的游客,离开了克劳德镜[53]就发现不了自然景色之美,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颇具讽刺性的例子。
对“如画美”的风景美学,郁达夫想必也是熟知的。《钓台的春昼》中他这样描写从西台所见的风景:
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54]
“芜杂不整齐”,“变化更多”,正符合“如画美”所要求的“参差多态”的原则,而由此表现出来的“颓废荒凉的美”,当然也不只是代表“东方民族性”。钓台恰如西方浪漫主义诗文中被反复书写的废墟,但它不是用来表现“大自然芟夷一切的傲慢暴政”[55],而是意在揭示对反抗异族入侵的民族历史记忆的令人痛心的遗忘。
风景拟像化的关键也许不在于知识的炫耀以及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而在于模式化的观看方式会造成感知与认知上的钝化与窄化。
郁达夫自言“特别喜欢向没有火车飞机轮船等近代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56],但他出门旅行却从来离不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利器。杭江路之旅是乘火车西行,去沿途各景点则换乘汽车;杭徽路之行搭乘的是巴士汽车;《桐君山的再到》《南游日记》《国道飞车记》《过富春江》诸篇中均是乘小轿车出游。
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提供的体验、性能表现以及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s)都很不一样。[57]乘火车或汽车旅行,与徒步旅行,或是坐轿子、坐船旅行,身体运动的方式,所能看到或感知到的事物,甚至感知方式本身以及通过感知而获得的意义,都迥然相异。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就指出,十九世纪晚期铁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移动方式、社交方式和观看方式。[58]火车速度的加快产生了大量有待处理的视觉印象,使刺激倍增,同时也让人感到压力与疲倦。但铁路在景观中的穿行,也使那些就其原本的空间性而言是分属于不同领域的对象事物和风景片段,以即时连贯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景式的崭新感知。它与传统感知的不同在于,感知的主体与被感知的对象事物不再同属一个空间。使旅行者得以穿行于世界的机器及其产生的运动,都被整合进他的视觉感知,他因而只能看到运动中的事物,这些瞬息幻灭的对象事物构成了一种新的现实。[59]汽车也同样提供了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新的感知,尤其是轿车,它创造了“基于瞬息时间、碎片化以及强迫的灵活性之上的个人化移动”[60],也带来了情感和意义感知上的一连串变化。
在郁达夫的游记中,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给旅行主体带来了哪些感知与情感方式上的新变化?《杭江小历纪程》和《浙东景物纪略》是应杭江铁路局之邀而作,但其中与火车相关的内容却很少,也看不到有对希弗尔布施所说的全景式感知经验的描写,而在同样收入《浙东景物记》的傅东华的《杭江之秋》中,倒是有这方面的精彩描摹:
火车上看风景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
风景本是静物,坐在火车上看就变动的了。步行的风景游览家,无论怎样把自己当做一具摇头摄影器,他的视域能有多阔呢?又无论他怎样健步,无论观察点移得怎样多,他目前的景象总不过有限几套。若在火车上看,那风景就会移步换形,供给你一套连续不断的不同景象,使你在数小时之内就能获得数百里风景的轮廓。“火车风景”(如果许我铸造一个名词的话)就是活动的影片,就是一部以自然美做题材的小说,它是有情节的,有布局的——有开场,有climax也有大团圆的。[61]
傅东华还用“山来了”“水也出来了”这样的句子,来描述景物的动态展开,火车的疾驰使得窗外的山水田畴都被幻化为抽象的几何图形:
一切的图形都被打破了。你这一瞬间是在这样畸形的一个圈子里,过了一瞬间就换了一个圈子,仍旧是畸形的,却已完全不同了。这样,你的火车不知直线呢或是曲线地走了数十分钟,你的意识里面始终不会抓住那些山、水、溪滩的部位,就只觉得红,红,红,无间断的红,不成形的红,使得你离迷惝恍,连自己立脚的地点也要发生疑惑。[62]
速度使景物失去了稳定的形态而变得畸形,主体亦无法在意识中准确把握这些对象。视象的移动虽然尚不至于导致现实本身的涣解,但对自身立脚点的疑惑,却说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固定关系有了变化,原先在对风景的凝视中获得的作为支配主体的稳固的、自主的自我意识开始发生了动摇。
《国道飞车记》是郁达夫游记中少有的写到现代交通工具所产生的新的时空经验的文本,其中特别写到车过太湖时,“同做梦似地”从车窗里看到的“一点点风景”:
烈日下闪烁着的汪洋三万六千顷的湖波,以及老远老远浮在那里的马迹山、洞庭山等的岛影,从飞驰着的汽车窗里遥望过去,却像是电影里的外景,也像是走马灯上的湖山。而正当京杭国道的正中,从山坡高处,在土方堤下看得见的那些草舍田畴,农夫牛马,以及青青的草色,矮矮的树林,白练的湖波,蜿蜒的溪谷,更像是由一位有艺术趣味的模型制作家手捏出来的山谷的缩图。[63]

《东南交通周览会应征文艺作品·洋画第一名》,《人言周刊》1934年第1卷第24期
湖山都只呈现为远景,汽车的疾驰又使之成为流动的风景。从国道高处看到的乡野景象,则像是一个模型缩图。这种风景描写传达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看风景的人不是在风景之中,而是置身于风景之外,因而不免有一种疏离感,这与徒步旅行带给人的那种“遥山近水皆可亲”的感觉很不一样。有趣的是汽车半道抛锚,反倒创造了一次步行游瓶窑古镇的机会,热闹的街市和不落红尘的回龙寺都令人难舍,“简直有点儿不想上车”了。这段插曲与其说表现了汽车旅行与闲散漫步式的传统旅行的“交错与转换”[64],不如说是表达了对汽车所代表的现代性的微讽。汽车旅行虽然灵便而自由,却充满了不可控的偶然性,而且也无法提供那种如在家园的与周遭世界的亲近感。其后在宜兴善卷洞的不愉快经历和在碧浪湖感到的失落,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讽刺感。善卷洞让人不快的是现代商业开发的逐利倾向,碧浪湖的淤塞恐怕也与水路运输的衰落有关。
国道飞车一日,虽然领略了汽车旅行带来的诸般新经验,但那个正在破坏中且看似终将消逝的传统生活世界,似乎才是郁达夫更欣赏和眷恋的。《桐君山的再到》和《过富春江》记叙的乘小轿车的一日游,比之于《钓台的春昼》,明显有一种走马观花的浮泛感。乘轿车旅行,在压缩了空间和时间的同时,也减弱了视觉专注的程度和情感投入的强度,其结果是描写景物鲜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除了不断重弹江山之思的老调,似乎难有别的新鲜情感。
在郁达夫的这些游记中,很少写到这种现代性的移动经验。而在其早期小说与散文中,铁路旅行的经验却是被反复书写的,它们几乎都与孤独、忧虑、愤懑、自我哀怜的情绪相连,车窗外的景色只是映现并反向增强了这些情绪。换言之,移动的经验实际上是强固而不是涣解了主体的内在性。
虽然移动的经验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对风景的感知方式,但如前所说,通过风景而呈现的主体的主观情绪和自我意识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应该怎么理解这种“变”与“不变”?感知风景的方式的“不变”是否反映了主体意识中或潜意识中的某种努力?在特定的“凝视”中以相对固定的形态而呈现的风景,又在何种程度上折射了主体的内在状况?
四 “重读”风景与自我的延展
风景之于郁达夫,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许诺了对孤独忧郁主体的“补偿和治疗”,还是生产了一种自恋的、排他性的匮乏主体?[65]这些问题牵涉风景与主体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美国文化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格罗夫认为,风景这个概念意味着外部世界的呈现是以人的主体经验为中介的,“风景不只是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它也是一种建构,是对那个世界的一种构造。风景就是看世界的一种方式”[66]。而看风景的方式实际上隐含了一个与风景相对应的主体,通过分析看风景的特定方式,可以窥见与之相对应的主体,进而考察其在历史中建构与变动的轨迹。
郁达夫1930年代的游记看风景的方式有何特别之处?马力指出,郁达夫在游赏风景时“目光跳荡,观山览水既有较强的位置感,又不拘于一个角度,而是在放情纵意中变换多方,运用大尺度的物象结构营造立体化的视觉,浮现景物的空间格局”[67]。比如写福州鼓山的形势:“闽都地势,三面环山,中流一水,形状绝像是一把后有靠背左右有扶手的太师椅了。若把前面的照山,也取在内,则这一把椅子,又像是前面有一横档,给一二岁的小孩坐着玩的高椅了。”[68]不是固定在观看主体的位置上,而是拟想了一个鸟瞰的视角,居高临下,全局性地把握山水形势。这种看风景的方式显然与《感伤的行旅》《还乡记》等作品中不同,其间的差异恐怕不能全都归因于对象的不同,主体自身状态的变化或许才是更重要的。
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看风景的方式是自我投射性的,风景就像是主观自我的外化,看风景因而成为主观性的自我确认的一种方式,其结果是把自我更加固锁在一种忧郁孤独、与外界相隔绝的状态之中。在其1930年代的作品中,看风景不是对主体的某种内在性的直接确认,而更像是在自我延展中寻求突破的一种方式。比如《迟桂花》向来以风景净化情欲而为人称道,但其中风景的作用其实不在于提供了一条升华之路,而是昭示了一条进入现实世界的坦途,即在不受情欲与利益支配的新的价值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风景所建构的就不再是一个内倾的、自我封闭的审美主体,而是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新的伦理主体。这种自我拓展的蕲向,正是在他这时期的游记中有所展露的一种新质。
人们习惯于认为郁达夫在1930年代是走到中国式名士的老路上去了。[69]“名士气”在游记中的表现是文章体式和笔调都接续了中国古典游记的传统,穿插了录自方志等各种古代典籍的掌故、逸事与诗文,极富知识性。这样,风景就不再只是自然风光,而是被充分地历史文本化,成了人文化的景观。比如《游白岳齐云之记》中,多次引用《休宁县志》《安徽通志》《徐霞客游记》等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所写景观率多为道教的圣地古迹,连说到危岩石壁,也瞩目于摩崖石刻、石碣和碑文。这样的风景是通过各种文本和话语建构起来并在历史中层累的,看风景因而就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巡礼。
如果把风景理解为“一种铭刻着各种社会关系的文本”,它在社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维持了一整套观念和价值,以及关于一个社会怎么组织或应该怎么组织的各种未经质疑的假定”[70],那么看风景就是对风景的一种“重读”。合乎理想的“重读”不应是对作为文本的风景的不假思索的接受,视其为理所当然,而需要思考它在历史过程中是怎么通过各种文本和话语被建构起来的,以及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着何种互文性。如此才能揭示风景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人为建构性与意识形态性,从而将风景去自然化和去神秘化。
郁达夫这一时期的游记,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这种“重读”或再表征风景的意向。《游白岳齐云之记》中,他借关于海瑞的民间传说揶揄玄天上帝,就好比是佛头着粪,几乎使道教祖庭所在的齐云山的一切风景都为之黯然失色;接着又讲了唐越国公汪华显灵的传说,既借机嘲讽军阀的嗜杀,又表达了希望为政者能保境安民的愿望。汪华显灵事,始见于康熙三十二年修《休宁县志》卷八“佚事”,本是清初统治者为自我粉饰而杜撰的故事,郁达夫没有像对待海瑞的传说那样斥之为无稽之谈,是因为这个故事触及了他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19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如何才能保国安民?《方岩纪静》中,他对胡公显灵的传说表现出极大兴趣,也是基于这种关怀。可见对风景的“重读”,通过以历史为触媒,又迂回切入现实之中,风景所提供的因而不是遁世之路,而是入世之路。
“重读”风景,在揭示风景之人为建构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风景本身。《杭江小历纪程》记西施出生地苎萝村,转述了各种莫辨真假的传说,更令人发笑的是,在邑绅陈孝廉所建之西施庙中,竟藏有几块刻版的拓本,上载西施于乩盘开沙时降坛的一段自白,自辩如何忠贞两美,引得郁达夫题诗嘲讽“陈郎多事搜文献,施女何妨便姓西”。这种“多事”其实从来都是风景——特别是文化景观——得以不断再生产并发挥其特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主要途径。“重读”也伴随着对风景的改写。《闽游滴沥之二》中讲述涌泉寺坐韦驮的神奇传说,便与坊间流传的多种版本有所出入。[71]法印法师作为涌泉寺方丈住持的身份被隐瞒不表,其年龄也从传说中的十六岁降低到了十一二岁,被说成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备受别人虐待、奚落和欺侮的小和尚;走私贩卖的米商则被说成“剥削穷民、私贩外米的奸商”。这些改动大概是郁达夫有意为之吧。他挪用当时流行的阶级话语,在故事中重建了贫富强弱的对立结构,似乎也是意在影射现实。

《郁达夫先生近影》,《宇宙风》1936年第30期
将风景历史文本化以及伴随而来的“重读”和改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体自我意识的变化与调整。在《西游日记》中,郁达夫指出游西天目的一大乐趣,在于“翻阅翻阅西天目祖山志上的形胜与艺文,这里那里的指点指点,与志上的全图对证对证”[72]。这种乐趣显然不完全是知识性的,更多的是作为指点江山的主体所带来的那种愉悦。以《祖山志》这样的历史文本为媒介,看风景的主体得以控制和支配作为风景而存在的地理空间。这个主体是否还是一个自恋、排他性的匮乏主体呢?如果把自恋理解为一种产生自我意识的构成性机制,那么郁达夫游记中的确不无自恋的痕迹,比如对典籍的征引,对代表着文化权力的各类象征符号的使用,特别是效仿骚人墨客的题诗吟哦,都有自我炫耀的意味,其所映现的是一个有着良好传统修养的文人的理想自我形象。这个理想自我又是一种典型的男性主体,他对风景的凝视兼具爱欲性与侵凌性。如《杭江小历纪程》中将山水比作佳人,就是将自然女性化;《二十二年的旅行》中提到浙东的风景,也津津乐道于金华附近的女人的肤白秀丽与健康高大,看风景因此就像是男性的自恋性认同,是以侵凌性的目光对自然对象的占有。题诗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标记或铭刻符号而实现的占有。但也需要看到这种带有自恋印记的男性自我认同不是绝对排他性的,作为凝视对象的风景,虽有小他者——即作为自我的某种映象或投射——的一面,但也是大他者所代表的象征秩序的一部分,是它的延伸与赓续。正因为有此面向,对风景的凝视尽管有男性自恋的意味,却还不至于将主体完全闭锁在虚假的自我想象之中。大他者所代表的象征秩序的介入,使主体得以重构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对象客体不再只是自我的主观投射与确认,而更是一种媒介,促使自我经由象征秩序的中介而实现转化与生成。从这个角度看,所谓风景的拟像化,实际上也是主体变相把握对象客体的一种方式,把风景比作绘画或书法,山水木石便变成了线条与色块,从而在特定的象征秩序中得以重组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对风景的凝视重构了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不再是那种疏离的、对抗性的关系。经由象征秩序的中介,主体找到了一条曲折进入现实世界的通道,并发现了与他者之间原本就隐秘存在的现实联系。“闽游滴沥”系列便是这方面的好例子。《闽游滴沥之四》中记鼓岭之游,那天适逢当地百姓举办清明酒宴和敬神社戏,郁达夫一行亦被邀饮共欢,村民的淳朴、热情让他感动留恋,惜别时甚至产生了千秋万岁化鹤重来的愿望。而在《感伤的行旅》中,作者于汽车上目见江南田园风光时,所想的是有朝一日能在此置地筑室,过悠游自在的田园生活,于酒醉饭饱之余听听西洋音乐唱片,想读新书时就去上海购买……在这种想象的隐居生活里,只有自我而没有他人,自我被隔绝于俗世之外。两相对比,前后的变化显而易见。对鼓岭村民及其淳朴生活的赞美,虽然不脱古典诗文“农家乐”的书写传统,但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现实世界及其生活秩序的肯定,并促使主体在与他者的对等关系中去重新定义自我。由此看来,这个主体并非排他性的,恐怕也很难说是匮乏的。退一步说,即使存在匮乏,那么这种匮乏也通过与他者、与对象世界的关系重构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弥补。
结 语
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游记写作的整体背景中,也许就更能看清郁达夫游记中所浮现的那个主体的面貌。当时《旅行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游记,有很多仍然用文言文写作,采用经典的日记体。这类游记的作者多为老成的文人与政府官员,他们逐日记录游历行程,状物写景多袭用陈语,即使时而穿插几首吟山咏水的旧体诗,仍难掩文章个性不足之憾。蒋维乔的《因是子游记》[73]堪称此类游记的代表。另一种数量在日渐增多的游记,是大众旅游兴起后的衍生产品,其作者更年轻,多半是江浙一带城市中的高级职员和大学生。他们视旅游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是有一种Taste的。这种Taste就区别了那有文化的”[74],旅游因而是一种身份标志,能够检验你是否现代、有无文化。这类游记使用白话文写作,虽然不像前一类游记那样规矩刻板,貌似有更多个人性的内容与特征,也更贴近当下的社会时代,但实际上同样是模式化的,所谓个性只是一种高度雷同的伪个性而已。郁达夫的游记与上述两类游记都不同,他对中国古典游记书写传统的继承,不只是体现在对古典游记的文章体式和行文笔法的挪用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将山水在某种程度上道德符号化而表达了对中国传统价值的部分认同,其隐含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75]不无相似处,即视传统文化价值为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但正如其游记写作并不恪守古典游记的科程,他对传统价值也绝非全面认同,而是基于个人对当下现实的感知与思考,有所取舍。因此在其游记中,认同与质疑、赞美与反讽往往并存,由此形成的较为复杂的思想情感织体,使之已无法再被简单地视为“旧文学的游记”[76]了。
与更时尚的新兴游记相比,郁达夫的游记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古典的风雅和名士的才情,但更深刻的区别恐怕在于,它们虽然都是大众旅游所催生的文化产品,且都烙有时代流行话语的印记,但郁达夫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话语及其运作,却始终有所警惕。尽管在游记中常常寄寓江山家国之忧,但他又明确拒绝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对国家和政府所推进的有着民族主义目标的政治进程,不是盲目拥护,而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乃至批评。他肯定旅游可以带来精神的解放和增广阅历的快乐,但也指出旅游只是“有闲有钱有健康的人的最好的娱乐”[77]。这就揭穿了当时骤然兴起的大众旅游热的令人尴尬的一面,也是对如同炫目的光环笼罩于这类新兴游记之上的民族主义及现代化话语的一种微讽。
郁达夫游记中所呈现的那个“屐痕处处”的主体,显然既非寄情烟霞的旧文人,也非城市精英阶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主体,而是一个在逐渐调整、变化中的有着内在深度的个人主体。他淡化了那种以“零余者”自居的孤愤和自我哀怜,尝试通过象征秩序的中介,使自我在历史与现实中获得一定的拓展与延伸,由此建立与他者以及生活世界之间的有效联系。这种自我调整与变化当然还远不够彻底,毕竟这个看风景的主体还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其感受与认知世界的方式,无论是将风景历史文本化还是拟像化,乃至对风景的“重读”与改写,实际上都表明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既有的各种新旧象征秩序,而文本化、符号化的习惯倾向,同样也限制了其个人的感受与认知方式在更积极主动的生活与斗争实践中的不断更新与转化。换言之,这个主体仍然保留着类似于游客的身份,对风景的凝视虽然寄寓了他的历史认同与现实关怀,但他与对象世界仍然是有距离的,与历史、与现实都还不能有一种真正深切的联系。所以这个主体尽管有着敏锐的现实感,也不乏清醒的批判意识,但他对现实的批判认知始终只停留在一种相对浅表的层面上,并总是归结为一些看似正确实际上却非常模式化的结论,而无法深入把握现实世界的内在机理。对个人生命经验的信守,虽使他能不被流行话语所蒙蔽,保持思想的某种独立性,但这也限制了自我向现实的充分敞开,失去了在一种新的基质上全面重构自我的可能性。
“江山也要文人捧”[78],郁达夫这句常为人称道的诗,或许可以为其游记写作下一个恰切的注脚。“江山”通常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地理象征,捧“江山”,就是通过风景的书写“为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赋形”[79],它也是一种自我书写,在刻画风景的同时将自我铭刻在历史与现实中。在此意义上,对风景的书写就是“江山”与个人主体之间相互塑造的过程:一方面,有赖于无数个人的精神创造,“江山”才能如此壮丽,万古如新;另一方面,“江山”也在不断召唤并塑造着时代所需要的特定主体,给艰难跋涉的个人提供一种超越性的意义,使其在历史与现实的洪波中实现自我的拓展、延伸与转化。
倪伟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043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
注释
[1]关于游记研究在当代西方学界的发展概况,可参阅下列各书的导论:Alasdair Pettinger & Tim Youngs, eds. The Routledg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1-5; Nandini Das &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16; Peter Hulme &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3; Julia Kuehn & Paul Smethurst, eds. New Directions in Travel Writing Studi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4 ; Corinne Fowler, Charles Forsdick, and Ludmilla Kostova, eds. Travel and Ethic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1-3.
[2]Carl Thompson, Travel Writing, Routledge, 2011, p.3.
[3]Jaś Elsner and Joan-Pau Rubiés, eds. Voyages and Visions: Towar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vel,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9, p.4.
[4]梅新林、俞樟华:《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460页。
[5]郁达夫:《两浙漫游后记》,《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6]郁达夫:《〈屐痕处处〉自序》,《郁达夫全集》第11卷,第125页。
[7]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8]1933年12月18日,杭江铁路局在金华举行竣工通车典礼,《浙东景物记》被作为礼物赠送与会嘉宾。见秦瘦鸥《杭江路走马看花记》,《旅行杂志》1934年3月第8卷第3期。
[9]刘荫堂主编:《江苏公路交通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1934年2月18日《申报》刊载新闻稿《蒋委员长令筹备东南交通周览会》,其中明确说到,因为认识到筑路关系“军事之便利、防剿盗匪、巩固治安,至为巨大”,蒋介石下令举办东南交通周览会,借此“令饬苏浙闽皖赣五省边区公路处长曾养甫,将各线已赶筑之公路,限于本年六月前,一律赶筑完成”。
[10]《东南交通周览会章程》,《浙江省政府公报》1934年5月7日第2113期。
[11]Eric G. E. Zuelow, A History of Modern Tourism, London: Palgrave, 2016, pp.9-10.
[12]Tim Oakes, 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1998, p.23.
[13]关于1930年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可参见王淑良等《中国现代旅游史》第2章“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参见Pedith Chan(陈蓓), “In Search of the Southeast: Tourism, Nationalism, and Scenic Landscape in Republican China”,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43, No,3,October 2018, pp.207-231; Miriam Gross, “Flights of Fancy from a Sedan Chair: Marketing Tour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37”,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36, No.2, July 2011, pp.119-147。
[15]《新运总会颁发〈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及生活三化初步推行方案》,《申报》1935年4月14日。
[16]新生活运动通常被认为与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有隐秘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柯伟林的《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和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中的相关讨论。
[17]1933年至1939年,纳粹德国推行了一项名为“通过快乐而强大”(Kraft durch Freude)的计划,内容包括美化工厂的劳动环境和生活设施,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组织安排各种工余休闲活动,包括教育、运动、旅游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定期安排工人到国外旅游,或是组织国内的集体旅游。推行这个计划,既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也意在借此消弭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普通劳工大众建立起对民族共同体以及纳粹政权的认同。参见Shelley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Consumerism and Mass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Shelley Baranowski, Strength through Joy: Consumerism and Mass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 p.119.
[19]敦庆:《观东南交通周览会文艺展纪感》,《时代》(半月刊)1934年8月1日第6卷第7期。
[20]Rudy Koshar,“‘What Ought to Be Seen’: Tourists' Guidebook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Modern Germany and Europ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ul.,1998,Vol.33 No.3, pp.323-340.
[21]Travel Writing, Form, and Empi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obility, ed. by Julia Kuehn and Paul Smethurst, Routledge, 2009, p.1. 关于旅行写作与欧洲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可参见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Laura E. Franey, Victorian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Violence: British Writing on Africa, 1855-1902, Palgrave Macmillan, 2003,Nigel Leask, Curiosity and the Aesthetics of Travel Writing, 1770-18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Yajun Mo, Touring China: A History of Travel Culture, 1912-1949,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83, 7.
[23]关于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和《中华景象》的编辑出版,参见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5~83页。
[24[[25]《中华景象·发刊旨趣》,伍联德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4年版。
[26]黄伯樵:《导游与爱国》,《旅行杂志》1936年1月第10卷第1期。
[27]郁达夫:《艺术与国家》,《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57~62页。
[28]任兰萍主编:《中国共产党德兴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167页。
[29]《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30][31]郁达夫:《浙东景物纪略》,《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64~65、66~68页。
[32]俞元桂、姚春树、汪文顶:《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33]何瞻:《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冯乃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151页。
[34]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35]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李文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214页。
[36]此处乃郁达夫记忆错误。徐霞客虽曾多次游五泄,但现存《徐霞客游记》中无记。参见郭西村《徐霞客与五泄》一文,《西湖夜话》,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86~87页。
[37]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3.
[38]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184页。
[39]Michael Kowalewshi, “Introduction: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emperamental Journeys: Essays on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ravel,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2, p.8.
[40]Norman Douglas, “Arabia Deserta”, in Experiments, New York: Robert M. McBride & Company, 1925, p.9.
[41][42]John Urry and Jonas Larsen, The Tourist Gaze 3.0, Sage Publication, 2011, p.2.
[43]Carl Thompson, Travel Writing, Routledge, 2011, p.115.
[44]郁达夫:《二十二年的旅行》,《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180页。
[45]关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对旅行中不幸经验的书写,可参阅Carl Thompson的The Suffering Traveller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6]郁达夫:《浙东景物纪略》,《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57页。
[47]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48]William Gilping, 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 on Picturesque Travel; and on Sketching Landscape: to which is added a Poem, on Landscape Painting, London: R. Blamire, 1792, p.42.
[49]Malcolm Andrews, 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 1760-18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1. 参见中译本《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张箭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50]Susan Glickman, The Picturesque and the Sublime: A Poetics of the Canadian Landscape,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
[51]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第88页。
[52]Paul Carter, 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and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7, p.231.
[53]克劳德镜是一种光学仪器,有多种形制,其中最典型的是托马斯·格雷所使用的那种平凸透镜。镜子的凸面性使反射出来的风景被缩小,除了前景之外,各种细节大都会消失,从而使某种类似于理想美的东西浮现出来。参见《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第94~100页。
[54]郁达夫:《钓台的春昼》,《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29页。
[55]Malcolm Andrews, 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 1760-1800, p.46. 参见中译本《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第64页。
[56]郁达夫:《住所的话》,《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223页。
[57]John Urry, Mobilities, Polity Press, 2007, p.37.
[58]参见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9]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第83~94页。
[60]John Urry, “The 'System' of Automo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21, Issue 4-5, 2004, p.36.
[61][62]傅东华:《杭江之秋》,《东方杂志》1933年3月16日第30卷第6期。
[63]郁达夫:《国道飞车记》,《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188~189页。
[64]张一玮:《汽车旅行:郁达夫游记的跨文化书写》,《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30卷第5期。
[65]李思逸:《铁路与中国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文化想象》,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课程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53~265页。
[66]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8, p.13.
[67]马力:《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68]郁达夫:《闽游滴沥之二》,《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205页。
[69]孙百刚:《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70]J.Duncan & N.Dancan,“(Re)reading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8, Vol.6, p.123.
[71]关于坐韦驮的传说可参见王铁藩搜集整理的《神奇的鼓山坐韦驮》,讲述者为原鼓山涌泉寺方丈普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台江区分卷》,福州市台江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印出版,1991年,第202~206页。亦可见卓启书采录的《涌泉寺的传说》,《福建文艺创作60年选·民间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2页。
[72]郁达夫:《西游日录》,《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78页。
[73]蒋维乔:《因是子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74]叶秋原:《旅行之片忆与话》,《旅行杂志》1933年11月第7卷第11期。
[75]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恢复孔子诞辰纪念,并派人前往曲阜祀孔,又重修孔庙,标志了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回潮。次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教育杂志》亦发起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文化保守主义俨然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种时代思潮。关于1930年代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可参见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36页,及《民国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338页。
[7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77]郁达夫:《二十二年的旅行》,《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180页。
[78]郁达夫:《乙亥夏日楼外楼坐雨》,《郁达夫全集》第7卷,第144页。
[79]Stephen Daniels,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