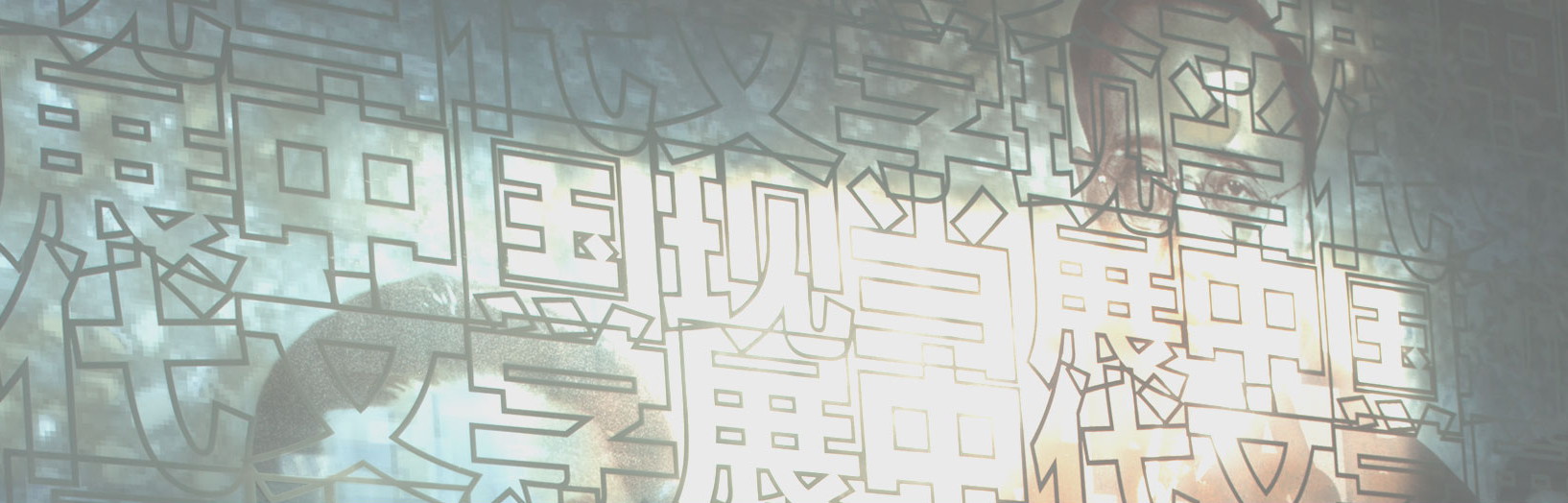|
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中国当代文学自有其文学史的年代学指称和内涵,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进一次聚焦在“当代”,则常常感受到它超越年代学的暧昧与滑脱,辨察出不断成为历史的“当代”与不断展开的“当下”之间的连续与断裂、向史而生的质的规定性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本期“文学史研究”栏目中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一文,将“当代性”界定为一种“文化的境遇意识”,是“(中国)现代性对自身的反思和超越”建构起来的“主体意识”,成“叙事关系”,而创作实践中强调“当代性”,则有助于在开掘历史纵深的同时,揭示复杂的当代境遇。那么,在穿越了诸如“一体化”与“现代化”的“历史纵深”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今天又呈现出一种怎样复杂的“当代(当下)性”.这始终是一个无过摆脱的恼人又迷人的话题。吴秀明《论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则从“代际”角度探讨当代文学研究中三代学人的知识学养问题,厘析学人在此“大端问题”上的努力与局限,及对当代文学研究之基本面相的影响。孙晓忠的文章以土改和合作化小说为中介,通过文书行政的运行轨迹来考察国家和自然村庄如何相遇,文学如何形塑土改—合作化的历史进程。文章读的是“老”文本,用的却是新方法,因而也读出了新问题、新关切。阎浩岗的文章提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概念,用来指称现当代文学中那些”以显示土地革命正当性和必然性为特征”的文学文本,并历时性地研究其接受与传播的内外机理。练暑生的文章试图在启蒙与革命机制下产生的“现代文学”和以艺术自律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学”所构建的宽阔光谱内对“先锋文学”进行谱系学考察。李建立的文章则通过梳理新发现的“赵一凡书目”,考察其对“文革”“地下文学”的贡献,进而辨析“地下文学”的精神资源。
去年11月,陈映真先生不幸去世,本期特组织一辑论文,以资纪念。虽为纪念,却都是有分量的好文。赵稀方的文章结合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论战,阐述其对台湾社会和文化殖民性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文章对陈映真与大陆作家之间错位的分析,尤有启迪。赵刚的文章把陈映真的小悦《夜行货车》置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语境中细读。作者将此文本视为一篇“战斗与导引”之作,既在与台湾文化界的殖民依附意识、本土分离意识进行战斗,又蕴含着某种通向左翼第三世界观与素朴人道主义的政治导引。文章对作品的解读可谓“锱铢必较”,鞭辟入里。熊辉的文章则重点讨论陈映真如何借助并扩展文学批评,对台湾诸种知识分子精神症候以及分离(台独)意识和文化展开批判,同时竭力阐扬台湾文学的民族精神与国家认同。
“作家与作品”栏中,陈昶的文章把顾城与海子并置思考,认为他们所遭遇的困境,虽然最终表现为精神世界的坍塌,却始于日常生活的损毁。正是这种困境强化着他们“背向生活的理想主义者”的自我认同。郭剑敏的文章讨论《傅雷家书》,通过文本细读,并佐以大量相关史料,试图还原通信时真实的父子关系及各自的情感与处境、揭示难言的亲情与政治隐痛,从而读解出一个交织着愧疚之情和政治重压的父亲和知识分子形象。而包括《家书》在内的“傅雷形象”的打造,则汇入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重塑自我主体性的潮流当中。
本期“文献史料研究”栏目中的文章,既有史料发掘与考证上的具体贡献,又能就相关论题展开富于学术推进的论述。其中日本学者中里见敬考证冰心《春水》手稿在中日学者间的流转,及最后藏身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的过程,细论周作人与冰心、滨一卫等后学的交谊,对他们的提携,为中日两国学者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几篇书评也都是对新近出版的有一定反响的学术著作的严谨评介,在此恕不一一具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唯一官方投稿邮箱为ckbjb@wxg.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