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因病于2021年1月15日去世,享年82岁。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吴福辉先生辛勤耕耘、投入热忱的地方,全体文学馆员工沉痛哀悼敬爱的老馆长。现发布先生旧文一篇,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走上它的第30个年头了!对于别人来说,文学馆可能要从1985年正式成立之日算起;而对我来说,无论是重读研究生直至毕业或参加文学馆的筹备,都要从1981年开始纪事。这是我的文学记忆深刻之年。1981年3月,巴金在香港和北京先后发表了《创作回忆录》之十一,提出了建立文学馆的倡议。查他的晚年巨作《随想录》,有两篇题目仿佛孪生的散文即《现代文学资料馆》和《再说现代文学馆》,第一篇便是最初建议,后一篇是稍后的推动,可见他对此事的关切、用心之坚之勤。同月稍后,茅盾逝世,巴金很快接替了茅盾的中国作协主席职位。不久,作协主席团接受巴老提议,组建了名至实归的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这年年底,我到作协报到,罗荪直接与我谈分配,安排到筹备中的现代文学馆工作。巴金和现代作家的事情天然地与我发生了关联。这一“关联”便像眨了一下眼睛,30年过去了。

1984年6月22日,吴福辉(左一)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建立前在上海访问巴金。
文学馆的筹备,起始于北京城内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文科第一院)北面的“五四广场”。当时恢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就在那里的“地震棚”办公。文学馆筹备小组的屋子挨着司机班,因陋就简,一无所有。组里已有三人:李枫,从空军宣传部门调来,做作协副秘书长,筹备组长是兼任,嗜读杂书如命。王乃瑾,是参加过国庆大典前第一次文代会的进城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曹琳,50年代的老同志,兢兢业业有实际能力。我是第四人。在“地震棚”的院子里,开过几次筹委会。九位委员我都有幸见过:巴金在上海,冰心年事已高,都是以后见的,且不是见一次两次;其他的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张僖都在会上见到;罗荪是主任委员,由他这个与巴金长期在上海共事的评论家来主持此事,真是天造地设一般的适宜。我是列席兼管一点会务。那时筹备工作的重心是选馆址、找房子。李枫见无事让我干,就天天动员我去图书馆看书写作。记得隔些日子就传来消息,说谁谁谁给找了什么地方了,过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再过几天又叫人兴奋了,说是古庙潭柘寺如何,可惜太远一点;颐和园藻鉴堂怎样,该多古雅、多幽静,但领导们勘察回来说太小了,不够用。一年过去,没有能落实,巴老才写了后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说88岁的叶圣陶已写好了馆牌,就不知道挂在哪里才好。最后找到了西三环路畔(当时刚在铺路)的万寿寺西院,就是我们做了15年临时馆舍的地方。找着万寿寺真不易。这本是京郊的大庙,清代几朝皇帝在此替母亲做过寿,皇家西出城墙去圆明园、颐和园的时候,历来作为小行宫打尖使用。所以西院的第五进“后照楼”,因住过慈禧了,俗称为“梳妆楼”。西院前后共六进,一直是“总政”歌舞团在那里驻扎,现在由胡乔木替巴金“化缘”,难于迁出也要迁出,部队方面请杨尚昆打通,北京市方面找白介夫支持(属于暂借北京的),这才扫清了障碍,确定了我们的落脚之处。
文学馆刚入万寿寺西院,起先只占后面的两进,门也在后面开的。前面的四进很晚才交到手,这段时间真是捉襟见肘。冯振山是作协老办公室的干部,他调来后建立起保卫制度。可一共也没有几个男的,到夜里我无数次一个人值班住在黑洞洞的院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瞪着第三进大殿的废墟感觉有一丝瘆人。到1982年10月16日,后照楼西墙门户大开,在楼底下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举行了“筹备处”成立仪式。现在看我手头的照片,可见当日团团围坐的胡乔木、周扬、曹禺、艾青、贺敬之、罗荪、唐弢、王瑶、朱子奇等人。我任记录坐在一侧。发言时,大作家们都说这是我们现代作家的新家呢,这个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很好啊,现代文学虽受外国文学影响但仍具有中国民族气派,与此很相称等等,纷纷表示满意。最后由胡乔木挂上了一块竖写的牌子,上有“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的字样,标志着临时馆址的正式确立。
文学馆真正是白手起家,接下来花去两年多时间用来修缮古建筑,初步征集、购置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旧书、旧期刊。馆内初建的图书大库所藏旧版本书籍,是以“文革”前原中国作家协会资料室的珍贵藏书为基础的。这些书与文化部、文联的图书在“文革”期间被“革命”了,混杂在一处,交涉归还费了好大的力气,而且由于某些书籍的实际归属存疑,许多明明是作协的书都没有物归原主,十分可惜。这期间我们创立了作家捐赠书籍、手稿、书信、实物,不打散而单独成立以该作家命名的“文库”制度,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征集方式(作家的实物如书桌书橱、文房四宝等,都是用此名义收集的,后来部分出国去参展过)。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间,开始举办茅盾、老舍的生平展,这项服务于广大读者的文学普及形式,成为我们日后的主要业务内容。这时的具体领导成员除罗荪、李枫之外,又增添了杨犁。杨犁后来做了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这三位和全体筹委会成员,现在都已辞世,他们对文学馆是有很大功绩的。
到了1985年初,文学馆具备了开馆的条件。当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了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文学馆的发起人、名誉馆长巴金亲自来京主持了开馆典礼。文学馆是巴老的一个理想。他有许多理想,这个晚年的理想终于在他手里实现了。当他从上海赶来,坐着轮椅进入万寿寺西院第六进大悲坛的礼堂时,他是欣慰的。参加典礼的二百多位现代著名作家也是深感欣慰的。连胡风这样复出后几乎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作家也来了。王蒙、巴金、胡乔木先后致辞。在大门口终于挂上了叶圣老在目力成双影的情况下书写的馆牌。数天后,4月4日,巴金为了见全馆人员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一进门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交代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并宣布,在已捐出15万元(不要忘记这是有“万元户”称呼的1985年)的基础上,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无论多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全部作为文学馆的基金捐出。记得那天他还参观了“文库”,包括他的“巴金文库”。他赠给馆里的自己著作(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国译本)都是他一本本从上海寓所的书架亲自挑选、包好寄出的,许多都重新题签,说明书的来历和版本的特殊性质等。还有大量别的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本,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仅印77本,国内赠送10本,给我们的这本,上有鲁迅亲题的第7本的“七”字。另有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一函六册,当年只印100部,这是送巴金的第94部,上面有鲁迅、郑振铎的签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也是鲁迅的。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这次参观后,巴金继续赠书,甚至因事必躬亲,不要李小林等的协助,他还摔了一次。现在馆里他“文库”所藏共八千册珍贵书刊,还不算他以后赠的书信、手稿等。从这次来京参加文学馆开馆后,巴金便再也没有能到北京来过。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文学馆了,尽管他的关怀在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一刻停止过。
回忆老馆草创时期,充满了艰辛。文学馆的领导年龄有些偏大,造成交接周期较短。杨犁有夺回失去时间的那股子劲儿,顶真、严厉,处处身体力行。在上海出差去见巴老、赵清阁、赵家璧、魏绍昌,他能坐公交就坐公交,虽然巴老再三招呼要把他的车子让给我们坐。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招待所的房子里,杨犁坚持与我两人一室。后来任命了副馆长刘麟、舒乙做他的助手。到1991年杨、刘两位离休,李凖为第二任馆长,舒乙任常务副馆长,我做副馆长。后加上周明副馆长来馆,舒乙已是第三任馆长了。其时巴老反复交代,趁许多老作家还健在,抢救资料是工作重点。我们就是按此方针办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冰心、萧乾最操心文学馆的事,一幅字画、一枚奖章、一块碑石地把东西送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萧三、张天翼、周扬、吴组缃等生前或身后的捐献最为丰富。茅盾《子夜》的手稿、闻一多失而复得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手稿,价值连城。《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的手稿都可“等身”,有的是十易其稿写出的。尤其是许地山为编梵文字典所抄写的八万张卡片,岂止“等身”,摞起来竟可有5米多高!还有海外李辉英留下遗嘱给了我们全部藏书。林海音将他们夫妇办的纯文学出版社的全部书籍、他们家族十几个作家林林总总的作品都赠送了一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不远万里送来老舍20世纪20年代在伦敦教汉语的16盘灵格风中文留声机片,这是中国作家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声音。翻译家高莽的作家画也很有特点,每一幅都有当事人的题款,随着越来越多老一代文人的离世,弥足珍贵。我们在那十几年里还尽可能地去给作家拍照、录像、录音。我本人就参加过文学馆一天之内按沙汀访问冰心、访问吴组缃的顺序,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朗润园拍摄的全过程,至今难以忘怀。我读过孙犁晚年的散文,那里清楚地记载着文学馆女工作人员冬日访他,并替他录音的场面。到了上世纪末,文学馆的专业图书已藏13万册,文库30多个,算是初具规模了。
那时的物质条件差,但大家的精神面貌丝毫不差。我们在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学教育、普及活动。如没有展览厅,就与附近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等联合举办巴金、冰心、老舍、丁玲、萧乾、胡风、阳翰笙、沙汀和艾芜、陈白尘、臧克家等十四五个著名作家的生平创作展。开过青年学者参加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此会条件差到代表就在“庙”里住宿,每顿饭步行到紫竹院的一个饭铺去吃,但是现在全国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科带头人,回忆起这次“盛会”还十分神往。在1985年我们不顾自己的经费不足,毅然接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一期补贴五千元到后来陆续补贴,到作家出版社补贴。25个年头过去了,我至今没有忘记与杨犁到北大镜春园王瑶先生寓所去谈刊物的情景。我们还举办过小型多样的学术活动,发挥我们馆的部分民间弹性,把一些别人不便纪念的作家的会议,放到馆里来开。比如在“胡风集团”或一些敏感问题未彻底解决前,举办过胡风、路翎、聂绀弩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请过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到馆。我们在北京最早举办学术普及讲演。那时的周末,馆里小礼堂经常被从通县赶来听讲的热情听众挤得爆满。文学馆的星期讲坛一直延续到新馆,一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很有些气候的。
这样,文学馆在万寿寺办了15年。我们对院子里的楼阁、游廊、古树、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它。这是为了文学馆的明天。因古建筑再好,是要退回文物部门的,而且它有千条优点却有一条缺陷,即难于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还是巴老及时为文学馆铺路,他和冰心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致函,要求择地另建新馆。这个新馆从一片菜地变成今日充满现代民族气派的馆舍,馆里和作协的上下同仁所付出的汗水,是无法估量的。2000年10月,我们搬进了明亮的有朝气的新文学馆。文学气味浓厚的环境、多彩的藏品、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北京也属首先引入“志愿人员”的单位),展览、讲演都上了新的台阶,处处展现出芍药居馆的全新面貌。仅是我国著名新文学藏书家唐弢先生的五万册极珍贵书籍的入藏(经与全国兄弟馆的竞争才获得),就是一桩大事件。由于文学馆成立较迟,我们在旧版本书和旧期刊这两项的收藏上尽管下了大力量,仍是不能尽如人意。直到“唐弢文库”与新馆同时建立,才标志了现代文学馆1949年前书刊收藏的大体齐全,可以无愧于后人了。
30年的文学馆历史几乎就是我的半生,但是它的道路要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宽敞得多。新世纪的10年里,在第四任馆长陈建功的带领下,有常务副馆长李荣胜、副馆长周吉宜各位的辅佐,全馆给力,文学馆又跨上了新的里程。除了收藏的进一步充实,对藏品的利用更加扩大,60年“当代文学”的收集资料任务也已然摆在面前,第二期繁巨的馆舍建筑工程也在这一时期宣告完成。对这一阶段我的描述虽不能提供更详的细节,但看到馆里的展览布置一新,藏品目录和画集陆续出版,文学活动不断举行,这个作家和读者的“家”更加温馨,我的兴奋也是不可言表的。现在又迎来了第五任馆领导的时期,学者兼作家的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到任,年轻化、专业化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是显然的。就以我长期从事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一学术刊物而言,从季刊到双月刊曾经走过怎样漫长的道路,今年,它决定要改为月刊了。这似乎象征了、预示了文学馆的远大前景。任何有生命力的事业都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文学馆这个巴金等文学前辈所开创的事业正在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文学馆已经不是孩童,它的举步将更加沉稳、坚实、成熟。文学馆你任重而道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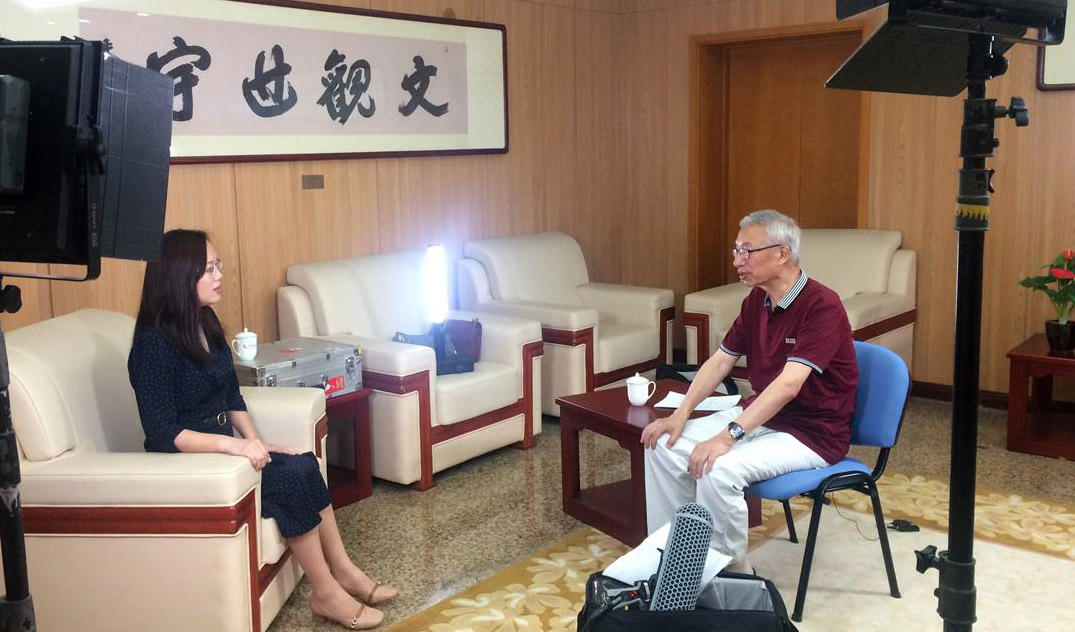
2019年8月31日,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访谈,
拍摄文学名家资料片——“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我走过的路”。
原文发表于2011年1月17日《文艺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