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第1集第1期封面
内容提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丘东平、曹白和阿垅积极投入战争文学的创作,奉献了一批有别于当时抗战文学主流的作品。它们不仅以遒劲的笔力描绘了抗战前线壮烈而残酷的战斗场景,也细致入微地叙写了战争给平民造成的创痛。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这些作品敢于直面全面抗战初期的失败,把批判的笔触伸向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场域和人性的幽暗,从而突显了七月派一直高扬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刻画的以青年军官为代表的新的主体形象,以及他们在文学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想象与伦理意识,也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尼采所说的“精粹的英雄主义”。
关 键 词
抗战文学 战争书写 七月派 丘东平 曹白 阿垅
一 面对战争,抓住生活
卢沟桥事变吹响了全面抗战的号角,此后不久爆发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更表明了全国上下一致抗战的决心,抗战从此进入了全面战争的状态。潘汉年当时即指出,在“八一三”之后,“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1]。
抗战军兴,举国群情激昂,很多人为之欢呼雀跃。黎烈文就激动地说:“看着飞机在天空翱翔,听着大炮在耳边轰响,我满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的喜悦使我快要发狂,我没有功夫想到一颗炸弹要毁掉多少生命,一声大炮要轰去多少房屋,我只觉得我们复仇的日子已经到来,我们用自己的血和敌人的血来洗涤我们积年的耻辱的日子已经到来。在这种伟大的抗战的空气里,我们活固活得痛快,死也死得痛快!”[2]这样欢呼战争的到来,让人不禁联想到一战刚爆发时的欧洲,当时欧洲各国思想界也都视战争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德国,知识界普遍认为“战争将是振兴停滞不前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理想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手段”[3],是保卫德国文化使之免受盎格鲁-撒克逊实用主义文化和物质主义文化侵蚀的一场壮举,马克斯·舍勒因而认为这场战争通过阐明德国独特的战争性质而揭示了“最高的伦理价值”,[4]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则在德国民族解放的层面上来肯定德国所作的战争努力。[5]当然,中国的抗战性质完全不同,它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战,而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但战争所激发的热烈响应却仍有相似处。战争曾给德国人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亲密的、患难与共的感觉”[6],它不仅使“个人的、阶级的私利得以超越”,而且也“见证了那种基于享乐的生存审美化倾向的消失”。[7]在中国,抗战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在战前,国内政局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局者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对日本步步进逼的侵略行径一味地忍让退缩,一般民众精神颓靡、唯求苟安,抗战的全面爆发使为此忧心如焚的爱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自我解放的希望。茅盾断言:“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8]他还乐观地预言:“在长期抗战的火焰中,我们社会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将必净除,在发动民众力量以保障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的过程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可能自然而然消解去,因而抗战的结果又将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真正的全部的实现。”[9]但中日两国毕竟在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这决定了抗战必将是艰苦卓绝的血战,因此很多人在展望战争前景时便不免语含悲壮。傅东华在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所作的诗中写道:“我们要把我们的尸体,供后继者作砂包,/我们要留我们的血迹,让后继者去踩践。”[10]芦焚也在诗中号召人们“掮起我们的枪/去为自由而死/……跨上我们的马/去为要活而死”[11]。这种慷慨赴死的壮烈情怀回荡在当时很多诗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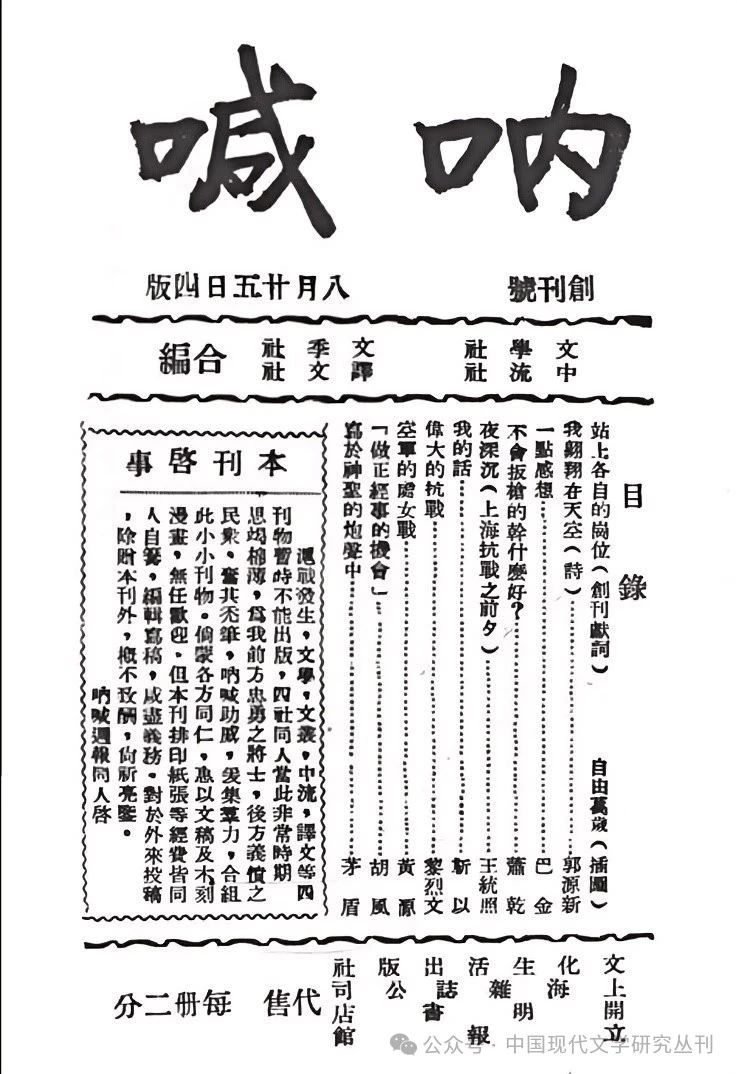
《呐喊》创刊号
伟大而悲壮的全面抗战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文艺应直接描写抗战与民主斗争,“要用铁的笔,蘸着鲜红的血,在大众心头,着力刻画,使每一个人都怒吼,暴跳,这才是抗战的文艺”[12]。1938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对抗战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明确的要求。但是,要求文艺直接描写抗战,也滋生了一些流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胡风所指出的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由于政治要求的过于迫切,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和认识不够,却往往弄成了廉价的表现,写兵士的英勇就难得看到生活上的根源和曲折的成长道路,写汉奸就给他一型的脸孔,写青年就把他们一律地印上预先安排好了的结论……,新文艺里面一向存在着的公式主义的倾向,不但延续,而且滋长了”[13]。
文艺到底应如何描写抗日的民族战争?对这个问题,胡风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七月》发刊致辞中,他强调“这个战争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对于意识战线所提出的任务也是不小的”,“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14]他编《七月》,从最初三期周刊起,就很注重反映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吁请大家多投寄关于民众活动、抗日英雄、战地生活的各类特写和地方通讯。在他看来,“这些是一代底伟大的历史材料,是培养抗战魄魂的宝贵粮食”[15]。1938年1月,在于武汉召开的《七月》座谈会上,萧红说躲警报也是战时生活,只是大家抓不住罢了,作家若是抓不住生活,那么即使上了前线,也还是会写不出来。胡风对此表示赞同,认为“现在大家都是在抗战里面生活着”,“随时随地都有材料”,关键就看作家能不能抓住。端木蕻良也指出:“战争场面只是关于抗战生活的一方面,如果不懂得政治内部种种复杂情形,不懂得后方民众的各种变动的情形,那就不能够写出这个战争。”[16]可见七月派同人对于如何写战争和战时生活,看法基本一致。
《七月》上发表的各类作品,尤其是被胡风视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的“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有着胡风所说的“史诗的形态”的小说,都体现了七月派作家对战争书写的独特理解。本文以《七月》作家群中特点最鲜明的丘东平、曹白和阿垅为例,考察他们是如何描写战争和战时生活的,进而探讨在其战争经验书写中所包含的各种复杂意义的丛结。
二 战场上的失败及其社会根源
“战争最核心的所在,是战斗的体验,它被厌倦和期待层层包裹,被困惑所遮掩,又被恐惧、痛苦和野蛮之火可怕地点燃。”[17]混乱复杂、往往难以言表的战斗体验,通常都是战争文学表现的核心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目标、规模和范围,以及具体的战斗方式,都会因军事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士兵在战场上的战斗体验自然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现代军事技术获得飞速发展,机枪、大炮、坦克、飞机、毒气弹等有着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被大规模使用之后,战斗体验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由于双方武器火力太强大而很快变成了“堑壕战”,不仅作战方式改变了,战斗的体验也完全不同于以往。数百万士兵躲在长达几百公里的潮湿、寒冷又肮脏的战壕里,随时待命,虽然看不见敌人的身影,却无时无刻不在忍受大炮轰鸣和炸裂的声音。每一刻都是死亡的时刻,你甚至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作为战士的勇气、骄傲和自尊。这样的战争是荒谬的,战斗几乎失去了任何积极的意义,变成对于死亡的充满恐惧而又无助的等待。这种把人逼入绝望的战壕经验在巴比塞、雷马克等一战文学作家笔下,获得了充分的表现。可以说一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文学对战斗体验的书写方式,以往那种对战斗的浪漫的、理想化的想象,几乎完全被对现代战争的残酷、恐怖和非人性本质的揭露所取代。

淞沪会战中的堑壕战
中国的抗战文学,尤其是描写正面战场的作品,对战斗场景的描写也深受一战文学的影响。丘东平和阿垅关于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战斗描写,与巴比塞、雷马克有诸多相似处,这自然是由这两场战役的现代战争性质以及具体的作战方案所决定的。在淞沪会战中,中国方面投入兵力70余万人,包括了战斗力最强的三个德械师和中央军、地方军的其他精锐部队,动用海军舰艇约40艘、飞机250架,日军投入兵力也有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架、坦克300余辆。在这场长达三个月的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逾25万人,毙伤日军4万人,战况极为惨烈。[18]淞沪会战与随后的南京保卫战都是典型的防御战,构筑多道战线,依托战壕和碉堡逐次阻击敌人,因此在丘东平和阿垅的战场描写中,时常可见“堑壕战”的影子。比如在《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里,都写到战壕被雨水浸透,变得异常湿冷、泥泞,让士兵们苦不堪言。在一战中,密集的炮火制造了一种“远距离暴力”[19],给士兵带来的感官体验最可怕也最具创伤性。丘东平就用不少笔墨描写了炮火给士兵们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敌人的炮兵的射击是惊人的准确,炮弹象一群附有性灵的,活动的魔鬼,紧紧地,毫不放松地在我们的溃兵的背后尾随着,追逐着。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的鲜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20]
敌人的炮弹已经开始延伸射击了,密集的炮弹依据着错综复杂的线作着舞蹈,它们带来了一阵阵的威武的旋风,在迫临着地面的低空里象有无数的鸱鸟在头上飞过似的发出令人颤抖的叫鸣,然后一齐地猛袭下来,使整个的地壳发出惊愕,徐徐地把身受的痛苦向着别处传播,却默默地扼制了沉重的叹息和呻吟,……。[21]

丘东平《第七连》封面,生活书店1944年第1版
在这种从天而降的、无法预知也无从逃避的暴力面前,个人的雄心和力量似乎都是渺小而可笑的。这正是骄傲的青年军官高峰所感到的一种幻灭。在踏上战场前,他想自己“也许能够在战斗中培养成一个杰出的人材”,但第一次的遭遇战就让他痛感自己完全“认不清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最使他痛苦的,是“当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被限制在被袭击的地位。我们的枪是在手里拿着的,但是我们始终找不到战斗的对手,……”[22]找不到对手的战斗是荒谬的,它对人的精神意志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
阿垅对战争文学之“真”有着异乎寻常的严格要求。他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专业性,认为从步兵的各种动作到炮兵的射击口令和射击法,对这些细节都必须具备专门的知识,才能描写得真实可信。[23]对战斗场景的描写,他也力求做到科学般的精准,连对毁伤身体的描写也是如此,因而常常是满纸血腥,惨不忍睹。如《南京》中写五台山的炮台阵地遭到敌机轰炸,幸存者眼中所见,都是一些“可怕的东西:蛇一样的一条肠子、一只露出在浮土外面的带血的手臂、一个直径十公尺以上的重磅爆炸弹炸成的漏斗坑”[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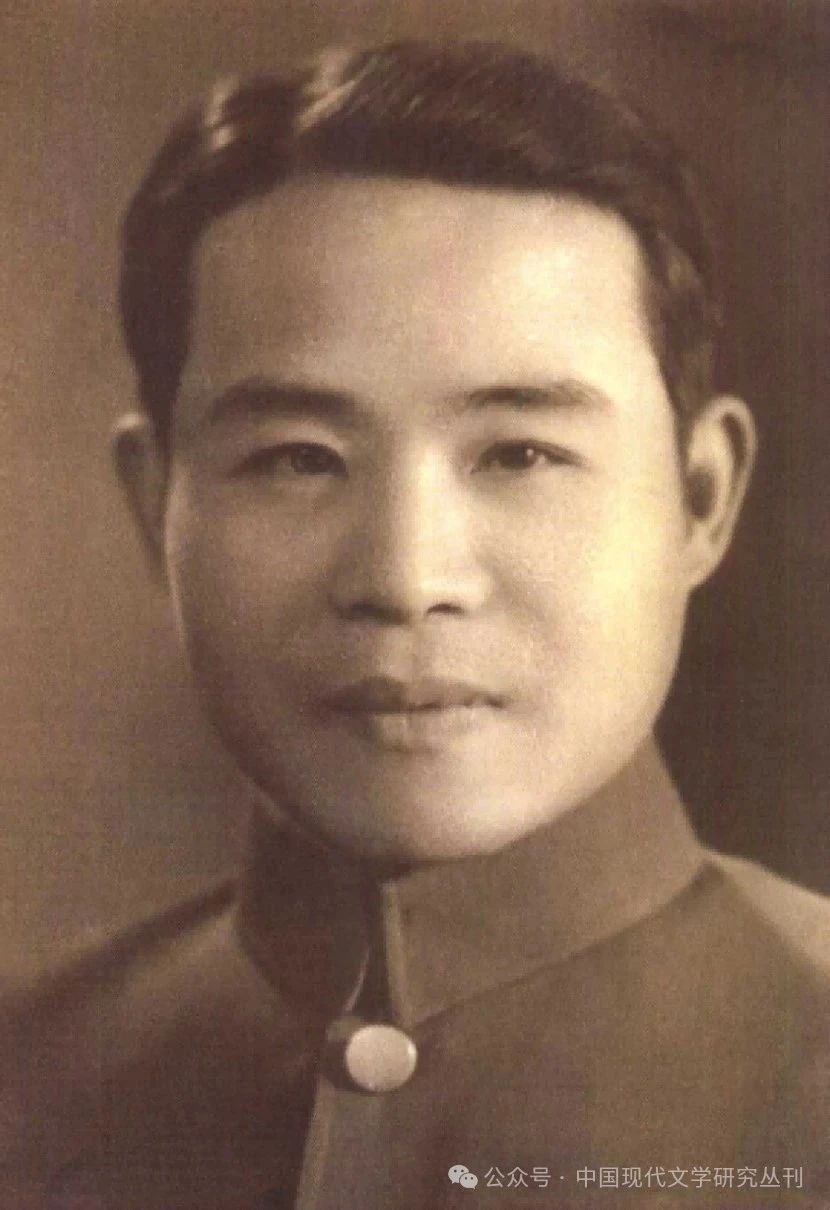
阿垅像
丘东平和阿垅都有前线作战的经验,他们对战争之残酷、可怕有深切的体认,因此才能有如此生动真实的战斗场景描写。基于对抗战性质的认识,他们对战斗体验的描写不可能像一般的反战文学那样,着重渲染现代战争之惨烈与非人性,而必定要强调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浴血之战,必须众志成城、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然而,获取胜利的过程又必然是艰苦卓绝的,正如阿垅所说:“胜利决不是廉价的,也决不是直线的,何况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国家和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停滞在农村经济状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胜利是跋涉的长途,需要怎样艰困地去争取啊。”[25]那么,抗战文学就不能只是鼓舞斗志的呐喊,它也应该对跋涉的长途中遭遇的失败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而这正是丘东平和阿垅有意识追求的一个创作方向。
众所周知,战争作为有组织的暴力形式,总是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现代战争,它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如查尔斯·汤森德所说,“现代战争是行政管理、技术和意识形态这三方面的不同变革的产物”[26]。行政管理方式的变革决定了维持军队和发动战争所需要的行政的和财政的制度支持,技术的变革使得杀伤力更大的武器火力得以大规模使用,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战争的形态,而意识形态主要是指18世纪末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它促成了众多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也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提供了政治目标和动员手段。现代战争必须调动社会的全部资源和力量,才有可能谋求胜利,这就对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抗战全面爆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被迅速点燃,全国上下斗志高昂。但与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相比,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武器装备落后,军队素质和训练水平低下,工业基础薄弱,无法持续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补给,社会组织的涣散和行政管理的低效率更是形成了全面的掣肘。上述各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决定了淞沪会战以及后续的南京保卫战都不可能以正面防御、逐级抵抗的作战方式取得胜利。
丘东平和阿垅都写到了导致这两场战役失败的一些具体原因,这些在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所反映的其实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一些积重难返的痼疾。阿垅身为排长亲历了在闸北的揭幕战,他的两篇战地报告《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是对淞沪会战第一阶段战况的真实报道,其中写到不少令人振奋的现象,如国军甫到上海,民众夹道欢迎,递茶送水,军队和人民之间如此亲切,是北伐以后所不曾有的,这大大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热情,他们在开战后个个奋勇争先,不怕牺牲……但同时也能看到军队内部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在部队开拔前,竟发现每个班兵员均不足,一个连队挂名吃空饷的竟有十个之多。连长因此大骂“中国军队真黑暗!……非杀不可”,但吃空饷他自己也有份。兵员不足,必须携带的武器军火就只能加重摊派到每个士兵头上,连长却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他向来认为“兵是狗、猪,非压迫不可!”[27]这种事情见多了,士兵们难免感到寒心和不值。阿垅后来提到,由于连长和代理连长先后卷款潜逃,他所在的那个排前后有好几位士兵开小差。[28]类似的这种负面现象还真不少。如部队到了上海,却找不到驻防地,原来是上级下达的命令里竟然把止园路与济阳桥错弄成了正园路与洛阳桥。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可见备战做得有多草率!指挥方面同样是一团糟。临战前,师长却空洞地训话:“我们要不依赖飞机、大炮,用我们步兵自己底兵器,就是轻机关枪、步枪,用我们血肉的身体,把敌人底司令部占领起来!”[29]轻言牺牲而不顾惜将士之生命,难怪军官们要在底下骂娘了。指挥作战的混乱无能在《从攻击到防御》里有更详细的描写。八字桥的攻击战先是错失了奇袭敌人的良机,之后的强攻又没有及时上预备队,使得好不容易获得的战果得而复失,导致攻击目的最终落空。转为防御后,修筑工事未经实地踏勘就胡乱下达了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还要求各排征集粗二十厘米、长四米的圆木三百根,限时缴送团部,这些盲目的指令让底下的士兵苦不堪言,怨言四起。军官们却在“掩蔽部里吃红烧鸡肉、酒,甚至把太太偷偷接在掩蔽部里来”,士兵们自然也上行下效,“放哨以外就打牌,烧东西吃,有的是猪、墨鱼、南瓜、四季豆,……到什么地方去拣些心爱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两军阵前,纪律如此涣散,让排长梅墨法(阿垅本人化身)不禁要怀疑:“唉!我也在抗战里么?这也是抗战么?”[30]《申报》上“全是血战和胜利的字样,但是自己是躲在掩蔽部里,象个刺猬。他一心厌恶,难以分辨那到底是愤怒呢,还是真是厌恶的厌恶”[31]。他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没有政治认识上,“政治问题不第一位地提出,……军事底价值是小得很的啊”[32]。从攻击到防御,闸北的阻击战竟然暴露出这么多问题,这是听惯了“八百壮士”之类热血故事的读者所想不到的。

淞沪会战中血战罗店的战斗场景
丘东平的《第七连》以谈话的形式讲述了其弟丘俊率第七连在淞沪会战中作战的经历。从作品中所述作战时间和地点看,应是十月中下旬会战第三阶段的战事。1937年10月21日起,国军以新调来的桂军21集团军的四个师为主力,实施蕴藻浜两岸反击战。桂军虽作战勇猛,但武器陈旧,新兵不少,又缺乏现代战争的经验,结果伤亡惨重。反击战失败后,日军猛攻大场,26日大场失守,战局急剧恶化,败象已露。在蕴藻浜两岸展开的十月鏖战中,国军错误地采用了阵地战的方式,与火力占优的日军正面硬抗,战况惨烈,兵力消耗巨大。[33]《第七连》写的就是其中一个局部战斗。[34]这篇作品所揭露的问题不少。首先是后勤补给极差,部队进入阵地两天后就“已无饭可送”,只能吃“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田里的黄菲子和葵瓜子,致使丘俊“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35]其次是士兵训练不足,军事素养差。第一线士兵遭到敌人炮火攻击即行溃散,“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的鲜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36],扰乱了第二线士兵的军心。埋伏在第二线的士兵又不听从命令,在敌军斥候诱使下擅自开火,轻易地暴露了阵地,造成重大伤亡。最后是战略上与指挥上的失误,先是错误地实行阵地消耗战,在阵地已被敌人炮火摧毁的情况下,上司不作变通,仍命令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把阵地的存亡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让士兵们白白牺牲,这种愚蠢的战法只能让丘俊“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了。[37]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所写故事发生在1937年11月18日之后。在此之前,日军已于11月12日占领南市,上海全境(除租界外)陷落,淞沪会战已告失败。由于事先没有制订周密的撤退方案,仓促拟定的计划又未能贯彻实施,11月9日后,北线国军的西撤出现失控,局面极其纷乱失序。[38]这篇作品写的就是国军败退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同样还是徒然糜耗兵力的阵地战,对这种愚蠢的战法,士兵们只能以唱歌来表达不满:
我们这些蠢货,
要拼命地开掘呵,
今天把工事做好了,
明天我们开到他妈的……。
……
后天日本兵占领我们的阵地!……[39]
如果严格执行营部的命令,第四连极可能被敌人延伸的猛烈炮火摧毁在阵地上。在危急之际,士兵们自发地越出壕沟往前冲,将敌人的炮火甩在了身后,但也因此违背了上级的命令。在脱离大部队之后,第四连穿插到敌人身后,打了漂亮的伏击战,终于与友军第三十六团会合。但没想到的是,友军非但不愿帮他们解决断粮之急,反而以“来历不明”为由勒令他们立即缴械。第四连反抗失败,被悉数歼灭。他们没有被日本人的炮火消灭,却还是没逃过友军弟兄的枪口。虽然无从证实在淞沪抗战中是否确有此类事情发生,但它所反映的国军内部派系林立、沟通不畅的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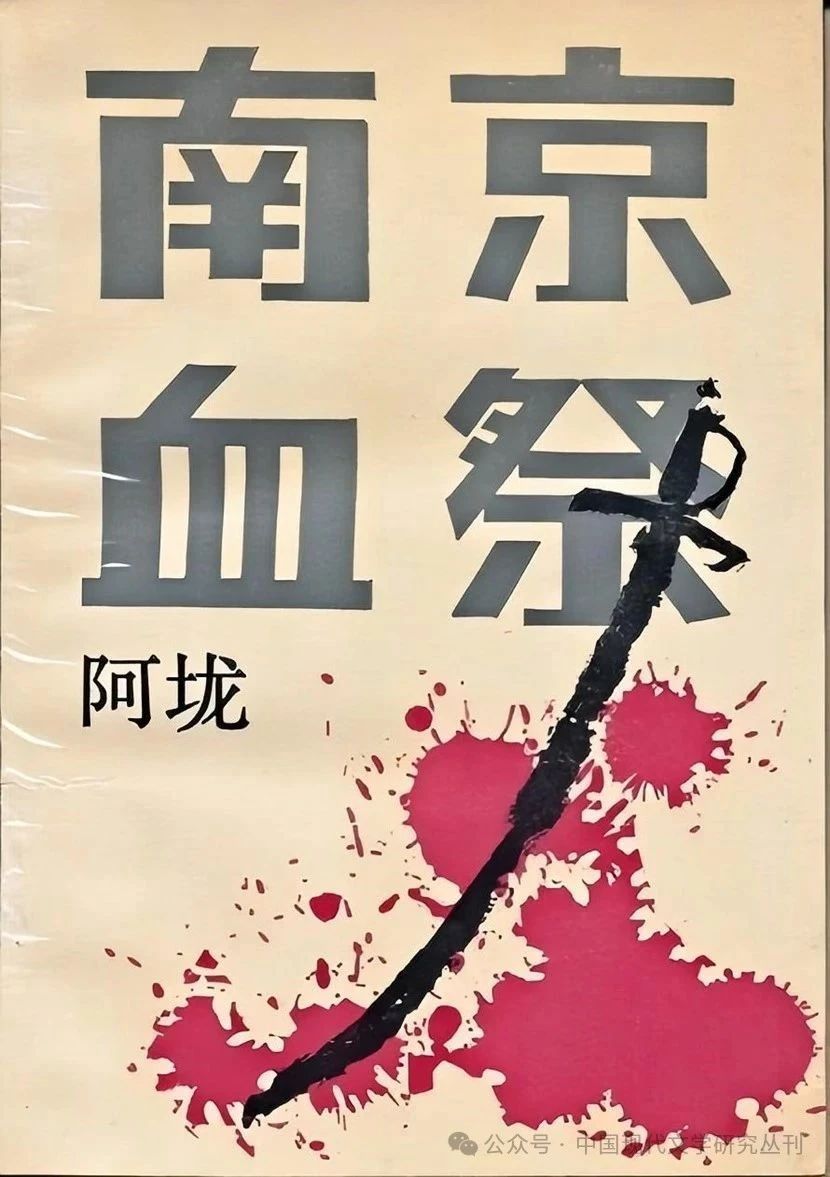
阿垅《南京血祭》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南京》是阿垅全景式描写南京保卫战的力作。在这部作品中,上述各种问题同样存在,而且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临战前却发现早先构筑的国防工事的图表不见了,没人知道重机关枪的掩体和指挥部坐落何处,即使经实地踏勘发现了,也因为没有钥匙而打不开那些特制的异常坚固的钢门。[40]又如第88师在闸北战损后补充了不少新兵,但这些新兵缺乏训练,上了战场一触即溃,白白送命。[41]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南京卫戍司令部事先竟然没有做任何撤退的预案,导致南京失守后大量溃兵和难民拥堵在挹江门前,守城门的部队为阻挡人流竟贸然开枪,引来溃兵的回击,有人甚至还向人群中扔手榴弹,导致很多人无辜受难。[42]那些侥幸逃出挹江门的人,到了江边,却发现无船可渡,不少人在绝望中跳江,唯求速死;也有人想靠着抱一块木板、门板或一根木头漂到江对岸去,但他们很快就在寒冷的江水中冻僵了。

南京失陷前夕的挹江门
全面抗战初期的文学,慷慨激昂的战歌是官民皆乐见喜闻的主旋律。丘东平、阿垅的作品却揭露了那些早已存在的痼疾,它们并没有随着抗战军兴而自行消失。在抗战的高光照射下,它们反倒是越发地触目惊心,从而提醒人们要赶快积极行动,湔除旧疾隐患,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通过自我更新而焕发生机活力,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丘东平屡屡鼓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写战争,他倒未必像未来主义诗人那样,视战争为“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43],但或许如诗人彭燕郊所言,战争之于他,“不是一种题材,不是一种场景,一个故事,战争只是生活,即使是被扭曲了的生活,也还是生活。战争当然是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充满希望并被希望所照亮”[44]。换言之,战争照亮了一切,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能借此从灾难和破坏中洞察其缘由,并从深刻的反省中看到未来的希望。胡风在给《第七连》所写的“小引”中称:“这些是英雄的诗篇,不但那艺术力所开辟的方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加进了一笔财产,而且,那宏大的思想力所提出的深刻的问题,也值得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反复地沉思罢。”[45]这话用在阿垅身上,自然也合适。正是这种促人沉思的思想迫力赋予丘东平和阿垅的战争文学作品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品格,它们对战争的描写结合了深广的社会历史批判,在思想的含量与力度上超出了当时很多的抗战文学作品。
三 平民的受难与痛苦:战争的另一面
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在战争中遭受最多苦难的,从来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手无寸铁,最容易沦为敌人施暴的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创了全面战争的模式,需要集中举国之力投入战争以争取胜利,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称之为总体战(total war)。他指出在总体战中,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两国对垒,“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46]显然,总体战的设想为战争中无差别地攻击平民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战是总体战的一个极端例子,战争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全民对抗,“士兵与平民已变得可以互换角色”[47],而且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尤其是大规模的轰炸,已经成为一种惯用的战略手段,用以打击和瓦解对方的战斗意志。在整个二战期间,针对平民的攻击和伤害非常普遍,平民死亡人数与军人死亡人数基本持平。[48]在中国,日军的逆天暴行导致平民伤亡率更高。[49]在淞沪会战中,平民伤亡亦极为惨重,光是公共租界内平民死亡人数就有37753人,战区内原属江苏省各县及沪宁线两侧各县遭敌残杀共计76941人,难民人数超过392万人。[50]

淞沪会战中上海难民逃往租界
日军的暴行,平民遭蹂躏、被杀戮的惨状,是抗战文学反复书写的内容。这样的血泪控诉,能够激发全体国民同仇敌忾、誓死抗战的决心。丘东平的《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以人物自述的方式,叙写了淞沪会战伊始平民百姓逃难的惨痛经历。W女士与其表姊及姑母在开战前一天就搬到租界,租了一个亭子间,却被乘机抬价的二房东赶了出来,她们只能回到东宝兴路上自己的家里。没想到第二天就打起仗来了,W女士亲眼看到日本兵闯入邻居家,杀害了男主人。当晚七点多,她们决定出逃,在惊险万分地翻过围墙、暂时脱险后,她们在大马路上碰到一大群逃难者。这些人昨晚很早就到了租界北端的靶子路口,但未获通行,又遭到日军驱逐,只能返回。可怕的是,作战双方都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在马路上无处可藏,不断被枪炮惊吓,为流弹所伤。W女士在奔逃中与表姊和姑母失散,从此失去了她们的下落。她还目睹了一家五口遭罹的惨剧,四个年青的儿子先后被日本人杀害,悲痛至极的母亲“象一只被袭击的狼似的”冲进路边没人的洞开着的商店,直上三楼,跳了下来,白色的脑浆溅了站在一旁的W女士满身。这个故事里最耻辱的是,难民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竟然无处可逃,被阻拦在租界的铁丝网外,而中国的军人又沉醉于战斗,只是喝令难民们躲开、别喊叫,却没人站出来给他们一点帮助,任由他们被流弹所伤,被敌人杀戮。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国军士兵无情,根本责任在于政府,在决定开战之前,他们竟然想不到要提前疏散平民,开战后又没有任何援救措施,这说明政府并没有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
战端一起,平民百姓就是最脆弱的人群。没能逃出火线的,惨遭敌人杀害;逃了出来的,在车站也难逃轰炸;躲进租界的,很多只能流落街头。据当时的报道,逃到租界的难民有70多万人,他们都“处在饥饿、寒冷、疾病的死亡线的威胁之下。……男人、妇女、儿童聚集停车处或商店橱窗的前面,……有些人坐在行人道的边上,蜷曲着,身上背着一个蓝布包,或者一卷席——这是他们所有的一切。据说,因痢疾和饥饿而死的,每天有二百多人”。[51]难民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众多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建议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7日颁布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虽然“这一大纲的基本思路是采取消极的救济和实行强制的管理方式”,但在当时“对上海乃至全国的难民救济工作,曾起过一定作用”。[52]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左三为曹白。沙飞摄影,经AI修复
在当时,难民救济委员会、慈善团体、国际救济组织以及各地同乡会都办了不少难民收容所。曹白的作品即描写了难民收容所内的真实状况。曹白是青年木刻家,曾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而被捕入狱。“八一三”前夕,他正处于失业,“深感古国的迫害和文明的严酷”[53],为之烦恼、痛苦不已。炮声一响,他觉得自己应该出来做点实事,就参加了慈联会所办的金城难民收容所。因为工作和生活都无着落,他觉得自己未尝不也是一个“难民”,那么“‘难民’与‘难民’之间,怎么会不交流着脉脉的温情呢!”于是,他怀着“热烈而悲凉”的心情,“在无可如何中”,写下了《这里,生命也在呼吸……》等一批作品。[54]这些写难民收容所的作品有报告、散文和通信等,陆续发表在《七月》上,颇受读者欢迎。聂绀弩曾说自己拿到《七月》,总是先读曹白的作品,因为觉得曹白不像丘东平和阿垅那样,有“写小说的样子”,而是很随便,“碰见什么写什么,想到那里写到那里”,“篇篇都画出了他自己,画出了他的周围,也画出了战争的一面”。[55]
但是曹白所画出的“战争的一面”,却不免有点残酷。难民收容所让他觉得“阴暗、凶狠、刻薄……。仿佛象监狱”。有些收容所的主任甚至还“施展刮剥的伎俩”,“把领来的米只给难民每天喝两碗薄薄的稀饭,剩下的便车去卖给粮食行。战时的米是飞贵的,他就此赚满了腰包”。[56]有油水可捞,也便有人抢着要来管理难民收容所。《“活魂灵”的夺取》便写了这么一出闹剧。“我”被委派为互颂收容所的主任,收容所设在一家已停业四个月的银行里,满屋污秽,连水电装置都已被银行老板们完全拆除。“我”刚到那里不久,就有三个“穿着印度绸衫的汉子”走进门来,声称这里的收容所是YB同乡会开的,只收YB同乡,他们奉命来接管。“我”愤而回去问上司,却被告知因“强不过YB同乡会”,只好把互颂给了他们。“我”于是愤恨地想:“难民每顿的十六两饭,……也许要减成十四两了吧。”[57]因为是一桩好生意,办难民收容所的人也难免要被怀疑。在给友人的信中,曹白就屡次吐苦水:上司常叫他去算账,以防他“揩油”,他的心因此是“悲凉的”;[58]自己“担任许多事,但没有一点薪水”,上司反倒“常常和我捣蛋,说我揩了难民的油,天下还有比这样事情更岂有此理的吗?”[59]既然把难民收容所当生意来做,那么“活魂灵”们的生死也就不怎么放心上了。带了三个孩子的女人得了霍乱,额角和手心都已冰冷,非得在电话中说“快死了”,才勉强把人接到医院,但已经晚了,这女人当天夜里就死了(《在死神的黑影下面》);收容所所在的电影院老板为了省电,巨大的电影院,四百多个难民,却“只给难民开了五十支光的两盏”,还横竖说自己是“牺牲”了,对难民“是开口猪猡,闭口猪猡的,以显出他是高踞‘猪猡’之上的大人物”;[60]战情稍有稳定,金城大戏院就被老板收回,“在开映《红运高照》,教同胞以‘发财’的方法”[61]……这些阴暗的东西看多了,难怪他要感到“心是悲凉的”。
《杨可中》是更沉痛的一篇作品。杨可中是一个左翼文艺青年,“八一三”后参加了别动队[62],却被当作共产党去挡头阵、做炮灰。他来到收容所勤奋做事,又遭到别人忌恨,收到了恶毒辱骂的匿名信。他患有肺炎,难民医院中那些“涂着口红的苗条的看护们”[63]却对他视若无睹,他的胳膊也因为打针没做好消毒导致针眼发炎而被迫开了刀。他的肺炎已变成“脓胸”,虽然动手术取出了脓液,但他最终还是死在了伤兵医院中。让人心酸的是,好不容易从慈善家那里化缘来的一口棺材竟是那么小,让他躺在里面好不委屈。这是一篇长歌当哭的作品,读来令人抑郁、悲愤,也因此遭到彭柏山的批评。彭柏山认为它虽然“真实,富于感人的魄力”,但仍是失败之作,因为没能“由死引起活的希望”从而给读者以力量。他强调我们的写作要征服“死”,“把人类带到光明的世界”,“即使写黑暗的牢监”,也要“把光明带到铁栅里面去”。[64]曹白黯然接受了批评,他甚至因而觉得自己的文章“是有毒素的”,但胡风却不以为然。他指出:杨可中的死,“诚然是凄惨而哀伤的。……然而,凄惨而哀伤的死并不一定使人堕入‘黑暗’;只要是‘真实’而且‘感人’,读者也能够生起对于不能不死得这样凄惨而哀伤的环境的憎恶,反抗”[65]。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是笼笼统统地向作家要求‘光明’”,而“只应该要求作家写出生活的真实来,写出生活的本质的方向来,所谓‘光明’就一定附随在这‘真实’,这‘本质的方向’上面”。[66]胡风随即又指出,其实无论是在别动队还是在难民收容所,都存在着“健康的力量和黑暗的力量的斗争”,但曹白却只侧重于其中一面,对杨可中的不幸遭际和“凄惨而哀伤的死起了大的共鸣,被抓住了同情之心”,而没有对杨可中的“那个人生现象(题材)作更深的探求,作更进一步的肉搏”。比如,只着重写杨可中的“阴冷”,却把他的“勤奋的工作”轻轻地一笔滑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胡风认为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的困迫和心境的暗淡”使然。[67]胡风的这个说法或许能够解释曹白所写的难民收容所为何会与史料中所载有比较大的差异。
曹白先后工作过的金城、正大、康悌这三个难民收容所,都是慈联会所办。[68]因为有许幸之、曹白等中共党员负责,这几个难民收容所在当时算是办得比较好的,特别是金城收容所,在当时的《救亡日报》等报纸上常有正面报道。比如组织女性难民替战士缝寒衣,[69]开展难民教育,[70]带领难民儿童到伤兵医院慰劳伤兵,[71]等等。而且还曾组织青壮难民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疏散难民到温州垦荒自救。总之,慈联会的难民收容所总体上还是不错的。[72]当然,指出这些事实不是说曹白所写的不真实,他只是对阴暗的东西更敏感,因而也更自觉地侧重于写这一面罢了。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自己所希望于《七月》的,“就是能在这战争中揭发黑暗和疾苦。……至于对于光明的讴歌,我的意思是:暂且还是最好慢一慢,或者就让给那些善于歌唱的人们罢”[73]。

曹白《呼吸》书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他为何要自觉地做这种选择?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理智上的认识:“我们的山河被日本轰毁得够多了。但我们也得一面时时省察,将卑污的精神、黑暗的灵魂、妖精的伎俩、愚昧的方法、老谱的新翻,在这残酷的猛烈的炮火中,一同轰毁,一同洗礼。锻炼自己,沉着坚韧,这才是到达新中国的大路。”[74]另一方面,更直接的原因是,战争的残酷所带来的震惊和创伤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感知方式。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说,一战后士兵们从战场归来,个个变得沉默寡言,他们可交流的经验不是更丰富而是更匮乏了,就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崩地塌的暴力场中,人的躯体是那么渺小而孱弱。[75]曹白也有类似的经验,尽管他不曾作为士兵血战于战场。在给胡风的信中,他说:
我去前线五六处,总想写一点文章给你,然而,不能够。它给我的感想太多,它给我的印象太惨。故事是那样伟大,而热血是那样的奔突。凡这些,都是叫我无从下笔的。墨写的字能够表现血写的事吗?不能够的啊![76]
他虽不像一战老兵那样只能沉默无言,但要让他讴歌,却是不能。这是一个人在亲眼目睹了战场上的血腥残酷之后的一种自然反应。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看到的一个伤兵:
不是一个伤兵,那简直是一团发紫的血块。头、手掌、脚腿肚上,我看见筷子头一样大的伤口了。然而在右腿肚,医官剪去右腿肚的绑腿的时候,半个腿的肉就顺打的落到了地上。在烛光下的发黑的鲜血,像线一般的往下流,而这一团血块似的伤兵,努力的咬着嘴,医官皱皱眉,随手按住了这伤兵的眼睛,说:
“唔!达姆达姆[77]!”
这伤兵也到底苦痛的呻吟了,我不忍看,扭过头去,西斜的落月是橙红色的,象发窘,象哀愁,似乎在宣告着灾殃的到来。[78]
伊莱恩·斯卡里指出,身体的疼痛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它“不仅抗拒语言,而且还有力地摧毁语言,使人立即回到前语言的状态,回到人学会语言前就会的那些哭叫中”。对语言表达的抗拒,使得身体的疼痛从根本上是无法分担的。[79]目睹伤兵残破的身体,听到他疼痛的呻吟,发窘的恐怕不只是西斜的落月吧,也还有一个曹白。既然别人的身体痛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也无从分担,那么对于一个敏感的作家来说,直接描述这种身体的痛苦就会带来一种道德上的负疚感。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曹白几乎很少直接去描述难民的身体痛苦,而主要通过他们身处的环境从侧面烘托。在《“活魂灵”的夺取》里,难民收容所开在一家已停业的银行里:
满屋是蛛丝,当门的一个柜台,从前,金银钞票们是在这里很翻了一通筋斗的,而现在,却堆积厚厚的灰尘。扑过来的是很重的霉臭,还有老鼠们的屎尿味道,我知道,这已成了耗子的乐园了。
然而难民是苦的,他们就在烟尘陡乱里迂缓的活动,象一群黑色的动物,鼻尖上都蒙着一层淡淡的乌黑,那是灰尘的粒子。[80]
在这里,身体的痛苦因为被钝化似乎已感受不到其存在,但那种沉重的压迫感却让人感到崩溃、绝望。身体的痛苦因为没有所指内容,所以不能被直接对象化,而只能通过符号转换的链条来间接表现。濒死的“生着虎列拉的所谓发痧的女人”,她的额角和手心都是冰冷的:
她闭着她的凹陷的眼睛,呻吟着,吃力地掀动着鼻翼;但她一只手却护定了她自己的一个最小的孩子,还有两个大的孩子在偎着她。[81]
她的身体痛苦以及比这更大的痛苦,正是通过她垂死之际护定孩子的那只手来表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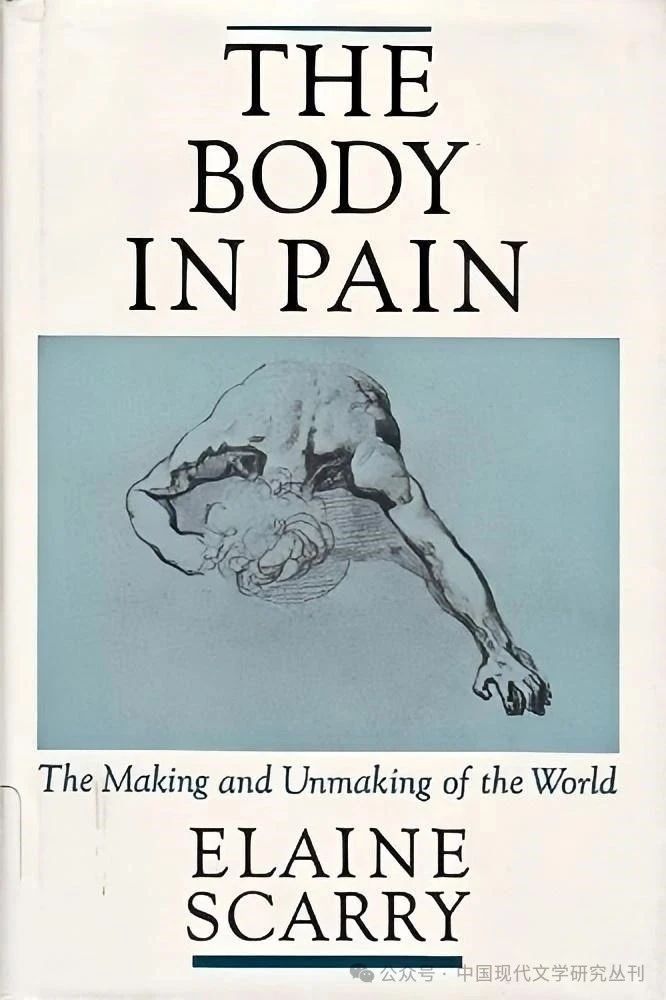
伊莱恩·斯卡里《身体之痛》书影
斯卡里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与结果是伤害”[82],它“总是无情地将受伤的、洞开的人类躯体的内部容纳当作其自身的内部容纳”[83]。当这种伤害被大规模滥施于无辜平民并造成巨大的身体痛苦时,战争似乎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目标,即通过给对方施加无法弥补的伤害,从而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击倒对方。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此,为了最终的胜利,就不应该忽略战争造成的伤害,也不能因为身体痛苦的无法表达和不可分担的性质而拒绝描述战争伤害。但怎样恰当地描述这种伤害?显然,对于受难身体的过于血腥的描写是不恰当的,它把暴力和痛苦呈现为一种景观,却无视身体痛苦的不可分担性。这样的景观化描述往往呈现为不加节制的语言狂欢,它所掩盖的是一种隐秘的道德上的冷血症。从这个角度来看曹白,他对难民收容所的看似偏于一端甚至未免过于黯淡的描写,就不能完全用胡风所谓的创作心境的暗淡来解释,它其实也体现了因为意识到不能分担他人的身体之痛而感到的内疚与不安,以及一种服从内心的不忍与怜恤的自觉的写作伦理意识。
四 “神圣的死”与主体的自我完成
丘东平、阿垅对前线战场所作的线条劲健的刻画,曹白对难民收容所的曝光式描写,都借助战争的强光暴露了在军队内部以及社会层面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战场上的失利,以及后方的种种掣肘。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所写的基本都是失败的经验。因为预见作品可能会招来批评,阿垅在《南京》后记中,第一句话就强调“本书不是为失败主义者写的”。失败是暂时的,胜利也决非直线的。南京一役的失败作为事实必须接受,没必要用美丽的颜色来涂抹、遮盖失败。如果把写失败看作暴露,那么这暴露所给予我们的是经验和教训,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现在和未来”。[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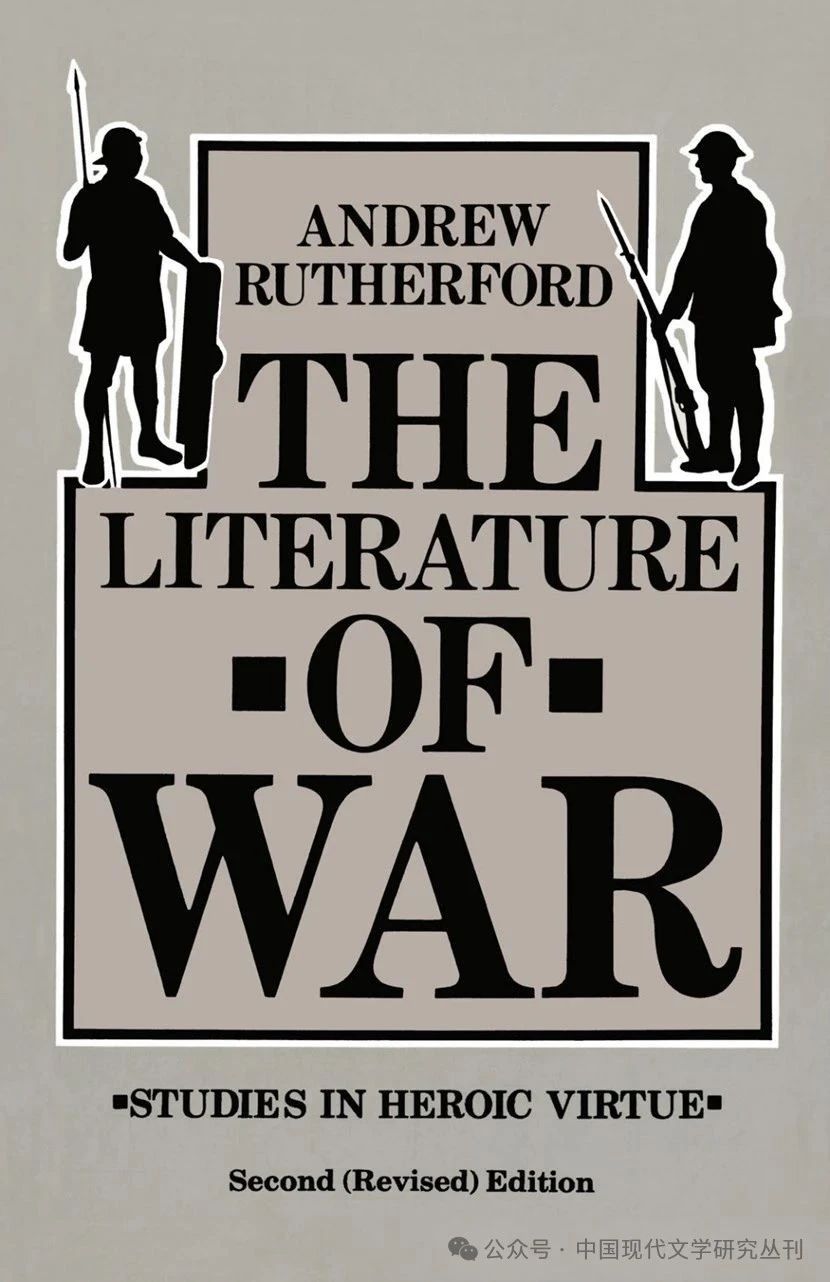
安德鲁·卢瑟福《战争文学》书影
但不管怎样辩解,他们书写战争的方式毕竟与抗战文学的主流不尽相符,因此无论是在战歌响遏行云的当时抑或后来,都遭到了批评或误解。比如舒允中认为,丘东平和阿垅“在他们的战场报告文学中无情地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无能和战争造成的创伤,并以此向战场英雄主义公式提出了直接挑战”[85]。他还引述安德鲁·卢瑟福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体现出战争的现实不是战场上的荣耀,而是战场上的混乱、痛苦、劳累、恐惧、野蛮和死伤,而士兵们也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个人,因此现实主义必然会向英雄主义进行挑战”[86]。但卢瑟福其实并没有把现实主义与英雄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认为“现实主义对战场的描写,因其极为残酷,可用以彰显人们在面对这种经验时所展现的勇气和忍耐力”,承受的苦难越多,面对的恐怖越大,在道德上没有被它们摧毁的人所取得的胜利就越是高尚。“因此,对士兵们本身而非对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所作的‘现实主义’描画,才是对传统的英雄主义观念的重大挑战。”[87]照此看来,丘东平和阿垅的作品或许就不能简单地说是反英雄主义了。他们笔下的士兵的确有各种毛病,愚蠢、笨拙、贪婪、纪律性差,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往往会在慌乱中溃退,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作战方式,他们也会很勇敢,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里,敌人的炮火覆盖了整个阵地,此时与其守在阵地上挨炸,不如往前冲破火力网、险中求生,所以士兵们没有听从林青史的命令,而是自发地爬出了战壕:
一个个象鸵鸟似的昂着头,他们的杀敌的雄心依据着蠢笨的姿态而出现,他们一个个都象抱着最单纯的意志而死去了的尸体,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吸引着这尸体的行列,叫他们无灵魂地向着危险的阵地行进,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88]
丘东平反复强调士兵们“灵魂是早就已经和战斗合抱了,在战斗中沉醉了”[89],因为“他们交出了一切,把一切都给予了战斗”[90],所以表现出“无视一切的惊人的勇猛”,“像夜行的野兽似的,单薄地,寂寞地踏上了他们的壮烈而可悲的行程”。[91]明明知道这个行程的终点必定是死亡,但他们却无所畏惧,甚至在自编的歌曲中以貌似愚蠢的方式,嘲讽了不断逼近的死亡。这大概也可以说是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吧。所以,准确地说,丘东平所要挑战的,并非英雄主义本身,而是以英雄主义为名迫使士兵们作无谓牺牲的不合理的制度。
事实上,丘东平的作品向来都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气概,而且他很迷恋于通过表现人物的勇敢赴死来讴歌英雄主义。《滦河上的桥梁》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它写的是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中国军队已全线后退的危局下,一个仅有一百人的连队和二十名义勇军组成了一支混合部队,义无反顾地孤军挺进即将陷落的卢龙城。他们突破了敌军炮火的封锁,来到滦河边,却发现我方的一队工兵在奉令炸桥。应他们的要求,工兵们在完成炸桥任务后又马上开始恢复桥梁。四十分钟后,他们终于渡过了滦河,卢龙城“展布着忍苦的齿”在对他们微笑。[92]卢龙城的露齿微笑,暗示了这支队伍全军覆没的结局,而这是他们出发前就已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路的,日本人和死亡都是他们必须打败的敌人。胡风认为这篇“很短的报告式的或速写式的东西”,其“形式上的抗日民族英雄主义旋律正吻合着内容上的抗日民族英雄主义的气魄,使人感到一股雄壮的迫力”。[93]但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却是对死亡的热烈渴望。渴望死亡即是为了征服死亡,这似乎是丘东平特别钟爱的一个主题。
怎么理解这种对于死亡的热烈拥抱?是基于死亡本能吗?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在每一种生物中都起作用,并力求使生物走向毁灭,使生命退回到无机物的原始状态”[94]。在丘东平的作品中,的确可以看到士兵们从一些攻击性和破坏性行为中得到了满足,对包家宅阵地前方一座独立房屋的破坏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他们的出击或是撤退,以及作战过程中的耐心和坚韧,都表明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求生意志,并非单纯为死而死。这就如弗洛伊德所说,死亡本能总是与爱欲本能相互作用的,而“爱欲的目的是先把每一个人,再把每一个家庭,然后再把每一个部落、种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95]。那么是否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士兵们是为祖国而死?他们甘愿以死来证明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死亡因而象征着对超越自我的更高存在的忠诚,个人通过自我牺牲融入共同体的历史并获得了永生。
丘东平的散文《神圣的死》描画了淞沪抗战中收殓阵亡士兵尸体的庄严场景:三辆卡车“装满着英勇的斗士的尸体”,停在大场的街道上,“两边的民房里荡开了一片惨烈的令人深思的哭声”,两个民夫“屏着气息”把尸体一具具抬下来,“我整个的灵魂和肉体都静止下来,赤裸裸地浸浴在这凛肃的气氛中”,和身边围观的市民们一起低下头来,祝祷“我们的斗士的灵魂”安息:
——同志们,你们都安息吧!安息在我的心里,只要你们能够获得一点安慰,凡是你们所需要的我都无条件的交给你们!在这残酷的战斗中我要锻炼出一副钢般坚硬的肩背,用这肩背来荷载你们的骷髅!……[96]
尽管这不是一场正式的葬礼,却也有着仪式的庄严。阵亡士兵的尸体已成为值得人们尊敬和崇拜的神圣的身体,在无声地教育人民,并激起他们复仇的决心。尸体被赋予了超越性的象征价值,能够增进人民对国家的认同,这就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巴雷斯所谓的“尸体的社会美德”[97]。“神圣的死”让为国捐躯的士兵在人民的集体记忆中获得了永生。然而,为国牺牲并非绝对无条件的,在国家制度废弛、社会全面腐败的情况下,人民生如蝼蚁,基本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又如何能够慷慨赴死?显然,若是避开了政治认同、单方面地强调个人对国家的忠诚,以及他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为国捐躯未必就能被视为一种意义圆满的死,“神圣的死”也可能会被怀疑是一场欺骗并遭到抗拒。阿垅作品中写到士兵们因为长官携款潜逃而临阵脱逃,所揭露的正是这种铁一般坚硬的真实。
丘东平的散文《申诉》对战争中的死亡有着更复杂的思考。这篇作品以一个刚刚战死的士兵的口吻,诉说了死亡的不公:
我们不要说死亡的结果是痛苦,我们要说死亡的缘由是振奋,是义勇,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之跳荡!
然而,不是慰解,这是欺骗。[98]
这个士兵的亡魂祷告神灵“以权威的臂膊开创死亡中之死亡;不要减轻死亡的痛苦,宁以痛苦加重死亡!”“死亡中之死亡”即是身体之肉体属性和象征属性的双重死亡,当死亡之神圣价值不被认可,死亡就不再是不朽的,它既是肉身的消陨,又是神圣性的消散。正是这双重的死亡使作为亡魂的“我”慨叹:“这是无聊的,为战争而死,是多末的蠢笨,痴呆!”杀敌,被杀,只是“一套空洞而无内容的把戏”。对“死亡中之死亡”的祷告,亦即揭示了“神圣的死”并不能涵盖战争的全部意义,战死的痛苦、愤恨与不甘显然无法用死亡的神圣价值来消解,但是也不能因此认为这是在表达一种反战的意愿,因为“我”并没有指斥战争即是虚无,恰恰相反,“我”认为战争仍然是“人类最伟大的玩具”。虽然“我诅咒战争之野心家,我痛恨战争之策划者”,但并不“以战争为痛苦之事而必须逃避”。坚强,义勇,“凡是足以面当战争而无恐者我也齐全俱备”,“我亦以友战争为可喜”,愿“以战争答报战争”。既然“我”以自己全部的坚强和义勇来拥抱战争,那么所谓“欺骗”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以民族国家的神圣之名骗取个人的生命牺牲吗?但死亡原本不就是战争赐予的鸩酒,是无法拒绝也无从后悔的吗?“杀敌而后被杀,即使是空洞而无内容的把戏,这正是恨散冤消,死也愿意。”真正令“我”不甘心的其实是,战争并非以我所愿的方式进行:“战争所临于我者是凶狂的巨炮,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战争所临于我者是暴烈的飞机,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战争所临于我者是残酷的达姆达姆弹,横行无阻的坦克,威猛莫敌的火焰机与毒瓦斯,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使得“我还未对敌人张目正视,而敌人已经扑杀了我!”由此可见,战争的“欺骗”在于它允诺了伟大的战斗,却以强大的机械力量否定了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部力量,人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是如此渺小又如此孱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荒谬的,它所赐予的死亡也是无聊而痛苦的。

丘东平像
战争必须是砥砺战士的磨刀石,才值得去热烈拥抱;死亡必须见证人的强大意志所具有的超越力量,才终能意义圆满。丘东平对战争以及死亡的理解主要是通过林青史这样的青年军官来表现的。普通士兵们虽然也英勇、无惧死亡,但在丘东平笔下,他们总是被描写为“死的躯体”或是“尸体的行列”,姿态蠢笨,行为疯狂。总之,他们是听从了本能的驱使而沉迷于战斗,死亡的每一次逼近带给他们的,是平时无从领略的极端体验,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与刺激。林青史们则不同,身为年轻一代的职业军官,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更高的责任,不仅要为手下的士兵负责,更要为国家担当,因此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与冷静,决不能像普通士兵那样沉迷于战斗。简单地说,他们必须时刻恪守职业军事伦理。
亨廷顿认为职业军事伦理实际上是“持续客观地履行专业职能所产生的一种持续存在的职业世界观”,它所“包含的价值、态度与观点,既内在于对专业军事职能的履行,又能从那种职能的性质中推导出来”。[99]具体来说,“军事伦理强调人性的永恒、非理性、脆弱与邪恶。它强调社会高于个人以及秩序、等级和职能分工的重要性。它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与价值。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并认识到民族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它坚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军事是政治家的仆人,文官控制对于军事职业化至关重要。它称颂服从是军人的最高美德”[100]。在林青史、丘俊、高峰等青年军官身上,的确可以看到上述军事伦理意识的萌芽。他们是人性的悲观论者,所以能够理解和包容手下士兵的过错,但悲悯的姿态也决定了他们无法真正与士兵们结为一体,而只能在清醒中和他们保持距离。他们视忠诚和服从为最高美德,忠诚于国家,认定自己的职责就是为国而战,高峰就这么说过:“什么时候我们战死了,我们个人的任务也尽了。”[101]服从也是基于忠诚,即忠诚于军事理想,相信军队组织那种基于上下服从的层级结构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军队的职能,服务于国家。职业军官的服从,不是听命于上级个人,而是服从自己的信念,同时捍卫作为军人的职业精神。
林青史最终选择回到营部接受处罚,而且并不以所取得的战斗功绩来为自己申辩,这是军人职业精神的完美体现。众所周知,军事职业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劳动分工的加速发展和社会职能的专业化,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构的建立和完善,都是军事职业化的必要前提。因此,作为职业军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恪守职业军事伦理,就是在表达个人对于整个现代性价值体系及伦理原则的信奉。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林青史是以自己的生命为祭品,跃入了铸造现代中国的烈焰熊熊的洪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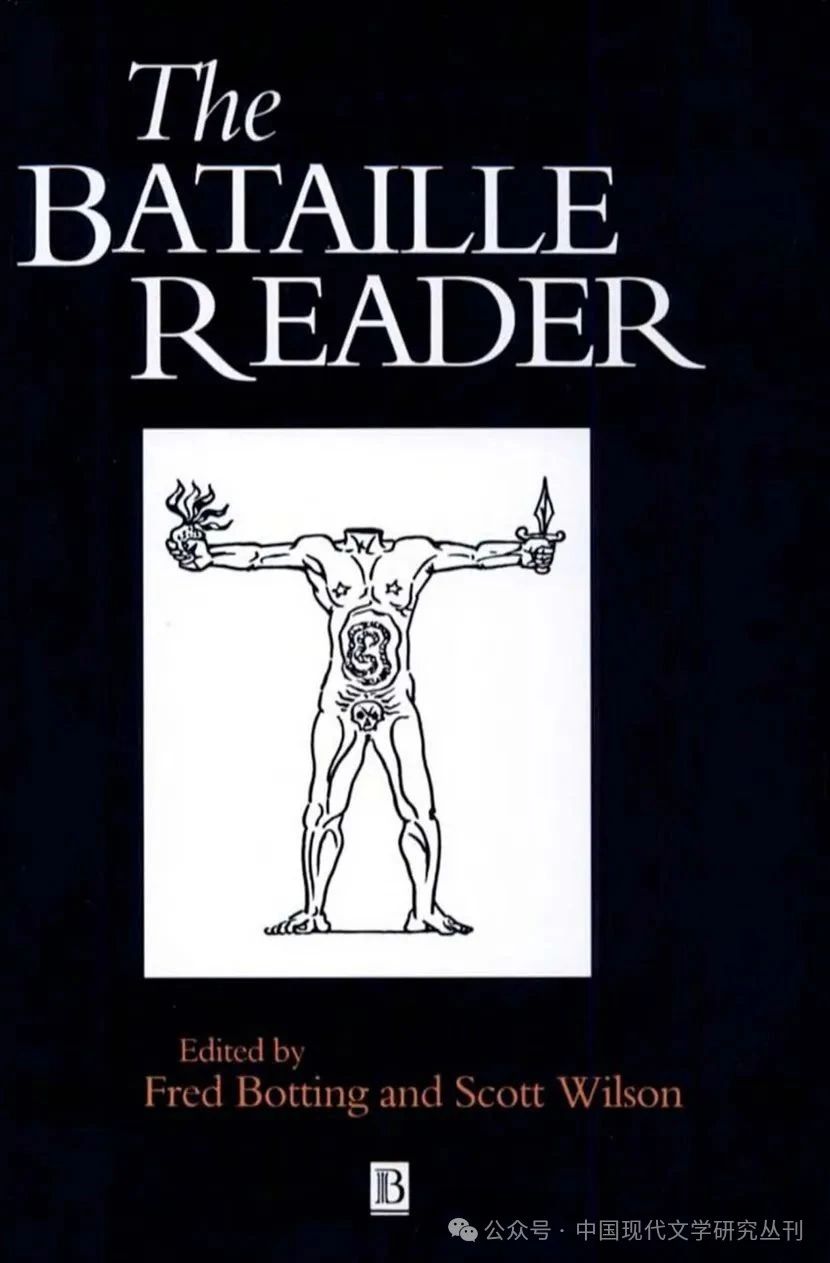
《乔治·巴塔耶读本》(Blackwell,1997)书影
应该怎么看林青史的这种自我献祭?乔治·巴塔耶认为,“在词源学意义上,献祭无非就是制造神圣之物”[102]。献祭给神,就犹如投炭于火炉,“火炉通常有一种不容否认的实际用处,炭即从属于这一实际用处,而在献祭中,祭品则脱离了一切实际用处”[103]。林青史的选择犹如自杀,如果这是献祭给铸造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那么个人的生命真就没有别的价值了吗?他分明自认为是“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而他所要成全的,似乎也并不只是一个绝对服从的职业军官的人格。可以说,丘东平是在林青史身上寄托了自己对于现代中国的一种理想化的个人主体的极高期许,职业军官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美德——严谨、自律、忠诚、勇毅等等,只是这种理想人格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丘东平原本就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对创作以及自我人格都有极高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以及“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104],这显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他对自我完成的要求更是趋于极端:
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因此我时时陷在绝望中……我几乎刻刻在准备着自杀。[105]
他的强烈的死亡意识,以及将死亡与主体的自我完成联系起来的思考方式,让人联想到黑格尔。
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死亡被认为本质上是自愿的,唯有通过自愿的死亡,人才能摆脱任何给定的生存条件的制约。[106]换言之,正是在直面死亡的斗争与工作中,人才真正成为主体,脱离了动物性,并被抛入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中。因此,成为主体即意味着要坚持死亡的工作,不惧死亡,也不躲避自身的毁灭,而是接受死亡并与之共存。[107]黑格尔还强调,正是“死亡在战争中的存在使战争成为创造历史的动力”。战争是自我的实际的牺牲,个人要面临死亡的危险;在战争中,代表了国家的普遍意志的罪行是被允许的,每个人把自己变成一种绝对的权力,视自己为绝对自由的、自为的,并作为普遍的否定性与他人真实对抗。科耶夫因此概括道:“事实上正是蓄意杀人的战争确保了历史的自由和人的自由的历史性。只有积极地与国家生命相连,人才是历史的;在甘冒生命危险的纯粹政治性的战争中,这种生命相连达到了顶点。也就是,一个人只有成为战士,至少是潜在的战士,他才真正是历史的,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人。”[108]
丘东平对死亡以及战争的理解与黑格尔所论颇多相通处。时刻准备自杀,即是迫使自己始终有意识地面对自身的死亡,在直面死亡的斗争中实现理想的自我,成为自己所期许的主体。渴望并拥抱战争,是因为战争能够有力地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使个人在历史的运动中实现作为“人”的真正存在。但从林青史以及《申诉》中的战死者等有着鲜明的个人精神印记的人物形象看,丘东平所渴望成为的那个主体,似乎又不完全等同于国民主体,也不能彻底消融于其中。他仰慕的仍然是尼采的强者,这样的强者如尼采所说,“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中有一种精粹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不屑于像它粗俗的兄弟那样,把自己献给乌泱泱一片的大众,变成他们崇拜的对象,而是习惯于悄悄地穿越这个世界,走出这个世界”[109]。在林青史一类的人物以及丘东平、曹白、阿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精粹的英雄主义”的影子,他们坚定勇毅地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把自己淬炼为一把锋利的剑,并敢于承受人所不能忍的诟谇、委屈与痛楚,不惮与身内身外的一切黑暗搏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坚忍的战斗决非为了赢得大众的膜拜或是“神圣”的桂冠,而只是他们穿越这个世界的方式,以此见证自我的完成,然后通过死亡与消隐悄悄走出这个世界。这份冷静、清醒与洒脱所展现的正是一个有着清洁的精神的真正强者的风采。
结 语
聂绀弩曾当面夸奖《第七连》写得好,丘东平却说:“写战争的东西是很容易的,只要没有砰砰碰碰,辟辟拍拍等字样就好了。”[110]话虽说得谦虚,内中却大有深意。写战争不能只描画战场上紧张刺激、令人热血偾张的战斗场景,而要揭示那些被战争的强光所照亮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性内涵,这才是战争文学的目标和任务所在。
丘东平和阿垅基于真实的战地经验,生动地描画了抗战前线壮烈的战斗场面,也颂扬了国军下层官兵奋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些都是当时很多抗战文艺作品共同表现的主题。他们还揭露了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装备落后、补给匮缺、指挥体系混乱、士兵训练不足等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等局部战役的失败即祸因于此。曹白的作品关注的是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的凄惨遭遇,他们的天真、愚顽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都获得了朴素而真切的表现。曹白还忧愤不平地揭发了难民收容所内外都存在的一些令人心寒的现象,悭吝、冷漠、自私、贪婪、怠惰……这些心灵的毒素在侵蚀民族的肌体,直接危害到抗战大业。不管写的是前线还是后方,丘东平、阿垅和曹白都自觉地把手中之笔探向更广阔的社会场域,聚焦那些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在战争这面放大镜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形态构造和病理机制。
在对社会展开针砭腠理的批判的同时,他们还刻画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人物形象,如丘东平、阿垅笔下有着英雄主义气概的青年军官,曹白笔下杨可中那样的外表阴冷内心却燃烧着巨大热情的左翼青年,都是在抗战的洪流中涌现出来的有着新的精神特质的主体形象。与其作品中的人物相比,丘东平、曹白和阿垅也许是更值得敬佩的,他们都是意志坚定的战士,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文学之于他们,是战斗的武器,也是自我创造的旅程。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践行的方式,以及在作品内外表现出来的写作伦理意识,都与当时的很多作家有所不同。或许可以说,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更饱满的新的主体形象。
战争造成了破坏和毁灭,也带来了创造与新生。抗战文艺记录了现代中国所经历的这个带着血污的艰难创造的过程,丘东平、曹白、阿垅代表的早期七月派的战争文学,以其独有的敏锐和勇气,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被战争的火焰所照亮的社会和人心的隐蔽角落。在他们作品中,展开的是一个不断延伸的战场,伸向社会、历史和人心的深处,他们所进行的带有英雄主义气概的战斗,不仅指明了民族和个人浴火重生的正确道路,而且也展示了文学探索所能拥有的潜力和深度。
倪伟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043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8期)
注 释
[1]潘汉年:《全面抗战释》,《抵抗》第18号,1937年10月16日。
[2]黎烈文:《伟大的抗战》,《呐喊》创刊号,1937年8月25日。
[3][5][6]沃尔夫冈·J·莫姆森:《德国的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和战争的意义(1914—1918年)》,约翰·霍恩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政府、社会和动员》,卢周来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4、21页。
[4]Nicolas De Warren, German Philosoph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5.
[7]Patrick Watier, “ The War Writing of Georg Simmel,”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8, no. 3 (1991), p. 225.
[8]《站上各自的岗位(创刊献词)》,《呐喊》创刊号,1937年8月25日。亦见韦韬、陈小曼编《茅盾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08页。
[9]茅盾:《还是现实主义》,《战时联合旬刊》第3期,1937年9月21日。
[10]东华:《盟誓》,《抗战(三日刊)》第2号,1937年8月23日。
[11]芦焚:《战儿行》,《烽火》创刊号,1937年9月5日。
[12]转引自苏光文《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3]胡风:《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页。
[14]胡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七月〉代致辞》,《胡风全集》第2卷,第499页。
[15]《启事》,《七月(周刊)》第3期,1937年9月25日。
[16]《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记录》,原载《七月》第7期(1938年1月16日),《胡风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315页。
[17]Richard Holmes, “ Battle: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 Combat,”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ed. Charles Townshe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4.
[18]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78页。
[19]Stéphane Audoin-Rouzeau, “Combat,” in A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 ed. John Horne, Wiley-Blackwell, 2010, p.177.
[20]丘东平:《第七连》,《东平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21][22]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东平选集》,第128、136页。
[23]参见阿垅《真——关于战争文学》,《七月》第6集第3期。
[24]阿垅:《南京血祭》(小说原名《南京》,出版时改为《南京血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5]阿垅:《南京血祭·后记》,《南京血祭》,第216页。
[26]Charles Townshend, “ Introduction: The Shape of Modern War,”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p.3.
[27][29]阿垅:《闸北打了起来》,《第一击》,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38页。
[28]阿垅:《我写〈闸北打了起来〉》,《第一击》,第112页。
[30][31]阿垅:《从攻击到防御》,《第一击》,第78、76页。
[32]阿垅:《从攻击到防御》,《第一击》,第80页。
[33]关于1937年10月淞沪会战的具体战况,可参阅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第9章“中央突破 大场陷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第七连》中所述作战时间和战况与战史记载略有出入。丘俊所在部队参加了罗店反击战,后又调防洛阳桥,据此判断可能是陈诚的十五集团军第十八军下属第十一师或第十四师,这两个师都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械师。但从作品中所描述的战场表现看,这支部队似更像桂军。桂军惨败后,第十四师和第十一师的一部接防了桂军阵地。
[35][36][37]丘东平:《第七连》,《东平选集》,第86、87、91页。
[38]参见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第364~368页。
[39]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东平选集》,第126~127页。
[40]阿垅:《南京血祭》,第91页。淞沪会战结束后,国军在撤退途中屡遭此类匪夷所思的惨痛之事。右翼军总指挥张发奎曾回忆说,部队撤退到嘉善,他在视察阵地时,得知因为保存工事图表的人和掌管掩体钥匙的当地保甲长都已逃走,导致部队无法进入既设工事。左翼军在西撤途中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第98师到达常熟以东既设阵地,也因为保管图纸和钥匙的保长逃跑而无法进入阵地。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第373~376、383~384页。
[41][42]阿垅:《南京血祭》,第160~164、177~179页。
[43]马里内蒂:《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44]彭燕郊:《傲骨原来本赤心——悼念东平》,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45]胡风:《东平著〈第七连〉小引》,《胡风全集》第2卷,第587页。
[46]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47]Raymond Aron,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p.9.
[48]二战军人和平民死亡人数达5000万人,其中平民死亡2400万人,占48%,而一战中平民死亡人数仅有50万人,在死亡总数中占5%。参见刘庭华编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二战期间伤亡人数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平民伤亡人数占比基本上在50%左右。如美国国立二战博物馆官网给出的数据是:战斗伤亡人数4000万人,平民死亡人数4500万人,
https://www.nationalww2museum.org/
students-teachers/student-resources/research-
starters/research-starters-worldwide-deaths-world-war。
[49]据中国官方统计,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为3500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国务院公布抗战数据研究成果 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扬子晚报》2015年7月15日,见culture.people.com.cn/n/2015/0715/c172318-27307203.html。另据卞修跃研究,抗战期间含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官兵、国民党军官兵及应当视同中国抗日官兵的兵役壮丁等在内的中国抗战军人伤亡总计达1140余万人,占中国抗战全部直接伤亡人口的27.61%,劳工伤亡达460多万人,占11.25%,此外中国大陆境内平民伤亡近2400万人,占伤亡总数约57%。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444页。
[50]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1937—1945)》,第310、314页。上海租界内死亡人数系公共租界工部局1937年底的统计数及世界红十字会在四郊掩埋之尸体数两者相加之和,各县数据依据的是1938年12月伪江苏省二科所编制的《江苏省各县灾况调查统计图》,数字可能偏小。另有人估算“八一三”战争期间,上海平民死亡10万—15万人。见张铨、庄志龄、陈正卿《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51]《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一辑,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年版,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92页。
[52]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第302~303页。
[53]曹白:《〈呼吸〉后记》,《呼吸》,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54][56]曹白:《烽烟杂记》,《呼吸》,第37、37~38页。
[55]聂绀弩:《怀曹白——作为〈呼吸〉的读后感》,《聂绀弩全集》第4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57]曹白:《“活魂灵”的夺取》,《呼吸》,第20~27页。
[58]曹白:《上海通信(一)》,《呼吸》,第28~29页。
[59]曹白:《上海通信(二)》,《呼吸》,第31页。
[60]曹白:《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呼吸》,第6页。
[61]曹白:《上海通信(四)》,《呼吸》,第42页。曾在金城难民收容所工作的胡静在回忆文章中说,金城大戏院老板不久把房子要回去了,收容所只好结束工作,归并到其他收容所。所以收容所在金城大戏院开办“时间只有九、十两个月”。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481页。
[62]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简称“苏浙别动队”)。它是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作组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浦东一带牵制阻击日军。别动队下辖5个支队共20个大队,虽然其中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由共产党组建和领导,但其骨干主要是青帮的帮会分子。参见《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517页。
[63]曹白:《杨可中》,《呼吸》,第49页。
[64][65][66][67]胡风:《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用〈杨可中〉(载〈七月〉第八期)作例子》,《胡风全集》第2卷,第517~518、519、522、520页。
[68]参见《焦明谈抗日初期的难民工作》,《革命史资料(总第九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11页。焦明是曹白当时使用的化名。亦可参见刘平若《我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一年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2003年第2期(总第107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2003年,第21~23页。曹白本名为刘萍若,刘平若亦是其常用名。
[69]《天气凉了!难民替战士缝寒衣》,《救亡日报》1937年9月24日。
[70]《难民教育在收容所 课外游戏——“捉汉奸”》,《救亡日报》1937年9月25日。
[71]《难民慰劳战士》,《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1日。
[72]参见赵朴初《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第472~476页。
[73]曹白:《从黑暗的海里来》,《呼吸》,第65~66页。
[74]曹白:《烽烟杂记》,《呼吸》,第40页。
[75]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6页。
[76]曹白:《上海通信(三)》,《呼吸》,第33页。
[77]“达姆达姆”即达姆弹,因由印度Dum-Dum兵工厂生产而得名。这是一种半金属包裹子弹,弹头铅芯裸露。子弹在射入人体后,受到挤压的铅芯会将铜披甲撑破,产生翻滚、扭曲,从而对人体组织产生更大的破坏。1899年《海牙公约》明确禁止使用达姆弹。
[78]曹白:《上海通信(三)》,《呼吸》,第34页。
[79]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
[80]曹白:《“活魂灵”的夺取》,《呼吸》,第24页。
[81]曹白:《在死神的黑影下面》,《呼吸》,第9页。
[82][83]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pp. 63, 81.
[84]阿垅:《南京血祭》,第216、218页。
[85]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0页。
[86]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第62~63页。舒允中对卢瑟福观点的概括与原文略有出入。在卢瑟福看来,那种认为现实主义对战争和战场的真实反映必然会削弱英雄气概的观点,其实是一半为真,一半为假,因此虽然看似有理,但实际上也具有误导性。参见Andrew Rutherford, The Literature of War: Studies in Heroic Virtue, Second (revised)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163。
[87]Andrew Rutherford, The Literature of War: Studies in Heroic Virtue, p.164.
[88][89][90][91]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东平选集》,第130、128、139、131页。
[92]丘东平:《滦河上的桥梁》,《文艺》1933年第1卷第2期。
[93]胡风:《忆东平》,《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94]弗洛伊德:《为什么有战争?》,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 12 文明及其缺憾》,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95]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 12 文明及其缺憾》,第127页。
[96]丘东平:《神圣的死》,《光明》“战时号外”第4号,1937年9月25日。
[97]“尸体的社会美德”是巴雷斯的小说《被连根拔起的人》(Les Déracinés)第18章的标题。转引自Philip Ouston, The Imagination of Maurice Barré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177。
[98]丘东平:《申诉》,《现代》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
[99][100]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61, 79.
[101]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东平选集》,第136页。
[102]Georges Bataille, “ 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 in The Bataille Reader, ed. 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170.
[103]Georges Bataille, “Sacrifice, the Festival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Sacred World,” in The Bataille Reader, p.213.
[104][105]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77、178页。
[106]科耶夫:《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概念》,《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63页。
[107]Achille Mbembe, Necro-politics, trans. Steven Corcor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68-69.
[108]科耶夫:《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概念》,《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第667页。参阅此文英译本“The Idea of Death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Interpretation, Volume 3 Issues 2 & 3 (winter 1973), pp.114-156;以及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6)with Commentary, by Leo Rauch,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71。
[109]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卷),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245页。此处译文据英译本略有调整,参见Friedrich Nietzsche, Human, All Too Human: A Book for Free Spirit,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ection 291, p.134。
[110]聂绀弩:《东平琐记》,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第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