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兆阳
内容提要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资深并且有着多方面作为的文学家。学界对作为文艺理论家、小说家和编辑家的秦兆阳已有诸多有价值的研究,但对他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厚关联关注很少。检视当代报告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秦兆阳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研究者,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编务的特殊条件,切实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在特殊时期的发展。在新时期,秦兆阳还提议将报告文学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等主流文体一样,列入中国作协全国文学奖的评奖系列,为提升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制度性安排作了铺垫。在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秦兆阳是一个具有历史线索性意义的人物。他集创、编、研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复合性,成就了其对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
关 键 词
秦兆阳 当代 报告文学
秦兆阳是一位资深的文学家。1916年出生的秦兆阳很早就投身于解放区的新闻和文艺工作,一生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作品,出版过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但大时代的运演对个人命运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制,在秦兆阳这里就是性格亦即命运。“从很小的时候起,故乡的父老们就给我起了个‘板大先生’的绰号。板者,古怪也,遇事爱咬死理和不通常理也。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旧本性难改。”[1]“板大先生”的“封号”与“何直”的自命,彰显了秦兆阳的性格逻辑,也预示了他的人生遭际。秦兆阳以“何直”之名发表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因为某种“不合时宜”而深累自己,直至1979年平反。我们“熟悉”秦兆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写作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影响很大的文论。
秦兆阳是小说家、编辑家和文艺理论家。秦兆阳作为《人民文学》曾经的主事者和《当代》十多年的主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见的。梳理当代报告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沉入时间之海的史料中,十分清晰地写有“秦兆阳”的名字:秦兆阳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研究者;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编务的特殊条件,切实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在特殊时期的发展。此外,他还提议将报告文学列入中国作协全国文学奖的评奖系列,为提升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制度性安排作了铺垫。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秦兆阳是一位具有线索性意义的人物。研究秦兆阳与当代报告文学史关联的课题,不仅可以有效地“活化”报告文学的历史,而且也可以真实地凸显他曾经被遮蔽的报告文学史意义。
一
在当代文学史上,秦兆阳不是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家,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却是一位重要的作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事件,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新题材。其时的热点题材,一是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类反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事件,另一类是书写建设成就和新人物等。秦兆阳所写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新面貌和新人物。“一九五三、五四年,我得到了回到战争年代老根据地去生活的机会,看到了经过艰苦斗争和重大牺牲以后的农村欣欣向荣的和平生活景象,于是从心里‘流’出了十几篇《农村散记》(这是五十年代出书时用过的书名,现在大部分选进了本书的第三辑)。”[2]秦兆阳这里所说的《农村散记》,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10月发行,其中多数是小说,属于报告文学的有《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2月出版的由中国作家协会编的《散文特写选》(1953.9—1955.12)就收录有这三篇作品。秦兆阳的《王永淮》、柳青的《王家斌》、沙汀的《卢家秀》和田流的《王运升》等作品,都是书写当时农村先进模范人物的名篇。尤其是秦兆阳的作品在对人物作非虚构而又具有艺术性的呈现方面更显示出特色。“作者始终把人物(个性化的形象、动作、语言、神情等)放在叙写的中心,摆脱了以往作品用普泛化的事件带动人物的旧有模式,所以笔下人物形象相对来说比较丰满,从而把报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位。”[3]

秦兆阳:《农村散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秦兆阳20世纪50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解放区书写的延续。秦兆阳1938年奔赴延安,此后在解放区学习、工作、创作。“1943年秋天,我为了不愿意过无所事事的日子,不愿意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处于旁观的地位,特别是由于听了火线剧社许多同志讲了冀中平原上残酷斗争的一些故事而深深激动,就主动要求到斗争最残酷的冀中十分区去工作……从此我才比较多地了解了人民,了解了战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自己,因而决定了我以后几十年文学工作的道路。”[4]“文学事业,系住你对于生活,对于人民,对于创造,对于艺术的感情。我愿意写作,为了表达这种感情。”[5]这里,秦兆阳说明了自己创作的“根据地”,并且给出了情系生活和人民的文学价值取向。1949年10月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的《平原上》,收录秦兆阳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娘》《仇恨》《路》《何花秀》4篇作品,这些作品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反映了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和他们中作为“民族魂”的英雄形象。作品融合了非虚构与虚构的叙事。《娘》有副标题“‘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自述看护伤员的故事”,《仇恨》副标题为“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大扫荡片断记”,由题目和内容可见,这样的“自述”和“断记”,是具有小说因素的写实作品,作品的纪实性显见。将《平原上》所收作品与作者20世纪50年代初所写的《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作整体性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后来的作品是此前创作的有机演进,两个时期作品的叙事基点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由根据地转换为新农村;写作的风格相承,真实,朴实,所写人物形神兼得,颇具文学的感染力。
自然,《王永淮》等作品写作的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其取材、主题、叙事基调等已迥然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关联写作。秦兆阳的写作聚焦新社会新建设,《钢都的老英雄——孟泰》《官厅少年》《到佛子岭去》《王家斌》《在柴达木盆地》《童话的时代》等是其中的代表作。所不同的是,秦兆阳“回到战争年代老根据地去生活”进而写作的这种有意为之的自觉,使其作品的主题表达更有深意。作者依凭切身的体验,以切实之笔,通过真实人物的具体叙事,描绘出“经过艰苦斗争和重大牺牲以后的农村欣欣向荣的和平生活景象”,有力地凸显了“斗争”和“牺牲”的现实价值,也昭示出新中国新建设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报告文学具有更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这种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其题材和主题的价值部分地规定了作品意义的生成基础,但这并不表示报告文学只需要主题正确。“主题正确”只有经由“审美达成”才能实现其最终的价值。因此,经得起历史沉淀检验的报告文学,必然是“报告”与“文学”的有机化合。秦兆阳的报告文学正是这样,虽然时过境迁七十多年,但我们阅读《老羊工》这样的作品,依然能感受到文学滋味流溢其间。他的作品之所以会保有文学的魅力,是因为作者身心融入了写作的对象,从实际生活中提取人物,又将人物置于生活本身的存在中加以性格化的呈现。作品叙写老羊工,突出其“老”。“老”关联着人物的经历、新旧社会的遭际、放羊独特的经验和在新时代所获得的尊重等。《王永淮》中的人物,“说起他来,一句话:是个好人”。作品突出这位战争年代在山里打鬼子战蒋匪十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县里当了科长”的主人公,主动要求重回故地建设山区,“年年月月,爬山过岭,为老百姓办事”。人物之“好”,“好”在能不忘革命者的本色,甘愿挑起建设者的责任。而对在荒山中创造出“一大片绿得耀眼的、葱茏茂密的树林”的姚良成,则主要通过“咱有手有心,就能”“就凭这两只老树根手,一大片荒山又变了色儿啦”等个性化语言,突出人物的业绩和精神特质。对这些作品,秦兆阳后来有自评:“既近于散文,又类似小说;或有头无尾,或似无结构;意在试探着与当时颇为流行的写法略有不同。”[6]这样的评价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王永淮》等作品既有别于当时同类的报告文学,叙写并不依仗新闻性,而更倚重所写人物独有特质的故事及其精神,对抒情有所节制,更少虚浮夸饰之语,同时又不复制自己作品,每一篇都能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设置各自相宜的结构和写法。“你打听王永淮吗?你算打听对了,我可跟他忒熟。”开篇扣题而来,通过结构性人物“我”的见闻,将“好人”王永淮作了多维度的叙写。“老羊工冯常福把羊群赶到背阴的地方歇着,自己靠着岩石坐着。夏天正午的阳光在满山满谷里闪耀着,照得他的老花眼眯成了两道缝儿。”语言简约而有味,将人物及其环境融合在一起呈现,既画出了人物形象的模样,又点出其爱惜公物的用心,在有限的篇幅中达成对人物富有表现力、感染力的真实再现,可谓短篇的精粹。秦兆阳报告文学的写作经验,对他成为卓有建树的报告文学编辑和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二
编辑是秦兆阳多重人生角色中最具贯穿性和显示度的一种。我们阅读《编辑大家秦兆阳》[7]中同时代人、同事或是稍后一辈写的回忆文章,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编辑大家”秦兆阳之“大”。他在冀中等游击区解放区担任过《黎明报》《前线报》《歌与剧》《华北文艺》的编辑或领导。20世纪50年代担任《文艺报》的执行编委、《人民文学》的副主编,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1994年担任《当代》主编。文学编辑,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有时还会直接生成具有某种文学史意义的存在。有学者认为,“文学编辑可成为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编辑是与作家、作品、世界、读者一样重要的要素,有时甚至比其他四要素更为重要,更具有丰富饱满的价值。”“文学编辑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文学出版事业某种意义上可理解成文学编辑的精神史与生命史。”[8]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人民文学》和新时期的《当代》为例,论说编辑秦兆阳对当代报告文学发展的特殊作为和重要影响。

1950年代初的秦兆阳
秦兆阳有两段时间在《人民文学》任职。一是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后担任编辑部小说组组长。1955年初《文艺报》因事进行改组,他被调任常务编委。二是“1955年冬天我就离开了《文艺报》,到《人民文学》担任了副主编的职务”[9]。第二段时间很短。“1956年冬,我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讨论。为了准备回答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我请假学习哲学,于1957年1月脱离了编辑工作。”[10]正是在有限的主持《人民文学》编务的期间(“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号的杂志上刊登了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到了批评,情绪低落,想撂挑子不干了”[11]),秦兆阳以其勇气和担当、卓识和创造,进行了一次具有报告文学史意义的文体实验,开辟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另一种可能的路径,提示了报告文学文体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
文体虽然是一种指向语言表达“功能分区”的形式,但实际上它也负载着意识形态的意义,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更是这样。夏衍《包身工》、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等现代报告文学名篇,取材于现实尖锐的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鲜明地表达了直击社会黑暗的批判主题,凝结成报告文学的重要文体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在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报告文学还要不要、能不能发挥它揭示社会问题的价值,怎样发挥它的价值,就成为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无疑,新中国亿万人民翻身得解放,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社会显示出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对于这种具有巨大历史性意义的社会进步,文学需要给予热情的赞美歌颂。这既是现实的规定,同时也是作家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
秦兆阳主持的《人民文学》所进行的短暂的报告文学文体实验,主要是在时代放歌之外,探索非虚构创作介入现实的可能性。从当时的结果来看,这种探索在时间节点上的选择并不适宜,因为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其时特定的国内外情势中,需要更多地凝聚奋发图强的合力和精神。但也正因为这样,秦兆阳编辑团队的工作具有了更显见的“实验”意义。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人民文学》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爬在旗杆上的人》《本报内部消息》《办公厅主任》《马端的堕落》《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作品。这些作品被指称为“特写”,它得之于苏联的文体命名。苏联的特写有两种类型,即“写实的特写”和“研究性的特写”。“有一种特写,它的任务是着重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概括一定的社会现象,战斗地帮助人民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特写“叫做深思的特写,同时也叫做研究性特写”。“它允许作家有更多的可能去想象、虚构,在形式上是特写,在内容上基本上与小说差不多。”这种特写的真实性并不体现为“记录真人真事”,“那里,问题是生活的真实”。以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揭示,“直接干预生活”,这是这类特写的特质和旨归。[12]很显然,以上作品中的“办公厅主任”“马端”“农庄主席”等,都不是生活中实有其人的人物,文本中的故事也不是实有其事的原真再现,但作品通过人物和故事所反映出的问题却是重要的真实的现实存在。作者以这样的形式将问题呈现给读者,用意在于引起对问题的关注、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以有效地解决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先进和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十分就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13]这一段“编者的话”,明确地反映了《人民文学》倡导“干预生活”特写的方式和意图。秦兆阳主导的《人民文学》之所以推出这些介入现实问题存在,一是受到当时苏联特写理论的直接影响,同期稍早苏联著名的特写作家奥维奇金访问中国,其长篇文章《谈特写》刊发在1955年《文艺报》第7号、第8号合刊,其中“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得到了中国文学界的快速响应。二是与1956年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生态有关,其时,党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针,由此激发出文艺界探索文艺表现题材主题以及形式等的兴趣和热情。三是由秦兆阳个人因素所决定。“秦兆阳并非文字工匠,而是思考型编辑。”[14]他的“思考”可直接见之于由其拟定的18条《〈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其中有第一条“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在发表作品上应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第四条“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15]“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特写的“关键词”。由于时代氛围的陡转,秦兆阳主导的《人民文学》“干预生活”的特写很快就宣告停歇,并且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人民文学》特写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种“结局”,是其“不合时宜”的时代命定,它并不表示这样的文体探索毫无价值。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伴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时代大潮的兴起,报告文学一方面报告时代发生的巨变,发挥着作为时代文体快捷反映现实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尤其是“问题报告文学”直接呼应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作品揭露的问题涉及基层治理、经济、教育、人才、环境、移民扶贫等广泛领域。严峻问题的呈现,为改革开放的推进提供了现实依据,其对人的精神困境的透视,对现实矛盾的直面,远得“五四”启蒙文学的精神,而又直接呼应了20世纪50年代“干预生活”特写的要义。即使像徐迟《哥德巴赫猜想》、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这样讴歌科学家精神、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作品,其内涵的批判力度也力透纸背。
三
不同于与《人民文学》的短暂相遇,《当代》是秦兆阳文学生命中最重要的驿站。他不仅参与了刊物1979年的创办,而且长期担任主编直到1994年去世。秦兆阳见证并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建设。“在他这位众望所归的主编的率领下,《当代》杂志形成了‘严肃、深刻、尖锐、厚重’的风格,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16]《当代》不仅发表多种体裁的优秀作品,更成为其时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高地。“由于《当代》在长时间内不断大量地组织发表报告文学作品,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佳作,形成了社会公认的我们刊物的一大特色。在那个时期,每一次全国性报告文学评奖,《当代》获奖作品总是最多。有人称《当代》为‘报告文学的重镇’。”[17]这里所说的“获奖作品总是最多”可能并不确切,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代》为获奖作品最多的刊物之一。截至1994年,刊发于《当代》、获得全国性报告文学奖的重要作品有《热流》《励精图治》《命运》《世界大串联》《强国梦》《中国姑娘》《播鲁迅精神之火》《继母》《希望在燃烧》《万家忧乐》《黄土地,黑土地》《飞向太空港》《希望工程》等。这些作品或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报告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和呈现出的新面貌,或扫描独具时代感的社会现象,或讴歌中国脊梁中国创造中国精神,或直面问题进行反思性的叙写,它们实录了一个时代富有特质的种种存在。这些作品既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同时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篇章。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秦兆阳与作家曲波、张洁、孟伟哉等
秦兆阳时期的《当代》对于报告文学的推动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总体设计中将报告文学明确为特色办刊的优先文体。在秦兆阳看来,《当代》之谓“当代”,充分关注社会的现实存在,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性”,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的“当代性”,在主编秦兆阳这里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要加强现实性。我们名为《当代》,作品就要有当代水平。《命运》就是当代水平。我也寄望于张锲的报告文学,就是要记录下时代的精神状态。光靠小说不行,要报告文学。”[18]这是秦兆阳在1980年8月27日下午《当代》编辑组开会时,对《当代》编辑工作谈话要点之一。其中的关键词有三个:“现实性”、“当代水平”和“报告文学”。这里所说的《当代》“现实性”,很明确的就是要发表能体现现实生活特质和主题,凸显“时代的精神状态”的优秀作品。秦兆阳以为《当代》的水平就存在于它的“现实性”之中。而要实现《当代》高水平的办刊目标,秦兆阳有自己的路径设计。“光靠小说不行,要报告文学。”对于这两种文体秦兆阳有自己的主张。小说作为主流文体,各家刊物大多重视,事实上在秦兆阳主编期间,《当代》也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小说,但仅有小说不只是会造成刊物的同类化,而且在秦兆阳看来也无法达成他所期望的《当代》水平。这从他所列举的作品可以知道,秦兆阳所说到的《命运》发表在《当代》1979年第2期,记录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张锲的报告文学”是指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4期的《热流》,这篇作品的副标题为“河南漫行记”,报告的是中原大地改革初期的各种“热流”。为什么在主编《当代》期间秦兆阳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这不仅因为报告文学是他人生行旅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未完成的事业”,而且也关乎他的文学价值观和作为资深编辑家的职责使命。“报告文学要坚持下去。社会、人民关心的我们要满足,以这个原则去选题。”[19]由这一段简要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秦兆阳力推报告文学的基本逻辑,其逻辑前提是“满足”“社会、人民的关心”,这种“关心”实际就是读者的需要,将其作为办刊的“选题原则”;其逻辑的推衍是在“一个变革时代”,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以其特殊的方式参与介入政治性很强的重大时代生活的议题,这种议题具体到当时的时代语境就是指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而对这样的时代议题的表达正是报告文学文体的特长,也是读者“关心”和期待看到的时代书写。“我们这个时代,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讲,要大力提倡报告文学。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许多新的事物在涌现,许多矛盾在起作用,小说、诗歌不可能那么快地来反映这些生活内容,必须同时提倡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翼,使得文学创作领域更加宽广,对现实的反映更快,更充分,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20]秦兆阳是从时代的大局、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长等来确定《当代》总体性的编辑原则的。此外,力推报告文学也是秦兆阳特色化、差异化办刊的一种具体的举措。“对报告文学的取舍标准可以宽一点。有的文艺性强些,有的政论性强些,都可以。《当代》如能在报告文学方面闯出一条路,也会很有特点。”[21]这是秦兆阳1980年2月20日在召集编辑组开会讨论用稿安排时对同事提出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当代》坚持的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正是在这里,《当代》闯出了一条路,成为其时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具有醒目显示度的重镇。
秦兆阳是一个务实的主编,他不仅提出办刊的重要思想,拟定编辑的基本原则,而且也善于将思想和原则落到实处。“报告文学不好抓,要注重事实的准确。平时看报,要随时注意有哪个问题可以抓。《励精图治》就是这样抓出来的。要经常有三四个人在外面跑,抓稿子。以后不要临时凑。”[22]秦兆阳知道有价值的报告文学不会自己找上门来,因此他要求编辑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发现好的题材,寻找具有写作能力的作家。他自己以身作则,以例示范,张锲《热流》的题材就是秦兆阳不经意间发现的:“这个报告文学的组稿线索是兆阳同志从报纸上发现的。他读到一条关于中共河南省委紧抓改革的报道,觉得从一个省的范围来反映当前的改革潮流,这是一个大题目,应该抓住。”编辑部的同事立即落实,“觉得正在北京的安徽作者张锲比较合适,当即跑到张锲住地约他去郑州采写,并给了他一个‘本刊特约记者’的名义,便于他进行采访”[23]。对于一些题材和主题比较好的重点作品,秦兆阳亲自把关操刀修改,使作品达成比较高的完成度。中国女排是中国精神的代表,女排精神成为时代精神标志之一。这是中国女排的创造,同时与《当代》通过报告文学的方式及时传播也深有关系。1981年在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之前,《当代》编辑部基于对女排题材重大价值的敏感,就约请在国家体委工作的鲁光写作。收到鲁光的《中国姑娘》后,秦兆阳亲自审读,认为作品“缺乏从弱到强、从败到胜的顺序发展的章法,并通过这种事实规律来写出中国人的志气,来写出人物特点,以取得逐步高昂的感人力量。全篇结构散漫,枝叶繁多而琐碎,篇幅拉得太长,平均使用笔墨,处处都是重点,反而使得总的脉络不鲜明,变成素材的堆砌,文字也较差”[24]。但秦兆阳又很灵活通达:“考虑到这个题材内容很好,同意发表。他动手从头至尾做了不少的删改,又把‘编者按’作了较大的修改,突出地提出:‘倘若我们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能像这样为了祖国的荣誉、尊严和富强而贡献自己的一切,那么,社会主义祖国腾飞之日还会远吗?’”[25]由这一个案,我们看到了一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是如何炼成的过程,其中凝结着主编秦兆阳的许多心血。《中国姑娘》在1981年第5期的《当代》如期刊出,随即中国女排也“如约”荣获首次世界冠军,一时女排冠军热掀动《中国姑娘》热,汇成强劲的爱国主义热潮。

1980年代,秦兆阳与《当代》同仁在一起
此外,秦兆阳还注意培养优秀的报告文学作者。他的培养既立足严格要求,指出作品的不足不留情面,但又能尊重作者,以诚相待,帮助作者完善作品。程树榛就是一个例证。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程树榛是经由《当代》这一平台走上这一文体的写作之路的。《当代》编辑组的朱盛昌从《工人日报》上看到反映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厂长宫本言改革事迹的报道,“我觉得这是报告文学的好题材,符合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祝词的精神,塑造四化创业者形象。我在电话中向兆阳同志报告了这个想法,他表示同意”[26]。程树榛写出《励精图治》初稿后,秦兆阳仔细审读,他对题目并不满意,建议“将程树榛写宫本言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改题为《闯将》”,“程树榛不同意他的报告文学改题《闯将》,秦同意维持原题《励精图治》”[27]。这里体现了一位资深编辑家对年轻作者的尊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秦兆阳亲自约见作者,面对面地提出作品的修改建议。“秦兆阳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亲自沏了一杯茶放在我的面前,简单地叙了寒暄之后,谈话便切入正题:关于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他一章一节地加以剖析,耐心细致地指出必须修改和补充的地方。看得出他是经过认真思索的。”[28]经过作者认真的修改,《励精图治》刊发在1980年第2期的《当代》,成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获得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由此,程树榛结缘报告文学,成为新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
四
秦兆阳作为文艺理论家,其主要的理论贡献是由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奠定的。这是一篇长篇论文,其论题十分明确:“我想以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来谈一谈教条主义对于我们的束缚。”[29]在秦兆阳看来,其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二是对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三是对于世界观与创作观的教条主义理解”[30]。对此,秦兆阳对这些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问题症结和怎样克服它们的束缚作了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系统论述。可以说,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和作者理论思维的特点,成为文艺理论家秦兆阳的要素,其中的要义和他的报告文学(特写)研究关联相通。
秦兆阳研究报告文学(特写)的文章不多,作系统论述的文字则更少。但其理论贡献是显见的。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同期稍早发表的《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是秦兆阳言谈特写的重要文论。这两篇文章写作的背景是一样的,其基本话题是论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其中的现实主义论,指向文学的整体,强调的是回到生活本身的“广阔”,拒绝教条主义的偏狭。而特写谈,聚焦的则是这一文体的“真实性”。在他关于“现实主义”和“真实性”的具体论述中,真实反映时代、直接介入现实等是核心主题。这些言说直接的思想资源是奥维奇金的《谈特写》。“特写,是文学的一种战斗体裁”,“特写是一种很宽阔的自由的形式”,“有一种特写,它的任务是着重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概括一定的社会现象,战斗地帮助人民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文学应当“直接干预生活”[31]。秦兆阳基本接受了奥维奇金的这些观点,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秦兆阳以“何直”之名写作的《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是国内最早论述特写的论文。他的文章一段时间引发了文学界对这一文体的讨论。[32]讨论中有的是学术性的探讨,也有的是生成于特殊文化生态中的非学术批判。其中学术性探讨的话题在中断了二三十年后,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文体再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从某种角度上说明《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一文所具有的文体理论研究意义。
秦兆阳的《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其题目彰显了有关“真实性”的论题,但又不限于浅表的一般意义上真实性,而是从真实性的系统关联中,揭示真实性种种复杂的存在。检视秦兆阳关于报告文学(特写)的论说文字,其中涉及的话题较多,但最能体现出研究价值的是他的真实论。“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问题我是考虑比较多的。”[33]这是一个他长时间思考的重要课题,起于20世纪50年代达于新时期。在文学理论中,真实性的问题具有不同的指涉和意涵,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种总体性的基本表述,而在特写(报告文学)中,通常认为,非虚构的客观真实性是其文体属性的规定。但这里的客观真实性不只是一种可以意会的形而上的“道”,还是一种需要付诸于具体的创作实践的“术”,具有复杂性。因此,如何理解、把握和达成这样的真实性,文学界一直存有歧见。秦兆阳对特写(报告文学)真实性的理解是开放的,即承认在客观真实之外,可以有虚构的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满足于真人真事真名真姓的一般化的特写。我们不应该反对对于真人真事作适当的有益于真实性的加工。”“我们也应该大力提倡那种用文学的概括手法写成的,并非真名真姓的特写。”[34]这一段表述反映了《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的基本观点。很显然,秦兆阳接受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奥维奇金“两种特写”的观点。秦兆阳认同奥维奇金介绍并解释的苏联“写实特写”和“虚构特写”之说,认为对这两种特写中的真实性应有不同的考量。秦兆阳在20世纪50年代对特写真实性的这种理解,到了80年代也未曾异变,还是“二分法”。“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都是写真人真事的”,“既然是真的名字、真的地点、真的事情,那就不能掺假”;“另外,我们是否还可以提倡这样一种报告文学,它根据一些事实,但它不用真名真姓、真地点,它又不像小说有完整的结构,它又不像散文那样不大注意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而及时反映当前某一种值得关心的情况”。“这种东西似乎也应提倡。如果可以提倡这样一种报告文学,那么报告文学的路就更宽了。”[35]由此可见,秦兆阳对特写(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基本理解是基于不同的情况而持相应的尺度,要点是对真人真事写作中的“真实性”和本于事实而又不拘泥于事实“真实性”应予区别对待。当然,这种认可特写(报告文学)允许虚构的说法,在文学界颇多争议,同时,这也不是秦兆阳原创的观点,因此,并不具有更多的文体理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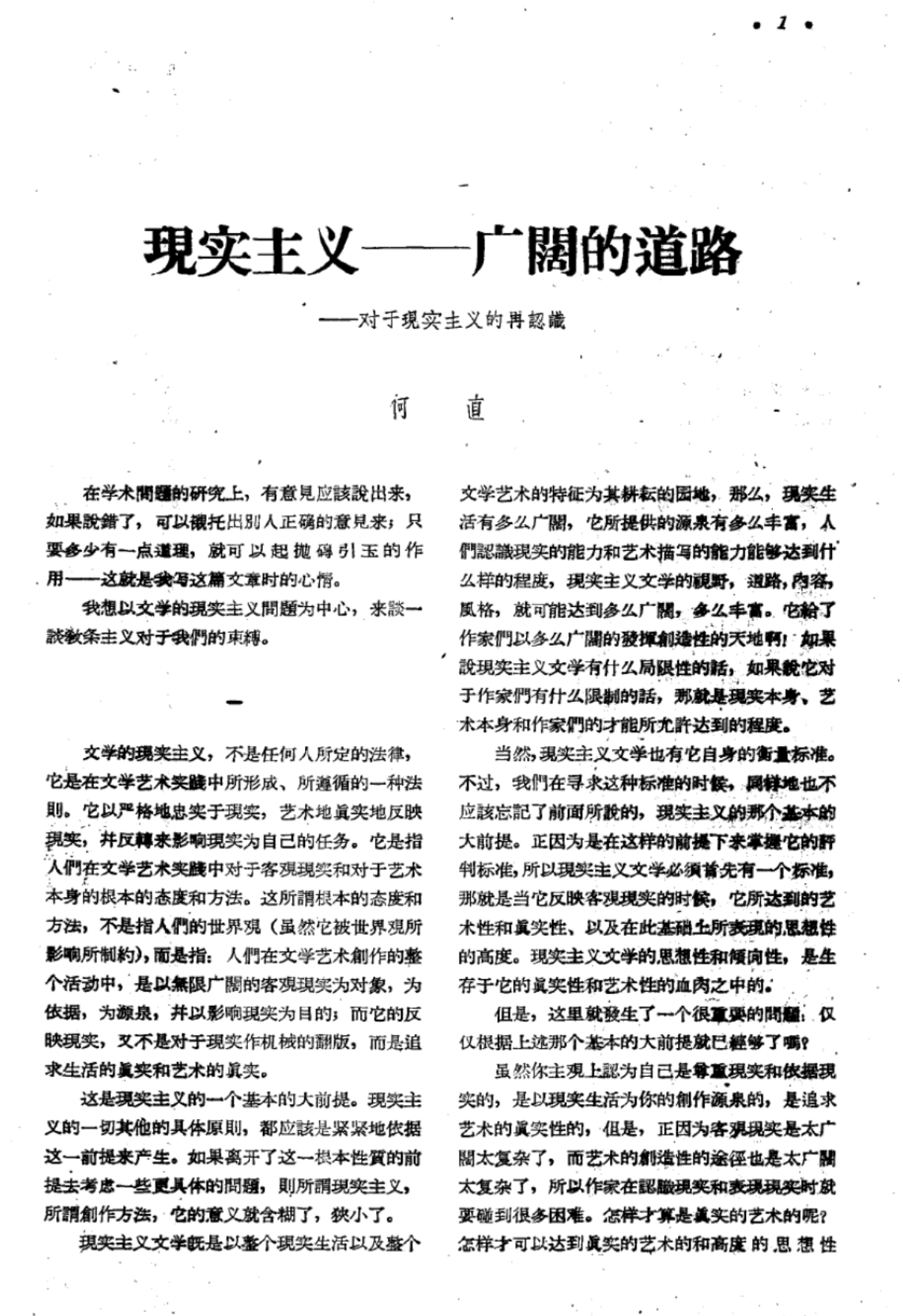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在笔者看来,秦兆阳特写(报告文学)真实论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真人真事写作中“真实性”的具体解析。在这一维度中,秦兆阳是非虚构真实性的维护者。“特写如果是写的真人真事,真名真姓,则它的内容必须是符合于真的情况。”[36]“事情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站不站得住的一个根本的条件。”[37]但秦兆阳没有停留在对真实性作简单认定这一层面,他充分注意到这种真实性内在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作出了相应的提示。“须知写出完完全全的——或者说,写出读者所需要的最大限度的真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了解一件事情的经过,是比较容易的;要了解做事情的人,却比较困难。要了解做了什么,怎样做的,比较容易;要了解怎样的人做的,却比较难。”“读者需要知道事,却更需要知道人。”[38]这里秦兆阳给出了真实性达成的重点难点,这是一种只有获得过真切写作体验的作家或是懂得这一文体写作之道的编辑,才会说出的及物得“体”之言。秦兆阳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他的言说更切实际。秦兆阳深知真实性之于报告文学的意义,强调“达到真实”的“困难”。他的意指并不是要放弃报告文学的真实,而是要让人明白真实来之不易:唯有知难而为,深入采访,由事及人,由表及里,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对象的本真。秦兆阳对于真实性不作概念式的浮泛之论,而是将其置于实践的环节中加以具体的指说。“所谓真实,一般地讲,主要是指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结果如何;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结果如何。”这是基础层次上的真实,要求呈现出的是物理性的事实的真实。“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这涉及内在的核心层次上的真实。在秦兆阳看来,要获得这一层次上的真实最具难度。“一个人的内心,一种精神状态的东西,是不容易说清楚的”,要“挖到心灵深处,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刻画出来,却有一定的困难”[39]。尽管这是获得作品真实性的难点,但却也是它的关键所在,因而是作者最应该用心用力的着力点。以上两个层次的言说,秦兆阳是从写作对象这一端考虑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从写作客体与主体关系共构的角度思考真实性的问题。“报告文学往往是,由作者去访问一个对象。这就发生作者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上是否准且深的问题。主观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的事实是不是能够融为一体?是不是完全符合客观?是不是能够深入到客观事物的肌理中去?”[40]在这里,秦兆阳揭示了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极其重要但往往被人忽视的真实性有效转换的问题,即客观真实的人与事的存在,只有经由作者准确的认知和叙事,才能成为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真实性。“真实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是决定于作者对那个事实了解得如何,另一方面也决定于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他运用文学手法的能力。”[41]秦兆阳这一句结论性的表述,真实地指出了报告文学(特写)真实性达成的要素,从中我们可得许多有益的启示。此外,秦兆阳在研究写实作品真实性问题时,并不只是就真实性论真实性。一般认为,真实性关联着报告文学的“报告”,而在秦兆阳这里真实性也直接影响到“文学”。“报告文学必须真实,达到真实有三难:一是了解事实,二是发掘底蕴,三是深入灵魂。这第三点可以说是难中之难。只有在攻克了这三道难关以后,才有可能达到剖析深刻、形象生动和文笔感人。”[42]“剖析深刻、形象生动和文笔感人”等,是秦兆阳看取报告文学之谓文学的要素,而这些要素获得的前提是作品充分的真实性,尤其是深入人物灵魂所得的精神之真。这样的表述既得之于秦兆阳的经验,也来自他卓然的学识。秦兆阳关于报告文学(特写)真实性具体而系统的论述,帮助我们打开了认识理解这一核心理论问题的视域和思路。这是他为报告文学文体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
五
秦兆阳与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关联,除了体现在其创作、主编刊物和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之外,还有一点也具有文体史的意义,这就是秦兆阳对报告文学进入国家文学评奖机制的建议,直接促成报告文学列入全国文学奖的评奖系列,有效提升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报告文学是一种基于近代新闻事业而衍生出的文体。在新时期之前文体没有定名,作品常常归类于散文或新闻通讯之中。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以它独特的方式记录并介入重大的历史进程,在文坛内外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的主潮之一,由此也获得自身独立的文体地位。1983年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工作的张光年热情洋溢地指出:“我热烈祝贺我们的报告文学近两年来获得丰硕的成果!”“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由附庸蔚为大国。”[43]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确立和创作成就的确认,一方面来自报告文学作家所取得的突出的创作实绩,另一方面也直接受惠于文学评奖机制的激励。我国国家层面上正式的文学评奖始于新时期初年。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举办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4月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在1981年中国作协的评奖安排中,原来只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诗歌,报告文学是临时动议,经研究后补入的。“1981年三项评奖的设置,报告文学是最大的受益者。评奖客观上提升了报告文学的位置,将其纳入主流文学的组成部分。”[44]将报告文学列入评奖系列的动议者正是秦兆阳。当时,秦兆阳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代》主编。张光年在《文坛回春纪事》的有关日记中,清晰地记录了报告文学奖动议、决定、评奖和颁奖的全过程。1981年3月29日日记:“秦兆阳在电话中建议中篇小说评奖与报告文学评奖同时举行,使评奖结果增加昂扬气息,我表示同意,请他在明天评奖会上提出供商讨。”[45]这里记写了秦兆阳的建议和张光年自己的态度。3月31日的内部沟通:“下午3时,应邀参加中篇评奖会,听了吴强、韦君宜同志发言后,我谈了对评奖工作的希望与建议,表示赞成秦兆阳同志提出的与报告文学同时举行或同时公布的意见,请大家考虑。”[46]到4月7日上午召开党组办公会扩大会,“讨论举办报告文学评奖问题。我对此作了说明,提出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同意由《文艺报》《人民文学》两家合办,提出设以冯牧为首的评委会,以阎纲、周明等组成工作组,及早形成一个备选名单,征求各地编辑部意见,希望能在5月中、下旬完成任务,请剑青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47]。党组决定举办报告文学评奖后,随即就启动具体的评奖程序。5月18日上午,“刘剑青迎我去新侨饭店六楼开报告文学评奖会,冯牧主持讨论,定下了三十篇获奖篇目”[48]。刘剑青当时是《人民文学》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主编由张光年兼任。5月25日的日记张光年特地备注了“三项评奖发奖大会”。短篇小说奖的颁奖会议已于3月23日召开,这里“三项评奖发奖”是指中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早餐后去京西宾馆礼堂,9时许开会,冯牧主持会议。宣布开会后,由我致开幕词。”“今天大会开得好,大家都高兴。”[49]笔者没有读到秦兆阳自己有关动议举行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评奖的文字,倒是他《当代》同事朱盛昌1985年1月6日的日记有记录:“开了一天年终总结会。秦兆阳、屠岸、张伯海均参加。”秦兆阳说:“从全国局势看,有我们这么个刊物还是好,有人唱花旦,没有个正旦也不行。《苦恋》事情发生后,张光年睡不着觉,我出个主意,搞报告文学评奖,就好多了,平衡了局面。”[50]这里的记录与张光年日记所记的内容相一致。正因为由于秦兆阳的建议和作协领导的重视,才使报告文学和小说等主流文学样式获得了同样的制度“待遇”。也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使报告文学后来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鲁迅文学奖七大门类评奖的制度安排之中。

秦兆阳晚年
丁晓原
常熟理工学院
21550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注 释
[1]秦兆阳:《秦兆阳小说选·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2]秦兆阳:《秦兆阳小说选·自序》,第1页。
[3]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01页。
[4][5]秦兆阳:《风尘漫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2页。
[6]秦兆阳:《秦兆阳小说选·自序》,第1、3、3页。
[7]秦晴、陈恭怀编:《编辑大家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2013年版。
[8]黄发有:《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意义——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9][10]秦兆阳:《风尘漫记》,第47、47页。
[11]王培元:《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191页。
[12]奥维奇金:《谈特写》,《文艺报》1955年第7号、第8号合刊。
[13]《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
[14]王迅:《执拗的现实主义者与逃不掉的宿命——编辑家秦兆阳精神图谱素描》,《当代作家评论》2020 年第1期。
[15]参见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人民文学》1958年4月号。
[16]王培元:《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91页。
[17]朱盛昌:《秦兆阳编〈当代〉》,《当代》2014年第3期。
[18]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19]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续一)》,《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1期。
[20]秦兆阳语。参见刘剑青、秦兆阳、梅朵《报告文学的现状与展望——〈人民文学〉〈当代〉〈文汇月刊〉编者答本刊记者问》,《文艺报》1982年第2期。
[21]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22][23][24]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25]朱盛昌:《秦兆阳编〈当代〉》,《当代》2014年第3期。
[26][27]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28]程树榛:《化作春泥更护花——怀念秦兆阳同志》,《人民文学》1995年第2期。
[29]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30]秦兆阳口述,秦晴、陈恭怀记录整理:《我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由来》,《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
[31]奥维奇金:《谈特写》,《文艺报》1955年第7号、第8号合刊。
[32]主要的文章有以群《谈直接干预生活的特写》,《文艺月报》1956年第9期;李希凡《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刘白羽《论特写》,《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井岩盾《真实和虚构——关于特写、传记、回忆录等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33][35]秦兆阳语。参见刘剑青、秦兆阳、梅朵《报告文学的现状与展望——〈人民文学〉〈当代〉〈文汇月刊〉编者答本刊记者问》,《文艺报》1982年第2期。
[34]秦兆阳:《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
[36][38]秦兆阳:《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
[37][39]秦兆阳语。参见刘剑青、秦兆阳、梅朵《报告文学的现状与展望——〈人民文学〉〈当代〉〈文汇月刊〉编者答本刊记者问》,《文艺报》1982年第2期。
[40][41]秦兆阳语。参见刘剑青、秦兆阳、梅朵《报告文学的现状与展望——〈人民文学〉〈当代〉〈文汇月刊〉编者答本刊记者问》,《文艺报》1982年第2期。
[42]秦兆阳:《爆炸事件·序》,张卫华、张策:《爆炸事件》,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3]张光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83年第5期。
[44]赵天成:《重温“新时期”起点的“报告文学热”——以“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1977—1980)”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45][46]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3页。
[47][48][49]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第236、249、251页。
[50]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续一)》,《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