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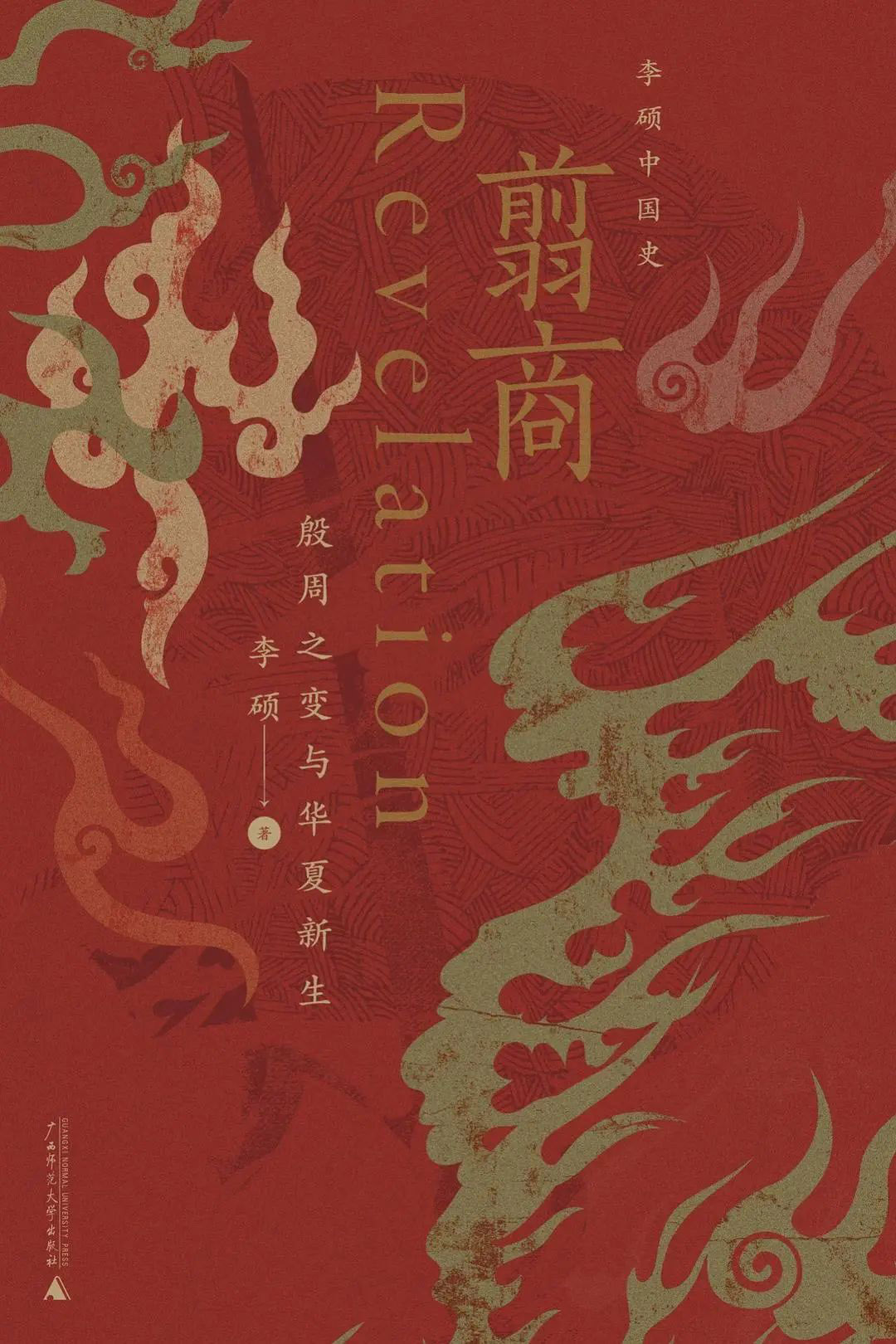
李硕:《翦商: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内容提要
李硕《翦商》一书以美国电影《启示》为元文本,视觉化、景观化地呈现作者所理解的以人祭宗教为核心的商代文明。《翦商》中,李硕将文王塑造为受启示者、武王塑造为革命者、周公塑造为启蒙者,并指认周公的启蒙事业在根本上造就了“华夏新文明”,在这一事业中,周公使用的核心方法是“遗忘”,即消灭商人的历史记忆。在书里,飘荡着一个“当代人-穿越者的幽灵”,当代史的事件和话语极大地影响了李硕在本书中对历史的书写。
关 键 词
《翦商》 《启示》 启蒙 遗忘 历史幽灵学
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以下简称《翦商》)一书,自2022年出版以来,在市场与舆论中均获成功。如潮好评中,多是将其作为史学专著来阅读与理解的。有趣的是,文学评论家基于文学批评的标准给予本书的好评,在面向图书市场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往往被错位地以“述行性”效果来再生产本书具有“高专业水准”这一印象。[1]
当然,《翦商》的专业性也有史学家支持,为本书作序的考古学家许宏就肯定了李硕的若干创见,还在拟刊的学术普及新作中引用该书对偃师商城仓廪规模的估计。[2]不过,本书的学术水准显然未有定论。有书评指《翦商》运用《周易》相关材料时,滥用“六经皆史”之方法,师心自用,未采《周易》成书史的主流观点,还原主义地看待《易经》文本。[3]另有书评认为书中有一些论断“有立场先行之嫌”,对部分考古材料断代失察,史实错误时出。[4]还有学者在本书相关活动中说:“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样都需要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节制这种想象力,在某个时刻适可而止,才是历史研究中更珍贵的品质。”[5]仍以本书许宏代序总结,《翦商》在学理上“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 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6]。可以明确的是,《翦商》在当下的流行,并非缘于其在学术上的扎实或新意;不考虑图书市场上的偶发因素[7],该书的主要优势正在于其“文学性”。
一 从电影《启示》到著作《翦商》:《翦商》文本的形成过程

电影《启示》海报
2012年,李硕为其时颇为流行的“杂志书”《读库》写作了长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8](以下简称《周灭商》)。在《翦商》出版后,他曾多次自承《翦商》是对该文的改扩写。[9]《周灭商》初次发表时,前有附言:“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电影和电影人:库布里克的《斯巴达克斯》、梅尔·吉布森的《启示》与《勇敢的心》。他们讲述了弱小者遭受凌辱与暴政时的奋起抗争。”[10]这几部好莱坞电影的共同点,是宏大的场面、刺激的视觉效果与将不同历史情境中的政治对抗,化约为当代易于理解的“面对暴政争取自由”的思想倾向。后来,李硕又在这几部影片中突出强调了《启示》的作用:“真正让我想写一篇东西的,是一部美国电影——梅尔·吉布森的《启示》,故事背景是玛雅帝国的人祭制度。这部电影让我感觉特别震撼。我看完后就想,哎呀,人家好莱坞可以把人祭拍得这么好,拍出了那种真实的、原始的、茹毛饮血的感觉。”[11]他认为,该片在“视觉层面”“非常血腥、非常真实”地展现人祭,“殷商时代的杀人献祭场景,一下子就复活过来了,好像在我面前徐徐展开了一样”[12]。他强调《启示》“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13]。正是看到《启示》让李硕动手写作《周灭商》。
在《翦商》封面上,印有本书拟用英文名“Revelation”[14],而电影《启示》原名“Apocalypto”。两词均可译为“启示”,后者来自希腊文,与《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章希腊文与拉丁文本之名“Αποκάλυψη”与“Apocalypsis”,出自同源,而这最后一章正是预言了现世毁灭后将出现“新天新地”的“启示录”[15];而在最为通行的英文圣经詹姆士国王本中,同一章节名为“Books of Revelation”。《启示》导演梅尔·吉布森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偏爱希腊-拉丁文圣经用词,《翦商》英文书名,则使用宗教改革成果的英文圣经用词。这里暗示了李硕对于“启示”的看法,即对除旧布新的预言应以大众更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达。
《翦商》对电影《启示》的“致敬”不仅体现在书名上。第十三章“大学与王子”中,李硕推定殷墟宫殿宗庙区丁组建筑基址为一座商人训练贵族子弟的“大学”,其主要科目是搏斗,并根据附近祭祀坑中曾受非致命伤的有限遗骨推断,他们生前是“陪练角斗士”,进而描绘商人让俘虏在“大学”里与“王子”们演练打斗的情景。[16]这种对丁组建筑功能与其附近人牲生前身份的看法,为前人所未发,缺少过硬的证据,几乎未见中国上古时期用战俘训练己方人员战斗技巧的记载。而在电影《启示》中,却有主人公在内的数名俘虏被放在搏斗训练场内,供捕俘一方的青年武士追杀,练习战斗技巧的情节。[17]尽管阿兹特克人文明确实有训练武士的学校“Telpochaalli”,但《启示》的历史顾问理查德·汉森(Richard Hansen)承认,类似的追杀练习在这种学校中未必存在,片中设定是为后续情节展开服务的。[18]《翦商》与《启示》中两段情节的相似或非偶然。第十八章中,李硕一如本书他处,将《周易》之爻辞按古典旧说视为文王所作,用作史料,摘句寻词,论证其中有记述文王押解捕获俘虏至商,目睹商都献祭典礼的场景[19],包括俘虏紧张地顾盼四周,或因精神崩溃而号哭;而在《启示》中,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俘虏在被押入捕俘者的城邦,送往金字塔祭场时,分别有如上的表现——考虑到李硕一再强调自己是见《启示》而作,且暗示自己的文字想达到与之近似的“如见目前”之效,此种场景的趋同似非偶然。李硕还特别强调,爻辞中“有孚,维心,亨”一语,是描绘掏心祭祀的场景,而“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人祭仪式就最为重视剖心献祭”[20]。以上可以看出,电影《启示》构成了《翦商》的元文本之一。
李硕在引子中谈及中美洲文明与商代人祭的区别,“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不像中美洲人祭在景观建筑上于公众面前进行,具有更明显的表演性,并确认殷墟内不曾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遗迹。[21]而在描绘殷墟中的刘家庄遗存时,李硕却说:“杀祭仪式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西大路上满是往返于王宫区的车队和人流,在这里公然杀祭、屠剥人牲和牲畜,有助于路人更深地领略殷商王朝都城的气象。对于初入殷都的外来者,刘家庄北祭祀场的一幕会相当难忘。”[22]之后提道:“献祭是一种公共的仪式和典礼,从这种血腥展示中获得满足感的,应该不只是使用刀斧的操作者,更还有大司空村从贵族到平民的广大看客。”[23]可以看出,李硕在写作过程中,似乎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将晚商人祭展现为公众化的视觉景观的冲动,以至于到写作过程后期会推翻自己前面的论断,令他笔下的商代人祭与经当代媒介视觉化后的中美洲人祭趋同,假想“外来者”初入殷都时会震撼于人类肢体的公开展示,正与《启示》一片中对俘虏队伍进入城邦后之所见所感的表现一致。
《启示》使用以当代尤卡坦玛雅语构拟的古玛雅语为对白,并设定无论是捕俘的城市武士,还是被捕的村落猎人,都是玛雅人;而其中表现的剖心人祭手法、宏大人祭规模以及西班牙入侵前夜的时代设定,却更接近阿兹特克文明的特点[24];李硕在谈及本片时,时而以之为对玛雅人祭的表现,时而又以之为对阿兹特克人祭的描绘[25]。事实上,《启示》这部被李硕认为“非常真实”的影片,曾遭受美国玛雅学家的密集批评,除上述对不同中美洲文明的拼贴与挪用外,它被普遍认为夸大了人祭在玛雅文明中的作用,贬低了玛雅文明在宗教活动以外的世俗领域如商业、农耕等成就。[26]有电影批评家更进一步指出,本片以西班牙人的到来结尾,暗示血腥的玛雅文化在伦理与精神上已耗竭衰微,因而正如片名所暗示,有待基督教意义上的“Apocalypsis”的降临,这对玛雅人持有近乎种族主义的态度。[27]《启示》呈现的观念,是一种萌芽自西班牙征服后,在随后几个世纪内发展起来的“忧伤原住民神话”的变体:认定原住民社会或因“原始而纯真”,或因“野蛮而血腥”,注定将在与欧洲人接触后“化为乌有”[28];《启示》对这一“神话”的改写,是令原住民社会的上述两种他者形象,分别由主人公出身的村社与他被捕捉后送往的城邦来承担。当李硕自觉地以《启示》中景观化、符号化的人祭视觉形象作为书写商代的动力与参照时,他是否可能超越这一视野中的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语境?
除《启示》外,李硕还提到写作《翦商》时,“我主要借鉴的是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失落的文明》那一套丛书,尤其是学习这套书通过考古现场复原历史的写法”[29]。该丛书并非学术专著,而是改编自1995年的同名电视系列片[30],由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策划出版,并以邮购方式售卖[31],共24本。国内于2002年翻译引进了该丛书,其中介绍阿兹特克文明者题为《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32]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充分体现了其电视片起源,配有丰富的插图,以图像而非文字为中心;二是采取了如下的叙事顺序:先写阿兹特克文明被征服的历程(第一章 金玉之城的覆灭),再写前阿兹特克的同区域文明及其被现代人发现的过程(第二章 寻觅历史的人们),然后浓墨重彩地渲染人祭习俗(第三章 神灵骇人的必需品),最后再揭示阿兹特克文明也存在人祭外的日常生活(第四章 阿兹特克人生活中的温柔一面),其总体写作策略,是尽可能地将阿兹特克人陌生化、他者化。第一章和第三章几乎完全采取了西班牙征服者的视角,除考古学材料外,依靠最多的文献是征服者一方著述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33],而在引用被征服者一方的材料时,则单纯地使用图画,并使用西班牙一方的记述解释这些图画[34],也就自然继承了征服者突出人祭的视角[35]。《失落的文明》中对阿兹特克文明的叙述,被《翦商》用作比拟的对象。在《翦商》作历时性叙述的主体部分之末章“诸神远去的世界”中所概括:“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36]在本书的最后,李硕宣布中美洲文明为某种商文明的“精神续作”,他所建立的由此及彼的理解关联,表现在叙事上就是按他所理解的中美洲文明的样态来“还原”商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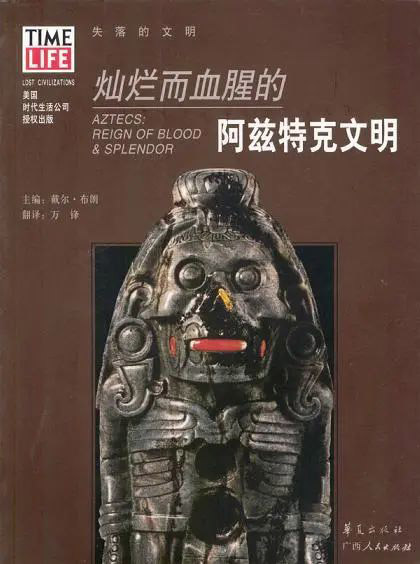
《失落的文明·阿兹特克》中文版封面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第二章的“当代人主视角”与第一章、第三章的“征服者主视角”间构成自然的连续;“过去即是异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对于“失落”的“文明”,即连续、原生的“现代性”中心之外的所有“他者”文明而言,其“当代”视野不得不受“殖民者”视野的塑造。《翦商》的引子中,李硕将他扫描各文明中人祭现象的一节命名为“打捞失落的文明”,采取了他曾称赞过的同名丛书的视角,同章节中提及中美洲文明时,他唯一引述的材料是《征服新西班牙信史》。《翦商》主体部分的第一章中,李硕以“一个穿越假设”作为其书写开端,在这个假设中,穿越者初次出场后试图与古人和平沟通,但被古人杀死,重新穿越后,他“点燃了烟花爆竹”并“呐喊”着冲进村落,驱散了古人,“于是,这群现代人(不情愿地——引者注)成了征服者”。[37]尽管很快“全副武装的‘原始人’成群出现在村外”,最终“不论死活,入侵者都将被斩首奉献给本地的守护神祇”,[38]即沦为祭品,正如《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中作者提到的他“可怜的西班牙同伴”那样。这位“当代穿越者-征服者”的“幽灵”徘徊在整个《翦商》文本上空,担当着全书的隐形主视角。换言之,读者们都将带着成为“过去-异国”之牺牲者的焦虑来读完本书,却不曾考虑自己之被“献祭”,到底是缘于过去的“陌生”和“野蛮”,还是缘于这场“穿越-征服”的现代性戏码。[39]
二 启示者-革命者-启蒙者:《翦商》中文王、武王与周公的形象
作为《翦商》“元文本”的电影《启示》有浓厚的基督教神学色彩,使《翦商》不能不于此有所染。李硕对这一点是自觉的,这集中体现在书中对周文王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尽管在传统观点中,周人视具“农神”形象的“后稷”为祖,李硕却多次强调,周族本来以游牧为生,日常骑马或牧羊[40],换言之,姬昌是一位“牧羊人”。而在《旧约》中,“与上帝立约”的希伯来人,自其世系前三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祖孙起,均以牧羊为业,此后其他“先知”也往往有放牧经历,如离开曾为岳丈放羊四十年的摩西,或曾身为“牧童”的大卫等。[41]
第二十四章“西土之人”中,李硕集中地讨论了姬昌为翦商大业“解决宗教理论上的难题”的成果,径直为这一节命名为“投身上帝信仰”[42],并概括“文王最推崇的是商人的至高神,也就是上帝——他最先把商人的上帝概念引入了周族,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主宰着尘世间”[43]。李硕以“‘一神教’改革”来指称他所勾勒的姬昌主要事功:“周昌更像是推行了一场比较彻底的‘一神教’改革”[44],还在引述《诗经·大雅·皇矣》后,分析说其中“描述的上帝,崇高而孤独,只有文王能够与他沟通,获得他的指示”[45]。并且,文王“还垄断了对上帝的解释权,只有他能见到上帝,面聆上帝的神谕。这上帝代言人的角色也让周昌有了神性”[46]。亦即,李硕笔下的姬昌类似“一神教”语境中“先知”的形象,执着于寻找和接受“上帝”关于“翦商”的启示。李硕还认为:“周昌对上帝的很多认知,很可能就来自他在殷都期间与商人上层圈子的交往,特别是箕子。”[47]
这一节中姬昌的形象,颇似据说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在《圣经·旧约》里,以色列长老摩西带领族人逃出埃及之后,多次获得犹太教上帝的当面指示,使以色列成为上帝的立约之民,把族人带往上帝的应许之地。文王周昌自殷都返回之后,则把商人的上帝阐释成普世的上帝,从而使自己成为上帝在周族和人间的代言人。这两位通神者都改变了各自的文明;所不同的是,摩西是把上帝和特定族群绑定,文王则是解除上帝和特定族群的绑定。”[48]李硕的这处对比有一点错位,应该用来与“李硕-姬昌”形象类比的,不是宗教典籍中的“古典摩西”形象——其对应物是儒家传统中的“古典文王”,而应该是同样经由现代人“再发现”过的摩西形象,以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中的摩西形象为代表。在这一类看法中,一神教思想来自于古埃及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以阿吞神为唯一神的、最终失败的宗教运动,经由熟知埃及宗教文本与仪式的摩西发展为更完备的形式,并传授于希伯来人。[49]而一旦找到了这一正确的喻体,李硕所认定的这种姬昌与摩西间的“不同”也就涣然冰释了;这位摩西和“李硕-姬昌”一样,解除了“上帝”与特定族群(埃及人)的绑定。
李硕并无意将姬昌简单构拟为一神教传统中的“先知”,他之所以大量使用相关宗教古典元素来塑造文王的形象,并非出自宗教动机;而恰恰是要曲线经由现代性视角更新过后的“启示”-“立法”宗教传统,将姬昌塑造为有为的政治领袖:“现代人的视角看,文王周昌为翦商而推演的‘理论’,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一、宗教的,即他对商人‘上帝’概念的重新诠释和利用。文王的身份类似犹太教的摩西、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身兼部族政治首领与神意传达者两重职能。二、巫术的,即他在《易经》里对商朝施展的各种诅咒、影射与禳解之术。三、理性的(或世俗的),即各种‘富国强兵’的策略和行施。”[50]李硕对于文王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理论”似有犹豫,一边在书中称“文王自居为上帝代言人”只是“策略”“神道设教”[51],一边又铺陈“文王演周易”时的虔诚、笃恭,但根本上,他的书写还是落脚在“翦商”事功的实效上。换言之,李硕是基于“翦商”及“殷周之变”确实发生过的认知,去塑造开创者文王所“应该”具备的形象,一如弗洛伊德是从“一神教”之随后兴起出发,反推摩西“应该”具备的身份。弗洛伊德只有一个参照,即“现代”;而作为后发现代国家中后来写作者的李硕,则由不得在参照“现代”之余,还要参照从摩西到弗洛伊德们的“西方”。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李硕对周文王形象的塑造,对应着传统史学中周人在何时由何人“受命”的问题,学界为此聚讼纷纭,依传世《尚书》及新出土文献,文武甚至周公都有受命之说。[52]李硕的观点是,文王以崭新宗教下的“天命”观造作了此当受之“命”。然而,相比于“文武受命”之争,由《周易》中革卦彖词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53]而出的“革命”之功,则如上所引,似无争议地属于武王。
在清末以来,“革命”一词逐步获得了全新的内涵[54],用来指称全面的社会制度变革。新时期以来,对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及作为其“原型”的俄法革命的批评与反思,以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提出所谓“告别革命”论为高峰,抽空了民间对“革命”话语中“旧邦新造”、革新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意涵的认知,肯定“革命”正当性者,将其视为一种对之前压迫的同态复仇;反对其正当性者,则片面强调其暴力之烈度,人道后果之惨重。[55]在如上认识的历史叙事中,“革命者”往往并非对革命理论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坚定的信念,而只是出于切身经验的残酷或对混乱乃至暴力的爱好,而卷入革命。在《翦商》文本对武王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符合1990年代以来部分大众意识形态中想象的“复仇者”-“革命者”。
与本文论题更加息息相关的是,在现代中国革命中,“武王伐纣”也是“革命话语”的核心部分。从丰子恺《口中剿匪记》的“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道了”[56],到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把武王伐纣说成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57],都把腐朽的国民党当局比喻为“商纣”,体现了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共有的“历史心性”。中国革命对“武王伐纣”的征用不仅仅停留在言论上,还曾在抗议运动的现场发挥作用。1945年昆明大中学生召开“五四纪念会”游行时遇雨,部分学生准备散开,闻一多登台讲述了武王伐纣遇雨的故事:“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上来,走近来,勇敢的人走拢来!”于是游行得以继续进行。[58]这说明“武王伐纣”话语有机生动地“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现场,并在与历史行动者的互动中得到了现代语境之“革命”的“革命化”。
李硕认为,武王并不确信文王所造作的天命观[59],之所以坚持翦商的事业,根本上还是由于他经验和见识过商人的暴行。因而在成功克商后,武王出于精神的迷茫与对商人的仇恨,逐步地“商化”[60],相信必须以更多的牺牲才可能取悦于“上帝”,“用商朝人的宗教理念来解释周灭商,则需要更深地进入商人的宗教思维。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武王对商人宗教的依赖也越来越强”。李硕还认为,武王继承了商人的人祭传统,而且是“常态化地接受了商朝的人祭宗教”[61],进而认为武王就采取商式人祭而言,“比商人更变本加厉”[62]。李硕还一再猜想,武王临终前给周公的交代中,曾提出过将商人全部屠灭祭天的方案。[63]在李硕的笔下,武王伐纣本来具备反抗暴政的正当性,但却因为片面地以暴易暴,并受到旧制度之意识形态的诱惑,而几乎误入歧途。联想到1990年代以来“屠龙勇士终变恶龙”的西方寓言,以及“新启蒙”意识形态指“革命中国”的部分激进政治实践为“封建传统”之说,不难识别出,李硕试图以同情、理解但又批评的态度塑造武王形象,从而暗示采取以暴易暴的“革命”方法,无法斩断此前的暴力链条,实现其“解放”目的。

发现较多殉人的商周易代期西头遗址2022年发掘全景
在武随后的“周公新时代”[64],基于对“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的理解[65],周公选择与商人一起“咸与维新”,在全新的人道精神指引下教化“群迷”。在李硕笔下,周公试图将上述“德”的观念注入对“上帝”的认识,将人格神“上帝”转化为较为含糊的“天”。为此,他提出了新的“天命观”,即王朝兴替“背后,虽都有天-上帝意志的改变,但唯一能影响天命的因素,是人的‘德’,也就是人处理现实问题的准则”[66]。周公从长远来看,试图将商人“彻底同化于周人的文明”[67],因此在对管理殷商遗民的卫国首封君的训话中,要求他还要让“商人改变陋习,成为新民,为王朝继续赢得天命:‘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68]也就是说,欲革此“天命”,关键不在于杀伐翦克,而在“新民”。“新民”概念,经过近代以来的改造,与梁启超所开创的该词“启蒙”用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周公(和召公)在这一时期还发明了指称王朝中被统治者的“小民”概念:“按照周公和召公新发展的理论,王应当关注小民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让贵族)虐待和过度剥夺他们,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69]一般认为,相较于商代,西周的“臣民观”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70],这种变化的具体内容,以及是否完全应该归功于周公个人的“创造”,似有待细究。从整体上看,李硕的叙事,显然突出了周公在政治观念进步上的贡献。
对于周公所造的新思想体系,李硕不仅在主体部分历时性地予以叙说,又在“尾声”——“从周公到孔子”重加总结:“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使“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对于‘帝’甚至其他神灵都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此外,李硕认为,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李硕在此特别指出,周公的上述天命观是为回避统治者对暴力的过度使用,“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以此区别于商人“直言不讳”的暴力。[71]李硕认为,“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72]如此伟大的事业,在李硕看来,绝非武王使用暴力与同态复仇的方法所能完成,而只能是在文王所受“启示”的基础上,由周公以启蒙造就“新民”才得以实现。
李硕对“文王-武王-周公”家族的形象寄托着深重的感情,在叙事过程中,他忍不住慨叹:“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73]支撑他书写血腥人祭的力量是“周文王家族的故事,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变化”[74]。李硕想象中的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这一父权小家庭中的情感与伦理连接,成为推动“翦商”事业得以不入歧途的保证;尽管在李硕看来武王已经“商化”,但出于家人之亲,武王还是正确地将权力交接给周公,保留了启蒙与改革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在李硕看来,商人的观念充满“成人”的血腥,而周公所作的新思想正宜于向儿童传授:“我们传统对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叙事,都是周公和孔子奠定的,看上去都比较低幼,适合讲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周公、孔子本人所了解的上古史肯定是更残酷、更真实,是原装‘成人版’的。”[75]李硕还径直使用“启蒙”一词描述他认为是周公写定的历史版本:“《史记》里的夏商往事,大多叙事过于程式化,或者说,其中的古代圣王往往言行幼稚,不近实情,如同写给儿童的启蒙故事。”[76]此处之“启蒙”是指其古代的原意即“小儿初学”,以周公所制定的商周之变叙事为枢轴的新意识形态,朴素而单纯,看似“低幼”,却正符合“启蒙”之本义,即让儿童习得基本的“正确道德挂念”;“启蒙”本来就更多指向伦理而非知识意义。[77]
李硕此处依其“本义”对“启蒙”一词的使用,却带有近现代以来百余年间,掺入“enlighten”之意的“启蒙”之色彩。贺桂梅曾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至1980年代末,所谓“新启蒙”意识形态曾一度在中国大陆享有某种“领导权”(hegemony)[78],其特点是试图接续中国革命发生前近现代之“启蒙传统”,为补上曾为“救亡”之现实政治议程(这里的“救亡”实质上所指即是“革命”,而在“救亡”发生的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参与政党也都称自己在“革命”)所“压倒”的“启蒙”课业。然而,此种领导权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遭遇多元消费主义文化的解构[79]以及内部共识之断裂[80],从而迅速失落,催生了部分论者对“后启蒙”这一描述的使用;陆续有学者以“后启蒙”视野来把握21世纪的学术领域或文化事象,如现当代文学研究[81]、“儒学复兴”[82]和曾经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的民间教育实践[83]等。取其最广义,“后启蒙”话语与“启蒙”立场形成了某种拉锯,在厌弃占据伦理与政治高点说教的许多当下大众心目中,可以接受的“启蒙”话语,正是被还原为“教授基础正确价值观与知识”的那一种。
在李硕看来,周公事业之伟大与对自身的叙述之朴素形成了对比,而他对“伟大”的反复铺陈与“启蒙孩童”的贬低评价的对比,构成了解读其“启蒙”用法的钥匙:这种“启蒙”是对作为现代性组成部分的宏大启蒙方案的“举重若轻”。周公“启蒙”,又是对武王“顺天应人”“伐一夫纣”式征讨暴君之“革命”的扬弃;这一革命依然有其最低限度的正当性,但却有待于“启蒙”来将其使命彻底完成;二者加上之前的“启示”环节,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翦商”方案。可以补充的是,学者刘小枫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送回它的起点,认为早在先秦和两汉,它就已经内在地具有“道德-宗教”维度。[84]此为反对“现代中国革命思想”全系舶来之说,却依然以“现代中国革命”即“社会-文化-政治-伦理”全方位变革为标准,来考察古代的“革命”之说。
综上所述,通过将文王塑造为经过现代性改造的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中的“启示者”“立法者”,将武王塑造为以暴易暴、杀伐过甚的“复仇者”“革命者”,将周公塑造为以人道、理性革新旧物的“改革者”“启蒙者”,《翦商》隐秘地重新呼应了新启蒙命题,确认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方案,在心灵启示与政治革命后才能得到彻底的推行。[85]只不过,在新启蒙话语的起点,它所期望的是用“启蒙”所译写的“enlighten”去扬弃用“革命”所译写的“revolution”;而《翦商》,看似还原了“启蒙”与“革命”在汉语里的原初语境和语义,不过,正如刘小枫的阐释,即使极力想摆脱“revolution”对“革命”意义的改写,生活在革命的“效果历史”之中的当代中国人,也要参照“revolution”的视域去理解“革命”,进而无法在使用概念、认知概念由来及
其叙事时,自限于其“本义”之内。对“启蒙”而言,自是同理。因此,以“原初”“启蒙”来扬弃“原初”“革命”的思路,在根本上依然是当代思想史上的以“启蒙”扬弃“革命”的“维新”。进一步说,回到话语所指更新以“前”,正是为了介入话语能指衰微之“后”。
三 “遗忘”——《翦商》中“李硕-周公”启蒙方法
近代以来,自王国维提出商周之变以来,将传统上“制礼作乐”的“圣人”周公指认为新文明的设计者,即绵延不绝,逐步形成传统。[86]在《翦商》中,绝非重复性地塑造了周公的“启蒙者”形象,它的创新,除通过突出商代人祭而衬托周公兴革之功外,还有意识地将制造“遗忘”指认为周公“启蒙”的核心方法。
在《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中,李硕说:“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移民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87]《翦商》多次强调这一点:“(周公)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于是留下三千年的记忆空白”[88];(周公)“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89];周公“必须毁灭殷都,断绝商人的血祭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90];“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91];“本书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在周公辅政时期,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的‘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血祭行为”[92];“周公执政时期不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为,同时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商人的这些风俗,结果,铲除人祭的记录也和人祭行为一起消失了”[93];“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94];“周公的目的: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95]。李硕还将“周公新时代”章其中一节,命名为“修改历史记忆”[96]。

安阳殷墟遗址王陵区航拍图,考古显示所有王陵都在商周之际遭到过严重破坏
李硕塑造的周公(以下简称“李硕-周公”)有意制造遗忘,是为了将商人重塑得“和周人一样”,而不是将商人“他者化”,尽管文本中的商人正是彻底的“他者”。李硕对周公的这一目的反复申说:“让他们(指商人——引者注)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97];“周公……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98]。“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99]在“启蒙”与“新启蒙”言说与行动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将往昔塑造为“他者”的方法,来树立当下“思想转型”“精神洗礼”的合法性。此一传统或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启蒙运动,其成立的认知基础,则是对时间性的线性连续观念;因时间之“线性”而能别“古”“今”,因时间之“连续”而需断“旧”“新”;旧制度-旧文化在此种启蒙方案中,应是判然区别于光亮的“黑暗”,因而才有待于“照亮”即“enlighten”。而以“遗忘”“旧文化”真实或假想的极端残忍为方法,指认时论正合古人,从而诱导“群迷”跟从的“进步”方案,则一般认为更多见于英美思想之中,例如英国近代以来利用对大宪章神话的发明构造本国所谓“宪政传统”[100]。黄德海也对《翦商》作出了类似指认:“《翦商》这本书类似于历史的辉格解释,将历史发展一刀两断,并且在一刀两断的过程中,代表先进的一方要更改历史,还要把痕迹抹杀。”[101]确切地说,“一刀两断”,在这里正是“以不断断之”。而在使用这种手法时,如果有明确的自觉性,又要故意在特定的知识或政治精英圈层内保留关于“历史真相”的知识,则又几乎逾越启蒙传统,与施特劳斯的“显白-隐微”二分“教诲”相似了。不过,《翦商》中相关表述暧昧;一方面,作者似认定周公(和孔子)所留下的“教诲”确“显白”已极,以至是“孩童版”;另一方面,他又以本书说破此事。这样看来,书中两种“教诲”并非适用于不同人群,而是先后相继,人人可知。
李硕-周公选择以“遗忘”的方法来重塑与周人相似的商人形象,从而实现和解与启蒙。然而,“遗忘”与“记忆”正是互为表里的过程,在社会性层面上自不例外。如保罗·利科认为,遗忘是记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102],“在记忆之术达至极致时,遗忘将彻底被遗忘”[103]。李硕-周公正是运用“记忆之术”的大师,几乎就达成了使“遗忘彻底被遗忘”的效果。社会学家卢曼在其系统理论中也认为:“记忆的主要功能在于遗忘,预防系统因为固守先前的评价而为自己设置障碍。”[104]祁和平从卢曼的这一论断展开说,记忆可被“定义为当下对于记忆和遗忘进行区分的一种操作”,而“‘文化’则可被理解为一种调节和控制这个区分过程的‘过滤器’”,“它经常要决定是否应该将交流与过去联系起来”,抑或“删除与过去的某种潜在关联,寻求新的发展”。[105]李硕-周公所操作的“记忆”与“文化”,似正与此。然而,对普通个体来说,这种“选择”在实际上却不可能如此“自主”,而一定会受到某种“训练”,成为利科所谓“记忆之术”施加的客体。
事实上,李硕似对记忆能被有效抹杀一事有所犹豫,“在没有经典文本叙事的前提下,零碎的、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很容易走样失真,以至消亡”[106],因而,周公只要有效地改写了所有文字记录,并毁灭商人在地表上的物质文明,就可以实现对人祭的遗忘;另外,口头记忆“是朝廷禁令难以销毁的”,“可以合理推测,有关商代人祭行为的记忆仍会在周朝的民间和贵族中私下流传,成为和官方意识形态很不同的暗黑历史记忆”。[107]他以宋襄公处死会盟来迟的鄫子一事,及其兄对此的批评为凭据。[108]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创导者的阿莱达·阿斯曼,将文化记忆分成“储存记忆”与“功能记忆”,前者作为后者的背景,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109]关于人祭的“记忆”,作为“储存记忆”而持续存在于其时的社会中,而具备转为“功能记忆”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将周灭商与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相比,则“周朝和最近五百年的世界有很多不可比之处”[110],也就是说,李硕在评估周公“记忆抹煞”的可行性时,所依据的正是商周之变的久远,以及当时缺少口头之外的记忆载体,似认定在古代推行文化遗忘比现当代简单。不过,21世纪全球化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文化遗忘”造成了“一系列断裂”[111]。在“数字记忆”的时代,信息来得快存得多,但也消失得快,“只需轻轻一个点击便化为乌有,了无痕迹。更不要说一九八四式的恐怖想象”[112]。当代历史书写提出“真相被系统掩盖”的看法,可能包含了将切身经验与现实焦虑向过去投射的成分,因此李硕的犹疑体现了商周之际即使存在着某种“消灭人祭记忆”的意图,也未必能得到有效的贯彻与实施,毕竟,传说在以口传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时代,是不那么容易彻底消散的。
关于启蒙者,除了塑造李硕-周公外,李硕在《翦商》前的写作中就塑造了孔子的启蒙者角色,他在《孔子大历史》中描绘齐鲁郊之战的一节命名为“春秋战争与和平”[113],在转述大多数是受过孔子教育的鲁国贵族青年们主动参战的事功后,他写道:“颇有点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国贵族青年们告别了莫斯科或彼得堡的文艺沙龙,投身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都是贵族社会晚期,上流社会小圈子的年轻人走向战场的心路。甚至欧洲近代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一些萌芽,在孔子的时代也零星出现了”。[114]李硕以热烈的笔调进一步歌颂道:“它们虽然远比欧洲的大革命时代粗朴瓠陋,但这两千年的时差本身就是一个奇迹。”[115]李硕在这里脱离其原有时空使用了“启蒙主义”概念,而暗示“启蒙”在许多历史情势与人群中都可能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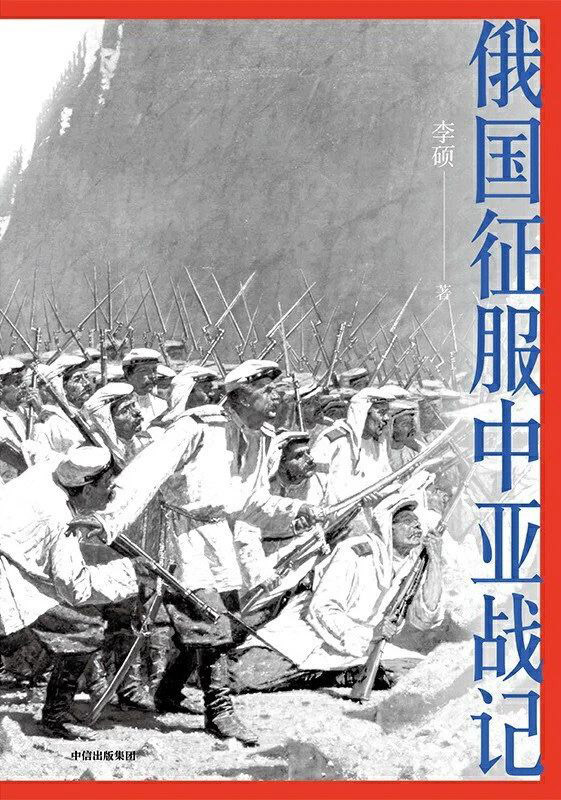
李硕《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封面,使用了征服者的纪功画
李硕的“启蒙观”之中,尚有另一重维度。在2020年出版的《俄国征服中亚战记》中,李硕对沙俄一方流露出了一定的同情:“我们将欣赏将军们的睿智或笨拙,士兵们的勇武或怯懦,就像观赏一场拳王争霸赛。不需要太多的矫情和多愁善感。”[116]“大陆已经历过无数次战争、屠杀、征服。俄罗斯的征服,只是这一系列征服中的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所以,没必要故作公允地指控胜利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正因为经历过一次次冷兵器砍杀,硝烟烈火甚至核武器的毁灭战争,人类才走到了今天的‘文明’世界。”[117]亦即,“文明”将不得不使用暴力来维系。李硕使用了大量19世纪欧洲画家的版画与油画,以及同期沙俄征服者拍摄的照片作为配图[118]——这种对视觉效果的痴迷在《翦商》中得到承继,这不只体现在《翦商》中也有大量配图上,更体现在其叙述中——其中大部分绘画的描绘对象是泛化的、东方主义化的“伊斯兰世界”,如“后宫女性”“阉奴”等母题。在同书的叙事中,类似倾向也时有流露。如在记述希瓦汗国一方违背条约时,李硕写道,“俄国发现,希瓦人……已经不记得签署过什么和约了——中亚人还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的外交观念,这里的游戏规则从来都是征服者全赢,还没有对等的‘国际关系’”[119],而在写到俄方的背约行为时,他却出以完全相反的笔调,强调俄方定约者没有权限定约,因此俄方不承认约定似理所应当。[120]他还将尾随俄军试图捡拾物资的当地人队伍比拟为“非洲鬣狗”,并称“同在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的征途中,也被同样的食腐大军一路尾随。这也是前现代东方社会的一大特色”[121]。
在《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后记中,李硕解释之所以在新疆工作期间立意写作本书,是为了把“之前一直生活在东部地区,忽然到了大陆深处的乌鲁木齐,感觉地貌、自然环境、气候颇不一样”的“异域感”[122]写出来。具体地选择写俄国征服中亚,是因为“两千多年来,汉人一次次走进西域,甚至穿过中亚,前往印度或者西亚;西域甚至来自更遥远的西方的人也一波波进入中原。这些远行者踏过戈壁,翻越天山葱岭,涉渡流沙之河,和19世纪里俄国人看到的风景,感受到的新奇、艰辛没太大区别,而俄国人留下的记载最多、最详细……所以,此书不仅是想写俄国或战争,也是想从一个角度展示、还原古老丝路的风貌。解忧公主、班超、鸠摩罗什、玄奘和尚、岑参、丘处机、林则徐等人一路看到的,大致也是这些。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又要睁眼看世界,还有‘带与路’的考量与探索,更需要对帕米尔以西那个陌生世界多一些了解”[123]。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政治与社会身份的中亚行旅,被李硕以“睁眼看世界”这一经典的启蒙命题统一。古代的朝圣与传法、和亲与流放、现代的征服战争与贸易被共同纳入了“启蒙视野”,一起构成李硕所理解的新全球化。
在本文第一节,我们曾引述过李硕对穿越者因为无法和古人沟通,而“不得不”成为征服者的假设,与李硕在本书中对沙俄中亚征服之”被动性“的认可,两者之间似构成了某种同构。现代人-征服者视角之重合的“合理性”,于焉再次显现。即使施展“遗忘”这一最重要的“记忆之术”,我们也很难解决这种“文明的负担”所带来的问题:“应在何处止步?”
结论 历史非虚构写作中的“视觉现代性”与“当代人幽灵”
在写作《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和《翦商》时给李硕启发最大的两个文本,均属于当代视觉艺术之范畴;在《翦商》的写作中,李硕自觉追求“想象力”,意欲视觉化地呈现商代的人祭场面,书中的许多情节和场景,都带有摹写自《启示》的图像之痕。李硕创作谈中曾多次暗表,以《周灭商到华夏新生》为起点最终呈现为符合“学术规范”的“专著”,并非必然:“我一直想,文章已经在那里了,如果有其他学者把这个素材写成一个非虚构作品,或者写成像《冰与火之歌》那样的纯虚构的作品,我会觉得非常开心。”[124]“其实在2019年,我曾想把商周历史写成小说,因为那时看了个美剧《高堡奇人》。这片子的格调非常阴郁、灰暗,我觉得和周文王家族的故事风格特别像……我那时还向当影视编剧的朋友请教,怎么写文学作品,但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不行。我想象力的翅膀已经被我所受的学术训练捆住了,只能像侦探破案或者法官断案一样,在充分的论据上形成推论。”[125]
以上透露出李硕对历史非虚构写作的一系列认识。第一,从“虚构作品”到“非虚构作品”再到“专著”之间,三者间具有连续性。第二,连续的三种写作所共同需要的“技巧”,往往需要自影视文本输入。第三,《翦商》体现的“想象力的翅膀”被学术捆住了,“不得不”写成“非虚构”或“专著”,
而不能进一步发扬文学性,这成了一种遗憾。从以上三点看,李硕似认为,一切由想象外化的视觉图像,即是“艺术”的“元形式”。李硕又认定,影视艺术的视觉呈现,又是最为“真实”的[126];也就是说,最真实的东西,在李硕看来,正是“想象”这个动作所造就的“图像”(image a image)。由此看来,李硕理想中的写作,不依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而依赖视觉中心主义的“图像”,贯穿《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和《翦商》的正是视觉中心主义立场。[127]可以补充的是,李硕非常明确地追求镜头感与场景感,《翦商》经常以重构某处遗址的生活场景为中心,一如历史纪录片中常见的,从一片遗址逐步还原为完整的空间,随后再淡入正在人群的视效过程;在衔接场景时,李硕则往往采取运动的类镜头视角。如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所设想的那样,镜头的移动,是以持有镜头的、运动中的观看主体-摄影者为基础的。而在《翦商》中持有镜头的运动-观看者,正是历时性叙事开始时死去的当代人-穿越者的“幽灵”。
李硕对“画面感”的追求得到了考古学家许宏的认可[128],同时许宏认为:“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在视频和音频节目中,呈现得肯定都是有限的。”[129]李硕从图像到文字的“降格”遗憾,在许宏却是一种“升格”,他认为,最能实现“画面感”的正是看似最为远离画面的东西。此处的区别正是当下流行的历史非虚构写作——包括大部分“ip”多重文本生产,与主流文学现实主义技术观之间的区别,即作为认识与审美基础的“图像”是否可以被直观地、不依赖中介地“看见”。

对商周之变的最新视觉呈现——电影《封神》
阿兰·巴迪欧曾讨论过“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图像”已不再反映“现实”,而本质上是一种作为欲望对象的“色情”,然而,这不是说“现实”与“图像”无关,恰恰相反,“图像”以“象征”的方式,重新牢固地锚定在“现实”之上。[130]因而,巴迪欧所指认的“当前时代”的主流“图像”,可被想象为以“看见”的方式来把握的“虚拟现实”(例如所谓“全息影像”),看似取代“现实”本身,然而也正借此隐藏与捍卫了最坚硬的那种现实,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掌握的“赤裸的权力”。《翦商》一再展示的“看见”动作,有效地隐去了观看主体所内化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语境,“视觉现代性”的、以“想象-图像”为核心的写作技巧,也正与李硕的“欧美-当代-征服者”视角适配。
彼此嵌合的内化视觉现代性与欧美-当代-征服者三位一体视角,与李硕的历史观相互支撑。汪晖近年提出,“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五四’之后的古史辨运动,由欧洲的historia翻译、转换而来的历史概念及其空洞、匀质的线性时间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一旦发生时间性错乱,就会陷入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131]。然而,“编与重编、形成时间与编成时间的错置不仅是古史形成的特征,而且也是现代历史叙事得以确立的路径,只是后者将过去的一切历史化,没有将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化”[132]。汪晖关于鲁迅的“历史幽灵学”,暗示了汉语为载体的现代性叙事在定型过程中,不能不受到其借以言说自身的“古代史”事象的影响。正如《翦商》的结构上,前有“引子”,在文明比较中显明“人祭”主题;后有“尾声”,再次总结书中“周公在隔代知音孔子的帮助下再造华夏文明”这一观点;而在两者之间,则大体上依历时性顺序铺陈;俯瞰这一整个线性时段的,正是那位“穿越者-征服者”被“献祭”后的幽灵,这一幽灵是无法被纳入古代史空间的绝对剩余物,也就是他从当代携带而来的种种在巴迪欧式“图像”中尽情“享乐”的欲望。这个“幽灵”与汪晖所描绘的鲁迅“幽灵”的区别很明显,后者难以判断其来处与去处,其存在于根底上由此当下的参与来保证,而前者则明确来自当下,然而其存在却又依赖着当代穿越者理解乃至把握彻底陌生的古代的欲望。于是,《翦商》的幽灵以其牺牲所把握“上古史”也就必须是他者化的、异国化的,与今日无法沟通的。[133]这就是《翦商》召回历史的方式。
在线性时间基础上的启蒙-进步宏大叙事已遭遇动摇的当下,《翦商》试图重新树立启蒙的合法性,重构线性历史,在其他文本中,李硕试图将中国文明重新安放于这一线性历史之中,这可见于《孔子大历史》中对中国“启蒙主义与人道主义”领先西方“两千年的时差”之判断中。汪晖认为,《故事新编》中诸篇题目的动宾结构可能将历史去主体化,从而释放出之前不被认可是历史行动主体的“无名”者或者说是“鬼”[134];《翦商》这个书名同样是动宾结构,然而在书中,李硕尽管重塑了文武周公的形象,却又将他们安放在了神坛的原位,从而将历史进程再度还原为几位英雄的有意营为。汪晖指出:“历史的每一次再现都是寓言性的,每一次变形都有当下的指涉,每一次重演都被由未来所充塞的过去或被过去所装扮的未来所激活。”[135]对《翦商》的这一次历史再现而言,亦莫能外;然而,《翦商》却正是“寄托于某一个理想化的人物”[136]、“凝固于某一(被认定——引者注)可以被实证还原的名目”[137],而拒绝承认,自身所指涉的那段历史中的行动也正可能即是当下的行动,因而也就失去了像《故事新编》一样争得其“未来性”的机会;也就是说,《翦商》因拒绝承认自己的当下性,而恰恰完全被“当下”的“现实”,亦即巴迪欧指认的那种“赤裸权力”所捕获,最终被回收进“欧美-当代-征服者”的三位一体视角内部去。
在谈及“翦商”(也包括指代同一事件的“伐纣”等)意象的当下效用时,可提及的是“翦商学”“入关学”一类借历史隐喻来展望中美之争,为全球化打造中国中心新秩序之前景的“键盘政治”话语,学术界的相关讨论,见于《东方学刊》杂志2020年第3期的“入关学专题”中。在这类话语中,“翦商学”被参与上述讨论的学者给予了较高评价,孔元认为:“‘伐纣’的历史意义,在于从中国历史脉络中挖掘革命的意义,再将它贯穿到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138]提出“翦商学”者认为,相对于自比“蛮夷”,并认定取代美国霸权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只要夺取原有世界体系的主导权,就能自动获得这一“夺取”行动的合法性的“入关学”,“翦商”不仅隐喻了美国的腐朽,更隐喻美国的残暴,并内涵有取代美国后中国将建立全新的世界体系与文明秩序的举意。[139]该话语的使用者对用以比拟美国为“商”的描述,如“以商业和血腥的神学立国”,还有“东亚各族人民心中的永恒阴影”;以及对于“翦商”后被继承至今的“中国”的创造者“周”事功的描述,如“塑造了人,奠定在了每个人的重要性和存在价值,创造了一个孔子念念不忘的黄金时代”[140],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翦商》前身《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描绘,以至于有匿名知乎网友在问题“如何评论李硕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下回答:“翦商学核心文本,真正的历史神学”[141]——尽管为后启蒙时代的民间外向性国家主义方案提供镜像与话语,并非隐秘重申启蒙的作者之本意。《翦商》是游戏的开场动画与设定,而在“翦商学”这里,我们的玩家要开始通关了。[142]
李昌懋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100084
注释
[1]例如,在由上海书展延伸而出、于沪上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思南读书会”所推荐的2022年书单中,该书就被列入“年度人文社科(专著类)”;然而,列《翦商》入该书单的推荐者复旦大学中文系金理教授对本书的推荐语却相对聚焦于该书对“讲故事”的“自觉”,以及“将史迹与想象力作合理绾结”,并坦陈自己作为(上古史知识稍欠的)“普通读者”,对本书的阅读兴趣正主要来自于上述优点,思南公馆:《“思南书单·2022”正式发布:正榜、评委特别推荐榜、提名作品总目录》,微信公众号“思南公馆”,2023年2月18日。不止文学评论家,在《翦商》封底上,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的推荐也以“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文学家的想象”来称赞本书,使用“文学家”的标准来证明本书作为“历史著作”的价值。
[2]许宏:《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未刊书稿,2023年,第106页。
[3]冯夷:《从〈翦商〉谈起:“六经皆史”的限度在哪里》,《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年2月20日。
[4]林屋公子:《〈翦商〉:商周革命的另一种书写》,《廉政瞭望》2023年第7期:“如称二里头——夏朝存在近四百年,但抛开二里头性质争议,其绝对年代是前1750—前1520年,顶多算夏朝晚期都城;如认为王子孝己在西晋之前没有记录,实际上战国《吕氏春秋》就有;如认为崇国国君都可以叫崇侯虎,并以西周虢仲虢叔举例,但虎是私名;如认为狄人姓隗,但这只是赤狄;如认为春秋齐侯丰作了一件尊彝,实际上是西周丰国国君作了一套青铜器;甚至使用《伪古文尚书·泰誓》的材料。”必须指出,李硕在《翦商》中以注释解释了自己为何会使用被学界主流观点视为晚出文献的《泰誓》(李硕:《翦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5章“牧野鹰扬”,第506页,注释3)。这说明李硕具备该古典文献知识,不过,该文献以武王口吻铺陈了纣王种种残民之举,而李硕明知其未必可靠也要坚持引用之,这或能说明,他有意无意地偏向使用能证明商人残暴的材料。
[5]发言者为阙海,思南读书会:《〈翦商〉:中国历史的转折性时刻》,微信公众号“思南读书会”,2023年5月24日。
[6]许宏:《代序:我们陌生的形象》,李硕:《翦商》,第5页。
[7]例如作者李硕罹患重疾消息之流传,或进一步增加了公众对本书的兴趣等。
[8]张立宪主编:《读库1205》,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297页。
[9]经观书评:《专访:〈翦商〉作者李硕:深究历史深处的黑暗》,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2023年3月16日;忽友功德箱:《与李硕漫谈〈翦商〉:上古先民的黑暗史话》,微信公众号“忽左忽右Leftright”,2023年1月15日;李硕:《后记》,《翦商》,第576页。
[10]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张立宪主编:《读库1205》,第275页。
[11]经观书评:《专访:〈翦商〉作者李硕:深究历史深处的黑暗》,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2023年3月16日。
[12]忽友功德箱:《与李硕漫谈〈翦商〉:上古先民的黑暗史话》,微信公众号“忽左忽右Leftright”,2023年1月15日。
[13]李硕:《后记》,《翦商》,第576页。
[14]本书还未曾出版英文本,笔者也未见其译介计划。
[15] “启示录”是以“和合本”为代表的新教系统汉文圣经译本中对该章节名的译法;在以“思高本”为代表的天主教系统汉文圣经译本中,该章节名多译作“默示录”。
[16]李硕:《翦商》,第249~268页。
[17]梅尔·吉布森:《启示》,北美公映版,1小时23分35秒至1小时30分59秒。
[18]转引自Robert W. Welkos,“ In ‘Apocalypto’,fact and fiction play hide and seek”,Press Reviews,Los Angles Times,2023年12月9日。
[19]李硕:《翦商》,“押解俘虏的经验”一节,第347~351页;“目睹殷都献祭仪式”一节,第354~355页。
[20]主流学术观点认为,阿兹特克人祭的确是掏心为主,而玛雅人祭规模上较小,方法较多元,相对而言以斩首最常见。
[21][22][23]李硕:《翦商》,第15、398、408页。
[24]西班牙入侵前玛雅地区依然有城邦存在,但其规模与文化辐射力等均已远不如同时代的阿兹特克文明。
[25]前者见忽友功德箱《与李硕漫谈〈翦商〉:上古先民的黑暗史话》,微信公众号“忽左忽右Leftright”,2023年1月15日;后者见李硕《后记》,《翦商》,第576页。
[26]可参看Traci Ardren,“Is ‘Apocalypto’ Pornography?”online reviews,Archaeogoly,2006年12月5日;Andrea Stone,“Orcs in Loincloths”,online reviews,Archaeogoly,2007年1月3日,以上两文见于具一定叙述权威的美国考古学会网站。也可参看 William Booth,“Culture Shocker:Scholars Say Mel Gibson’s Action Flick Sacrifices the Maya Civilization to Hollywood”,Washington Post ,2006年12月9日,采访多位玛雅学家而写就的本文,其题目即概括自专家们的意见:《启示》影片将玛雅文明献祭给了好莱坞。
[27]可参看Obert A. Yelle,“The Ends of Sacrifice: Mel Gibson’s Apocalypto as a Christian Apology for Colonialism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23”,No. 1;James J. Aimers and Elizabeth Graham,“Noble Savages versus Savage Nobles: Gibson’s Apocalyptic View of the Maya Apocalypto by Mel Gibson ”,Latin American Antiquity, Vol. 18, No. 1。此外,危地马拉政府(该国人口中玛雅人占比据2018年普查为41.66%,当代国家中最高)的时任种族主义事务专员(Racism Commissioner)Ricardo Cajas也认为本片是“种族主义”的,转引自Allan Wall,“‘Racist’ Apocalypto Opens in Latin America”,2007年2月,网址
http://www.banderasnews.com/0702/edop-apocalypto.htm,最后浏览时间2023年10月4日。
[28]关于“忧伤原住民神话”及其在拉丁美洲的特定形式,参看马修·雷斯托尔《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第六章“印第安人气数已尽——忧伤原住民的神话”,李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0~216页。
[29]经观书评:《专访:〈翦商〉作者李硕:深究历史深处的黑暗》,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2023年3月16日。
[30]该纪录片的imdb页面如下
https://www.imdb.com/title/tt0112054/。
[31]参看《时代生活》杂志维基百科页面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_Life。
[32]戴尔·布朗编:《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万锋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3]该书有中文版: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全二册,江禾、林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中将本书名译为《墨西哥征战史实》,本书作者名字译为“博那尔·戴兹”。该书被较新研究认为,应被“抱有更深的怀疑”“必须谨慎地审视每一段话”(马修·雷斯托尔:《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李音译,第263页)。
[34]以被征服的阿兹特克人立场进行的历史书写,可参见米格尔·雷昂-波尔蒂利亚编《战败者的见闻》,该书西班牙文版出版于1962年;中文版收录于氏编《战败者见闻录》,孙家堃、黎妮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其中包括阿兹特克传统上的图画抄本,也有征服后阿兹特克人使用拉丁字母拼写其语言纳瓦特尔语写下的文本,还有传教士使用西班牙文译写的纳瓦特尔语口述史。必须说明,对其中的图画抄本而言,必须结合阿兹特克人的口述传统,才能在其原初语境中得到理解;而如果仅仅把它们当作西班牙人记载的配图和插画使用,其意义将有很大不同。
[35]最近二十年来对西班牙征服的研究中,随着建立在“新语文学”(New Philology)即利用征服前后多种原住民语言文献基础上的“新征服史”(New Conquest History)研究范式的发展(对此可参看马修·雷斯托尔《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增订版后记中“对于材料的处理”这一段落,《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李音译,第262~266页,及该后记注释8、注释9、注释13,上揭书,第280页),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面对所有人类社会中常见的仪式性杀戮,只要是在原住民群体(尤其是阿兹特克人)中进行的,那么就会被视为——伴随着某种深入骨髓的价值判断——残忍的‘人祭’传统,这是一种带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重新分类”(马修·雷斯托尔:《西班牙征服的七个神话》,李音译,第285页)。
[36][37][38]李硕:《翦商》,第549、24~25、24~25页。
[39]这种对现代中国人穿越中国古代后,大展征服与殖民拳脚的类型学叙事,在中国当代网络小说中颇为火爆。穿越者或抢在帝国主义者之前成为“帝国主义”,占领并开发当代中国领土外的地区,或对中国历史版图内的“古人”“揠苗助长”,后者本质上也是一种“殖民”想象,只是由“当代人”殖民“古代人”而已。
[40]李硕:《翦商》,第291、299、307、315页。公元前1000年前,骑马出行是否已经广泛存在仍存疑问;典型的游牧生活此时才刚露端倪,且相关人群以目前考古证据看或也以用马拉车为主。参看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部。
[41]在后来的基督教传统中,“羊群”与“牧者”成为信徒与教会关系的隐喻,更是尽人皆知。
[42][43][44][45][46][47][48]李硕:《翦商》,第454、454、455、456、456、457、457页。
[49]弗洛伊德的演绎参考氏著《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弗洛伊德认为摩西本人是埃及人;但在笔者看来,摩西是否是犹太人并没有摩西是否是一神教的实际创始人那么深切地体现现代性视野下“以今观古”的普遍症候,而更关涉弗洛伊德本人的犹太人身份。此外,考虑到李硕对存在一场相对轻视人祭的“中商宗教改革”的猜想(李硕:《翦商》,第133~142页),以及这场改革失败后或有当事者投向周人的推论(李硕:《翦商》,第300、463页),上面提及的这种一神教埃及萌芽、摩西完善说就与李硕本书中对文王“上帝”信仰的相关描述更相似了。
[50][51]李硕:《翦商》,第463~464、465页。
[52]今人坚持武王受命说者,见刘光胜《真实的历史,还是不断衍生的传说——对清华简文王受命的再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更近的研究,多持文王受命或文武皆受命的观点,见李忠林《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晁福林《从清华简〈程寤〉篇看“文王受命”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53]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03页。
[54]关于“革命”含义在清末民初之变,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5]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革命”话语在大众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形象又有新的变异;但这似未影响李硕的观点,也未曾体现于《翦商》之文本中,因此不赘。
[56]丰子恺:《缘缘堂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7页。该文原载1947年12月21日《京沪日报》第1卷第50期。
[57]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页。
[58]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70页。
[59][60][61][63]李硕:《翦商》,第482~483,497~499,502,504、510、515~516页。
[62]李硕:《翦商》,第525页。越来越多的周初考古材料能够证明,周灭商后并未在一夜之间废止人祭、人殉;较新的例子,如在被评为2022年中国十大考古成果的、被发掘者定年为西周初期,且猜想为周人祖地“豳”的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中,发现墓道中有殉人38具,二层台有殉人5具,共计殉人43具的大墓M90。该墓是目前所知商周易代时期殉人最多的墓葬(宋阿倩、豆海锋:《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商末周初殉人植物性食物组成分析——来自牙结石中的淀粉粒和植硅体证据》,《第四纪研究》2023年第1期)。对于类似情形,李硕或认为是来自武王时期对周人传统的偏离,或认为是商人的旧习,而未曾考虑,周人当时未必对殉葬习俗完全排斥。
[64]本书第二十六章名称。
[65][66][67][68][69]李硕:《翦商》,第484、526、541、535、527页。
[70]关于商周“民”字及“民”概念,可参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298页;周法高、林日升《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877~6822页;黄瑞云《关于春秋典籍中的“人”与“民”》,《文史哲》1978年第3期;林国敬《“民”字本义为奴隶说补证》,《理论月刊》2019年第5期。
[71][72][73][76]李硕:《翦商》,第562、561、521、451页。
[74][75]经观书评:《专访:作者李硕:深究历史深处的黑暗》,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2023年3月16日。
[77]古代儿童之“启蒙”自隋唐起,就更偏向伦理道德教育而非识字教育,见孙太雨、马彦超《我国古代蒙学教材发展历史与启蒙教育特点》,《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78]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79]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氏著:《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8~97页。
[81]坂井洋史:《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82]高瑞泉:《论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83]国家玮:《后启蒙时代文学教育的抵抗与超越——以钱理群的“屡战屡败”为中心》,《名作欣赏》2020年第3期。
[84]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3页。
[85]李硕在其较早写就的孔子传记中,曾使用“革命”一词描述周公的事功:“今天看来,不仅商人的血祭是千古之谜,西周和春秋人怎么刻意把这些历史记忆抹去的,也是个千古之谜,只有一部来源不明的《逸周书》,里面对周武王刚灭商的时候大搞杀人献祭记载得非常详细,说明周人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些,甚至很想学习这一套做法。真正的革命也许是从武王死后,周公掌权‘制礼作乐’开始的。”(氏著:《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4页)可见李硕对“革命”一词的使用是比较随意的。本节的相关论证,无意暗示李硕像刘小枫那样,自觉地试图对“革命”之内涵进行重构;而是强调李氏书写与“革命”相关的历史意象如“伐纣”时,会无意识地与其时大众中的主流“革命”认知形成互文。
[86]某种意义上,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也可归纳入这一传统之列,即认定“周公封建”在“五阶段论”的意义上,标志着社会形态的根本演进。
[87][97]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读库1205》,第293、293页。
[88][89][90][91][92][93][94][95][96][98][99]李硕:《翦商》,第1、16、516、529、529、554、560、573、528~531、528、529页。
[100]可参看丹·琼斯《权力之笼:1215年〈大宪章〉诞生始末与800年传世神话》,李凤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版;李红梅《历史与神话:800年的传奇》,《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王栋《神话与现代之间:〈大宪章〉在20世纪初的两种叙事》,《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101]思南读书会:《〈翦商〉:中国历史的转折性时刻》,微信公众号“思南读书会”,2023年5月24日。
[102]确切地说,保罗·利科这里所说的是“被训练的记忆”,参看氏著《记忆、历史、遗忘》第一部分第二章“被训练的记忆:使用或滥用”,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0~117页。
[103]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第79页。
[104]Luhman Niklas , Thoery of Society Vol 1,Trans Rhodes Barret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349.
[105]祁和平:《当代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02~203页。
[106][107][108][110]李硕:《翦商》,第564、554、555、564页。
[109]参见阿莱达·阿斯曼《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一部分第六章第二节,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56页。
[111]Paul Connerton, How Modernity Forget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132.
[112]祁和平:《当代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第192页。
[113][114][115]李硕:《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第274~279、276、277页。
[116][117]李硕:《俄国征服中亚战记》,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5、5~6页。
[118]李硕在本书第5页强调了这一点:配图是他(而非出版者)精心选取的,而且在行文中他常有“请看这张图片”之类的表述。
[119][120][121][122][123]李硕:《俄国征服中亚战记》,第55、101~102、208、362、363页。
[124][125]经观书评:《〈翦商〉作者李硕:深究历史深处的黑暗》,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2023年3月16日。
[126]如李硕欣赏过《启示》后,在“视觉层面”感到“非常真实”,觉得“殷商时代的杀人献祭场景,一下子就复活过来了,好像在我面前徐徐展开了一样”。忽友功德箱:《与李硕漫谈〈翦商〉:上古先民的黑暗史话》,微信公众号“忽左忽右Leftright”,2023年1月15日。
[127]这里所说的“视觉中心主义”,或改成“视听中心主义”更恰当些;李硕引为书写范本的,均为现代视听技术基础上的影像艺术;而讽刺的是,前文已在注释中提及,阿兹特克文化正具有以图像记事的传统,当然不难将这种传统区别于上述现代影像艺术,因为它们必须与口头传统相互配合才能得到符合本来语境的完整理解。而尽管李硕对表现中美洲文明的视听影像兴趣极大,但更多在意其人祭等符号化意象,而并未提起过当地人的图画-文字传统。
[128][129]许宏:《代序:我们陌生的形象》,李硕:《翦商》,第2、2页。
[130]阿兰·巴迪欧:“民主和商业世界的图像是具有微妙的可塑性和诱惑性,赤裸的权力隐藏其后,它本身没有图像,是一个赤裸的现实,但是它不能将我们从图像中解放出来,反而保障着图像的权威。”阿兰·巴迪欧:《当前时代的色情》,张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31][132]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文史哲》2023年第2期。
[133]需要指出的是,在《翦商》的书写中,李硕同样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现当代事象来描绘商人的活动,然而这种描绘停留在比喻而非通约的层次。例如,他说:“商族传统精神离不开那些分散而自治的商人族邑,就像美国的白人精神离不开南方种植园的‘红脖子’一样。”(李硕:《翦商》,第227页)又如,他以“西进运动”指称商人进出关中的行动。(《翦商》中有一节名为“第二次西进运动”,第274~277页)
[134][135]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文史哲》2023年第2期。
[136][137]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文史哲》2023年第3期。
[138]孔元:《“入关”与“伐纣”:关于中国崛起的两种知识论图景》,《东方学刊》2020年第3期。
[139][140]对“翦商学”话语的内容可参考知乎问题“如何评价知乎用户山高县的‘蛮夷入关学’?”下“姬轩亦”的、得到自笔者最后浏览为止8833赞的回答,网址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
359737298/answer/962015086,最后浏览时间2023年10月6日;及“二手圣经”:《从入关到伐纣》,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2020年4月10日。
[141]网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031670?sort=created,最后浏览时间2023年10月6日。
[142]将“入关学”“翦商学”等话语与即时战略类或寻宝类电脑游戏相联系的分析,可参考马逸凡《“入关学”的话语生成结构及其出路》,《东方学刊》2020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