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孙玉石先生是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在鲁迅研究与新诗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越,他的著作《〈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诗歌及其他》等享誉学界。孙先生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做讲座,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孙玉石先生,摄于2010年6月23日
孙玉石先生是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在鲁迅研究与新诗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越。孙玉石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重要作者,自1981年至2011年,三十年间,先生在本刊发表长短章共十五篇。惊闻孙先生离世,《丛刊》同仁哀悼不已。
孙玉石先生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第1期《论〈野草〉艺术构思的特色》一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鲁迅《野草》艺术构思的独创性与多样性之所在,之后孙玉石先生陆续在本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新诗研究的重要论文。2009年,适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三十周年,孙玉石先生出席纪念座谈会,对办刊提出期许:一、坚持学术的高品位;二、要学术的坚实性;三、要坚持文化立场。孙玉石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深厚情谊与深切期许,至今仍铭记于《丛刊》同仁心中。
为纪念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事业,我们在此推送先生1981年发表在《丛刊》的第一篇文章,以慰逝者。
论《野草》艺术构思的特色
孙玉石
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象阿尔迷达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
——杨格:《论独创性的写作》
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中,《野草》所以能够成为异峰突起的瑰宝,就艺术方面来讲,首先在于它那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艺术劳动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一个艺术家的全部创作过程,就是不断地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激发的思想和感受寻找新的艺术形象的过程。他总是依靠自己特有的艺术想象和幻想的能力,为概括深广的社会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创造独特的艺术结构和形式。这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所谓作家的艺术构思。
在一个作家创作活动的全部过程中,艺术构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精湛新奇的艺术构思,也就不可能产生富有魅力的艺术作品。艺术的生命是真实。但是,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要把生活的真实变为艺术的真实,没有作家的艺术构思是无法实现的。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构思的好坏优劣决定了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缺乏富于独创性艺术构思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作品。艺术的各种形式,大都如此。
比起其他一些文学形式来,象《野草》这样一类散文诗,更需要讲究艺术构思。
这主要是因为,散文诗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既不能象一些小说戏剧那样,多半是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或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来征服读者;也不能象一些诗歌作品那样,主要以作者真实的激情与和谐的韵律的一致来打动人心。散文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就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作家只有靠独创新颖而又优美隽永的艺术构思,才能为自己深刻的思想和感受找到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为此,作家付出的创造性的劳动越大,他的散文诗也就越富有独创性,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鲁迅的《野草》,就是这样一部以独特新奇的艺术构思传诵于世的散文诗集。就我们看到的“五四”以后出现的同类体裁的作品中,《野草》应该说是在艺术构思方面最有特色的一部。《野草》诸篇,虽然全都不是宏篇巨制,有的才只有几百字,却无不凝聚了鲁迅巨大的创造性的劳动。
人们都知道,鲁迅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向抱着自谦的态度。但对于《野草》,他却始终怀有一种珍爱的感情。一直到多年以后,他在写给肖军的信里,对于这部自己颇为珍爱的作品还自誉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这里所说的“技术”,自然是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以为如果首先用来指这部散文诗集特异的艺术构思而言,那可能是更为恰当的。
把诗情和哲理织进构思的蓝图
作家在创作中对艺术表现追求的基本倾向,往往决定了一部作品构思的主要特色。
从《野草》的第一篇《秋夜》开始,到最末一篇《一觉》结束,以至于稍后鲁迅将这二十几篇作品集印成册时写的那篇著名的《题辞》,鲁迅始终把这些抒发自己“小感触”的“短文”,当作抒情咏怀诗来创作。《野草》在《语丝》上连载发表的时候,鲁迅自然把它们看作散文诗,同时也一直被视为优美的散文诗而为人们竟相阅读。还在《野草》成书之前,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的文学青年台静农编了一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本书收录了一篇由许广平撰写、经鲁迅亲自校订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在这个目录里面,把《野草》称作“小品”。到了一九三二年写的《鲁迅著译书目》和《〈自选集〉自序》中,鲁迅更是径直把这些作品称为“散文小诗”或“散文诗”了。
鲁迅不仅努力使这些作品写得富有诗意,而且刻意在抒情诗意中阐发自己在战斗中体味的种种人生哲理。
当年与鲁迅一起办《语丝》的一个同人,在谈到鲁迅的《野草》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述:
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就看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去,对鲁迅说。
“这种争斗我看得够了,由他去罢!”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这段记述,写于鲁迅创作《野草》的过程中。所叙述的内容,应当是可信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鲁迅明白地告诉别人,“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了。
既注意追求散文诗所应有的浓郁的抒情诗意,又努力在其中蕴蓄自己深刻的哲理思想,这就决定了鲁迅《野草》艺术构思所必然具有的突出的特色。
散文诗《秋夜》,是《野草》的开篇,应该说是鲁迅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所写出来的了。在这篇作品中,鲁迅想表达他在现实斗争中长期积累所获得的一个感受:对于象秋夜严霜一般冷酷黑暗的社会,必须进行韧性持久的战斗。
鲁迅是怎样把这一点深刻的感受化为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形象的诗篇呢?
在构思这篇作品的时候,鲁迅没有使用直抒胸臆的描写手段,而是采用了托物咏怀的传统手法。他透过自己敏锐缜密的观察,在一个普通的秋夜所看到的自然景物里,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感受的最合适的手段。于是,秋夜中枣树与夜空的斗争,便成了这篇散文诗构思的基础与核心。找到了这个核心,也便找到了这篇散文诗构思的钥匙。鲁迅正是围绕两株枣树对那“奇怪而高的天空”不屈不挠的战斗为中心,展开了自己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艺术描写。
作品一开始,作者就以倔强的笔调写道:
在我的后园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对于这个颇为奇特的开头,过去一些评论者不能从全篇构思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因此便做出了众说纷纭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故作闹剧”,“徒弄花样”;有的人甚至说这一描写“简直堕入恶趣”;即使反对上述意见的同志,也没有了解鲁迅的意图,说这是按自然顺序观察事物过程中“得来的事实如此,就必须如此去写”。这些看法是不对的。其实,如果我们从鲁迅以枣树对夜空战斗这一艺术构思核心来看他对枣树这样的描写,就很容易了解鲁迅的用心了。这个开头,是诗意的开头,也含着歌颂枣树精神的哲理味道。
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接下去鲁迅没有写枣树,而是写枣树的对立面。写压在枣树上面“奇怪而高的天空”,这‘“夜空”䀹着“冷眼”,口角上现出“微笑”,以统治者的威严和姿态,“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由此,作者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极细小的粉红花”怎样在秋夜的“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通过这些描写,作者为我们暗示了现实中黑暗势力的沉重以及那些“做着好梦的青年”被摧残的情景。在这样带着鲜明时代特征的自然景物描写的背景上,鲁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枣树的长枝怎样“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怎样“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得天空为之“不安”,月亮也悄悄地躲避。作者以象征的手法,赞美了枣树的无私和坚韧,歌颂了他与黑暗势力斗争的不屈和刚强。
但是,作者的构思并没有在这里停止。鲁迅由这幅秋夜斗霜的画面又转到了自己的房里。许多小青虫,在玻璃灯罩上撞得丁丁的响,有的被火烧死,有的栖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于是作者引出了这样一段寓意深长的抒情描写:
猩红的栀子花开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到这里算是完成了这首散文诗的全部构思。最后这一段描写,似乎与枣树无关,其实不然。在作者完整的构思里,这并非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它不仅写得充满了诗意,同时也把鲁迅的哲理思想引向了更深的地方。鲁迅以诗的语言喻示人们:对于黑暗的社会,既不要象小粉红花那样做着天真的好梦,要象枣树那样清醒;也不要象小青虫那样做无谓的牺牲,要象枣树那样坚韧。鲁迅所体味到的这些深刻的哲理和全篇浓郁的抒情诗意,就是通过这一完整的艺术构思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秋夜》插图,《〈野草〉: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诗意和哲理的结合,是一般散文诗在构思上都应具备的特点。鲁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艺术构思上又有自己的特色。他重形象而少议论,重意境的创造而不务词藻的华丽。在一些作品中,鲁迅或是通过优美的生活图画,或是创造深远的抒情意境,达到了诗意和哲理相结合的效果。
在散文诗《雪》中,鲁迅生动地描绘了南北方冬天雪景的图画。这个画面里,有象“暖国的雨”一般江南的雪的滋润美艳,有这雪野中美丽的山茶和梅花,有那忙碌地飞着的蜜蜂,有孩子们塑雪罗汉的欢快情景;在这画面里,同时也有凛冽的寒冬中“朔方的雪”蓬勃奋飞的景象: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鲁迅在这幅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对比的优美图画里,展开并完成了自己的艺术构思。这画面,写得那么诗意盎然,情趣横生,同时又是那么不露痕迹地蕴含着鲁迅所深刻感受的生活哲理。对“隐约着青春的消息”的“江南的雪”的赞美,对“旋转升腾”于凛冽寒冬的“朔方的雪”的冷漠,展示了鲁迅对于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爱憎分明的态度。
与《雪》这篇散文诗不同,在《美好的故事》中,作者的艺术构思,是通过创造深远的意境来完成的。《秋夜》也写意境。但是,与《秋夜》不同,这篇中的抒情意境,不是自然景物的真实写照,而是想象中景物的虚拟的描写。
在昏沉的夜里,抒情主人公“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接着,作者逐一展开了对这有着“许多美的人和美的故事”图景的描写。这里有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的美景,有“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上织成的一篇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的故事。作者的巧妙构思把我们带入了这样美好的境界: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刺奔进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这幅图景,是那样清秀多彩,那样幽雅有趣,构成了一个深远优美的抒情意境。在这个深远的意境里,作者驰骋着自己对现实中不存在的美好事物的无边遐想。作者写“我”正要凝视他们的时候,故事的“美景”骤然消失,化为碎影。他又回到这“昏沉的夜里”。留下来的只是对这一篇“好的故事”的记忆。
身处“昏沉的夜”一般的社会,心存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憧憬。这一深刻的哲理思想,巧妙地织入了作者描写的那充满诗意的抒情意境中。
鲁迅在写作《野草》中,努力通过独特的构思达到诗意和哲理的结合,是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艺术构思中的诗情哲理来源于生活中的诗意和哲理。别林斯基说,“那里有真实,那里也就有诗”,“现实诗歌的任务就是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底诗,用这生活底忠实描绘来震撼灵魂。”鲁迅作品中的诗意和哲理,不是凭空的杜撰,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来自对现实生活和斗争的深刻观察与感受。“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生活底诗”,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鲁迅《野草》艺术构思的生活基础。
鲁迅不但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战士,也是一个诗的气质极强的抒情诗人。他有锐敏的诗人眼光。他能在为一般人所忽略的平凡生活中寻出不平凡的诗意的矿藏。他能在那些极为普通的生活现象中寄托很不普通的思想。
我们来看一看《求乞者》吧。
这是一个怎样司空见惯的平凡的故事啊!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这时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拦着磕头”,“追着哀呼”。看到这种情景,鲁迅写道: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腻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下面,作者的构思把我们引向了“我”怎样设想自己变成了一个乞丐,用什么方法求乞,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布施,得出的结论是: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全篇都是人们常见的生活情景,但却不是人人都可以从这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的诗意和哲理。鲁迅透过日常的生活现象,看到了其中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鲁迅以对求乞者的态度做为中心,构思了这篇充满象征意味的散文诗,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那个灰暗吃人的社会,决不能奴隶式的求乞和哀呼,应当进行义无反顾的战斗。
《求乞者》以及《野草》许多篇章说明,艺术构思不仅仅是个技巧问题,也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问题。没有对生活的真正认识,没有由生活激发的创作冲动,就构思不出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诗篇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诗意和哲理,又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把诗意和哲理写进自己的诗篇,这正是鲁迅《野草》具有优美的诗情和深警的启示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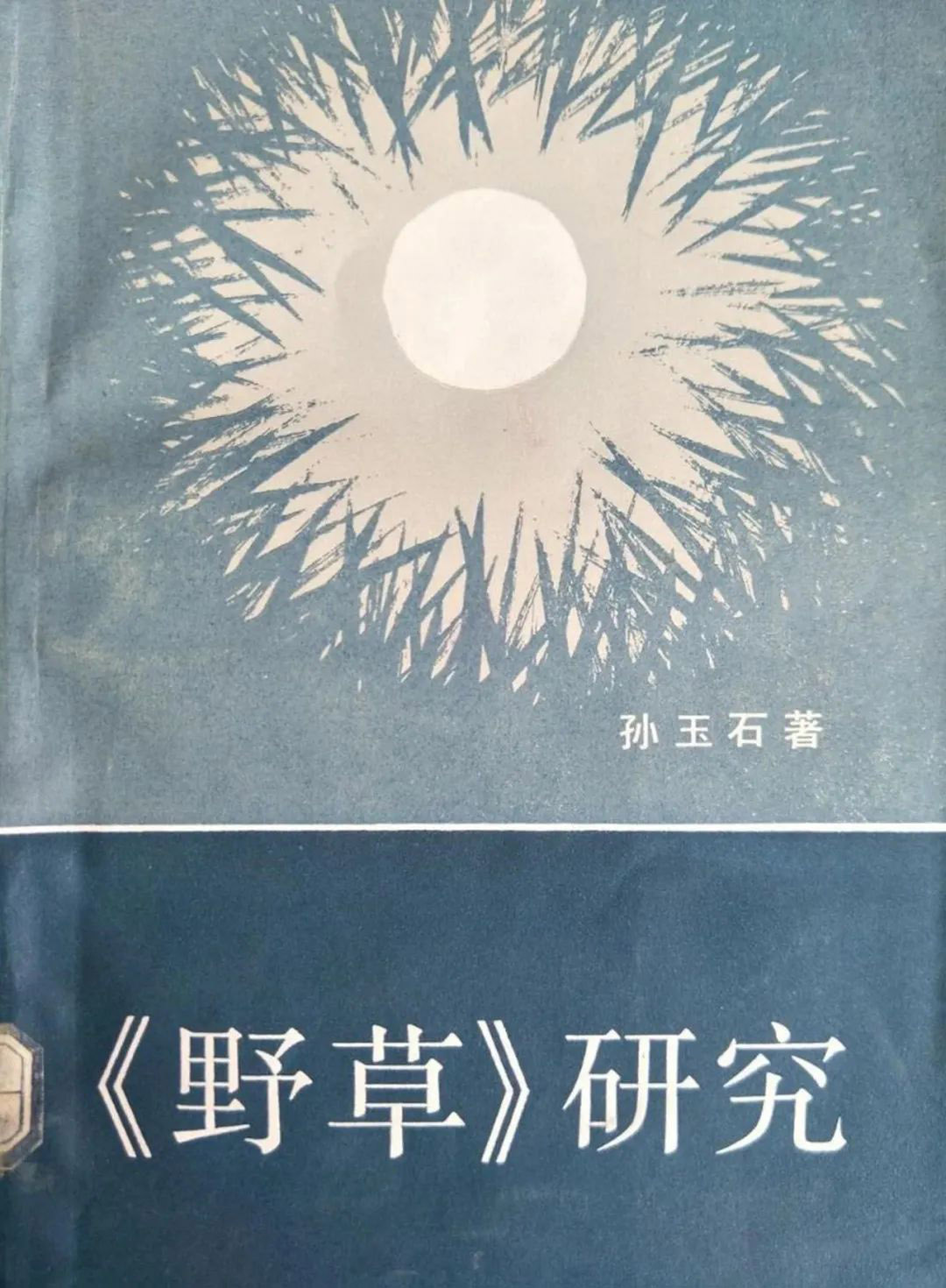
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给现实情怀披上梦境的面纱
《野草》追求诗意和哲理相结合的艺术构思,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方法表现的。描写梦境,就是其中之一。
在《野草》中,从一九二五年四月写的《死火》,到同年七月创作的《死后》,有七篇散文诗连续是以写自己梦境的形式出现的。这些散文诗,每篇都毫无差别的以“我梦见自己……”的格调开头。这样,就形成了《野草》中这一组散文诗在艺术构思方面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幻想的梦境中抒写自己的思想感受。
鲁迅描写梦境中的种种景象,是为了抒发现实生活的感受。他把虚幻的梦境和真实的生活是那样奇特而又和谐地编织在一起,使得这些作品中的现实的情怀披上了一层梦境的面纱。同样是抒情散文诗,却表现了更加幽深曲折的色彩。
《死火》是以“我梦见自己”开头的第一篇。在这篇作品里,鲁迅是以极为离奇的想象来展开自己的艺术构思的。构思的中心和契机,是象征革命力量的“死火”。构思展开的内容是“我”在梦中与“死火”的相见和遭遇。鲁迅分三层意思来发展自己的思路。首先,写“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忽然坠在“冰谷”中了。这象征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黑暗中国的“冰谷”,是那样寒冷而无情,“一切冰冷,一切清白”。其次,作者接着写“我”梦中于冰谷中看见“死火”后的见闻和对话。他看见了被冰冷的山谷冻结了的革命的“火焰”。这“火焰”虽被冻死,仍然保持珊瑚一样美丽的颜色。“我”努力用自己的温热,使“死火”重新燃烧起来,并且决心带着“死火”逃出“冰谷”,以便使这革命的火焰“永不冰结,永得燃烧”!这一部分,是全篇构思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在梦境中见闻的中心。梦境的第三部分,写“死火”忽然跃起,“我”被突然而来的“大石车”碾死在轮下,而象征黑暗势力的“大石车”,也同时坠入冰谷中,与“死火”同归于尽。而那死去的“我”仍然得意地庆幸“死火”永远不再受“冰谷”的摧残了。

《死火》插图,《〈野草〉: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是一篇完整的梦境与现实相结合的故事。鲁迅在奇幻的艺术构思中编织的故事,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内容。这就是鲁迅所赞颂的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点燃革命之火的高尚品格。全篇的构思都以梦境中的冰谷为背景,通过我与“死火”的相遇,解救,对话,直至最后与“大石车”同归于尽的几个环节,展开了这篇作品的艺术构思,使作者的思想情怀表现得深刻而又含蓄,取得了正面描写和直抒胸臆的方法所不可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在梦境中展开艺术构思,并非就是作者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鲁迅一直反对用臆造代替现实的“说假话”的艺术,认为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鲁迅说:
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
鲁迅写梦境,是抒真情,不是说假话;是艺术创造,不是凭空捏造。在鲁迅的笔下,不论自己梦见的事物和情景是如何离奇,如何怪诞,都无不打着现实生活的深刻烙痕。幻梦的构思仍然必须以现实生活和真实感情为基础。在《死火》中,幻梦中的“我”与“死火”离奇的际遇和结局,明显地展示了鲁迅对现实生活中革命者遭遇的同情和对革命火焰的赞美。在《狗的驳诘》中,“我”在梦中与狗的饶有趣味的对话,离不开鲁迅对现实生活中反动阶级及其走狗文人的洞察与认识。《失掉的好地狱》中,那个梦中出现的“美丽,慈悲”的大魔鬼给“我”讲的全部故事,那地狱中人与魔鬼的斗争,分明透露出鲁迅对反动军阀以及以新的面貌出现的统治者的强烈憎恶和清醒认识。即使是象《墓碣文》这篇最离奇的梦中情景,也是以鲁迅思想中自我解剖的心境为蓝本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描写梦境,只是为了更好的抒情的一种手段。描写梦幻的情景,只有以真实生活为基础才能构思出诗意盎然的艺术篇章。鲁迅这几篇散文诗的艺术构思,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艺术创作的规律。
在七篇以梦境为构思手段的散文诗中,《颓败线的颤动》、《立论》和《死后》表现了更加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这些作品虽然也是以“我梦见自己……”开头,构思的展开也依然是梦中的情景,但是它们与《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不同,梦中的故事和情境,不尽是现实中所不可能有的幻象,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写梦境与写现实在这里达到了更好的统一。
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构思是通过梦中先后的两段故事展开的。这两段故事全是梦中的境界,却充满了人间的生活气息。在这一篇里,梦境实际上只是抒情的一种假托手段。作者用心着笔的是现实中常见的那一出多么令人颤栗的生活悲剧:母亲年轻时由于贫穷,用出卖肉体养育了自己的女儿;多年以后,这位成了家的女儿和丈夫一起,却以怨恨和鄙夷来对待为他们牺牲了一切的垂老的女人。象征性的结尾溢满了作者的愤怒:垂老的女人在夜深的荒野中以全身躯的战栗,向那些忘恩负义者复仇。这里没有离奇的描写,几乎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至于《死后》和《立论》,更是运用严肃而又富于幽默感的笔调,展开了梦境中的故事,使得这些故事成为现实生活图景真实而又生动的再现。《立论》一篇,倘若去掉了“梦见自己”的开头,整个故事仍然不失为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讽刺诗篇。至于《死后》一篇的构思,则更加巧妙地体现了梦境与现实在构思中交相辉映的特色。
《死后》这篇散文诗的构思是极为奇特的。作品开头就说:“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接着又记起了生存时一种恐怖的设想:“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毁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鲁迅在这篇散文诗中,就是以这样的奇想为依据来进行艺术构思的。篇中所描述的,就是“我”在死后由于“知觉还在”所经受的一切。
鲁迅写梦中死后的几个寓意很深的场景:第一,是死后躺在路上,黎明时所感到的种种景象:几声喜鹊与乌老鸦的聒叫,看热闹人的切切嚓嚓的议论,讨厌的蚂蚁和青蝇在自己身上和脸上爬来爬去。由于一阵风吹来,青蝇临飞走时,还为它未能找到“做论的材料”而叹一声“惜哉!”为此,“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这里写的种种现象,或者是现实中存在的内容,或者是象征着现实生活的情景。鲁迅的愤怒和讥刺,具有鲜明的现实战斗色彩。第二段,鲁迅沿着自己构思的路子,写了“死后”的另一番经历。这里有巡警恶狠狠地申斥“怎么要死在这里?……”有装进棺材后所感到的“六面碰壁”的悲哀。对于社会的冷酷,正人君子们的攻击,鲁迅含蓄地进行了讽刺。第三段,鲁迅把他讽刺的笔锋又伸向了更加广泛的世态人情。那个勃古斋书铺跑外的小伙计,在顾客死了以后,还那么不厌其烦地推销明版《公羊传》,这一段对话写得那样真实,那样辛辣,读了令人叫绝。最后一段在整个构思中是十分重要的。作者在这里点化了他构思这篇“死后”故事的真正用意。对于那些祝我死亡的仇敌,“我”偏偏使他们不快地活着,又影子一般地死掉,“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从作品开头进入梦境,到结尾离开梦境,“我”又“坐了起来”,全篇都是梦境中死后的感觉和经历。其中“我”死后的所见所闻,直到最后发出的深沉的感慨,又全部都是鲁迅对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观察与感受的结果。鲁迅在梦境中“死后”的特定构思里,展开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图画。在这样的图画里,鲁迅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愤怒,对世态人情的讥讽。现实的战斗情怀披上了一层梦幻的面纱。鲁迅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说梦,就难免说谎。”这是对那个只有在梦中才是自由的黑暗现实的愤激之谈,和艺术上的梦境的构思不完全一样。在《死后》中,鲁迅是“说梦”,但并非“说谎”。这里浸透着鲁迅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离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感受,梦境中的一切,就不可能那么真切生动,妙趣横生,使人读了都无不为之感到惊叹不已!
七篇散文诗都在梦境中展开艺术构思,但各篇的表现方法又变化多端,避免了雷同的毛病。同样写梦境,描写的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是不同的。有的是想象中怪诞不经的对话,如《狗的驳诘》;有的是幻象一般奇特的故事,如《墓碣文》、《失掉的好地狱》;有的则又是一幅幅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的图景,如《颓败线的颤动》、《死后》。在这些奇妙的作品里,鲁迅以丰富的想象和幻想,为自己的诗情和思想创造形式。他以摇曳多姿的梦境的描写,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整个现实的幻想的世界,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天地。鲁迅在这些散文诗中,显示了艺术构思方面的匠心和功力。
在散文诗中,用梦境与现实结合的构思方法抒情,并不是鲁迅自己的创造。一八八二年,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在《欧洲新闻》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五十首《散文诗》(原题为《衰老》)。其中,就有几篇作品是写梦境的。而且这些篇也是以“我梦见自己……”开头的。鲁迅《野草》中这七篇散文诗,在构思上显而易见是受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启发和影响。但是,鲁迅的作品不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简单的模仿。鲁迅同样用梦境抒写现实情怀的构思方法,却进行了自己精心的创造。鲁迅这几篇散文诗在艺术构思方面的独创性,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散文诗中别具一格的艺术珍品。
描写个别——迈向艺术构思的起点
歌德说过:“理会个别,描写个别,是艺术的真正生命。”“到了描绘个别这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构思也就开始了。”
从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这是一般艺术创作所遵循的原则,也是一切作家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小说戏剧如此,散文诗创作也如此。越是描写一般的作品,雷同者越多。越是描写个别的作品,就越富于独创性。任何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总是善于寻找出新颖的个别的事物和情景,开始自己构思的起点。鲁迅《野草》的构思就是这样。
《野草》是鲁迅思想中一些“小感触”的艺术结晶。《野草》的这种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在构思上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以小见大,通过个别的形象和情景,来抒写自己热烈而又深沉的诗情。这种构思的特点,表现在《野草》的许多篇章中。
《腊叶》在《野草》中是写得颇为深情的一篇。黑暗社会的残酷压迫,永无休止的战斗生活,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他长期陷于与疾病的交战之中。多少身边的青年和亲友,对鲁迅的身体表示真挚的关切。他们出于至爱的深情,劝慰鲁迅先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以利更持久的战斗。对于青年和亲友这种“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的心情,鲁迅是十分了解的。为了表示自己感激的心情和不惜生命而战斗的决心,鲁迅写了《腊叶》。
关于这篇散文诗写作和构思的深意,孙伏园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
……《腊叶》写成以后,先生曾给我看原稿;仿佛作为闲谈似的,我曾发过一次傻问:何以这篇题材取了《腊叶》。先生给我的答案,当初便使我如获至宝,但一直没有向人说过,至今印象还是深刻,觉得说说也无妨了。
“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雁门集》等都是无关宏旨的。”这便是先生谈话的大意。
这里所说的“许公”,即许广平。从这段忆述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这篇散文诗中是寄托怎样的深情了。

《腊叶》插图,《〈野草〉: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样的深情却是通过最平淡无奇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一片小小的病了的枫叶,成了鲁迅抒情构思的中心。对病叶的联想,成了全篇抒写自己“感兴”的主要内容。“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四百余字的短文,作者就从这里展开了自己的构思。这枫叶是怎样来的呢?去年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凋零,绯红的枫叶,落在地上。其中一片被虫蛀孔的病叶,被拾了起来,夹在《雁门集》中,目的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到了第二年,这病叶又出现在眼前,但斑斓的颜色已不复从前了。于此便引出了作者的感慨:“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鲁迅这里集中写了对斑斓病叶的回忆和重见病叶时的心境。鲁迅就是在这样个别的事物上进行艺术构思,写出了自己一个深情的思绪:用“病叶”象征自己的身体,说将坠的病叶的斑斓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想长期保存是不可能的,以此曲折含蓄地对那些想保存自己的亲友表示了感激和谢意。鲁迅告诉人们,社会又如严冬一样冷酷,连耐寒的树木“也早经颓尽了”,更何况枫树呢!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只能无所顾忌地进行战斗。鲁迅在一片病叶的构思里表达了多么一往深情的战斗思想。
诗的构思必须从描写个别开始,但并非一切个别都是诗。这里就需要作家创作时的艺术概括力和想象力。在鲁迅的笔下,从描写个别开始的艺术构思,并没有成为对生活中个别情景和事物的单纯临摹。鲁迅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诗,也善于在生活中提炼诗。在把自己那些来自生活的“小感触”构思成一篇篇散文诗的时候,鲁迅充分发挥了他提炼生活的本领和艺术想象的才能,因而找到了最能抒发自己感情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段,也就是从个别艺术形象开始的多样新奇的艺术构思。由于鲁迅构思的独创和新颖,这些艺术描写,不仅没有与别的作家作品雷同的现象,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很难找到一点因袭的痕迹来。
《野草》二十几篇,大都是通过对个别事物的描写来进行抒情的。这些作品通过描写个别情景和故事展开构思的方法又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借景抒情或托物咏怀,如《秋夜》、《雪》、《风筝》、《好的故事》、《腊叶》;有的是通过描写人物形象抒情,如《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过客》、《这样的战士》;有的是写故事和事件表达思想,如《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颓败线的颤动》、《一觉》等。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通过个别事物展开抒情的构思是一样的,但是在选择什么样的形象,怎样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些具体的构思方式上,就各有千秋,大不相同了。同样是写作者内心自我解剖的,《影的告别》和《墓碣文》,在怎样通过个别描写展开艺术构思方面,就完全不同。
《影的告别》,是同自己思想中彷徨怀疑情绪告别的一篇十分优美的抒情散文诗。作者没有象一些作品那样,采用直接抒发自己的心绪然而加以否定的构思方法来完成作品的主题。他依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选取了人在睡梦中将会有影来向自己告别这一极为新奇而又具体的情景,来展开自己全篇的艺术构思。整篇散文诗,除了开头一段极简要的叙述外,全部都是影在向睡着的形告别时的自白。影的形象是具体的,又是一种思想情绪的代表。他不信虚无飘渺的天空,憎恶残酷黑暗的地狱,对未来的黄金世界也感到渺茫。他要告别形而独自运行。他不能不彷徨于光明与黑暗之间,又不甘于这种彷徨。他宁愿被黑暗吞没,让形独占光明。在那个世界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这些全是影缠绵幽深的自白。这些自白所表达的,正是鲁迅当时产生而又决心摈弃的消极思想。鲁迅通过影的告别所进行的艺术构思,是那样的奇特而又具体,使这篇作品在《野草》乃至整个现代散文诗中都是不多见的佳篇。
同样是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批判自己思想中旧的影子,在《墓碣文》中,由个别到一般的艺术构思又有新的创造。这里不是睡着的人影子向形的告别,而是梦中的“我”同墓中死人思想的决裂。在这一篇中,作者描绘了墓碣上含意深隽而又颇为费解的文字,孤坟中脸上蒙蒙如烟然的死者,墓碣阴面残存的谜一般的字句,死尸在坟中起坐时的对话,我怀着恐怖决绝心境逃离墓碣。这些是作者依靠丰富的想象创造的一个具体的特定的情景。它是那样荒诞不经,那样阴森可怖。这个梦境中的特殊情景表达了鲁迅同旧思想决裂的情怀。艺术构思贵在创造,贵在新奇,贵在具体,《影的告别》和《墓碣文》以不同的艺术构思体现了这一共同的特点。
我们说描写个别是迈向艺术构思的起点,并不等于说在构思中只能以具体的小的事情和小景物作为描写对象。所谓的描写个别是艺术构思的起点,是指作者要通过独创的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和意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怀。这个形象和意境,可以小到一片病叶,一个秋天的夜景,一段有趣的对话,一次奇妙的邂逅,也可以大到梦境中一次神与魔的交战,一次梦中死后的见闻,一段寓意深远的荒野过客的经历。以这种更为广阔的生活场景描写做为艺术构思基础的作品,同样体现了具体而鲜明的独创的特色。
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过客》的构思。
在《野草》中,《过客》可以说是艺术构思上最有独创性的一篇。这是一篇短剧体的散文诗。在这篇散文诗中,鲁迅是以过客形象的描写做为构思的起点和中心的。跋涉于旅途上一个困顿倔强的过客,在黄昏时分,经过荒野上一间土屋的时候,与住在那里的老翁和小女孩发生了一段对话。过客没有听老翁要他停下来的劝告,没有接受小姑娘好意的馈赠,又沿着是路非路的荒野前进了。这就是《过客》构思的基本内容。过客的形象饱沾着鲁迅自身战斗经历的血泪,寄托了鲁迅坚韧不拔而又苦苦思索的思想情怀。鲁迅构思这篇意味深隽的故事,就是从这位久经跋涉而永不停步的过客形象开始的。围绕这个过客形象,作者构思了另外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用艺术形象揭示了过客的精神世界。那个老翁,暗示了昨日过客的形象。他虽然象过客一样,经历了很长的道路,体味了人生的酸辛,但在重重的艰难困苦面前,他没有勇气走到终点。对于前方叫唤的声音,他不理睬,这声音也渐渐不叫了。这是一个在革命和人生的漫长征途中停止下来不再前进者的象征。那个小女孩的形象,则象征着美好的人生的青年时期。她没有经过痛苦压迫生活的煎熬,也没有品尝死亡恐怖的滋味。对过去,她不了解。对未来,她充满幻想。老翁说前边是一片坟墓。她却说那里开满着美丽的鲜花。老翁,过客,小女孩,象征了人生道路上的三个时期。鲁迅把这三个象征性的人物安排在一起,让他们围绕停止还是前进的问题展开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告诉人们,在同旧社会的战斗中,在对革命路途的寻求中,不能象老翁那样消沉颓唐,不能象小女孩那样天真烂漫,要象过客那样坚韧不拔,永不停步。战斗的哲学思想浸透在鲁迅充满诗意的构思中。这里找不到脱离艺术形象的空泛议论,全篇都是形象的描写和诗情的对话,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又多么富于生活的真实气息。作者的艺术构思从具体的个别的艺术形象开始,却孕含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最富于独创性的构思,是不可模仿的。《过客》就是一篇以个别形象描写概括广阔生活内容为构思特点的散文诗。它是独创的,因而它也成了一篇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模仿的艺术珍品。

《过客》插图,《〈野草〉: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从个别描写开始做为艺术构思的起点,根本上就是在散文诗的构思中不要以空泛的议论代替形象的抒情。构思的生命就是让艺术形象说话。离开了形象的独创性,艺术构思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在《野草》中,有些作品看来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没有描写一个人物形象,没有一个具体的景物描写,但它在构思上仍然没有离开从个别形象开始这个基本特点。《希望》写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惊异于青年的消沉和冷漠,鲁迅借用裴多菲的诗句为全篇的线索,提炼并运用了“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这样形象而又诗意很强的感慨,把自己痛苦的心境写得回肠荡气,委婉动人。作者内心积郁的感情,通过形象而曲折的构思表现出来了。《希望》、《淡淡的血痕中》、《一觉》,这一类的散文诗,都不是写景,写故事,写人物,而是写作者内心的激情。这激情,同样在构思中以个别的形象描写为起点,找到了十分形象而又贴切的表现形式。鲁迅《野草》构思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在这些散文诗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艺术构思的独创性是一个作家才能最显著的标志。十八世纪英国启蒙主义诗人杨格说:“一个天才的头脑是一片沃土和乐园”,在那里“享受着一个永恒的春天”。而富于创造性的作品,就是这个“春天的最美的花朵”。鲁迅的《野草》艺术构思的独创性,充分显示了他作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巨大艺术才能。《野草》就是这一才能所开出的“春天的最美的花朵”。
此文原刊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