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随
内容提要
顾随在数十年的诗学批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以人生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其“人生诗学”借助一系列中间概念型构了人生实践、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内在统一性。本文通过分析顾随的鲁迅论、晚唐诗论和毛泽东诗词论揭示其“人生诗学”的内在理路,试图增进对顾随诗论中一系列核心观念的认识。虽然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人生”对现代中国诗学的重要性,但多是从新诗人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忽略了顾随这种处于新旧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顾随的“人生诗学”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成为有别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分析框架的、构筑中国现代诗学的另一条进路,理应得到重视。
关 键 词
顾随 人生诗学 鲁迅 废名 晚唐诗风
由于著述较少,顾随长久以来不为学界所注意,而注意顾随的,又往往只有治古代文学、甚至只有治词学的研究者。旧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没有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而通过课堂讲授而非专业化、学院派论文传达出来的思想观点就更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就现当代文学界而言,缺少一种对顾随更为深入的专题式分析和对其价值的具体阐发。[2]
其实,顾随远非一位旧式文人。自广平府中学堂毕业后,顾随考入北洋大学预科,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有很好的西洋语言和文学的修养。[3]后来又与浅草-沉钟社诸人交游,与冯至结下终生的友谊,顾随创作的小说《失踪》更是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顾随的旧体诗文讲录中,新文学作家和作品随处可见,他常常使用新文学作品做例证,表达自己对新文学的观点,许多观点相当有见地。对顾随来说,创作“现在的诗”与分析、解剖、欣赏“古人的诗”应当用同一种态度。[4]他的总体诗歌观念(一种超越新、旧的对“诗”的本质的探讨)中包孕着他对新诗的评论,新文学的阅读体验与传统诗学的营养互相生发,统摄在一种总的现代精神之中。在笔者看来,顾随的诗歌观念不仅区别于以“纯诗”观念为核心现代主义的诗歌观念,同时也不同于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观念,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诗学中长期被忽略的另一条进路,即“人生诗学”。
本文将首先讨论顾随的鲁迅论,集中在顾随如何将鲁迅的小说看作是“诗”的描写,这在文体论的意义上可以反映出顾随对诗的本质的看法。其次将讨论顾随的晚唐诗论,在新诗被诟病“不是诗”的危机中时,现代主义诗人试图回到晚唐,以温庭筠、李商隐一脉的诗风来赋予新诗以诗意,而顾随对晚唐诗风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以同为周作人弟子的废名为代表的这一脉现代派诗人。最后,本文将讨论顾随对毛泽东诗词的评注,主要涉及一个概念,笔者称之为“诗的形容词化”,这是古代诗论中没有出现过,而在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一种“诗”的使用形式,这种使用体现着诗歌观念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 与文相对的诗
顾随讨论鲁迅的地方很不少,在《顾随全集》中,专文就有三篇,分别为《小说家之鲁迅》《论阿Q的精神文明及精神胜利法》《〈彷徨〉与〈离骚〉》。[5]此外,陈均还搜集到一篇佚文,是顾随于鲁迅去世后一周写成的《鲁迅小说中之诗的描写》,有一个副题是“纪念鲁迅先生”。[6]其中《鲁迅小说中之诗的描写》发表于《中法大学月刊》,而《小说家之鲁迅》则是顾随1947年在中法大学文史学会的演讲稿,这两篇文章在内容上有承继性。
在顾农看来,顾随的鲁迅论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是顾随对鲁迅的评价之全面,认为鲁迅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集许多‘家’于一身”[7]。第二是顾随特别强调鲁迅小说中的诗味。第三是强调鲁迅小说中的余裕,用顾随在演讲中用的另一个词来说,就是一种“多余的附加”[8]。虽然顾农在总结这三点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陈均发现的这一则佚文,但《鲁迅小说中诗之描写》的内容也可以被涵括进顾农所说的顾随鲁迅论的三个要点之中。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顾随的演讲稿,这三点可以归结为一点,也就是鲁迅小说与诗歌美感的同一性,或者也可以说是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与作为诗人的鲁迅的同一性。
如果说《鲁迅小说中之诗的描写》一文还是标举了“诗”作为论鲁迅的关键词的话,那么1947年的演讲则完全是要论述作为小说家的鲁迅。顾随在演讲中列举了鲁迅那么多“家”之后说:“现在我所要同诸位一谈的,乃是小说家的鲁迅(Lu Xun as a novelist)”,但他马上就说“在两部书(即《呐喊》《彷徨》——笔者注)中,先生表现出除了成为一个小说家、思想家而外,同时是诗人。我所要谈的特别是后一点”。[9]可见,虽然顾随给鲁迅加上了诸多的“家”的名号,但在顾随眼中,“诗人”这一身份是最重要的。鲁迅小说中的诗性、诗味是尤为吸引顾随的地方,也是顾随要着重申发的。同时,在顾随对鲁迅小说中的诗性、诗味的分析中,我们可以间接了解什么是顾随眼中的诗。顾随眼光的独特性背后,乃是他的诗歌观念的独特性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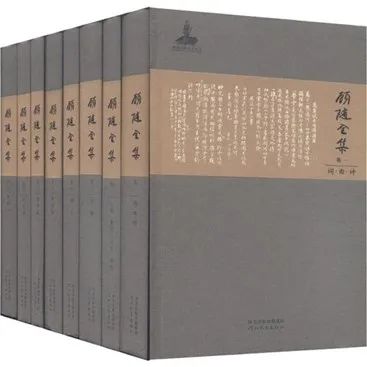
《顾随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文类“辨体”开始的时代,从六朝的“文笔之辨”到唐代由韩愈、杜甫引发的“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争论,再到宋代发端于黄庭坚、陈师道的“本色论”以及宋明以降的“诗文之辨”,中国传统诗论中积累了大量的关于诗文辨体的学说,而对诗的本体的认识往往正建立在文体互辨的基础上,其实对晚于诗兴起的词来说也是如此。通过“辨体”,不同文体的本质内涵被厘清,文体之间的尊卑、正变关系也逐渐确立。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尊卑关系都逐渐被打破。在“诗文之辨”的发展过程中,诗逐渐由“文之余”(韩愈“余事作诗人”[10])发展为“文之精”(唐桂芳“文之精者为诗”[11]),拥有了特异于文章的价值;而在“诗词辨体”的过程中,词这种文学体式也同样是由“诗余”发展成常州词派眼中的“比兴、变风”[12],从而取得了可以与诗相近的地位。
当然,顾随对鲁迅小说中的诗味的发掘一不是为了区分小说与诗歌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式,二不是为了提高小说这种文体的声价(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诗高于小说的价值阶序),但我们可以通过顾随的表述分析出他眼中的诗的特性。顾随在1947年的演讲中主要分析的,认为其中有诗性、诗味的,乃是以往不太为人们注意的鲁迅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小说,比如《肥皂》《兄弟》《高老夫子》《幸福的家庭》。
总的来说,在顾随的分析中,这些小说中的诗味主要体现在环境描写之中,所举的具体的例子基本上都在这些小说的结尾,也就是高潮之后的平静,正是在这平静中涌动着一种诗意:顾随评价《肥皂》中的描写“静穆”“纤细”,评价《兄弟》中的描写“调和”,评价《高老夫子》最后的描写的诗意甚至令国技“增价”。[13]这种诗味大概也可以用“温柔敦厚”来解释,因此,顾随说这三个还只是“旧诗的境界”,是“中国诗的传统的精神”。但他同样认可《幸福的家庭》中的幻想因为“象征”、“神秘”而又“写实”而具有诗意,《示众》中对夏天的描写因为可以作为当时整个北平城的象征而具有诗意。[14]通过“象征”而诗,这是中国传统诗论中不会涉及的一点,却是西方诗论与中国新诗理论的核心之一,至多可以与传统词学中对“意内而言外”[15]的强调发生一些联系。但顾随在这里非常强调的乃是象征中的真实,《幸福的家庭》中的象征体现着一种心理的真实、人物刻画的真实,而《示众》中则体现的是时代性的真实。真实是具有诗意的,诗歌也必须建筑在真实之上,这是顾随诗歌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有所谓“诗化小说”的研究传统,这大体上发端于吴晓东和钱理群。对吴晓东来说,诗化小说有“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但什么叫作“语言的诗化”,文章中并没有解释。吴晓东也诚实地说:“‘诗化小说’的概念也只是称起来方便而已,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界定。假如换个说法,称其为‘散文化小说’也未尝不可。”[16]对钱理群来说,诗化小说其实就是一种抒情性很强的小说,诗性就等同于抒情性。[17]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诗化小说的代表人物是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鲁迅的一些篇章也被认为带有诗化小说的特点,主要是《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故乡》。总的来说,“诗化小说”是一个在“叙事”与“抒情”的二元分析框架中诞生的概念,描述的是一类叙事性弱而抒情性强的小说。
顾随当然认可鲁迅的《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诗味浓厚,但通过将《肥皂》《兄弟》《高老夫子》《幸福的家庭》诸篇纳入“诗性”的范畴,顾随将鲁迅具有诗意的小说的范围远远扩大了。或许是一句启引下文的话,顾随说:“诸位知道:讽刺文章是最难写成为诗的。”[18]这句话同时表示,他认为讽刺也可以成诗,这与钱理群、吴晓东就诗论诗的抒情诗歌观念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顾随会将这些带有讽刺性的内容看作是“诗”的表现?这当然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诗论中对“美刺讽谏”的理解。《诗经》在汉儒的阐发中,明确标为“刺诗”的就有一百二十九篇,这形成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也就是说,顾随眼中什么构成诗,什么不构成诗,不是仅由诗歌文本内部所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一种诗歌与外部的关系,这个外部是时代,同时也是时代中的“人生”。这不仅和他其他的一些诗论(比如对传统诗人过分注重“作”而非“写”[19]、多是“字”而非“事”[20]的批判)共同构成了与新诗倡导者一样的对传统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比部分单纯强调诗相较于社会人生的独立性的新诗人看得更远。
但这些都不是这篇演讲中最深刻的部分,也不是顾随最要强调的观点。因为顾随认为上面这些“诗之描写”总的来说都有偏向于“静”的嫌疑,而“人生呢?可完全是动的。因此,那静的描写与表现也就不免减低了小说中人物的动力,并且冲淡了小说中的人生的色彩”[21]。顾随说:
那就是说:既爱人生,就不应该对大自然有着那么多的过剩与不必要的描写;然而居然有。这,我以为是先生的旧文人的习气还未洗刷净尽的原故。他是中国人,又读过许多旧诗人的作品,并且那么富于诗才,所以写小说的时候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22]
实在找不出比这样的表述更能体现顾随对“人生”的标举和高扬的了。对顾随来说,前面那些诗意的描写、诗意的表达并不完美,甚至有所缺憾,而最重要的诗意表达,最高妙的诗意表达,乃是将“人生与动力一齐诗化了而加以诗的描写和表现”,只有这样,“才是小说中的诗的描写与表现”。[23]顾随是通过举《水浒传》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的。顾随认为,只有做到了将人物的动力和人生完全诗化,并且避免单纯的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这才能“对得起鲁迅先生”,也才能在“在鲁迅先生园地之外开辟新园地”。[24]这是讨论现代“诗化小说”的学者所不会关注的,也是深刻建筑在“纯诗”观念之上的现代诗学理论所盲视的地方。这是一种动态的诗学观念,也是扎实地建基于人生的、以人生为最高价值的诗学观念。
这种观念在顾随1936年的文章中没有清晰表达,但依然有迹可循。那就是这样一句话:“但是鲁迅先生无论怎么在他的小说中有着诗的描写,始终是清晰而明净,带着散文的性质的。”因为“他不曾教读者去作梦”[25]。顾随在这篇题为讨论鲁迅小说中的“诗之描写”的文章临近末尾时,提出鲁迅小说所始终具有的“散文性质”,这自然令我们想到废名在1934年11月发表在《人间世》的《新诗问答》一文中提出的非常有名的论断:“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而新诗“内容是诗,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26]但很明显,在顾随这里,“诗的描写”是可以“带有散文的性质的”,“诗”与“散文”这两种文体的内在质素与其说对立,不如说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或者说应当统一。这种统一正建立在对“作梦”的抵抗中,即对“朦胧”“恍惚”“麻醉”“幻梦”这种逃脱人生、寻觅另样世界的拒绝,而要“睁了眼看”,要拥抱在人间中的真实人生并在人生中积极行动。与之相对,“作梦”(“诗人之梦”)却构成了废名等人的诗学观念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废名对温庭筠、李商隐一脉晚唐诗风的分析和赏鉴中。[27]这种区别其实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对诗人与人生关系的认识。其实虽然很多人都将顾随视为京派文人,但他对周作人、废名一路的文论和诗论并不完全服膺,虽然很少有直白的表露,但很多文本内部都潜藏着一种对话关系,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废名
二 新旧之间的诗
在象征派和新月派相继衰落之后,1930年代崛起的现代派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他们的诗歌创作自不必提,一大批著名的现代诗人产生了;他们对现代诗学理论的推进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在现代诗学理论和新诗创作同时进入危机之后的一次突破和革新。他们不仅吸取西方象征派、意象派的营养,同时发掘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碎金,掀起了一股在1930年代诗坛上影响甚巨的“晚唐诗热”。诸如卞之琳、何其芳等众多现代派诗人,尤其是居住在北平的现代派诗人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将他们自己的新诗创作追溯到晚唐温李一脉。[28]而为这股风潮进行学理上的总结,并将晚唐诗风与新诗创作在理论上统一起来的,是废名。废名明确地讲,“新诗将是温李一派的发展”,其原因乃是“这里无形式,意象必能自己完全,形式有时还是一个障碍了”。[29]这种评判标准直接根植于他的名言:“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而新诗“内容是诗,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30]
对新、旧诗的区分而言,形式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恐怕是二者最为直观的不同。顾随对诗的形式问题有许多论述,在总的关怀上,他与新诗理论是一致的。他赞许杜甫拗律中的一种非整饬的美感、一种能够对旧诗形式有所超越的创造,并将其与鲁迅那并不好听的话放置在同一脉络中:“鲁迅先生明知道说什么让人爱听,可我偏不爱说,杜甫拗律亦然。”[31]形式的“破格”是必要的,但这需要与诗歌中表达的总体精神一致。因此他甚至主张新诗不要用韵,这当然不是说新诗要放弃音乐美(他对要剥除音乐美的新诗理论是嗤之以鼻的),而是要向“表情周到,音节自然”的儿歌学习[32],这难道不是与新诗理论中对自然音节的倡导有内在的相通性吗?其关注的核心正是音乐上的自然、精神上的纯真。其实顾随非常赞同很多新诗倡导者对中国旧诗的批判,但同时也看到中国新诗由于“拨乱反正”而“矫枉过正”。顾随认为,旧诗是太讲技术从而忽略了内容,几千年是“陈陈相因”,而新诗则完全相反,注重思想,却完全忽略了文字的技术,“以致最低的文字技术都没有”。[33]因此,顾随强调一种“自由”的辩证法,这也是一种“自然”与“勉强”的辩证法、“学”和“能”的辩证法。不“学”就不可能“能”,不能经过“勉强”这一阶段,也就不能达臻真正的“自然”。如果单纯想要“自由”,不要任何“束缚”,那么“自由”也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需要学习的。所以“练拳的式子是不舒服的,功夫练到家则自在舒服;禅宗戒律束缚人,而大师则行所无事”[34]。这同样是对新旧诗体辩证中对诗歌形式的深刻见解。

卞之琳
就废名的这一著名论断来说,形式上的问题,即什么是“诗”的形式,什么是“散文”的形式比较容易理解。顾随与新诗人一样,都认可对束缚的破除,对自由表达的追求,只不过顾随并不认可在旧诗中没有任何“自由”,而新诗由于有了看似“自由”的形式便一好百好、就能通达诗的境界,因为核心毕竟在于诗人对语言文字的掌控力,在于诗歌中所体现的诗的精神。但什么是作为核心与本质的属于“诗”的精神?废名并没有对什么是“散文”的内容,什么是“诗”的内容作出清晰的表述。西渡对废名的这种说法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从诗歌与散文的分别来说,散文寄生于现实,从现实中获得存在的力量,诗歌则投身于可能性,倾心于尚未诞生的现实。散文是对现实的肯定,而诗歌常常是对现实的质疑,也可以说,诗歌是一个问题,而散文是一个答案。散文是应用性的,而诗歌是非应用性的。[35]
也就是说,散文的内容乃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内容,直接关涉现实世界,而“诗歌虚构的世界与现实并不相涉,它从根本性质上说是不及物的”[36]。这当然是一种带有很强烈的“纯文学”观念的诗学观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陈独秀区分“文学之文”“应用之文”[37]的回响。
而废名对以温庭筠、李商隐所代表的晚唐诗风的推崇,主要是认为他们的诗词创作很好地体现了“诗”的这种独立性。诗的内容不假外求,不用与时事政治发生关系,而自己就可以构成自己的合法性来源,自己就是一个自足完满的世界。废名认为温庭筠的好处就在于他的诗词来自幻想,也就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完全自造一个世界,“他的美人芳草都是他自己的幻觉”,而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理想中都寻不到,完全是一种“诗人之梦”。[38]
因此,在废名看来,温庭筠和李商隐这一类晚唐诗人体现着一种诗人的伦理、“贞操”,或者说就是一种诗人的理想。[39]这种理想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诗人的自觉意识,是一种力图去除任何附加在诗歌之上的、妨害诗歌本身自足之“美”的东西。诗的价值在诗本身,诗人的价值就在诗人本身。所以这样的诗学观念一方面是对专业的、以诗歌为志业的诗人的召唤,另一方面则是对一种独立于社会政治的诗歌评价体系的召唤。而专业的、以诗歌为志业的诗人正是废名在晚唐诗人身上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诗歌,在废名看来,就是“诗人的感情碰在所接触的东西上面”,所接触的又恰恰“与诗感最相适合”而成功的结果。[40]因此,成为一个专业化的、有“贞操”的、有个性的,并且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不对社会政治承担责任的“诗人”乃是作诗成立的前提:“你如不是诗人,你也便休想做诗!”[41]创作诗歌的首要因素乃是诗人的个性,同时要求诗人要持守专属于诗人的伦理,这是“诗的内容”的保障。诗歌完成于写作之前。
不过,硬要说温庭筠和李商隐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诗人意识、有诗人的“贞操”还是比较牵强的,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职业诗人,而他们的诗词创作跟他们仕宦生涯的不得志有很大关系,很难推断说在他们的意识中就将作诗看作是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诗人,还是应该首推在南宋末年出现的“江湖诗人”群体,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批真正的专业诗人也非常推崇晚唐五代的风格。日本学者内山精也认为他们对晚唐诗风的推崇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没有那种要为全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他们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他们放弃了传统士大夫所一直坚持的那种社会责任感,从而只是通过写诗来满足自己的表现欲;其次,乃是因为晚唐诗多是绝句,易于学习、容易上手,而且不尚用典,不以学力区分诗词好坏。内山精也说:“这里面隐藏着晩唐体流行的最大秘密。”[42]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废名的缺憾,他始终将“诗人”与“文人”做关联,认为古代的诗人所作的“散文的内容”的诗具有粉饰太平的功能性,而忽略了传统“诗人”与“士人”的统一性。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真正为人所宝贵、成为经典的作品,根本不是“应用性”的宴席酬酢乃至应制诗、粉饰太平的颂圣之作,而大量的都是这种“质疑”现实、针砭时弊的带有“美刺讽谏”性质的作品,这里面涵纳着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却是废名所推重的那种只注重美感的诗歌所缺乏的。
在这个前提下,顾随的晚唐诗论值得我们关注。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江西诗派与晚唐诗风的择取中,顾随同样反对江西派,推崇晚唐风,这一点与废名等新诗的倡导者和宋末元初的专业诗人群体具有一致性。顾随认为“江西派只是工具上——文字上的功夫。只重‘诗笔’,不重‘诗情’”[43]。相较于文字上的雕琢功夫,“情”在顾随的评价体系中显然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
在对晚唐诗风的讨论中,顾随当然同意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的晚唐诗人的作品非常美丽精致,并且认为他们就是可以跟西洋唯美派诗人相对应的中国的唯美派诗人。不过他尤其强调了小李杜与西洋唯美派诗人之间的不同:“西方唯美派似不满意于日常生活,于是抛开了平凡事物而另去找、另去造”,而“义山则不然,不另起炉灶,亦不别生枝节,只是根据日常生活,而一写便美化了、升华了”。[44]这种观察与废名大不一样,废名正是将西洋唯美派的特点套用在温庭筠身上,认为温庭筠正因为具有幻想的特质,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别造一个世界,所以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诗。顾随则说:“李义山好就是韵的文学好,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45]纵然认可李商隐的诗中有梦的朦胧美,但仍要首先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李商隐创作之人间性,李商隐是在人间中、在生活中发现美好,而通过他的诗心使日常生活美化,这便是通过诗心来“升华”了这“最不美,最俗”却最有意义的人生。[46]这才是小李杜的高妙所在。
然而,纵然高妙,却并不伟大。顾随虽然说如果只在中国诗人中举一个人做代表,在中国诗中举一首诗做代表,他要举李商隐,举《锦瑟》诗,这看似是很高的评价了,但他马上就说:“然此并非诗的最高境界。”[47]顾随一直称小李杜为“真诗人”,却从来不称其为“伟大诗人”,这个价值序列是很重要的:“小杜诗其好处只是完成得美,得到和谐。无论形式、音节及内外表现皆和谐。此点或妨害其成为伟大诗人,而不害其成为真诗人。”[48]换句话说,“完成的美”不错,但远不是最好。这种诗心或许是成为伟大诗人的基础,可以引领人们窥见诗的堂奥(因为在作为伟大诗人的陶渊明那里,顾随认为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的诗心和精神[49])。如果仅止步于此,也可以,毕竟可以涵养诗心,教人诚与真,但若以此为最高价值,则大谬。
以小李杜为代表的晚唐诗风所涵养的诗心,用顾随的话总结,便是“欣赏的态度”和“有闲的精神”。顾随认为“欣赏的态度”是任何诗人都不能缺少的,而诗歌发展到晚唐,尤其强调一种对自我的欣赏,“欣赏自己的一切”[50]。同时,诗人与常人不同,需要有一种“有闲的精神”。顾随认为,哪怕是写痛苦、激昂或者是奋斗,也需要“有闲”。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顾随就认为太像呼号,缺少一种“有闲的精神”,“快不成诗了”。[51]那么什么叫“有闲”?如果我们仅看顾随对小李杜的评价,很自然地会把这种“有闲”与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浪漫结合在一起,似乎就和废名等现代派的观点类似,可是他在批评杜甫这两句缺少“有闲的精神”时,则分明指向的是对待苦痛的态度。写美“有闲”似乎不难理解,写苦痛如何“有闲”?要人在苦痛中还要欣赏其美,坚持小资的浪漫情调,岂非人也?因此,顾随的“有闲”完全与现代派的诗学观念大异其趣,强调的乃是一种超越的态度,这种超越正是对“小我”之“实感”的超越。只有超越了一己之私,而胸怀众生,才有可能超越当下的苦痛,形成一种有距离的观照。
职是之故,对一般的、肤浅的、故作的“有闲”的姿态,顾随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因为那是一种逃避,是不敢面对真实人生的借口。针对李涉的“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顾随说:“宁愿同学不懂诗,不作诗,不要懂这样诗,作这样诗。人生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52]这种“浮生半日”的“偷闲”完全是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是对人生的厌弃和虚掷,是一种纵贯古今的帮闲文人的“无行”,在今天则毋宁说就是一种“小资”的浪漫情调。真正的“有闲”他则在冯延巳的词作中看到,那是“和泪试严妆”(《菩萨蛮》)。顾随说,这是在“极悲哀时,对人生也一丝不苟”[53]。无论如何,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人生,这构成了对一己一时的苦痛悲哀的超越。真正的诗与诗人对待人生的态度密切相关,其精神扎根在人生之中,其超越也绝不是自外于人生。只有人生是价值的最高尺度,只有人间才是个体生命的目的和依归,通过这个尺度,才能实现真正的“有闲”,达成真正的超越。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将李商隐看作是可以代表中国的诗人,但顾随对他是很有所保留的。因为顾随认为李商隐的“欣赏”只是欣赏自己,是顾影自怜、敝帚自珍,虽精妙有情调,却孤绝无世界。他的好处在于用诗心写了人生,但“其病在‘自画’,虽写人生,只限于与自己有关的生活”[54]。顾随非常严厉地说:“此类诗人是没发展的,没有出息的。”而真正伟大的诗人,却是他在前面说不完全“有闲”的杜甫,“其作品或者很粗糙,不精美,而不能不说他伟大,有分量”[55]。顾随一针见血地指出,写苦痛是一个诗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文字技法上的能力,而是一个诗人的心力。他从王国维那里借了一个词——“担荷”:“老杜敢写苦痛,即因能担荷。诗人爱写美的事物,不能写苦,即因不能担荷。”[56]“担荷”正是对一己之私的超越,是对众生之痛的体感。因此,顾随反复强调他所说的这种有闲和欣赏,乃是一种“人格的修养”[57]。诗的格调与人的格调密切相关,而人的格调恰恰就体现在对人生的态度之中。所以能写小我的生活之美,是一种真的诗心,具有“有闲”的基础,即不困于生活之中,而能有所旁观;但若要成为伟大的诗人,具备真正的“欣赏”与“有闲”,那就需要有对一己之私和只能书写美的双重突破,要能够欣赏众生,担荷苦痛,这当然是一种更广大的超越,才能谈得上“伟大”。
三 作为形容词的诗
顾随在小李杜身上看到的“有闲”,其实与他的另一个非常有名的、发端于王国维的诗论概念——“高致”有内在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说,“有闲”与“高致”都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讨论的都是诗人与人生的关系。顾随的“高致”说主要出现在他的两“词说”(即《稼轩词说》与《东坡词说》)以及讨论李白诗歌的讲录稿中,很大程度上承袭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高致”的看法,这一点往往被专事顾随研究的学者所忽视,已有台湾学者蔡莹莹指出。[58]但也必须要强调的是,顾随对王国维“高致”说有很重要的发展。

王国维
这种“高致”并不只是在就诗论诗的意义上的一种诗歌写作技法上的高妙,而与诗人本身的品格及其对待人生的态度密切相关。顾随最早是在讨论辛弃疾的词的时候采用“高致”这个分析概念的,他认为辛弃疾写作词,最初并没有一个想要在词中写出“高致”的动机,而且因为辛弃疾“用世念切,不甘暴弃”,所以他写作词的时候,往往用力过猛,用意太显露直白,顾随慨叹:“英雄究非纯词人也”,但辛弃疾毕竟“性情过人,识力超众,眼高手辣,肠热心慈,胸中又无点尘污染,故其高致时时亦流露于字里行间”。[59]因此,“高致”首先是诗人的品格,是因为辛弃疾的识见、胸襟和品格,所以他虽然稍显直白,不擅雕饰,但仍然可以将这种“高致”在文字中显露出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两次提到了“高致”。一次是在评价苏轼与辛弃疾的词作时,认为他们“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60]另一次则是对诗人与宇宙人生之间的关系发表了意见,认为“高致”乃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能够“出乎其外”的态度:“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61]从这两条词话中我们能看出,对王国维来说,“高致”与词人主体有莫大关联,词作中的“高致”正是词人“高致”品格的体现。彭玉平认为王国维的“高致”是“境界”说的延展,“从原先比较纯粹的创作特征扩大到作为创作主体的词人身上”,同时认为王国维用伯夷和柳下惠来比附苏轼与辛弃疾,乃是就“其气度高逸、情致脱俗而言的”。[62]也就是说,彭玉平认为王国维是在能够对宇宙人生“出乎其外”的意义上,即能够超脱宇宙中一时一地的束缚、人生中欢喜悲哀的牵绊,将苏轼、辛弃疾视为“高致”的代表。在文本证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似乎我们也只能做如此的解读。
那么就应该讲,顾随从技法与人生两个方面对这个概念有进一步的拓展阐发。就技法来说,顾随强调诗人应当有对语言文字“音”“形”“义”的掌控能力(他认为这一点是现代白话诗人所极端缺乏的),只有对文字有完全的掌控,能够“深入乎文字之微”,同时作者的神致能够“超出乎言辞之表”,才能达到“其高致自出”的效果。[63]所以顾随在评析辛弃疾的时候还是会说“英雄究非纯词人也”,言语表达对诗词创作的重要性在顾随的诗论中是有充分强调的。但对顾随而言,“高致”首先同时也更重要的是形容诗人主体的,这毫无疑问。从他的苏辛词说中即可看出,他当然认可只有一个伟大的诗人才能写出伟大的诗,诗中“高致”乃是诗人“高致”的反映。不过他将王国维的只针对“出乎其外”的“高致”扩展为一种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动态人生观。这体现在他对李白的评析中。
顾随承认王国维的看法,认为“身临其境者难有高致”,“高致”毕竟还是一种超出的精神,身临其境则往往容易为“得失之念”所困,这种“得失之念”从上一章对“有闲”的分析可知,就是一种仅仅关涉“一己之私”的“得失之念”。但顾随马上就对“高致”做出了自己的补充性解释,顾随认为有两种“出乎其外”。第一种是“与此事全不相干,如皮衣拥炉而赏雪”,也就是一种完全将这个世界客体化,而自己与此无涉,只是一种将对象浪漫化的观看,顾随认为“此高不足道”,这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要令人生厌;第二种乃是“著薄衣行雪中而尚能‘出乎其外’,方为真正高致”。[64]这第二种顾随认为是真正的高致,其实正是一种能够“入乎其内”,同时“出乎其外”的人生观,是在世界人生之中的超越。而李白却只是第一种“所谓的”“高致”,因为他入得不深,所以凌空蹈虚,好像显得品格奇高,其实那是一种“跳出、摆脱”,是为寻“高致”而跳出了人生。[65]只有“能入污泥而不染”才是真高尚,而这一点“太白做不到”。[66]
顾随认为,这第二种的真正的“高致”,古今以来只有陶渊明一人可以做到。[67]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顾随对什么是“俗”、什么是“不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放在今天也毫不过时,正可警世:
卧龙之“不俗”在其六出祁山,而不在其抱膝长吟;彭泽之“不俗”在其躬耕南亩,而不在其采菊东篱。换言之,能以六出祁山,乃可以抱膝长吟;肯于躬耕南亩,乃许其采菊东篱。不然者,抱膝长吟、采菊东篱,其“俗”入骨不复可耐也。[68]
这里的“俗”替换为“高致”有何不可?替换为“有闲”有何不可?一般的看法,“有闲”“高致”“不俗”不正是“抱膝长吟”“采菊东篱”?而顾随却认为不能“六出祁山”,只追求“抱膝长吟”,不肯“躬耕南亩”,只想要“采菊东篱”的人,不仅不是不俗,而正是俗不可耐。在顾随看来,“有闲”“高致”“不俗”是在对人生的深切体悟中生发出来的,意欲通过逃离人生的方式达致“有闲”“高致”“不俗”,其结果只能是“临阵脱逃”“此高不足道”“‘俗’入骨不复可耐”。而顾随对鲁迅小说中所谓“多余的附加”的强调,也可以在这个逻辑中获得理解。一方面,顾随认为作品中的“闲笔”和“余裕”可以“使那作品更为艺术化,更为有诗意”[69]。但另一方面,正如本文在第一节中提到的,这种“闲笔”和“余裕”却毕竟是偏于静的方面,妨害了作为“动”的人生的总体表达。因此,只有是作为“动”的人生内部的“多余的附加”,也就是诗化了这一“动”的人生的表达才是他尤其推崇的。
在顾随的诗论中,诗与人、与人生永远要建立第一位的关系,诗歌的优秀和伟大总是要以诗人的优秀与伟大为前提,而诗人的优秀与伟大则坚实地建立在他与人生的关系上。顾随虽然也多次提到诗词写作技法的重要性,但顾随对技法的强调终究远逊于对体悟人生和诗词创作之间的关系的强调。比如在讨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中“闹”和“弄”字的赞许时,一般人的讨论往往都“死于句下”,但顾随却说,对初学者而言,这些“拶”“捺”乃是不得已的着相,但绝不能将这两句的好处认作是单纯的“字面功夫”。[70]或许我们可以说,通过“有闲”“高致”“不俗”这些“中间概念”,顾随实际上在诗人、人生、诗歌之间建立起了坚实的通贯的逻辑,这些中间概念,作为价值尺度,在人生与诗之间画上了等号。因此,顾随在讨论鲁迅的结尾,就将“诗”的概念扩展到文学之外的人生:“小说中的诗的成分必须要多;岂独小说而已哉?人生、人世、事事物物,必须有了诗意,人类的生活才越加丰富而有意义。”[71]这是顾随的“人生诗学”最高的一层意思,即诗不是一种文学体式,而毋宁说是一种生活态度,在人与人间世界的关系上,在行为处事和品格修养的价值尺度上,“诗”与“人生”是一样的。“诗”变成了可以修饰人生的形容词。
因此,在顾随晚年几乎是最后的重要作品,也就是对毛泽东诗词的笺释中,顾随将毛泽东看作诗人,而这里的“诗”,其意涵已经无限扩大了。在以往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尤其是对旧式文人的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后与新中国成立前往往被划为泾渭分明的两个时期,认为他们的文艺观念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对这种变化的讨论和分析往往意味着对现实政治切断了原有学术思想的自然发展的批判。对顾随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学习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固然对他产生了影响,不过,从他对毛泽东《实践论》的批注上来看,他之前就形成的文艺观念或许正是他接受新观念的基底,他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六经注我”的态度。[72]笔者要强调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诗论不应被单纯地理解为受到革命现实主义影响的突变,新的文艺观念与他既有的诗学观念的接榫是非常顺畅的。
在《毛主席诗词笺释》的“总论”部分,顾随对毛泽东身份评价的段落非常类似于1947年《小说家之鲁迅》中对鲁迅身份评价的段落,也都在文章的起始部分。在《小说家之鲁迅》中,顾随说:
鲁迅,在学术与文艺上说起来,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诗人,又是小说家,集许多“家”于一身,简直无以名之,也许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与大而化之之为圣吧。[73]
而在“总论”中,顾随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具有这种铺排的性质: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大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同时,他又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学家……这可该怎么说才好呢?“博学而无所成名”呢?“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呢?[74]
虽然这两段文字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也都引用了《论语》中评价孔子的“博学而无所成名”[75],但这二者有很重要的不同。对鲁迅,列举了诸多“家”之后,顾随是没有下结论的,只是说应当用“圣”来进行总括性的评价,并且说明在这篇演讲稿中,着重要谈的是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但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顾随在提出“该怎么说才好呢?”的问句之后,是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的:“爽利点儿,一言以蔽之,主席是诗人。”[76]顾随明确地用“诗人”这个身份涵括了上面所列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大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同时,他又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学家……”“诗人”在毛泽东的评价中取得了与“圣”在鲁迅评价中的地位,并且可以作为在这些“家”之后的核心身份而提出,这不能不说是顾随诗学思想的一大发展,因为如果只是由于毛泽东创作了诗词,就说毛泽东是诗人,那么这种诗人身份是完全无法与毛泽东的其他身份相媲美的,遑论统摄其他身份了。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诗”的边界大大地拓宽了,不再只是一种文学体式,也不再只是文学的代表,而变成了对人生和事业的总的形容词。
顾随进一步解释,他说毛泽东是诗人有广、狭二义。广义中最重要的乃是“主席的事业就是壮丽的、伟大的诗篇……这美丽的河山、这强大的祖国以及各族人民的这幸福生活,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着六亿人民进行着革命和建设而写成的诗篇”[77]。广义之二,毛泽东是“一位语言艺术巨匠,所有他的语言不论出之于其笔下或其口中,无处不闪烁着诗一般的壮丽的、灿烂的火花。这些诗一般的语言塑造我们的灵魂,鼓舞我们忘我劳动地去做前人未有的事业”[78]。只有狭义才是指毛泽东的诗词创作。
文体意义上的诗词在这一种新的“诗”的观念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恰恰是以人间为取向的涵括众生的人生的事业。毋庸置疑,这样的事业也是最伟大的事业,而能够形容这种最伟大事业的辞藻,在顾随看来,正是“诗”。这样,顾随的诗论就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颠倒,从真正的诗是与人生紧密相连的诗变成了最伟大的人生就是一种诗的人生。诗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价值,这种价值因为诗的崇高地位而可以赋予实际人生以指导。此外,顾随之前在诗论中,也比较强调诗人对语言的掌控能力,但在此,这种属于诗的语言能力由比较指实的对字的“音”“形”“义”的掌控能力,变成一种塑造灵魂、鼓舞人前进的能力。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宣传意义上的工具论式的语言观,而强调的毋宁说是一种可以通达彼此人生的属于诗的语言能力。诗的作用,就不仅在于抒发一己之情,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沟通,而更是一种由心及心的普适性的感召能力,这种感召力是以伟大的人生作为基础的。这里或许正藏着作为20世纪革命与旧体诗词剪不断关系代表的毛泽东诗词的秘密,或许也才是中国革命中“抒情”成分的本质意义。
所以,在“总论”的最后,顾随得出了这一最重要的结论:“一切伟大的诗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活出来的。”伟大的人生即是伟大的诗篇,要去书写诗篇,就要去“活”出真正的、伟大的人生。而正如顾随在鲁迅论中所说的,人生的根本在“动”,因此在这里顾随也用了当时时髦的词说,“活”出来的人生就是在“斗争”中成长的人生。成为伟大的诗人与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人统一了起来,都需要生活的锤炼,取决于对待人生的态度。换句话说,相较于诗在文字上修辞的精妙绝伦,诗中的人生的“高低、大小、广狭和深浅”才是第一性的。[79]
这种观点其实在顾随1954年写给外甥孙书秀的信中就有了。孙书秀来信中开头有两句话:“生活呀!它使我知道了很多;然而,也告诉我,不知道的更多。”顾随就看作是诗,这正是一种超越文体形式,通过他所认为的诗歌本质来识别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的论断方式。而他认为这两句诗(按形式来看,这正是新诗、白话诗)写得好,其原因就在于“生活”。他教导孙书秀:“古、今、中、外,大诗人所写的诗,都是活出来的。即是说,就实际生活里学习来的。”[80]而想要学习写诗,则需要天才与努力的结合,没有天才的话,纵是“写到老掉了牙,也是白搭”,但有了天才,没有努力也不行,而努力的内容则有三项,即读书、写作和深入现实生活。[81]对顾随而言,无论旧诗还是新诗,其所需要的质素都是一样的,在诗人的天才之外,都需要与人生发生关系,诗人需要在人生中历练,需要形成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顾随在之后的信中教导孙书秀,要想写好诗,必须要先写好散文,“散文写不好,诗是不会写得好的”[82]。这当然强调的不是对散文形式的把握,更重要的正是废名所批判的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散文的内容”。诗正是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的“散文的内容”的“诗化”,也就是在现实人生中的超越,是在一己生命中对其本身所含纳的普遍性的追求。正因此,顾随说:“诗在文学中是最难于写作的一种。”[83]诗也就可以成为最高妙的文学形式,可以成为赞美伟大人生的形容词。
作为形容词的“诗”,也就是突破了文体形式之一种的概念而发展成对人生、事业的修饰语,甚至是一种总的修饰语,是一个现代产物。我们今天好像认为在传统中国,诗就具有这种意义的延展性,具有浪漫情调的象征性,所谓“诗意”。其实用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这乃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84]我们今天常常讲苏轼的“画中有诗”,其实苏轼所说的“画”和“诗”都有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王维自己的《蓝田烟雨图》与“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一诗。[85]在中国古代,“画中有诗”基本上都要做这样的理解,即具体而非抽象的诗。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但我们今天的诗意概念已经变得非常抽象了,正如前文所提示的,诗意、诗性、诗化往往就等同于浪漫、抒情,不仅可以修饰事物,也可以形容人生,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属性的形容词,这与中国现代诗学观念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私以为,这种转变至少要经历四个逻辑链条:一是文学相对于人生的独立性,即一种纯文学观念的产生;二是价值论上的,要使得文学价值高于个体生命而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三是诗歌地位的提升,诗歌成为文学中地位最高的文体形式;四是诗歌意涵的扩大,诗歌可以与人生产生比附和对应关系。前三项可以说或多或少都与西方思想(比如德国早期浪漫派)有关、与政治观念的变化有关,而最后这一项是对第一项纯文学观念的某种反动和批判,其完成有赖于中国传统诗论中“诗法”和“世法”的同一性,也有赖于这种诗学观念的现代转型,正是以顾随为代表的这种诗学观念完成了最后的这一项转变。
余 论
“人生”在近现代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汇,构成了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谢应光就认为“自我”、“纯诗”与“人生”共同构成了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86]正如苏雪林总结的:“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文艺鹄的都趋向于人生派。”[87]但其实,对于什么是“人生”,不同的人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胡适恰恰在杜甫的那些与社会现实关联不大的《绝句漫兴》等“小诗”中看到了“人生”[88],这与废名等现代派诗学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对谢应光来说,“人生”的诗学本质观可以说肇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平民文学”的倡导,后来发展成为“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其核心观念是文艺要描写现实人生,甚至要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季剑青说顾随的“人生”观以新文化中“为人生而艺术”的观念为底色,因而有异于王国维的源自叔本华的、希望求得人生解脱的人生观,乃是一种“近代人生观”。[89]
顾随的诗学观念当然与这种人生观有某种一致性,但差别仍是重要的。在顾随的观念中,似乎并没有“为人生而艺术”的这个“为”字,人生与艺术(诗)乃是合二而一的。这也是笔者将顾随诗学观念概括为一种“人生诗学”而不涉及一种逻辑上具有先后次序的命名法的原因所在。这既是方法论上的人生就是艺术(诗),艺术(诗)也是人生,同时更是价值论上的应当将人生活成艺术(诗)、好的人生本身就是艺术(诗),应当用艺术(诗)书写人生、好的艺术(诗)贯注着人生精神和生命关怀。
因此,在顾随的观念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顾随从来不认为文艺要直接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同时也反对那种超越于现实人生,在别处寻求意义的诗学观念和人生态度。顾随的“人生”绝非现实政治,同时也不等同于没有经过修养过程的自然人性状态,或一种单纯寻求享乐的生活方式(在今天,“这才是人生!”往往代表的正是这种生活态度)。如果说政治乃是一种激发能动性的过程的话,顾随的“人生”乃与这种真正的政治发生关联,却与那种短暂的、战术性的现实政治有不小的距离。顾随说:“文学的确是宣传,而绝非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文学宣传,因为他们太低能了。”这种不低能的真正的宣传,正是在人生的召唤的意义上进行的。
赵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100084
注释
[1]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辽宁教育》2013年第18期。
[2]其实孙郁在2008年就撰文赞誉顾随的“眼光”,即身处京派文人圈、对周作人执弟子礼却能发现鲁迅的伟大,见孙郁《顾随的眼光》,《档案天地》2008年第12期;季剑青也曾经讨论顾随作为新文化濡染下的知识人的本色,见季剑青《顾随与新文学的离合》,《泰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不过孙郁的文章偏于随笔性质,篇幅较短,而季剑青的文章则主要是通过对顾随材料的梳理,强调其思想观点与新文化众人的内在一致性。因此,都没有能引起现当代文学界足够的重视。
[3]顾随求学经历可参见赵林涛的考证,见赵林涛《顾随求学经历考证》,《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5日。
[4]顾随:《漫议N、K二氏之论诗》,《顾随全集卷六》,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5]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4~364页;《论阿Q的精神文明及精神胜利法——读〈阿Q正传〉札记之一》,《顾随全集卷三》,第365~368页;《〈彷徨〉与〈离骚〉》,《顾随全集卷三》,第369~373页。
[6]陈均:《“顾随与鲁迅”补说——顾随佚文〈鲁迅小说中诗之描写〉读后》,《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3期。
[7][9]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第355、354~355页。
[8]顾农:《顾随与鲁迅》,《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第3期。
[10]韩愈撰,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十律诗·和席八十二韵》,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16页。
[11]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五八五唐桂芳一·白云集自序》,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2页。
[12]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张惠言论词·附录·一、词选序》,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17页。
[13]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第355~356页。
[14][18]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第356、355页。
[15]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张惠言论词·附录·一、词选序》,第1617页。
[16]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17]钱理群:《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9]顾随:《说辛词〈贺新郎·赋水仙〉——糟堂笔谈之一》,《顾随全集卷三》,第83页。
[20]顾随:《〈文赋〉十一讲(增订)——体裁与风格之五》,《顾随全集卷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09页。
[21][22][23][24]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第361、361、362、363页。
[25]陈均:《“顾随与鲁迅”补说——顾随佚文〈鲁迅小说中诗之描写〉读后》,《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3期。
[26]废名:《新诗问答》,废名:《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页。
[27]废名:《谈新诗》,废名:《论新诗及其他》,第28页。
[28]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何其芳:《梦中的道路》,《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29]废名:《谈新诗》,废名:《论新诗及其他》,第95页。
[30]废名:《新诗问答》,废名:《论新诗及其他》,第211~212页。
[31]顾随:《杜甫诗讲论》,《顾随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页。
[32]顾随:《致卢季韶(1921年6月20日)》,《顾随全集卷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页。
[33]顾随:《文选选讲》,《顾随全集卷七》,第144页。
[34]顾随:《文选选讲》,《顾随全集卷七》,第298页。
[35][36]《西渡:新诗到底是什么——废名新诗理论探赜》,《名家读新诗》,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版,转引自中国诗歌网,https://www.zgshige.com/c/2016-09-18/1813792.shtml,2022年9月26日引用。
[37]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38][39]废名:《谈新诗》,废名:《论新诗及其他》,第28、30页。
[40]废名:《〈妆台〉及其他》,废名:《论新诗及其他》,第199页。
[41]废名:《十四行集》,废名:《论新诗及其他》,第185页。
[42]内山精也:《作为职业的诗人——宋末元初诗坛发生了什么?》,《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43][46]顾随:《论小李杜》,《顾随全集卷五》,第392、387页。
[44][45][47]顾随:《义山诗之梦的朦胧美》,《顾随全集卷五》,第403、407、409页。
[48][49][50][51]顾随:《论小李杜》,《顾随全集卷五》,第388、389、390、392页。
[52][53]顾随:《词之三宗》,《顾随全集卷六》,第39页。
[54][55][56]顾随:《义山诗之梦的朦胧美》,《顾随全集卷五》,第409~410、410、410页。
[57]顾随:《论小李杜》,《顾随全集卷五》,第392页。
[58]蔡莹莹:《顾随与王国维之词学传承关系蠡探——从“高致说”的几个疑点谈起》,台湾《东华汉学》第22期,2015年12月。
[59]顾随:《稼轩词说》,《顾随全集卷三》,第7页。
[60]王国维撰,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四五》,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18页。
[61]王国维撰,彭玉平评注:《人间词话·六〇》,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9页。
[62]王国维著,彭玉平疏证:《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7页。
[63]顾随:《稼轩词说》,《顾随全集卷三》,第8页。
[64][65][66]顾随:《太白古体诗散论》,《顾随全集卷五》,第290、293、292页。
[67]顾随:《太白古体诗散论》,《顾随全集卷五》,第291页。
[68]顾随:《“不可俗”》,《顾随全集卷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145页。
[69]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第358页。
[70]顾随:《〈人间词话〉疏义(残稿)》,《顾随全集卷三》,第102页。
[71]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第363页。
[72]顾随:《〈实践论〉学习笔记》,《顾随全集卷二》,第171~176页。
[73]顾随:《小说家之鲁迅》,《顾随全集卷三》,第355页。
[74][76]顾随:《毛主席诗词笺释》,《顾随全集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199页。
[7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十论语注疏·卷第九·子罕第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07页。
[77][78][79]顾随:《毛主席诗词笺释》,《顾随全集卷四》,第199、199、204页。
[80][81][83]顾随:《致孙书秀(1954年1月18日)》,《顾随全集卷九》,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23、323页。
[82]顾随:《致孙书秀(1954年4月9日)》,《顾随全集卷九》,第324页。
[8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85]明万历间茅维编刻:《苏文忠公全集》卷七〇,见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〇九题跋一三·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3043页。
[86]谢应光:《“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87]苏雪林:《中国文学史略》,国立武汉大学1938年印,第158页。
[88]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89]季剑青:《顾随与新文学的离合》,《泰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