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芜
内容提要
艾芜在1930年代对于上海的书写,一向不甚受人关注。其实,艾芜笔下的上海城市空间具有耐人寻味的复杂意义,其晦暗之处既显示出作家对于南行经验书写所开辟的精神和心灵空间的眷恋,也是艾芜在大都市不适感的表征;他基于上海期间牢狱经验的创作提出了“灾民暴动后怎样”的追问,人物疯癫与沉默的境遇与同时代其他左翼人士的灾荒书写和牢狱书写之间体现出犹疑不决的对抗性。要之,1930年代在上海的十年值得深描,这既是艾芜由受五四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意识转为建立较为稳定的革命者主体性过程的关键环节,而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在一位具体的作家身上呈现出怎样的复杂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关 键 词
艾芜 1930年代上海 左翼文学
1931年,艾芜从边地辗转来到上海,经好友王秉心介绍,租住在宝山县泗塘桥一家租金极为便宜的农舍里。初来乍到,籍籍无名,以文字谋生的计划并不顺利。《人生哲学的一课》便是这一时期所作:“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蔼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1]空有一腔抱负的主人公衣衫褴褛,步履踉跄,由人烟稀少的边远之地进入陌生的城市,身心都无处安顿。小说主人公初到昆明的这一幕,恐怕也是作者本人甫到上海时的处境写照。[2]
艾芜很快进入了左翼的阵营,面临着建立起自身“革命主体”的任务,这一任务无疑比此前在游民和读书人之间的游离与选择更为艰难和迫切。艾芜1930年代关于南行的书写中,基本上秉持了“游民/读书人”兼而有之的身份意识,但同时期创作的其他作品,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层次,尤其是对于上海的书写,历来乏人问津。[3]这些作品的写作空间与小说叙事空间之间存在微妙的张力:《南行记》等关于南行经验的书写与作者写作时身处的上海空间形成乡村与城市空间的倒转、对照关系;此外,艾芜笔下的上海城市空间的晦暗之处既显示出作家对于南行经验书写所开辟的精神和心灵空间的眷恋,也是艾芜在大都市不适感的表征;他基于上海期间牢狱经验的创作事实上提出了“灾民暴动后怎样”的追问,其中人物疯癫与沉默的境遇与同时代其他左翼人士的灾荒书写和牢狱书写之间体现出犹疑不决的对抗性。一言以蔽之,1930年代在上海的十年值得深描,这既是艾芜由受五四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意识转为建立较为稳定的革命者主体性过程的关键环节,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在一位具体的作家身上呈现出怎样的复杂性,也由此可见一斑。[4]
一 艾芜在上海:写作的外部空间与小说叙事空间
1930年代的上海已成为现代性在东方的象征之物,作为民族主义和殖民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它既是被想象缠绕的对象,也是生产想象的文化与权力中心,体现着资本和权力对空间的塑造。“租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整体秩序的坍塌和经验的重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资本将空间纳入生产对象的范畴形成了双重逻辑:显性的资本逻辑与隐性的权力逻辑。[5]除此以外,作为城乡二元体系的一端,城市空间是现代性的栖身之所,它由街道、百货商场、电车、公寓、工厂等建筑设施构成,与传统田园乡土截然不同。上海的存在本身就暗含着瓦解中国传统乡土经验的震惊,在割裂中显示出空间内部的危机感。
艾芜是在1930年代的上海,书写他1920年代云南、中缅边境等地的边地经验,他工作的起点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但最终的完成又是在“室内”。就此而言,《南行记》等边地题材小说在写作的物理场所与小说叙事空间之间暗含张力。如同沈从文在进入北京等大城市后意识到湘西的意义,边地的奥秘也在艾芜到上海之后真正敞开,成为他早期不竭的灵感来源。艾芜南行所积累的“那么多奇的经历”为左翼文学注入了新鲜的素材,也使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时期新文学作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硬写”困境。[6]不过,从广阔的南国天地来到上海,对艾芜来说也意味着另一重困境:创作领域的狭小和封闭。艾芜的困境同时可被视为空间危机:能否将此时此地的上海纳入自己的知觉结构进行书写?
说到这里,就必须要说明艾芜在上海的活动空间与方式。
“随后……放逐回国来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7]这次偶遇对艾芜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久他就搬进上海城里的德恩里13号亭子间,与沙汀夫妇毗邻而居。他也由此成为左翼亭子间作家中的一员。[8]
“法租界内的霞飞路给人以优雅的法式浪漫体验,日本人集聚的北四川路充满着浓郁的东洋风情,而公共租界内的南京路则给上海人展现了一幅‘世界主义’的图景。”[9]1930年代的上海北四川路,已是与霞飞路、南京路齐名的文化商业街,不仅聚集了大量书店、出版社、咖啡店,更吸引了大批出身底层的左翼文学青年,他们大多从外地来,在上海举目无亲。而文化名人如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也曾先后住在北四川路一带,北四川路逐渐因其“东洋风尚、平民气质和‘半租界’的权力状态”[10]成为当时活跃的左翼文化思想空间。
不过,由于上海城市空间明确的阶层划分,艾芜虽与文化名人同住上海,甚至享有共同的精确至街道的公共空间,其实际的居住场所却有天壤之别。现代城市空间的转换往往依托街道进行,“上海的街道发展过程中,那些凝结着文化记忆的空间实体消失了,譬如河滨、城墙”,租界扩张产生了新的街道,也催生了不同的街道文化。华洋杂居,房子被分隔成小间出租出去,艾芜即是这狭小亭子间的租户。不同阶层的人们混居在一处,居住条件的悬殊差异也加剧了亭子间作家们对于自身处境的愤懑情绪,制造了夹在知识分子与底层劳工之间的暧昧感。毛泽东后来曾在讲话中提到从“上海亭子间”来到革命根据地的作家,艾芜也被划为“亭子间作家”代表。亭子间作家的生活私人空间和收入水平,都更接近于底层民众。艾芜刚到上海时,没有稿酬、版税,也没有公职,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缺乏保障,靠友人接济过活,所谓读书人的自况并没能为他带来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
1932年,经由丁玲介绍,艾芜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地下进步活动,到杨树浦左联办的涟文学校做义务教师,“没有车钱,全凭双脚走路,从东边的杨树浦到西边的兆丰公园”[11],到工厂和工人联系,在夜幕掩护下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他穿梭于城市之中,以亭子间作家的方式厕身上海,艾芜笔下的上海,并没有同时期上海书写的标志性元素,诸如洋场、舞厅、咖啡厅等都市消费场所几乎从未出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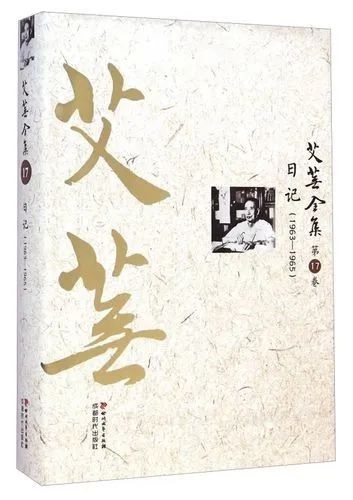
《艾芜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二 艾芜笔下的上海:“海上劳工”的梦幻泡影与“都市的尾巴”
总体而言,艾芜1930年代对于上海的书写所呈现出的上海是外在的,对象化的,它作为事件发生的场所而存在,且与人物的心理感受构成强烈的紧张关系;这与艾芜书写南行经验时边地与人物情境、心境的耦合与交融之感形成巨大反差。
《海葬》一文中,四位逃难的贫民在船上对上海展开了想象:
“到了上海,那愁什么?”
“拉黄包车,跑一条街,一角钱;两条街,两角钱,你看一条要找多少?乖乖,真是——”
“不要紧!上海那地方,会饿人么,你去卖大饼油条,也赚钱哪!”
“到了上海再说……”[12]
“堆着浓雾”的海上,“看不见天,看不见水”,一艘鱼龙混杂的客船上,走投无路的穷人们憧憬着到上海拉黄包车,卖大饼油条。这景象暗含反讽,似乎预示了梦想的破碎,风雨飘摇的客船象征严酷的现实,四个参与对话的人身处此岸的真实之中,这是一个遍布歧视、抢劫、偷盗与强权的小世界。而上海象征着美好的彼岸世界,物质富足,机会遍地,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希望。自始至终挥之不去的“浓雾”,既是人物混沌内心的写照,也是所处环境的隐喻。浓雾掩映之下,对岸那个抽象的国际大都市显得更加迷茫且触不可及。“海上劳工”最终葬身大海——人们背井离乡,试图来到上海寻求生存机会,却被永远地困在了海上。上海成为无法实现的梦幻泡影。这悲剧性的结局是否也映射出艾芜本人在面对上海这个庞然大物时复杂的心境?
总有人幸免于难,成功抵达“东方大都市”,《乡下人》等小说进一步显示出上海作为都市空间的压迫感。上海的“边缘”在作家笔下浮现出来:
伸入荒郊的这一长列矮小街屋——大都市的不必要的尾巴,渐渐沉入夜色濛濛的海里了,然也有几处早从工厂归来的人家,燃起了臭油的灯火,但由远处看来,那是稀疏点缀着的,仿佛海上的渔灯。[13]
这便是乡下人进入上海后的实景,贫苦的工人们聚居在“大都市的尾巴”上,这精妙的比喻令人印象深刻,相形之下,黄包车夫、卖大饼的,竟然成为令人艳羡的自由职业者。居所与活动空间彰显出个人在城市中的相对位置,而当下层人民试图跳脱出当前的处境,进入城市核心时,则可能遭遇更严峻的困境。《乡下人》中的“老毛”“样儿安详,嘴角上衔着廉价的香烟,在某某纱厂附近缓缓地踱着”,空间由郊外转换到工厂附近,暗示老毛身份的转变——由逃难的农民变身为在工厂领取固定薪酬的工人。此时的上海在老毛眼里“真像有块糖正贴在心上,甜蜜蜜地溶化”。然而,情况急转直下,老毛在寻租房子的过程中被密探误认为是地下工作者而拘捕,暴力刑讯逼供之下,他莫名其妙地承担了他完全无法理解的罪行。上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盘桓在他脑海中的,是故乡“田园的冲毁,房屋的倒坏,福儿的哀啼,病妻的呜咽”。“租房子”这一举动原本是个人试图在城市中拥有独立支配空间、获取基本自由和权力的表现,不可避免的日常行为竟然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显示出上海作为权力空间的强大的排斥性和压迫感。老毛终于意识到“上海危险的地方很多”,这个大都市繁华美好的一面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在被押送往监狱途中,艾芜借老毛之眼展示了都市局外人眼中的上海:
红绿色的电光闪烁着,忽明忽灭地跳着,都向车后窜去,又紧张,又兴奋,简直使得老毛眼珠发花,恍惚间觉得看见了故乡的烂熟的春天。这一切不正像红的樱桃花,红的杜鹃花……在翠绿的篱边,斗放着鲜艳的虹彩吗……而街上往来的男女呢,一对对地都沉醉在都市之春里。欢笑浮在唇边,愉快燃在眼里,是那么地自由,那么地舒畅。[14]
对外乡底层人的悲剧性叙述中,都市的灯光被比喻为乡间的花色,正像是前景与背景的重叠显现,构成视觉上的迷蒙感。老毛变成一部摄像机,深入内部记录拍摄下上海春夜的景致,其自身却完全外在于被拍摄之物。同时,比喻暗中恢复了“故乡”所暗示的都市以外空间的合法性,透露出忧郁而寂寞的情愫。欢笑、自由属于市街上的男女,乡下人老毛只有故乡烂熟的春天。
小说中乡下来的主人公虽身处上海,但却未能进入上海,他的精神世界驻留在曾经美好但如今正遭受灾厄的故乡田园,这或许也是艾芜本人心境的写照。

谭兴国:《艾芜评传》,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三 牢狱书写:上海的另一端
1933年3月,艾芜去往沪西曹家渡某工厂联系工人通讯员,被捕,在南市公安局拘留所关了两个月。5月,又转苏州高等法院第二监狱,被关押四个月。经左联各方人士设法营救,鲁迅亦出资五十大洋为艾芜聘请辩护律师,艾芜于9月获释出狱。他在狱中写下《咆哮的许家屯》《南国之夜》《乡下人》《伙伴》等小说。为期半年的牢狱生活和南行经历一样,成为艾芜重要的创作素材。和这段经历直接相关的小说至少有八篇:《张福保》《小犯人》《强与弱》《乡下人》《一家人》《囚徒们》《小宝》《饥饿》。[15]创作时间贯穿1933年至1937年。[16]这开启了艾芜笔下上海的另一重空间——牢狱。
牢狱是社会形态的缩微,进入这个压缩的“小社会”,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依然是艾芜的重点关注对象。其中,既有完全不知就里,含冤入狱的乡下人,也有多次混迹监狱的江湖游民,还有年仅十四五岁的青年学生。作为小说主人公,无论其身份、背景有何不同,多数都具有某种令人起敬的精神气质。或是来自过往生活的历练,如玩世不恭、来历不明的张福保,他狡黠聪敏,能够变戏法似的从“皮毛子的破地方”“夹出一只压瘪了的香烟”请大家轮流享用;又大方地在“皮背心里摸索出一张折得窄窄的纸币,对众人显了一显”,请大家晚饭吃咸鸭蛋;他还时常“充狠逞能”,完全是监狱里的老油条,连看守也让他三分(《张福保》)。而小犯人张汉宾则是个在校读书的学生,“十四五岁的光景,略略苍白的瘦脸上,明亮着一对微微带笑的眼睛”,看似稚嫩,却颇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质,监狱的恶霸也对他心存忌惮(《小犯人》)。或是牢狱生活赋予他们的,如乡下人最终陷于疯狂,以疯癫的形式和监狱空间形成决绝的对抗(《乡下人》)。
牢狱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更为边缘的“另一端”。在狱友衬托之下,老毛成为边缘人中的边缘人,他在倔强、沉默和不合作中发了疯。相比他所怀念的家乡野外的旷达,城市留给他的空间只有狱中一个不自由的角落。疯癫或许也是小说中人物被迫裹挟、含冤负屈的情境之下唯一的解脱之道。老毛在《乡下人》中的空间位移,从“都市的尾巴”进入城里的工厂,及至监狱,也正是艾芜抵达上海头两年行程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牢狱空间也构成作者内心深处城市空间压抑感的象征。
《饥饿》中卢小妹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这种压抑感的多层次性,除了所叙之事,“叙事”行为本身也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压抑”。卢小妹的遭际以梦呓的形式流露于文本之中,和乡下人在狱中的疯狂如出一辙,而和“我”有关的表层故事又将卢小妹的故事嵌入更深的叙事套叠。“我”既是卢小妹的观察者和同伴,也是小说中隐含的另一个主角,“我”不可避免地分散了读者对卢小妹的注意力,而严格的限制视角也阻止了读者直接进入卢小妹的内心世界。艾芜的处理方式像是某种症候,他可能在写作中面临着双重的阻碍。第一人称的“我”和“我”所代表的相对稳定的人物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作家的叙事困境,“我”有助于作家更好地完成故事,与此同时,真正的客观对象却在写作逻辑中被肢解为絮语和梦呓(卢小妹的梦:阎王、地狱和小鬼)。
相比《南行记》那种记述亲身经历的亲切笔法,牢狱题材小说中,“叙述人”与“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明显发生了变化。边地小说中与叙事者重叠的亲历者“我”不见了,艾芜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人物群像的素描方式。无论是出于塑造人物的必要考虑(保持神秘性),还是因为根本上的不了解(艾芜可能对于描写十几岁的孩子对革命的坚定内心缺少省察和自信),作者的笔触都未触及人物的内心,而是架起了摄像机,描述他们的外部活动,惟妙惟肖的动作描写之外,作者还花费了许多笔墨在人物话语之上,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主要通过人物的自我言说进行,这也体现出“我”消失之后,艾芜在小说叙事上所面临的困难。小说中你来我往的对话,承担了交代人物个性、梳理事件来龙去脉的重任,场景的串联、情节的推动都须仰赖对话,而对话本身又常常失于琐碎,读者很容易迷失在众声喧哗中,要费力去拼凑、揣测作者所云。对话的密集也连带着影响了叙事节奏,以致出现空白、卡顿,这与《南行记》流畅纯熟的风格形成鲜明反差。
自我描写、风景书写缺位的牢狱题材作品中,艾芜的创作似乎遇到了障碍。或许也可以看作艾芜试图摆脱南行书写中形成的较为成熟的风格、建立起左联话语所倡导的现实主义风格所做的努力。作家试图将素材以白描方式按步骤逐一落实。这种记录式的创作中“我”被隐没了,与之相应的那个年轻的流浪者新鲜而活泼、“寂寞而残酷”的生命体验也一并隐退了;与此同时,新的作者声音尚未建立起来,但琐碎絮语仍不乏可观之处,空间的逼仄之感由此渗入了文本内部。
在牢狱题材小说中,叙事者常作为观察者存在,艾芜很可能宁可做一个真诚的观察者,也不愿意做一个不真诚的参与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构建小说的方式都显示出作者避免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倾向。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牢狱书写相比,艾芜的革命者立场并不明确,尽管这些小说被列入牢狱书写类目,但无论在当时的批评家还是今日的研究者笔下,这些小说都未获得真正的关注。[17]他笔下的人物带着更生动的江湖气,而不是千篇一律坚决抵抗的革命者形象。放在艾芜本人1930年代的创作谱系中,它们似乎不及当时广受好评的南行题材作品舒展、流畅,但若放在同时期上海作家的牢狱书写谱系中,却又显出别具一格的品性。叙事安排上的逼仄和失度,恰恰显示出牢狱空间给作家带来的压抑感,以及作家在面临被拘禁的处境时的复杂心境。
艾芜的被捕,改变了他参与左联活动的主要方式。此前是在丁玲等人的引领下,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但出狱后,艾芜反省“左联真正的重要性,似乎并不是在马路和巷道中飞奔着躲闪巡警的警棍,而应该是用作品来参加战斗……因为只有文艺作品,才更能鼓舞一般青年”[18]。也因此,有意识地飞奔躲避巡警的革命者,并不是这时期艾芜笔下的英雄。他能够深入的,还是下层打工人的内心。他们被裹挟进来,茫然无措,既不完全明白革命是为何物,也没有马上分享到革命给他们境遇带来的改变。艾芜这段心路历程,是否可以看作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中间物?和鲁迅相比,他站在被启蒙的立场;和丁玲等人相比,他尚未洞悉革命文学的奥义。创作这些小说时,艾芜的身份意识更接近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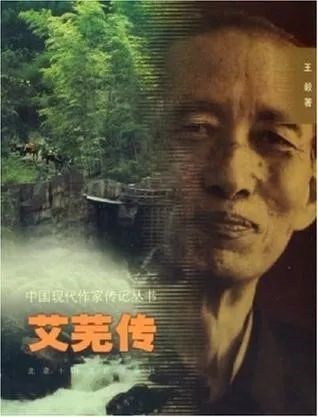
王毅:《艾芜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四 疯癫与沉默:《水》中的灾民暴动之后怎样?
《乡下人》和《饥饿》都有一条空间线索:乡下农民遭灾→进入上海→被捕入狱。《饥饿》这篇小说内部嵌套着两个时空:牢狱中正在发生的事和卢小妹入狱之前的生活。故事围绕“我”与卢小妹的交往展开。牢狱中的“现在时”致力于描写环境的恶劣、监狱生活的粗鄙和艰苦。此外,尽管“我”仍然主要作为观察者存在,意在以一种更为真实可信的方式为读者讲述卢小妹的故事,但由于“我”是卢小妹的狱友,卢小妹的境遇也隐含着“我”本人的境遇,“我”不仅是见证人,也成为另一个平行的主角。卢小妹用琐碎、神经质的话语零散地交代了他悲惨的过去,指向牢狱空间以外更深刻的历史现实:“在令人绝望的饥饿中,我呆呆立着,听着四下里正放着敬神的火炮,心里便禁不住酸了起来。恰巧这时又遇着韩老三了,还伙着一大批人,大约他们是来集合在那里的。他问明我在那里做什么,便在我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走呀,糊涂虫,你不帮我们,去拿点吃的,也好哪’!”[19]
由于“我”从始至终都未出面对卢小妹的讲述做梳理和总结,因此,卢小妹的过去依然是含混、隐晦的。当事人的自述隐含着一段走投无路的抢粮经历,其他话语多集中在对饥饿的描述、对死后下地狱的恐惧之上。凸显出脱离“大众”这一宏大叙事掌控的“个体”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不久(1931),丁玲发表了一篇与《饥饿》题材类似的中篇小说《水》,以1931年波及全国十六省市的水灾为题材,描摹天灾人祸下的农民如何觉醒并走上反抗之路。《水》展现出丁玲作为小说家的才华与能力,“农民觉醒、反抗的群像描写如一组组雕像凸现着”[20]。这篇小说也被看作丁玲在胡也频去世后“向左转”的代表作,是丁玲从五四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此前以描写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觉醒与叛逆而建立文坛声名的丁玲,正经历着人生中一段苦闷的时期,她将眼光转向更为宏大的农村、农民主题。[21]冯雪峰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一文中肯定了丁玲的这种转变和尝试——“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显示了作者对阶级斗争正确的坚定理解”;“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不是一个或两个的大众,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22]冯雪峰赞扬丁玲创作了“新”小说。
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艾芜的《饥饿》和《乡下人》等小说,它们无疑是“落后”的“旧小说”。与丁玲相比,艾芜既没有对“革命”的全局把握,也没有对农民的冷静观察,换言之,此时的艾芜尚未建立起“革命”的想象,甚至无法将自己从劳苦大众这一群体中抽离出来,“我”和卢小妹一样,不仅是就坐牢这一境遇而言,连入狱前的经历也并无实质上的不同。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是底层的普通民众被革命、运动波及所遭遇的困境,这困境如此真实而又沉重,以致人物最终被压垮甚至彻底毁灭,而非奋起自救或被拯救。艾芜致力于刻画他们的无知与无辜。同样是灾厄之后,《水》给出了解决的办法,《饥饿》和《乡下人》则书写出逃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出路时再次受阻的困境。
同样是灾民,丁玲笔下的人物在起义和反抗中确认自身,经由左联的理论家解读,更确立了代表着当时左翼文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为新形势下左联的运动斗争开辟了新的论述空间和文艺实践方向。然而,正如有论者指出,“冯雪峰把丁玲创作上的转变视作左翼文坛‘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清算’,如果说‘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清算’所暴露出的是主体与大众世界、革命与文学的分裂,那么《水》将大众以一种‘风景’的方式呈现,其实仍然是浪漫主义的” [23]。现代文学史上,理论家们对何为现实主义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定义,而其对位“浪漫主义”内涵也不断被调整。艾芜的书写很可能是出于对现实主义歪打正着的朴素理解。
将艾芜《饥饿》与丁玲《水》进行对读的意义还在于,在1930年代初期左翼文坛占据主流的革命叙事之外,在对“大众”的发现和叙述之外,艾芜无意中补充了“大众”名义下真实的个体的境况。20世纪30年代,“大众”一面为反抗反动消极的国民党政权、支持进步革命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不免威慑乃至杀伤着那些更边缘、更弱小者”[24]。《水》塑造了革命的“大众”,为意识形态提供了肉身承载,也可能遮蔽了艾芜笔下监狱角落中不幸的个体。

丁玲
《饥饿》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看作对于“起义之后怎样”的追问?“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25]的队伍,是由成百上千个卢小妹和老毛组成的。丁玲并未给出“往镇上扑过去”的后续,而艾芜则补写了苍凉的结局:“他的眼角边,湿润着,随即勉强悲凉地微笑一笑。”[26]1935—1937年间,艾芜至少出版了五部小说集。最初发表于《文学》(1935年第5卷第4期)的《饿死鬼》(后更名为《饥饿》)并未收录于其中任何一部。这或许也可作为这篇小说在当时处境的某种注脚。
结 语
初到上海时,艾芜一度遭遇写作的困境,也因此有了沙汀、艾芜、鲁迅三人共同完成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基于自己早年写作立场的反思,对青年作家提出诚恳的建议:要以“平等”的角度保持作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不能是“楼上的冷眼”,更要警惕包含着同情意味的“空虚的布施”。[27]艾芜深以为然,多次在文章中忆及此事,但今天看来,这段通信还只是艾芜创作观念疑惑的集中表达,无法据此断言作家是否就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写作道路。1930年,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支部,作为全世界普罗文学组织的一部分,其背后的国家想象和革命实践也进入了新时期。[28]初来乍到的艾芜对于左联的发展变化很可能并没有足够深刻的理解和体认。尽管如此,他仍积极调整小说写作的策略,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身上,而不是聚焦于南行书写抒情化的“自我”之上。早在1928年,《太阳月刊》七月号曾刊载藏原惟人著、林伯修译《到新写实主义之路》[29]。文章从历史进化和阶级斗争角度将浪漫主义定义为“渐次没落的地主阶级的文学”,“是空想的,观念的,传统的”,以革命的话语否定了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浪漫主义手法。这篇文章也被视为“革命文学”论争的阶段性结论。其后几年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向左转”逐渐成为当时文坛许多作家的选择。而艾芜《南行记》吸引批评家注意的,恰是它的浪漫色彩。[30]郭沫若曾在随笔《痈》中说:“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人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31]“《南行记》以静观的态度,以有诗意的笔调,描写了边疆的风土人情。”周立波一度将艾芜称作“流浪诗人”[32]。与此同时,艾芜在上海期间的另一些与南行书写风格差异较大的作品:关于上海的书写,特别是牢狱经验的书写,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却未受到评论家的青睐。这不能不说是“浪漫”与“现实”理论解读与实践批评之间的吊诡之处,或者说,批评家们对风格与题材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也因此做出了有据可依的取舍。事后回望,艾芜1930年代关于上海的写作正体现出作家创作观念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性。
1937年,艾芜离开上海,乘坐黄包车赶往车站途中感慨:“在这种不舒服的环境里,劳动的人是有福的了。”[33]作家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年离沪后,艾芜由于战乱先后在长沙、桂林等地暂居,于1944年辗转抵达重庆,再没有在上海长期生活过。上海的近十年,在艾芜生命历程和创作生涯中,究竟意味如何,仍然是个值得深究的议题。

艾芜:《南行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
陆楠楠 王明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 重庆大学出版社
100029 401331
注释:
[1]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载《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1932年11月,收入《南行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
[2]参见艾芜在《别上海》(1937)、《记我的一段文艺生活》(1945)等散文关于1930年代在上海生活的记述。
[3]对于1930年代艾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行记》。一些“牢狱”书写、“亭子间作家”等群体研究,也会涉及艾芜这时期的作品。
[4]1931—1937年间,艾芜在上海期间先后发表小说数十篇,并结集出版。
[5]林青:《空间生产的双重逻辑及其批判》,《哲学研究》2016年第9期。
[6]茅盾、鲁迅等人的指导意见对当时的左翼作家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艾芜作为初出茅庐的后辈作家,更是十分看重这两位文学前辈的观念和建议。参见《悼鲁迅先生》《记我的一段文艺生活》等文。
[7]艾芜:《原〈南行记〉序》,《艾芜全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8]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6页。
[9][10]童敏:《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6、87~88页。
[11]谭兴国:《艾芜评传》,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
[12]艾芜:《海葬》,载《文学》1934年第3卷第1期。
[13]艾芜:《乡下人》,载《文学》第1卷第5期,1933年11月,收入《夜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14]艾芜:《乡下人》,载《文学》第1卷第5期,1933年11月。
[15]艾芜1937年离开上海后,陆续还曾写到牢狱经验,如1984年定稿的《狱中记》,因本文研究范围为艾芜1930年代上海时期作品,故不列入讨论。
[16]牢狱小说甫一出现便引发了左翼批评家的关注,周立波在1935年写作的《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首次提出“牢狱文学”,并对萧军、艾芜的小说进行点评。1936年,周立波又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中点评了舒群、罗烽的牢狱小说。
[17]尽管关于上海“孤岛”时期牢狱书写的研究通常会提到艾芜,但多数时候,艾芜与陈白尘、荒煤、周立波、方志敏等人的作品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研究的,而这些作家们的牢狱书写面貌迥异。他们在狱中所处的空间、被捕入狱的原因、身份和对革命的认识等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18]王毅:《艾芜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19]艾芜:《饿死鬼》,《文学》第5卷第4期,1935年10月。后收入艾芜文集时更名为《饥饿》。本文在论述时取其后来通行的名称《饥饿》。
[20]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21]也就在此时,丁玲接管了左翼的重要刊物《北斗》。
[22]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23]吴舒洁:《“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24]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
[25]丁玲:《水》,《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
[26]艾芜:《饥饿》,《艾芜全集》第8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27]沙汀、艾芜、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见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28]艾芜加入左联时,左联刚刚损失了一批包括柔石、胡也频等人在内最早投身写作实践的青年作家,正处于一段沉潜的时期。1931年左联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为左联的活动指明了方向:反帝、反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宣传苏维埃革命,组织无产阶级斗争。并对文学中的个人主义提出批评。参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见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页。
[29]藏原惟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林伯修译,《太阳月刊》停刊号,1928年7月。
[30]艾芜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影响很大。早年也曾写过一些风格相近的新诗。《艾芜评传》,第40页。
[31]郭沫若:《痈》,《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25日。
[32]周立波:《读〈南行记〉》,见毛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芜专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33]艾芜:《别上海》,《国闻周报》1937年12月。
|

